蘸着咖啡吃油条的地方

“中国人爱喝茶,但我让他们爱上了喝咖啡。”
几年前,某全球咖啡连锁品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看来,这句话得罪了两拨人。一拨人打出“味道好极了”这句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广告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操持着全中国大江南北的咖啡生意。虽然人家卖的是速溶,但好歹也是咖啡。另一拨人,来自你可能连听都没说过的海南兴隆或者福山镇。他们听到了,肯定会把嘴里吃一半的香兰叶七层糕给笑喷出来。但这笑声你是不太听得到的。他们躲在中国咖啡史的旮旯里,是渺小的草根存在。
桂花姐
米黄色地中海式风格的兴隆咖啡文化馆大厅入口处,八十多岁的香港人蔡桂花穿着一件玫瑰花图案的绸衫,神采奕奕,坐在轮椅里。她的儿子陈伯宁刚刚推着她逛完整个博物馆的展览,旁边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太太素衣素裤,站在一边微笑着看她,并不言语。离她大概四五米开外,是一座被红色栏杆拦起来的铜质头像-陈显彰。现在,他是整个福山咖啡风情小镇的灵魂人物,早在1937年,为“实业报国”,舍弃海外产业,陈显彰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大规模成功种植咖啡,而被誉为中国咖啡之父。

“那是我的公公哦,我是他的四儿媳。”蔡桂花对我说,一口浓重的广东腔。
文化馆介绍陈氏家族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蔡桂花和陈家在福民农场的黑白合影照,拍摄于1953年。那年她刚嫁到陈家,不到20岁,齐耳短发,白衬衣,黑粗布裤子,而身边的陈夫人和三儿媳,都是上身白色对襟,下身白色的肥大筒裤。来到大户人家,又是华侨,蔡妈妈的神态多少显得有些拘谨。
“到后来就好了,咖啡农场里大家都很熟稔。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二哥还带头翻跟头,把家公他们给乐得不行。”后来我知道,来现场参加婚礼的,就有那几个素衣素裤的婆婆,那是农场里一起采咖啡的姐妹。

“家公后来很宠爱我,很多事情都要让我去做。”拿草木灰擦做种用的咖啡豆。作为新儿媳,闲下来也帮着做家务。陈显彰想念一种用豆角、芋头梗、咖喱等五种原料煮起来的印尼炖菜,就让桂花去学,做给他吃。至于咖啡,他反倒并不十分讲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让她煮一大壶,倒在一个大茶缸里,一天喝到晚,凉了也可以喝。”蔡妈妈回忆起年轻时的事情,眼神里都是光芒,本来约好了去隔壁咖啡馆喝咖啡,也不去了。
1953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那一年,陈显彰的儿子陈茂修去了两趟万宁兴隆镇,送去蔡桂花和姐妹们料理的咖啡种子。为此,福山文化馆郑重其事地把当年兴隆华侨农场为陈茂修开具的,让路上军警放行的介绍信放大装裱,以兹证明两地的关系。

福山镇位于澄迈县西北部,距离海口市只有49公里,海南岛西线高速贯穿其中。福山咖啡小镇就位于高速口入口处,建于2010年,由几十家咖啡店组成。装修考究,门面豪华。跑进一家餐馆吃饭,却被莫名其妙地拉入酒席。后来才得知,侯臣咖啡文化村正在庆祝海南特有的公期,祭拜神祖,挨家巡游,餐厅老板正在大宴宾客。吃饱喝足,大家都跑去看插科打诨的琼剧。
夹着糯米草的书信
何师傅坐在一颗木姜子树下啃文昌鸡,凳子上立着一个大手电,状如香槟瓶子。他是看车的,见过最远的车来自北京,四川广东常见。斜对面,一个男人正在关一个院子的门,木门上画着两个大肚子红绿天官门神,手捧咖啡和茶果。几年前,这里是福山咖啡馆创始人徐守义的旧馆址,如今漂亮的新馆开到了湖边,这里就沦为员工宿舍了。
我坐在湖边,点了一杯福山咖啡欧(欧是海南话,咖啡欧是黑咖啡的意思),外加一块绿缘糕。虽然写明了现磨,但还没听闻磨豆的声音,服务员就已经把咖啡端了过来。旁边2个从海口来的女孩在聊天,她们一直在跺脚,驱赶湖面飞过来的蚊子。远处,我听到一个服务员说,她喜欢现在的福湖,月光洒在水面上,打出一条路来。
“先生,咖啡要续杯吗?免费的。”她走了过来。

续杯问题,被兴隆香料研究所的陈鹏拿来揶揄福山和兴隆两地咖啡文化的不同。“在福山,咖啡可以续杯。在兴隆,咖啡卖一杯是一杯,而茶水免费,鹧鸪茶。”
我和陈鹏约在兴隆老咖路上的瓦西里咖啡厅见面,同时一起的还有兴隆巴厘村讲解员柏云。我没有见到瓦西里的吴老板,据说他长得很像《列宁1918》里的卫兵瓦西里,于是镇里人都这么称呼他,后来干脆就当了店名。瓦西里位于老咖街路口的把手位置,街对面是兄弟开的瓦东里,哥儿俩还真当成了这条街的哨兵。我望了望四周,气氛特别混搭。一群身着兴隆篮球队队服的年轻人正围着桌子埋头吃海南米粉,每人边上配一杯咖啡。离他们不远,一群人在下象棋,棋盘边上,也放着几杯咖啡。

陈鹏原籍海南儋州,苏东坡被发配的地方。前几年调来兴隆,在热带农科院做了20多年的咖啡种植研究。几年前,他跑去云南普洱学习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烘焙认证,后来创立阳光咖啡工作室,从事咖啡文化的推广工作。认识他,正是通过在普洱一家专业从事咖啡种植、生产和认证培训的Torch公司。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了国内两大咖啡产地的力量对比。
专业技术背景给陈鹏带来先天的优势。阳光工作室吸引来很多学习咖啡文化的本地人,后来名气大了,很多来海南度假的“候鸟人”也来参加。当一杯杯通过虹吸和手冲等不同萃取方法的罗布斯塔咖啡喝进嘴里,32岁的柏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味道很纯正啊。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一个年长的闯入者,用手肘碰了碰,叫醒了一个沉睡的年轻人。论喝咖啡的年龄,作为印尼华侨后代的柏云,比大他十几岁的陈鹏还要长。

每天早上起来,总有朋友在柏云微信里给他打招呼:在哪里啊,要不要一起去打锅B针?锅B,是海南人对咖啡的口头称呼,马来语和闽南语的杂交,英文里写成Kopi。在兴隆的早茶店,如果你说来一杯兴隆咖啡,那就是默认的咖啡加炼乳。如果只加糖,那叫咖啡欧。如果什么都不加,你得提前说。新加坡的kopidiam(咖啡店),甚至根据炼乳、奶度、糖度以及咖啡浓度的不同,已经发展处一套比星巴克还要复杂的咖啡行话,差不多有二十来种点法。如果你不懂这些,进去肯定会懵。
发源于琼中斩岭的太阳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过兴隆镇,注入万宁水库,最后汇集于中国南海。兴隆华侨农场就位于风情摇曳的太阳河畔,如今的兴隆人,大多是华侨农场的后代。上个世纪50年代排华时期,从南洋回国定居的三万多印尼马来越南等地的华侨难民,被安排在这里生产自救。在此之前,兴隆只不过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小集市。这些人带回来南洋的建筑风情、饮食文化。咖啡和九层糕,仅仅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普通兴隆人喝的咖啡味道重,炒制的时候已经加了糖,喝的时候,还会加点炼乳。“所以一般兴隆人喝过我做的纯手工咖啡,会觉得我是骗人的,因为口味太淡,一定是掺了水了。”陈鹏笑道。

开着电瓶导览车,陈鹏带我们去看兴隆热带植物园里的罗布斯塔咖啡种植园,见血封喉、香草兰、可可,一路上指指点点,对各种植物如数家珍。“我的太太比我强多啦,她是国内糯米草的研究专家。记得我们两地分居的时候,经常通信,她每次都会在信里夹上几束糯米草,那信纸,可香了!”夫妻俩现在终于团聚,就住在植物园里,可以看到咖啡树开花结果。岛上的空气本来就好得令人艳羡,园里更是绿野仙踪。万宁最近几年被评为世界长寿之乡,不是没有道理。
南洋锅B店
“我父亲炒咖啡的时候都要加牛油,喝的时候也会加一点点啊。后来回国在合作社炒豆找不到牛油,父亲还郁闷了一阵子。”
71岁的“南洋风味”餐厅老板能叔刚从热带风情园钓鱼回来。他坐在自家店门外,边桌上摆着一碗清补凉。几年前他开始和亲家在街头卖南洋小吃,发展到现在餐厅已经极具规模。他给我讲小时候自家在印尼开咖啡店的故事,满足了我对南洋咖啡文化的好奇心。

能叔的父亲叫黄兴义,小时候跟随父亲做猪仔船到印尼讨生活。能叔开始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在苏门答腊岛的亚沙汗市临近港口的地方置下一处咖啡馆。由于地处十字路口,咖啡馆生意兴隆。早上五点不到,父亲就要起来烧水。到了六点,就要开门迎客。和兴隆如今菜市场的早茶店一样,这家黄记咖啡店也是当地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很多顾客早上都会过来,点上一杯咖啡,外加一份七层糕和炸香蕉。这些常客中,能叔一直记得一个绰号叫693(当时流行的一种抗生素药)的印尼警察署长。这位警长为人正直,从来不吃霸王餐。有一次,一伙拿着长枪的印尼士兵在黄记咖啡吃完饭后想赖账,正好被警长碰到。他站在咖啡厅里大喝一声,掏出短枪,一群小流氓乖乖付钱,立即作鸟兽散。
父亲宠着能叔不让他干活,但四个姐姐却忙得不亦乐乎。每天甫一放学,四朵金花就从马路对面的华侨学校跑步回家,帮父亲打理生意,招徕顾客。“相比苏门答腊,海南还算有个冬天,天亮得没那么早。”能叔说。

天亮得晚,也抵不住人勤快。79年,陈鹏的好友黄来乡师傅在兴隆镇桥下早茶店炒咖啡,也是五点就得起床烧水。为了多睡一会儿,他干脆就住在桥下。一杯咖啡卖一毛二分,五个大桶,轮流烧水,而且也是六点开门。想象一下,当大半个中国还处在只知豆浆配油条的年代,兴隆人已经大口大口地喝上咖啡了。我依稀记得,当我在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喝到雀巢咖啡时,曾经象对待圣物一样用纸包着一嘬咖啡粉,坐火车从北京带回给浙江乡下的弟弟。
如果说黄兴义是兴隆华侨里第一代炒咖啡的,黄来乡应该算是第二代。在他的院子里,至今还摆放着几台八九十年代自己使用过你的炒咖啡机,搅拌式的,滚筒式的。整日风吹雨打,这些老家伙都已锈迹斑斑。院子里堆积如山的小木块是燃料,当陈鹏开始土耳其进口的Toper烘焙机烘豆时,黄师傅依然按照传统习惯使用炭火。按他的说法,南洋炒咖啡的工艺,还是炭火来得香。

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列出他几条不去咖啡店的理由,第一,他是不喝咖啡的,他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不喜欢,还是绿茶好;第二,他还要抄旧闻小说等,没有余暇;第三,嘲讽在咖啡店里的那些长相俊美的革命文学家,自己“满口黄牙”,还是不去亵渎了。
假如鲁迅住在兴隆,他的这段《革命Kopidiam》可能会这么写。第一,他是要去喝咖啡的,他不觉得这是洋人喝的东西,因为这里的人从小就喝,而且蘸着油条喝,很市井;第二,他不用抄旧闻小说了,这里的人有余暇,生活就应该这么过;第三,这里咖啡店里的人真是三教九流,既有长相俊美的文学家,但更多的是像自己一样“满口黄牙”的街坊,戴礼帽算彩票的爷们儿。能够听到许多社会的琐事,和下层职业的情况。
在新菜市场的一号茶店遇到的冯中华,就是这么一个满口“黄牙”的老咖啡客。进入这家咖啡店,时间一下子穿梭回到八十年代。在简易的灶台上,一把铝制茶壶里挂着发黄的咖啡漏网,旁边立着一个红色的保温瓶和一瓶国鹰牌炼乳。穿着竖条衬衣的冯中华把一只腿挂到边上粉色的塑料椅子上,边嘬着3块钱一杯的咖啡,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被卷成蛋卷形状的红白相间的纸条,那是他刚刚买的彩票。

在他边上,坐着几个他的好朋友,他们每天都约这里喝咖啡,吃早点,聊天。和他们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冯中华经常送进嘴的两样东西是咖啡豆和槟榔。这位老咖啡客还告诉我,他自己最喜欢的咖啡喝法,是光煮不过滤,喝完了还要把咖啡沫掏出来,放进嘴里嚼。这种几近失传的喝法,我在云南朱谷拉村和开罗亚历山大街头还能见到,应该是人类发现咖啡后最原始的萃取方法了。

我决定跟着去看看他的咖啡园,在附近的沙田村,24队。当初为了安置华侨,兴隆被整编成60个队,现在这个叫法还保留着。比如周恩来去过的古村,就叫20队。
七十年代,冯中华随父母从越南广陵来到兴隆落脚,那年他19岁。四亩地的罗布斯塔挨着太阳河的一条支流,长得郁郁葱葱,差不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比他们来兴隆的历史还要长。邻居家的走地鸡刚从林子里穿过,远处河边传来一阵鸭子的叫声。园子里间种一些槟榔树,都被他料理得很好。在园子的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树桩子,那是被队里前几年砍掉卖木材的一颗台湾相思树留下的。在咖啡园子里种相思树是特别常见的做法,可以给咖啡遮阴。建设牌摩托载着我飞快地奔驰在田野里,路边不断有槟榔树闪过。“他们种得不行啊!”冯老汉挥了挥手,自豪地喊道。的确,树冠上的叶子,很多已经发黄,显然是得了虫害。

“那颗相思树好可惜啊!”
“那些成片的咖啡树才可惜呢。你不知道,当年我们兴隆到处都是咖啡树,后来因为种橡胶,都被砍掉了。我们队就我这里还有一点。”
凋敝与兴隆
驱车在兴隆大街上走走,你会发现很多凋敝的温泉酒店、豪华公寓。这些从种植园原址拔地而起的建筑,见证了兴隆曾经的辉煌。我入住的康乐园宾馆是一家最老资格的酒店。酒店一名老员工告诉我,它的前身,是一大片咖啡园和胡椒林。十几年前,这家整体欧式古典风格加东南亚主题装饰的酒店承载着兴隆人对纸醉金迷的所有想象。当国内还没有流行去芭提雅普吉岛时,兴隆人已经把泰国人妖引进到这里的霓虹剧场。酒店入口处巨大的喷水池已经干涸,紧挨着的太阳河道没有疏浚,河边宽大的直升机停机坪无人修葺。绞杀的榕树独树成林,给酒店增添了古老的氛围(虽然只有二十来年的时间)。虽然酒店其他部分都还正常运转,但你能想见,当初的辉煌未能持续至今。

更为落寞的,是离酒店大概五分钟车程的兴隆温泉迎宾馆。就像全国各地所有的迎宾馆一样,温泉宾馆肩负过接待国家领导人的任务。现如今,整栋大楼陷入一片水泽地,房间阳台杂草丛生。曾经行驶红旗轿车的主干道布满了藤蔓,一盏八十年代风格的路灯倒在草丛里,倒是一种荒芜之美。唯独周恩来曾经栽下的那颗芒果,依然郁郁葱葱。我也去古村找过一块为了纪念周恩来访问华侨农场而设的石碑,却遍寻不见。问一个开拖拉机的村里人,对方看了我一眼:你还是去问兴隆镇的宣传科吧!

坐落在兴隆国家森林公园里的咖啡谷,似乎让人看到兴隆咖啡的未来。九点刚过,四月的太阳就已经很放肆了。四十多岁的刘振邦置身于一片密密麻麻的咖啡林中,头戴暗绿色木髓太阳头盔,一双长长的薄碎花护手套,把双臂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采摘用的指尖。他的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个沉甸甸的果箱,是用某优酸乳品牌的洋铁皮自行改制的。虽然已经过了挂果最多的季节,但农场里还是有需要采摘的咖啡果。在谷底的一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满了咖啡苗,等它们开花结果,还需要三年时间。磕完槟榔微醉的我,跑进谷底的水上咖啡馆喘口气。

服务员小蔡在户外巨大的梵天四面佛的注视下,与我分享小时候第一次拿油条蘸咖啡的故事。恍然间,山上刘师傅的抱怨又在耳边响起:“相比早茶店里三块钱一杯的咖啡,我当然更爱喝纯的咖啡啊,但是我喝不起,二十块一杯太贵了。”被唤醒的人,真是拥有更多的烦恼啊。当然,醒着的,也没必要觉得自己比睡着的有更多的优越感。
转角咖啡店的老板娘沈红梅,对兴隆曾经拥有的过去一直记忆犹新。她的咖啡厅装潢考究,光线暗淡柔和,一个人在中间的一张长桌上看《荆棘鸟》。在她看来,华侨带给兴隆的,不仅仅是咖啡,而是一些有品质的生活习惯。她给我举例子,过去在华侨家里,房子地面是要打磨得发亮的,衣服都要浆洗,并用炭火烧的电烙铁熨烫。老人衣着讲究,出门要化淡妆。这些生活细节,在几十年前应该是让人震撼的,但现在人们依然需要。她说她没去过东南亚,但她母亲和姐姐刚从新加坡回来,他们很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咖啡店,和这里的一模一样。甚至说话也一样,好多字都发第四音。

除了气候与环境,兴隆的建筑、饮食、乃至生活习惯,都给人以东南亚小镇的感觉。刘振邦的木髓头盔,和西贡我采访过的沉香林工人一模一样。能叔家的清补凉,也和我在马六甲吃到的没太大区别(除了没加薄荷油)。而在“巴厘村”风景区看到的建筑,几乎原汁原味地复制了岛上的房子。在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我遇到从印尼巴厘岛来的女雕塑家戴维和她的工作伙伴,她正在专心地打磨一批建筑构建-雕着蜗牛花纹的浮雕,而她的两位男性伙伴正在给几个罗摩(印度教神)塑身。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个印尼舞蹈演员。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

“这里的一切,气候、环境、风土人情,我都很适应,都和巴厘岛差不多啊,我很喜欢这里,除了有一点我还不太习惯,就是这里的饮食太清淡了。在我们巴厘岛,很多食物都是酸辣的。”戴维小姐快人快语,在兴隆,她有时候能碰到一些象能叔这样的第一代华侨,可以亲切地用乡音(印尼话)和他们交流,甚至在他的店里跳个印尼舞。业余时间,她也被老板安排学习汉语。随着更多航线的增开,将来会有更多的东南亚游客来到这里。去年下半年,英航开通了伦敦-雅加达-海口的旅游航线,兴隆大街的旅游巴士上,会走出更多来自东南亚的客人。他们也许会和沈红梅的母亲一样,坐在新菜市场一号店的粉色塑料椅子里,对着兴隆咖啡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没想到,原来这里的kopi,和新加坡一模一样啊!

能不一样吗。早在19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咖啡店老板,就已经基本上都是海南人,并形成了咖啡四大家族。关于为何是海南人经营咖啡馆,华东师大民俗学的研究员张海岚做过梳理:“相比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琼帮下南洋是最晚的,挣钱的行当早被同胞揽走。当时正好形成以英国人为中心的洋人生活圈,海南人因为眉清目秀、老实能干,就成了洋人厨师的帮手,学会了煮咖啡、制作糕点、西餐等工作。”等到英国人撤离,这些有一技之长的海南人,自然会开一个咖啡馆谋生。在英国人的厨房里,海南人不但发明了著名的海南鸡饭,还在炒制咖啡的时候淋入牛油和焦糖。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第一个发明这种炒制方法的海南人,他开的咖啡店附近有一群顾客是鸦片鬼,他们因为吸食鸦片变得味蕾麻木,为了让自己的咖啡卖得更好,这个海南人开始往里面加糖和牛油。这种说法倒也有科学依据,同样的例子也可以在嚼槟榔的人身上找到。在缅甸伊洛瓦底江的一艘游轮上,一个厨师跟我讲述了他因为嚼槟榔给菜里放太多的盐,因此差点丢饭碗的糗事。

最后一天,我驱车走向兴隆国家森林的深处,发现每一处村子,都有一个兼具小卖部和喝咖啡功能的简易咖啡馆。虽然是中午,咖啡馆空无一人,椅子散落在各处,但我依然能想象到人声鼎沸时的样子。这是当代中国大中城市十分缺失的公共市井话语空间,失礼存诸野。在充斥着星巴克和精品咖啡的中国,兴隆的咖啡馆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客人来了就先落座,先买单是失礼的。花钱坐得,不花钱也坐得。男的女的,熟悉的,陌生的,挣钱多的,挣钱少的,嘈杂的,安静的,话语真切有回声,眼波流转有真意,都在咖啡氤氲的空间里荡漾开来。如此草根与开放,或许只有开罗的街头咖啡馆、或者成都的茶馆可以与之媲美。

回想我在福山公期祭神中的礼遇,觉察出它与平民咖啡馆有相通之处:无论对熟人与陌生人,要持一视同仁的包容。不论贵贱,和主人是否相识,来了就是客。这样的咖啡,它就是一株普通的植物,人人得而采之喝之,最后留在老咖啡客的齿颊里。而这样的咖啡馆,就是供养众众之乐的所在。

看完聊一聊
可以跟我们推荐你常喝的小众咖啡
也欢迎一起聊聊
在一些特别的地方喝咖啡的经历。
文、摄影:朱英豪
悦食Epicure © 2022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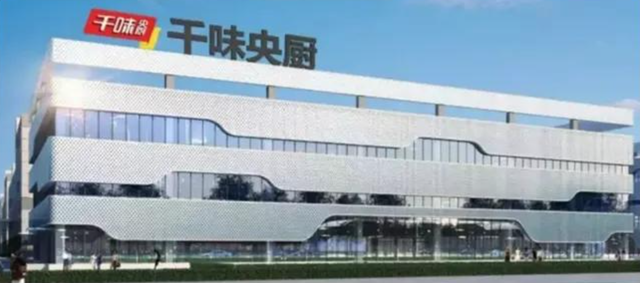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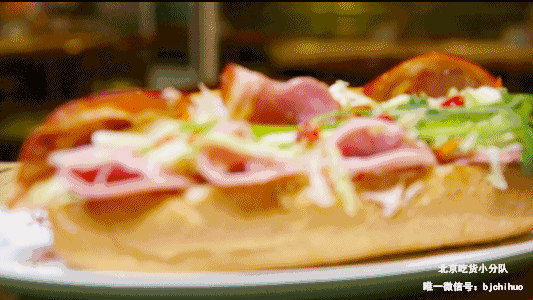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