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常玉更懂西方现代艺术,用东方人的情思征服了巴黎艺术圈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这样描述一战与二战之间,这个正处于「黄金年代」的巴黎:「巴黎永远没个完,每一个在巴黎居住过的人的回忆,与其他人的回忆都不相同。巴黎永远值得你去,不管你带给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
巴黎的文化,通常被穿城而过的塞纳河所划分。在塞纳河右畔,是激进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居住着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等超现实主义文学家;而在塞纳河左畔,则是离开故国,来巴黎闯荡的艺术家们。他们渴望着在这座兼容并包,又高手如林的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

不同于「超现实主义」这样明确的名称,艺术史用「巴黎画派」 来概括在塞纳河左岸的这个艺术家群。巴黎画派中,有毕加索、夏加尔、苏丁、莫迪里阿尼、藤田嗣治等艺术家。
由于背井离乡,身份的得失通常成为隐藏在艺术家作品背后的原动力。「贵公子」常玉,尽管在巴黎社交圈如鱼得水,对待画商却采取「不合作」的方式,最终在蒙帕纳斯的工作室,因煤气中毒而去世。他的作品,也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被画坛重视。

与常玉不同,藤田嗣治这位「巴黎的宠儿」,极盛时,能使毕加索在他的画前,驻足三小时之久;而他极衰时,却被贬为歌颂战争的帮凶,被故乡日本抛弃,在巴黎逝世。他应该是最能阐述这种「身份的焦虑」的人。
1886 年,藤田嗣治出生在东京,是一个标配的「高干子弟」:母亲是幕府官宦家庭的女儿,父亲是当时日本陆军军医总监,兄长藤田嗣雄是法学教授。由于母亲的过早离世,他的父亲藤田嗣章,对他的管教格外严苛,并且希望他将来能够子继父业,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医生。

自画像,1931
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家教,往往是一对奇妙的化学剂。14 岁的藤田嗣治用信件的方式,向父亲大人坦白了自己的理想:「我想成为一名画家,请让我做喜欢的事,我一定会成功给你看。」
他有志气,艺术缪斯也有眼光。这一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召开的前夕,日本当局挑选了少年藤田的一幅水彩画,将它拿到巴黎展出。能让万博会抛出橄榄枝,他的天才必定是耀眼的,他的个性也必定是特立独行的。

猫
1905 年,藤田嗣治考入东京美术学院油画系。他的老师黑田清辉,以明亮外光的印象派式的画法,为日本艺术家所著名。但叛逆的藤田不吃这套,他心中有自己的美的法则:
「指导我的黑田清辉老师说,要将黑色颜料从调色板上排除出去,这是不可理解的。我们作为东方人和日本人,熟知黑色的韵味,作为生命的黑色,为什么不能在油画中使用?我很快就决心在日本人的油画中,使用黑色。」

新信徒,1917
1913 年 6 月,大学毕业的藤田嗣治,终于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到达巴黎后,因为手头拮据,他住在房租相对便宜的蒙帕纳斯「Cite Falguiere」中。同住在这里的,还有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等人。
在蒙帕纳斯,他的西班牙画家朋友尔蒂浊·德·扎拉特,带着他参观了毕加索的画室。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初,以毕加索为中心的一批画家,在蒙马特高地掀起了现代主义的浪潮,并创作了第一幅立体主义作品《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的作品,让藤田嗣治感到了极大的震撼,甚至可以说,动摇了他所持的艺术观。尽管在日本修读油画时,他对印象派的创作手法和视觉方式并不很赞同,但他毕竟是在日本国内美术学校,接受过系统油画教育的学生,印象派对他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而在巴黎,他亲眼看到了「以新的形式毫不犹豫的大胆革命」,他决心立刻放弃在日本学到的印象派画风。从毕加索的画室回到家,他就将黑田清辉老师指定的画具,砸得粉碎。

自画像,1936
初来乍到的藤田嗣治,不懂得巴黎艺术圈的运作机制。没有打开他的社交圈,也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艺术品商人,买他画作的人因此寥寥。没有收入来源的画家,只好变卖自己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来换取生计,在冬夜只好烧自己的画材取暖。
他标志性的「西瓜太郎」式的发型,也是在潦倒的那时剪的。起初修剪的原因是他付不起去造型店的费用,于是只好自己动手,采用了这个傻瓜式的锅盖头发型。这个发型就像是他在巴黎文艺圈的个人符号,再加上那副圆框眼镜,他的形象,已然令人过目不忘。

自画像,1922
想要在巴黎扬名,拥有一个奇特的造型远远不够。艺术家总得学会经营自己,换句话说,兜售自己。他开始出入舞会,结交更多的艺术家和模特。
有时他穿着和服,有时穿着希腊服装,自称为「蒙帕纳斯的希腊人」,有时甚至穿着女装。不久,巴黎就记住了这幅东方面孔。朋友们唤他为「FouFou」,在法语里的意思是「迎合他人的人」。

德包尔肯和鸟笼,1917
与巴黎的生活相互磨合的同时,他也在磨合自己。接触到了毕加索、卢梭、苏丁、莫迪里阿尼等一众画家之后,他开始寻求艺术上东西方的融合。
与从前在法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不同,传统的学院教育对于藤田嗣治,毫无吸引力。每天 24 个小时,他有 14 个小时的时间呆在画室,研究、练习他认为的自由的风格。休憩的时候,除了社交,便是到卢浮宫去看画。

莫迪里阿尼作品
藤田嗣治在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之前,在各式各样的风格和流派之间徘徊。他练习过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仿照卢梭创作过风景画。而对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莫迪里阿尼。
在藤田嗣治的许多人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迪里阿尼式的,削长扭曲的脸型、色块平涂的眼睛,和曲线灵动的身体。在他的若干雕刻中,也可以看到莫迪里阿尼带给他的巨大的影响。

生活,1917
1917 年,藤田嗣治在巴黎举行了他首次个人画展,在此次画展上,毕加索在他的画前驻足了三个小时,这对他无非是莫大的鼓励。
这次展览的,主要是以线描为主的水彩画。在这些画中,我们仍可以看到鲜明的莫迪里阿尼风格。但与莫迪里阿尼不同的是,他的画作色彩更明朗,线条更清晰,人物动作更柔和,背景更平静,整体就像是换上了西方人面孔的浮世绘人像。

甘纳罗西塔,1923
西方世界显然对藤田嗣治这种,将浮世绘和西方绘画技法结合在一起的风格,非常感兴趣。如马奈、毕加索、梵高、高更等后印象派的画家们,也已经就如何结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画法,进行了长久而颇有成效的实验。
有了这些前人的铺垫,藤田嗣治日后的大放异彩,是可以预知的了。藤田嗣治来到巴黎的这个选择,是何其精准啊,巴黎与他是互相成就的。

侧卧的吉吉,1922
真正使他在巴黎名声大噪的,是 1922 年的法国春季沙龙展会。他的一幅《侧卧的吉吉》,吸引了全巴黎人的目光。
藤田笔下「乳白色的裸女」的名号,也遍布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在传记电影《藤田嗣治》的开头,卡车正载着藤田嗣治的一幅裸体画驶向画廊,连路边卖水果的小贩见到,都能认出这是藤田的作品,甚至能说出画中模特的名字——当时被称作「蒙帕纳斯的女王」的「吉吉」。

侧卧的吉吉,1922
东方人自古以来喜爱肌肤白皙的美人,庄子《逍遥游》形容姑射山的神女是,「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白居易形容杨贵妃是「雪肤花貌」;日本的歌舞伎在表演时,从脸到脖颈都会涂上歌舞伎白粉。
藤田嗣治从此以「藤田白」在巴黎画界驰名。对这种描绘裸女的方法,藤田嗣治说,在着手创作女性裸体画时,他想开拓前人未曾涉及的新天地、新想法,「我们的祖先铃木春信、喜多川哥麿,都曾描绘过妇人的肌肤。我既为日本人,理应踏着先人的足迹,去描绘人的肌肤。」

横卧的裸女与猫,1923
西方画家在寻找新的色彩表现时,往往寻求的是,如何以令人过目不忘方式运用色彩,如何突破古典绘画的「真实」,寻求强烈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色彩呈现。
而作为东方人的藤田嗣治,更多的思考是「无色彩」(黑与白)和画作本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他的众多裸女画中,可以看到乳白色肌肤与黑色毛发的对比,是如此鲜明,又是如此和谐。

女人像,1926
从日本漂洋过海而来的「异乡人」藤田嗣治,在此时终于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画中别人的影子越来越少,更多是他个人审美内的东西。藤田嗣治成为了「巴黎的宠儿」。他用东方人的情思,和东西方完美平衡的绘画,征服了巴黎。
192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箭在弦上,藤田轴心国公民的身份,多少让他在巴黎有些尴尬。于是在当年,藤田嗣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日本,举办了多次个人展览。之后他又前往南美,边旅行边画画。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日本躲避战火。

Moine Boudhistes Dans Un Temple,1928
艺术一旦沾上政治,就难以摆脱政治带来的阴影;政治一旦开始操纵艺术,就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滥用。
在当时,日本军政府将艺术作为宣传政治、鼓吹战争的工具,成立了一个「大日本陆军从军画家协会」。这些被挑选为「从军画家」的画家们,被派往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进行「写生」,借以鼓舞军人士气。

Chat couturier,1927
藤田嗣治作为「从军画家」的这段经历,使他获得了祖国的短暂的承认。他的一些画作,如《哈尔哈河畔的战斗》,用他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军队的勇猛气势,赞美着胜利的时刻。而他的另外一些画作,如《阿图岛玉碎》则表现的是伤亡惨重的日本军民。
如果说前者,或许带有迫于当局而不得已的缘故,那么后者应当是他真实的感情流露,他说过:「在战争中,我只为那些可怜的士兵而画。」

阿图岛玉碎
二战后,日本美术界开始清算这些艺术家的责任(要我说,真是有些忘恩负义)。朝日新闻曾经撰文批评他:「不惜出卖自己的艺术资质,堕入平庸的写实泥潭,对军部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这种娼妓式的行为,不仅是他自身的耻辱,也是对全体美术家的耻辱。」
对祖国失望了的藤田,对此的评论只有一句:「画家之间不要争吵,祝愿日本画坛早日达到国际水平。」1949 年,他返回巴黎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日本。他说,「不是我抛弃了日本,是日本抛弃了我。」

回到巴黎之后,曾经的「巴黎的宠儿」在此时,已不像此前那般得宠。人们对法西斯的仇恨,转嫁到艺术家的身上,曾经的艺术好友纷纷远离。处在夹缝中的藤田嗣治,又回到了他当初刚到巴黎的境况。
在身份上,他是「日本人」,而日本已经唾弃他了,巴黎是他的第二故乡,而此时的巴黎也以刽子手的帮凶的眼光,来看待他。

猫
究竟应该维持「日本人」的身份,还是应该成为「法国人」?藤田选择了法国,因为相比有些疏离的法国,对于日本他已经毫无眷恋。
「我归来是为了在这里永居;我想死在法兰西,然后葬在蒙帕纳斯公墓,莫迪里阿尼的旁边。」

教堂壁画
仿佛是一种「看透」,步入老年的藤田嗣治,将自己沉浸在宗教画当中,并且加入了若干慈善组织,试图抹平过去留给他的伤痕。
73 岁之后,藤田嗣治正式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加入了法国籍。从此之后,他是「法籍日裔画家伦纳德·藤田·嗣治」,住在巴黎的郊外,创作宗教化和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还造了一座小教堂,为它创作了壁画。

1968 年,他被安葬在了这座名叫「和平圣母」的教堂中,虽然不是莫迪里阿尼的旁边,但也至少是一个较为完美的句点。
电影《藤田嗣治》的一句自白,也许可以概括他的大半生:「我越是行事乖张,活得越是疯狂,就越接近真实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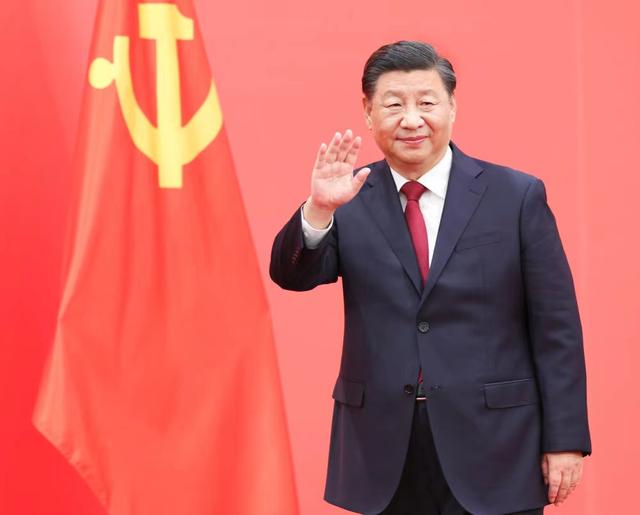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