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萧启庆先生逝世五周年祭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间萧启庆先生驾鹤西去,回归道山已经五周年了。由于素不做元史研究,加之孤陋寡闻,五年前11月11日萧先生仙逝的消息令我惊愕,但我知道这个噩耗却很晚,直到看了四世同堂网站有关社科院历史所举行追思会我才知道,当时感到甚是遗憾,因此无从祭典内心崇敬的萧先生,今此要写一点文字表达一下我的怀念之情。
其实我跟先生并无深交。读研究生期间曾读过萧先生的元史论著,撰写《宋夏关系史》也曾借鉴萧先生有关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方法。不过对先生的了解开始于1995年漆侠师应邀客座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讲学,恰好是接替1994年从国立新加坡大学辞职回到台湾的萧先生的教职。传说萧先生不到退休年龄而退职,只能一次性拿到退休金100万美元,那时一百万美金对拿三五百元人民币月工资的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很快不久于1997年在广州参加宋元国际研讨会就见到了萧先生,没想到萧先生面相特别显年轻,先生是1937年生人,1997年已年满花甲,看上去却像只及不惑之年,近1米9的颀长身材,显得特别帅气儒雅。记得那天是在陈学霖先生的房间,刚认识我的陈先生把我介绍给萧先生,那时39岁的我刚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长,但两位前辈给我很高的礼遇和呵护。我给萧先生送了一本《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先生回赠我一篇签名文章,“华瑞兄指教”着实让我紧张了好一会。虽然十几岁读鲁迅的《两地书》就知道长者给晚辈书名为“兄”是一种礼节性的谦词,但是面对国际元史大腕,着实还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在会议期间我曾专门到萧先生房间拜望,先生风趣、幽默、睿智、谦和,与他交谈总是感到很愉快。先生对我送他的书颇感兴趣,问我宋代那么多文人雅客喜欢饮酒,宋代饮酒风气很盛,酒俗也很丰富,为什么不在写酒税与财经关系之余写写宋代酒文化呢?我回答说漆侠师只让我专注于经济史的角度,以后有机会再补写吧。可是时过二十年我仍没有补写,很是惭愧。那时正是年轻气盛,也是酒量最好的时期,又逢会议主持人张其凡先生好酒,因而在会上畅饮过好几场。特别是会议闭幕后的聚餐,我与萧先生、戴仁柱(Richard L. Davis)、汤开建等先生坐一桌,这才知道萧先生喜饮酒,而且量也不错,那天真是豪饮,喝了不少会议准备的古井贡酒,喝完古井贡还不尽兴,又喝戴仁柱教授带的威士忌,我差不多总共喝了一斤半以上,萧先生也喝了不少。戴仁柱教授对我们用碗喝酒的豪饮很惊异,说你们喝酒怎么像喝水一样啊?酒席散后,汤开建请萧先生和我到他的新居喝茶聊天并参观他的书房。直到我要赶23点的返程火车才与萧先生和汤开建匆匆告别。
再见萧先生已是2009年。2009年秋季应徐泓先生邀请我到台湾东吴大学客座讲学一学期。在台期间曾与萧先生有两次会面,都是在宋史座谈会上。宋史座谈会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每年出版一辑《宋史研究集》,至2006年已出版了36集,是台湾宋史研究带有标志性的学术团体。台湾宋史座谈会主持人、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邀请我做讲演,11月8号下午,第174次宋史座谈会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会议室举行。那天来听讲演的台湾宋史界的师友达三十多人,王德毅先生对我说这是近五六年来座谈会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我能记住名字的有王德毅、萧启庆、柳立言、黄繁光、赵振基、黄敏枝、韩桂华、刘祥光、蒋义斌、李天鸣、方震华、林煌达、刘馨珺、吴雅婷、陈昭扬、雷家圣、洪可均诸位师友,有这么多师友来听我的报告,大概是因为1991和2000年我参与组织两次国际宋史研讨会,而且从1996年我开始负责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和《宋史研究通讯》的工作,与台湾宋史界的师友有较广泛联系的缘故。萧先生三年前曾做过心脏手术,平时已较少出门,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有点担心萧先生的身体,萧先生反而笑着说,“华瑞来了,我还是要听听你讲大陆宋史研究的情况,再说我们也可以喝两杯”,听了先生这样讲让我很感动。萧先生虽因疾病损伤了身体,风度不再翩翩,但是一如12年前潇洒睿智。我讲的题目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宋代历史地位研究若干问题述评。”讲演之前我特别抱歉声明,我的PPT没有用繁体中文而是用简体中文,萧先生诙谐地说,“你放心,我们虽然不用简体,但是我们识读简体的水平不比你们的学生认识繁体的水平低。”萧先生的话一下让我放松下来,那天我讲得比较自如。讲完以后,进入讨论阶段,萧先生提问说为什么大陆对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一直采取排斥态度,我回答说也不能算排斥,主要原因是大陆意识形态比较浓,五个社会形态分期说将宋代作为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都没有太大改变。萧先生又问你现在与黄时鉴先生还在打笔墨官司吗?先生这样问,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萧先生提醒说《徐规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不是有你的文章《酒与宋代社会》吗?这才明白萧先生说的是我对黄时鉴先生认为烧酒起始始于元朝的观点略有异议,我没有回答萧先生的问题,而是径直问先生,那您支持谁的观点,先生笑而不语。座谈会结束后,按照惯例,王德毅先生请大家共进晚餐,王先生带了一瓶58度1000毫升的金门高粱酒,可是很快就被喝光,这时王德毅先生问是否要再买一瓶,萧先生笑着说不用,我知道华瑞来了一瓶肯定不够,我早做了准备,说着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瓶600毫升的金门高粱,这瓶酒喝完聚餐才结束。萧先生的学生陈昭扬送先生回居所时,先生说有机会再聚会。

前排从左至右:萧启庆、王德毅、黄繁光;后排从左至右:刘祥光、方震华、雷家圣、李华瑞、李天鸣、陈昭扬、洪可均。
12月20日星期日下午,宋史座谈会举行第175次座谈,仍然是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会议室,由王德毅先生主持。讲演人是浙江大学的黄时鉴先生。黄先生当时在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学,黄先生讲的题目是《元代缠足新考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来听讲座的有近20人,我再次见到萧先生。黄先生开场前说他的文章涉及元人文集,而全世界对元代文集最熟悉而他又最佩服的有两人,一是大陆的陈高华先生,一是台湾的萧先生,所以特别希望借此机会听到萧先生对他文章的批评意见。黄先生由南宋末黄昇墓有记述缠足及图形,对元代和马可波罗游记缺少缠足问题记载进行考述。报告完后,进入讨论阶段,就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和宋元时期的缠足问题展开讨论,黄先生说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是从19世纪后期以来就存在。西方人基本都持怀疑态度,而中国学者则坚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萧先生不同意大陆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缺载史实是与他接触的多是色目人的观点,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二十年,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有更广泛的接触。这次会议结束后仍然是由王德毅先生请大家聚餐,不过这次聚餐跟上次不一样,由于黄先生的太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AD),黄先生和太太只吃了不多的饭,滴酒未沾就匆匆返回清华大学。12月下旬台北的天气已比较清冷,对心脏病很不利,所以大家担心萧先生的身体,但是萧先生依然酒兴甚浓,坚持喝完一瓶金门高粱,才同意返回府上。我和陈昭扬一同送先生,到了先生府上的楼下,先生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小酌,我也说希望先生能到大陆来,如果先生愿意我可以请先生到敝校讲学,我们也可在京城小酌。萧先生不无遗憾地说,恐怕我的身体已经不起往返两岸了,还是你来台北吧,台北的气候多宜人。说完先生便转身走向楼门,望着先生踽踽而行的背影,不免有点怅然,默默祝先生健康长寿。这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三年后先生发病遽归道山。虽然先生走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先生安息。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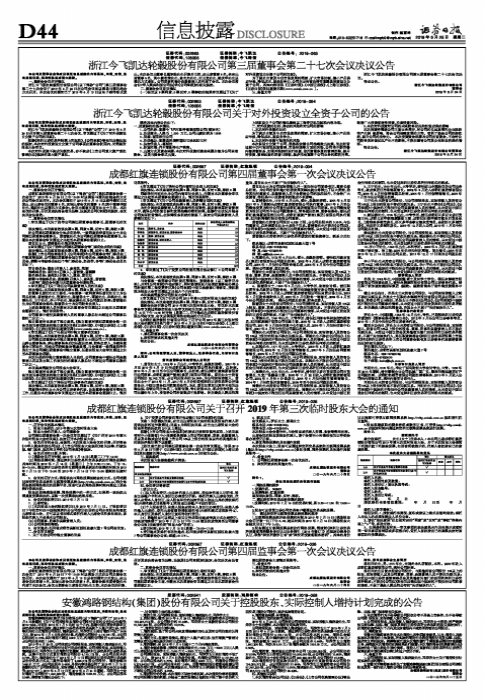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