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为人质,美国法律如刀肢解阿尔斯通
【2018年12月,华为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而孟晚舟女士并无违反美、加法律的行为。据报道,加拿大此举是应美国要求,当时中美两国就5G建设方面正在开展激烈竞争。
华为和孟晚舟并非是“独享”这种待遇的人。2013年4月14日,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法国阿尔斯通集团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之后,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7.72亿美元罚款。同时,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被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堪称是“法国版孟晚舟事件”。
在《美国陷阱》一书中,皮耶鲁齐以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以及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内幕。观察者网摘录书中部分内容,与大家共享。】

《美国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
第一次开庭
谁能相信,当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时,我竟然很高兴。在脱得精光,又被人搜过身后,我戴着手铐被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一路上,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罗恩和罗斯给我带了咖啡和一些百吉饼。他俩都是35岁,相谈甚欢。罗恩有3个孩子,他身材魁梧健硕,酷爱潜水。罗斯有1个小女儿。他俩都很想畅游法国。最后我们一同聊了起来,好像熟人一样。
到法院后,罗恩和罗斯把车停在外面,等候指示。我们来早了,所以坐在车里等了1个小时,直到纽黑文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羁押我的两位探员,庭审地由纽黑文改为布里奇波特——在另一个方向,开车要半个小时。于是我们又出发了。在把我交给法警之前,罗恩把车停下,罗斯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倘若在庭审中发生不测,这就是我最后跟某位亲友通话的机会。这里正值中午,而新加坡却是午夜。我选择打给阿尔斯通美国锅炉部门的主管库兰。我想向他通报昨天晚上我和卡尔的谈话内容。别忘了,卡尔白天的时候就应该抵达华盛顿了。我想,库兰肯定会和法务总监一起关注形势的变化。无论如何,我都会要求他这么做。
罗斯和罗恩跟一位法警交接后,我向他俩告别。然后,法警把我关进法院的一间小牢房里。法庭将会审查我的获释请求。庭审即将开始。因为获准提前和阿尔斯通委派的律师对话,我被带到一个小隔间,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
莉兹是一位年龄在35~40岁的女士。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对我的态度也十分冷淡,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
“为什么?他们来接手我的案子,岂不是更合情合理?”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
“我不懂。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案子,阿尔斯通正在和美国司法部做交易。那把我也算作交易内容之一就行了,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我和阿尔斯通之间哪有什么利益冲突?”
“皮耶鲁齐先生,事情没这么简单。但请您放心,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幸运?接下来我试着从莉兹口中了解有关我被控罪名的细节。在这个专为被告人和律师见面而设置的小隔间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铁丝网,谈话非常困难。她拿出几张纸,把它们紧贴在铁丝网上。不用说,我肯定看不清楚纸上的字。更意外的是,我发现她都没有读过起诉书。她轻率的态度把我惹火了。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
“贪污案,外加洗钱。”
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请您明白,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
罗斯柴尔德服罪了?获刑不超过5年?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尤其是给我和我的亲朋好友的生活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的传唤。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首先问我是否听得懂英语,接着就请我的辩护律师开始陈述。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莉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
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探视过我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厚颜无耻的他完全推翻了此前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对我说过的那番话,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在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拒绝了他的要求,诺维克现在要让我为此付出代价。紧接着,他从我的个人处境方面进行攻击: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无亲无故。他在美国工作时,已获得绿卡(永久居住权)。然而,非常可疑的是,2012年他又将绿卡退还给有关部门。我方已询问过当时接受皮耶鲁齐退回绿卡的员工。他告知我们,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当时行为古怪,令他十分惊讶。”
我简直要晕过去了。2012年,那是我多次美国之行中的一次,不再需要绿卡的我借机把它还了回去。何况我那时马上要迁居新加坡,至少要在那里工作几年,所以何来可疑之处?但是诺维克继续说道:
“如果本庭将此人释放,其必定会出逃。法官大人,您非常清楚,法国不引渡其公民。此外,此人在已遭受指控、逮捕证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仍未向当局自首!”
这位检察官用心之险恶,令我震惊。美国司法部封锁了对我签发逮捕令的消息,就是怕我躲在法国逃避追究。我对此毫不知情,又何谈向当局自首?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早知此事,那我很可能先向律师咨询,以确定是否可以前往美国出差。这一切简直可笑。尽管如此,加芬克尔法官看起来似乎被说服了。她说:
“本法官可以确信,当局呈交的起诉书很翔实。如想让本法官释放其委托人,辩护律师应起草一份更具说服力的缓刑意见书。拉蒂夫女士,本法官愿意给您一段时间准备新意见书。您认为何时能够完成?”
“法官大人,下午完成。”
“啊,这个时间不可能,因为不巧我一个小时后要离开,我已经与一名医生约好见面。我建议,咱们两日后再见。”
庭审即将结束,法官转过身问我:
“皮耶鲁齐先生,您要做何种辩护,认罪还是无罪?”
“无罪。”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这才明白:我仍须在监狱里待48个小时。被带回牢房之前,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和我的律师聊了几分钟。我的案子目前看来十分令人担忧,我恳请她立即将情况告知卡尔。
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就像一只野兽。
的确,我已经成了一只野兽。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词了。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之前我唯一一次瞥见像这副样子的人,还是电视报道的关塔那摩监狱里的犯人。因为被这堆链子捆住了双脚,我无法正常行走,狱警有时候逼着我双脚并拢蹦着前行。我们去找法院地下室停着的一辆微型囚车。这是一辆配有防弹玻璃的囚车,窗外覆盖着粗粗的铁丝网,很像特种部队使用的特种车辆。
车内还有两个犯人坐在我旁边:一个亚洲人和一个大块头黑人。我试着跟他们搭话:“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但我听不懂他们的回答。他们讲的是监狱里的黑话,还用倒错词说,外加很多江湖黑话。我精疲力竭,不再问下去。我已经快两天没有合眼。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变故一场接着一场,我快晕倒了。在这辆囚车里,在这个装着轮子的牢笼里,在这密不透气的小箱子里,我感觉自己像猎物一样被人揪住了脖子。我累坏了,睡着了。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第二次开庭
这一次,狱警没有忘记我。凌晨4点整,两名狱警冲进了我的牢房,把我弄醒。我又遭受了一轮搜身,之后被人用链子从头到脚拴了起来,就像第一次被押解到怀亚特看守所时那样。走出牢房后,他们把我塞进一辆装甲卡车,朝纽黑文法院驶去,车程3个小时。距离开庭还有几分钟,我获准和两位辩护律师——莉兹和斯坦会面。
再一次见到他们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有些萎靡不振。他们告诉我,他们刚刚和检察官诺维克讨论了几分钟。
“他表现得很顽固,毫不妥协,”斯坦向我吐露实情,“他对我们准备支付的保释金金额不感兴趣,并下定决心向法庭请求将您继续收押。我想,他仍然对贵公司拒绝合作耿耿于怀,他们觉得,这些年来阿尔斯通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坠落,好像永远都触不到底。因为此时此刻,我发现,从斯坦和我多次沟通的内容中得出的结论是,3年多前,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也就是说,调查自2009年底就在进行了!但卡尔有意不告诉我这个时间点。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企业还须承诺建立起一套内部反腐败机制,并且接受“督察”——一位连续3年向美国司法部做汇报的监督员——的存在。如果能遵守这些条件,那么法官就会和企业达成协议,结局通常是罚款。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员被捕(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协议并不会终结针对个人的起诉)。
在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阿尔斯通,更准确地说是柏珂龙想奉陪到底。正如我之后发现的那样:阿尔斯通使美国司法部相信它会合作,但在现实操作中却阳奉阴违。当美国司法部发觉被愚弄时,检察官气得发疯,于是他们决定改变策略,由警告变为猛烈进攻。

美国检察官气成河豚
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我中了这肮脏的圈套,成为柏珂龙阴谋的牺牲品,沦为美国司法部的“人质”。很快,我就能从诺维克口中证实这一切。当主持庭审的评审团主席琼•G.马格里斯法官请诺维克发言时,诺维克直截了当地揭开了他为何向阿尔斯通宣战的内幕。
“该公司在承诺合作后,多次滥用美国司法部的信任!阿尔斯通本应协助我方进行调查,但事实上却行动怠慢、避重就轻,其态度模棱两可。我还想提醒法官注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也提到了法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尽管阿尔斯通这家跨国公司受到了包括瑞士、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的行贿指控,但法国政府仍未对其采取任何行动。”
他毫不迟疑地继续说道:
“我方掌握了所有证据,其中大量文件披露了这些同谋是如何商讨收买印度尼西亚议员的。我方还掌握了银行出具的证明,还有证人,这些证人已经做好了出庭做证的准备。”
我心中再次产生了疑问:美国司法部是如何找到这些材料的?庭审开始之前,在我和斯坦、莉兹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了我这场斗争的底细。对我来说,这的确是沉重的一击。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觉得人为操纵的痕迹太明显,就像是电影剧本。“不,” 我告诉自己,“这样的故事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但是我错了。现在来看,这的确是现实。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所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才使他变成一名“叛徒”?是以长年监禁相要挟吗?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150万美元的保释金,以求将其释放。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保释条例中的担保人?
此外,我们尚不确定此案未来的发展态势。倘若有一天,阿尔斯通和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利益发生分歧,那时会发生什么?倘若皮耶鲁齐先生决定认罪,那又会发生什么?阿尔斯通会如何回应?到时由谁来担任保释金的担保人?请您不要忘记,佩戴电子手铐并不能提供十足的保障,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随时可以切断电源后逃跑。至于阿尔斯通承诺支付酬金给那些看守,一旦公司突然决定不再付钱,那又该做何处理?两年前,美国司法部曾批准在一名法国侨民——卡恩先生的公寓周围部署看守,但那和今天此案的情况完全不同。卡恩一案中,法官同意了判决主文,指控内容不可靠,指控卡恩的主要证人的证言失去了效力。但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靠。
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转过身去看我的律师。斯坦把头扭到一边,莉兹同样没有勇气正视我的目光——她宁可把头埋在笔录里。我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而接下来的30~40年,我可能都要在牢狱中度过!我被关押在怀亚特看守所才5天就受不了了。我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在这场噩梦里再坚持几个小时。而今,我可能要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甚名谁的中间人,而他有可能为了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接受一分钱的回扣。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阿尔斯通内部流程进行的。
终身监禁!这简直不可思议。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对我施压,想演戏来威胁恐吓我。这还不够,他坐下的时候,表情和我的两位律师截然相反,他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或者虚张声势。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那么我是真的有可能在监狱里终了此生吗?
我呆若木鸡,以至于在莉兹开始陈述要求释放我的文书时,我几乎都没怎么听进去。我隐隐约约能听到她的声音,就像是雾里看花,她在努力证明指控程序存在问题。据她说,我受到指控的事项已经失去了法律时效,超过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5年起诉时效。那些事是2003—2004年做的,而对我的控告则始于2012年11月。为什么她要纠缠这条法律依据?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法庭真相?直接向法庭说明我受到了毫无法律依据的不公正待遇,这难道很难吗?罗斯柴尔德承认了罪行就没有被关进监狱,而且要求其支付的保释金才5万美元,这和我为了被释放而被要求支付的保释金简直无法相比。
此外,诺维克检察官把我当作他和柏珂龙较量过程中向柏珂龙施压的手段,这种行为能被接受吗?他毫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在他和阿尔斯通下的这盘棋里,我就是他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
马格里斯法官退庭商议了一会儿。当她回到法庭时,我立刻明白,诉讼辩论结束了。
“对本法庭而言,本案非比寻常,”她开始唱高调,“本法庭通常受理的都是低收入家庭的请求,其保释金额不超过1500美元,这往往就是他们一生的积蓄。而在本案中,辩方请求支付的保释金超过了100万美元,但在我看来,这并不够。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我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释金的一部分。如果你们能带着这份承诺来见我,那么我将同意重新审查你们的保释请求。”
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也不信任我。为了让她转变观念,她需要一份来自美国公民的保证。相反,诺维克检察官则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她。他大踏步地走出庭审大厅,腰板挺得像根木桩,脸上洋溢着扬扬自得的神情。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阿尔斯通提出的那笔天价保释金就是一个错误的策略,这个策略对我反而不利。我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除此之外我还能怎样做呢?但是我错了。斯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诺维克和主审法官的反应?我开始严重怀疑:他到底是在为谁效力?
庭审结束时我还发现,斯坦的一位在巴顿•博格斯律所的同行(负责为阿尔斯通辩护)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庭审。他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的公司可以放心:我什么都没说。然而,由此得到的信息却很明确:我处于被监视之中,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律师控制着。
监禁125年
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些高墙了,但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又回到了怀亚特看守所的那间牢房。我将在这里再被关几天甚至几周,直到能够提出新的保释申请——第三次申请。
在看守所里,每个小时都漫长得没有尽头。我一直没有听到阿尔斯通的消息。斯坦告诉我,法务总监卡尔确实来过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进行过谈判。他刚好是在我被捕的24小时后抵达的,他却丝毫不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因为这位科班出身的律师10多年来一直担任公司内的要职,他了解公司的所有部门。
2004年,他成为电力部门的法务副主管,1年后被任命为诉讼主管,2011年再度晋升,领导集团的法律事务。他熟悉公司的所有商业“做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阿尔斯通是怎样招募中间人,并且是如何付钱给他们的。为什么调查人员没有逮捕他?他们能从他身上了解到的一定比从我身上了解到的内容多。为什么他们单单瞄上了我?这在我看来非常难以理解。
我还是希望卡尔能趁着在美国谈判的机会到怀亚特看守所探望我,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也无法与公司其他领导取得联系。商业界和工业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岁小孩。我虽然清楚这一点,但是仍然感到深深的厌恶。
转眼之间,我就成了公司里的害群之马。进入看守所以后,再也没有人与我来往,我就像是一个鼠疫患者,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从普通同事到领导层,我与他们朝夕相处20年,此刻能否给我一些同情?但是,埋怨他人又有何用?眼下还有很多更要紧的事。
这个星期,斯坦和莉兹再一次来看我。我们一起在我的美国朋友以及和我有工作往来的美国人中间,寻找愿意抵押房产帮我离开看守所的人。
“按照您提供给我的建议,”斯坦向我报告说,“我问过美国阿尔斯通锅炉部门主管库兰,也恳求过销售部门副总裁伊莱亚斯•戈登,但他俩都回绝了。他们给我的回答完全相同:为了取悦本案负责有条件释放的法官,您应该向阿尔斯通寻求帮助,而不是他们。”
“平心而论,我理解他们,”我向斯坦表明观点,“就算是我自己,也不一定会承担这样的风险。”
“您在美国有亲朋好友吗?”
“很少。我们已经离开美国7年了,在当地没有家人。虽然我和几个人还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不过,克拉拉和很多人都保持来往,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她的一位挚友——琳达。我们等待着包括琳达在内的各方面的回复。另外,如果我们提议将我们在法国的房产作为担保呢?”
“不行,法官会驳回的,过去美国司法部就曾因为查封贵国境内的财产吃尽了苦头。”
我感觉自己仿佛又继续坠向一条深不见底、内壁光滑的隧道里,没有什么能把我接住。我隐隐约约想到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却随即消失不见。我早就知道斯坦会告诉我什么,只是他的说法太过直白。
“眼下您暂且留在看守所里,”他说道,“今天早上,我们在律所收到了关于您上诉日期的首份提议,日期是2013年6月26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
我依然试图在那条隧道的墙壁上找到一处把手:
“但如果阿尔斯通把我的案件纳入和美国司法部的协议之中,那么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对不对?”
“我担心很可能并不会改变,”斯坦反驳我说,“这是两起不同的诉讼。美国司法部可以起诉一名法人,也可以和它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妨碍司法部对您个人提起诉讼。”
“我明白。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有可能把我的案子纳入协议当中。”
“理论上来讲可以。但是一旦您被收监,这样做的困难就会更大,眼下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相信阿尔斯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律师会忙于说服对手,使应付罚款数额降到最低,尤其是要保护尚未被起诉的其他管理人员。”
“那我呢,我能和他们谈条件吗?”
“能,您可以认罪。”
“我的意思是协商罚款金额以将我释放。”
“不,您只能认罪,之后由法官来决定您是否被判入狱。”
“那如果我和罗斯柴尔德一样认罪,我将面临5年的监禁?”
眼看着就到隧道尽头了,这可真是一条长隧道啊,但总该在某处结束吧,会不会是在这里呢?完了,即便是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出路,按照斯坦的意思,这个出路对我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不幸的是,”他向我解释说,“您的情况比罗斯柴尔德的情况更为棘手。请您明白,美国联邦调查局最先调查了罗斯柴尔德,之后他便立即同意合作,因而获得了谈判的最有利条件。而您是第二个,所以对于他们的调查,您能提供的帮助可能非常有限,而且您当时没有立即同意诺维克检察官开出的条件。”
交易!条件!协商!自从我们开始讨论目前的情况,斯坦和莉兹对我就只讲协商,而不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判断。就像地毯商之间的交谈,不过这回不是地毯,而是我!好吧,既然他们想这样做,那就做吧。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现实一点吧,不奢求正义和真理了!跟他们协商吧!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努力去尝试。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好,斯坦,如果您愿意,那就让我们重新开始。我可能面临的刑罚是什么?诺维克威胁我说是终身监禁。我想他这样说是为了吓唬人,这话不是真的吧?”
“啊,”斯坦说,“从理论上讲,这和事实也相差不多。您因10项罪名而受到起诉。第一项罪名是您策划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简而言之,这项罪名是指您涉嫌伙同其他高管密谋贿赂一名印度尼西亚议员,目的是签下塔拉罕项目的合同,而该议员隶属于雅加达议会下属的能源委员会。这项罪名应判处5年监禁。
然而,检察官们手中的证据表明,前后共有4笔款项相继支付给了这名议员的一位亲属。因此除了第一项密谋罪之外,您还因这4笔汇款受到指控,每一笔汇款都要被认作一项附加的控罪。这样,您可能会被判处5次5年监禁,总共25年。除此之外,您还有第二条主罪——密谋洗钱罪。一场以将黑钱洗白为目的的密谋。这项洗钱罪应被判处20年监禁,而考虑到已被证实的钱款总额,监禁年数还要再乘以5。因此,您将为洗钱罪面临100年的监禁,连同行贿罪的25年监禁。最终——而且是理论上的‘最终’——我们可以得出,总监禁时间是125年。”
这已经不再是隧道,这简直就是深渊。我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我依然据理力争:
“斯坦,等一下,这简直太荒唐了。涉案的仅仅是一份中间人合同!基于同一件事,检察官怎么可能针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洗钱行为提出10项指控?”
“美国的司法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皮耶鲁齐先生。我们和欧洲对洗钱的定义不同。在美国,只要有一笔金钱交易违法,美国司法部就会认定同样存在洗钱行为。”
“这太令人震惊了!我需要您提供更多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判例的材料。”
斯坦僵住了,好像我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一样。
“我认为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最好先协商您的案子,对吧?”
万变不离其宗,谈条件,达成交易。我了解过,在文章中读到过,也从别人那里听说过:美国司法体系就是一个大市场。但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些,才能明白这句话的内涵。现在我很疑惑,是不是律师、法官和检察官都拴在同一条“商业链”上。斯坦在为谁效力?怎么会搞出这样一个让人感觉如世界末日般的计算表格?125年的监禁!他难道也想通过恐吓使我屈服?我生气地问他:
“就像您说的,既然要协商,我就有必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检察官指控我的内容。他呈交的证据是什么?与我相关的罪证又是什么?我被关在看守所里已经超过了一周,但您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这次轮到莉兹向我发火:
“对您进行控告的起诉书一共有72页,非常详细。让我们开始读吧!开始工作!”
【本文摘选自《美国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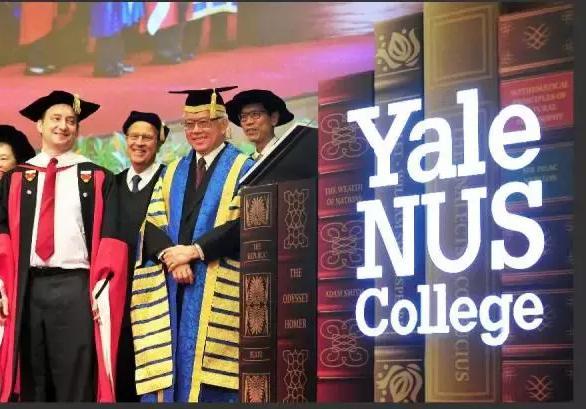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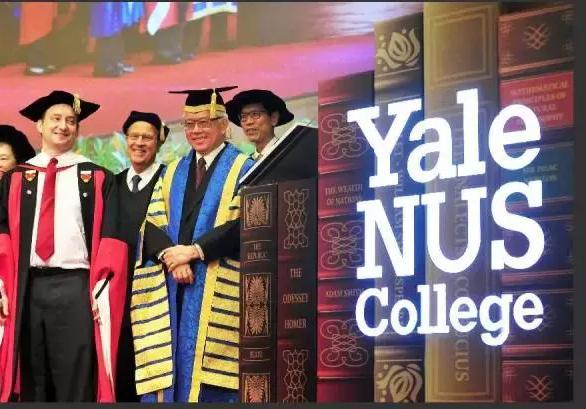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