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欣教授:司法为何淡化家庭暴力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作者:贺欣,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
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一则“电梯录像”刷屏了微博:一位男性,死拽着极力反抗的女性的双腿,将她拖出了电梯.....

这是美妆博主@宇芽YUYAMIKA 对于自己真实家暴经历的披露,其中包括多方采访与视频证据,一共十二分钟。视频中的“电梯家暴”就发生在不久前的今年8月21日。
本期推送香港大学法学院贺欣教授《司法为何淡化家庭暴力》一文,供读者参考。
文章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专论栏目“公平正义:司法的生命与灵魂”(第6—22页),原文19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贺欣教授
为什么离婚诉讼中几乎不认定家庭暴力或判付经济赔偿金?反家庭暴力法律的发展也没有改变这一情况。本文揭示那些使法官超越法律审判的动因——法官淡化家庭暴力的做法与他们身处的制度约束相关。
目次
一、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发展
二、司法调解对家庭暴力的忽视
三、审判对证据的不认可
四、罕见的“成功”
五、拖延判决中的延续暴力
六、人身保护令的有限作用
七、结论
原文为英文,由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肖惠娜译出。
人身安全是文明社会的最基本人权,但是很多中国女性的这项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根据官方报道,约1/3的家庭存在暴力。—项政府调查表明,1/4的妇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尽管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报道中近90%的案件是关于妇女遭受丈夫的虐待。登记离婚的案件中60%和家庭暴力有关。
寻求从丈夫暴力中解脱的妇女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中数量上升最快和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之一,这体现在离婚诉讼中对家庭暴力的普遍诉求。
最高人民法院发现27.8%的离婚诉讼原因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成为离婚诉讼的第二大事由;另一项最高人民法院报告表明10%的故意杀人案起因也是家庭暴力。巫若枝研究了310例华南某县1950年至2004年的离婚案件,发现几乎在所有案件中妻子一方都声称自己受到了丈夫的虐待。
然而,法院很少认定家庭暴力,更不用说给予经济赔偿。
基于重庆市某区基层法院起诉的家事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458个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仅有3个案件(0.66%)获得经济赔偿。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所有提交家庭暴力证据的案件中,只有17.3%的案件被认定有家庭暴力。
为什么离婚诉讼中几乎不认定家庭暴力或判付经济赔偿金?反家庭暴力法律的发展也没有改变这一情况。
本文揭示出那些使法官超越法律审判的动因——法官淡化家庭暴力的做法与他们身处的制度约束相关。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用安全的方式、有效率地结案。案结事了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这远远大于法律的要求。
本文首先介绍反家庭暴力法律的演变并表明立法保护的显著进步。然后围绕法官处理离婚诉讼的两个方式,即调解和审判,文章指出,即使法官已经确信存在家庭暴力,他们仍然在调解进程中视而不见;虽然这一情况在以判决结案的案件中有所改善,但差别不大。判决书中经常不认可家庭暴力的证据,而在一审中已经认定的证据也经常在二审中被驳回。
此外,在法院就明显无法复合的婚姻判决不予离婚时,也常常忽略家庭暴力对妇女产生的人身威胁。作为一项新设立的机制,人身保护令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总之,法庭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微乎其微。
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发展
过去,中国受害女性起诉到法院后遇到很多困难,执法人员并不特别关注家庭暴力投诉,他们把这类纠纷归为“夫妻吵架”或“家庭矛盾”。由于和谐社会中的儒家思想和中国人普遍不想介入他人的“家庭问题”,受害女性的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和亲戚一般都不会指证丈夫的暴力行为或出庭作证,“即使是受害妇女的兄弟姐妹都觉得介入其中是不合适的”。
![]()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然而,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越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被政府列为官方议程和公共话题。例如,在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说:“家庭暴力是一个跨越所有社会阶层的社会现象,并且变得越来越普遍。立法刻不容缓。”2010年,我国最大的妇女社会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宣布其全国各地分支机构共收到52,000例来自受害女性的家庭暴力申诉,它还进一步表示“家庭暴力严重威胁到中国妇女权益。”
政府长期将两性平等作为一项基本社会目标,但是直到2001年修订《婚姻法》,“家庭暴力”一词才出现在法律中。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32条规定,如果法院发现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应准予离婚。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受害妇女可通过民事诉讼得到救济,尽管这种保护很有限。
2000年,大量保障两性平等的法律条文出台。这些全国性的法律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保障法》。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是保护妇女权益和对抗家庭暴力的重要进步。
例如,与一般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相反,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并指认系被告所为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第40条)。尽管审理指南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但可以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引用(前言)。省级立法也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9月,已有20个省、市和自治区运用法律手段制止家庭暴力。至2008年10月,有23个省、市和自治区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计划,重点关注家庭暴力问题。
二十多年来,妇女权利组织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一直呼吁加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最终促成《反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颁布。公众普遍认为这部反家庭暴力法律是“社会和法律的一个巨大进步,它表明国家认可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家庭暴力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在中国不再被归为私人问题”。它宣示“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相较之下,之前的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为受害者提供切实的法律救济。《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一系列新的法律保护措施,最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在国家法律中定义何为家庭暴力。该法第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受害者“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危险”时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第23条)。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帕默(Palmer)列出“公安机关(第20条)和医疗机构(第7条)应法院要求应当提供侵害的证据”。“法院受理保护人身安全申请后应当及时作出决定(第28条),及时作出人身保护令需要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和具体的请求”。
另外,法院还需要有证据证明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第27条)。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禁止被申请人实施骚扰、跟踪或接触申请人或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第29条)。国家组织和相关机构应当协助法院执行(第32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罚款最高可达1000元或15日拘留,甚至面临刑事责任追究(第34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旨在打击相关犯罪。
理论上,这些法律法规表明我国正在向保护弱势妇女和儿童不受虐待的方向不断发展。为回应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关注,国家正通过法律方式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侵害。尽管目前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从2000年家庭暴力法律的空白到2015年单独就家庭暴力立法,对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两性等级观念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进步无疑是巨大的。
那么,法官如何应对家庭暴力问题以及受害者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司法调解对家庭暴力的忽视
以调解结案的离婚案件最能体现司法审判对家庭暴力的淡化。2015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仍然允许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涉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事实上,实证研究表明这类案件以调解或主动撤诉方式结案的比例高达62%。
调解的形式包括主动撤诉、调解离婚以及调解和解。主动撤诉是指第一次申请离婚时,法院不准予离婚;如果双方坚持离婚,他们需要重新起诉。对当事人而言,主动撤诉的法律效果和判决驳回一致;但对法官而言,这是一个调解案件。
调解离婚意味着离婚纠纷的解决: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和其他相关事项,其法律效果和判决离婚一致;然而调解和解是指夫妻双方和解并继续生活在一起。在这类案件中,法院不考虑家庭暴力的问题。以下将讨论主动撤诉和调解离婚,阐释法官在不同动态关系背后的相同逻辑。
1.主动撤诉
在主动撤诉的案件中,家庭暴力问题总是被忽视,就像它们从未发生过。由于夫妻双方仍属一个家庭,没有必要进行金钱赔偿。法官可能会口头教育或说服侵害人停止施暴,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任何法律后果。
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性第一次起诉离婚,指证婆婆殴打她以及夫妻性格不合。她的丈夫27岁,每月收入2600元人民币,拒绝离婚。丈夫的哥哥是聋人且没有工作,婆婆有精神问题。妻子两年前从陕西到上海打工(上海农民工案件),法官怀疑她可能有外遇,想摆脱现在的家庭负担。
然而,她的律师说真正的原因是“那男的有点毛病(暗示性无能),不能有正常的性生活。作为一个年轻的男人,他释放欲望的方式是抓擦她的外阴。这种伤害很严重,以致她没办法走路。但她不能去外面说”。但这些没有说服法官,直到丈夫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回家。她很愤怒,“我们每晚都打架。你相信我们能生活在一起吗?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恐惧!”丈夫的脸霎时变得难堪。起诉状提到婆婆的家庭暴力,法官并没有追寻家庭暴力的问题,毕竟女方主要关心的问题不是家庭暴力。她真正想要的是离婚。
对法官而言,其目标是找到案件的解决方案,要避免那些旁枝末节的问题。法官未加思索地向妻子的律师说明她的决定:
这段婚姻不可能存续,但是这次她不能离婚。我们必须尊重丈夫最后的尊严。尽管他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但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抹杀他对整个家庭的希望。我们必须保持这段婚姻的形式。让我们给丈夫的家庭一点时间,让他们从心理上做好失去她的准备。
原告最终“主动撤诉”。当然,原告并不是自愿这么做的,而是在法官的要求下。尽管法官没有作进一步调查,但法官看起来是认可存在家庭暴力的。不过,法官已经作出了不准予离婚的决定,便没必要调查婆婆或丈夫的家庭暴力行为。法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没有书面报告。在听到法官的强硬建议后,妇女和她的律师是配合的,就像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当事人一样。
如果家庭暴力问题在受到法官压力而撤诉的案件中没有得到处理,在完全主动撤诉的案件中自然也会被忽略。
在一个新加坡外出劳工案件中,法官说明一些实际问题之后,妻子便主动撤诉。在他们的对话中,妻子详细地讲述了春节期间她丈夫从新加坡回家后殴打她的经过:
原因是钱。我们总是为了这个问题争吵。我想让他直接寄钱给我而不是他父亲。打我的那天,他喝醉后很晚才回到家。他敲门时孩子们已经睡下了。我打开门后,他踢掉周围所有的箱子,踩在女儿们的玩具上骂我。我叫他小声点不要吵醒邻居。他向我扔了个杯子,我躲开后,杯子碎了。我的大女儿被吵醒了。她在她的房间看着我们,不停发抖。
他便开始骂女儿,说“我会杀死你们”,他还想要弄坏女儿们的房门。我挡在他前面,他便开始打我。他往我脸上揍了一拳,用手抓住我的头发。我没有回击,因为我当时想要保护孩子们。他打到筋疲力尽才停止,回他的房间睡觉。那天晚上我待在孩子们的房间,和两个女儿一起哭。第二天,我发现我的脸肿了,双眼充血。我休息了三天才能走出家门。
她说,丈夫打她的真正原因是她没有生儿子。不管原因是什么,法官对家庭暴力的指控并不感兴趣。法官没有追究丈夫的死亡威胁,也没有调查妻子所说的发肿的脸或有伤痕的眼睛。法官直接问:“离婚后你可以养两个女儿吗?”在伤心哭泣和慎重思考后,兼职商场收银员的妻子决定撤诉。
和诉讼一起消失的是她关于家庭暴力的故事,在案卷中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法官很有技巧,引导女方想到她脆弱的经济能力,假设离婚,她需要独自支撑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法官没有提到的是,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判决准予离婚。与此同时,法院可以要求在新加坡有体面收入的丈夫抚养孩子。如果女方知晓这个选择,她可能不会撤诉。然而,这种建议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结束一个案件,而可能是制造一个新的案件。
两种“主动”撤诉的区别仅在于法官遇到的抵触程度不同。在不情愿撤诉中,法官可能无法说服当事人接受撤诉的决定。这是为什么在上海农民工案件中,法官首先向女方律师解释自己的决定,律师多次代理离婚诉讼,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官的考量。在自愿撤诉案件中,法官面对的阻力很小。新加坡劳工案中的妻子在仔细考虑自己经济能力后撤回诉讼。
法官的意见很有影响力。不管是不情愿或是情愿撤诉的案件,法官对家庭暴力采取的方式是一致的:无动于衷,就像所有案件落入聋人耳中。法官们的想法很容易理解:只要诉讼双方当事人愿意撤诉,对法官而言这是最好的结果,为什么要管其他的?他们的工作是找到结案方法。
2.调解离婚
在调解离婚案件中,即使法院已经确定事实,家庭暴力问题也被忽略。
在下面这起离婚案件中,夫妻已经分居多年,丈夫和另一名女性同居;妻子提供了警察报告和伤痕的照片,证据表明丈夫实施过家庭暴力并有婚外情。夫妻双方同意离婚,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分割夫妻共同房产和承担对儿子的抚养义务。13岁的儿子一直和母亲居住。
和其他许多离婚案件一样,这对已经疏远的夫妻在法庭调查环节纠缠于种种指控而争执不休。庭审的第一个小时气氛紧张,双方对峙不下。由于法官想要阻止对抗进一步升级,她在没有宣布调查和讨论环节结束的情况下,直接进入调解环节。
事实上,她没有正式询问双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而这个问题大部分法官都会在庭审讨论结束时就询问。她知道双方无意停留在失败的婚姻上。经过30分钟的反复协商,就女方放弃夫妻共同房产而获得的补偿费用,法官计算出一个数额。
除了房产分割问题外,子女抚养问题也存在分歧。原告(男方)愿意每月支付500元抚养费,但被告(女方)要求每月800元。法官迅速决定促成双方以600元达成一致。出乎法官的意料之外,原告拒绝增加100元,这让法官犯愁。她已经向双方提供了一个她认为公平的让步,将妻子要求的800元降低了200元。她以为这样可以解决,但原告的顽固让事情陷入僵局。
根据贺欣和吴贵亨文章中的详细描述,为达成协议,法官用尽各种方法说服男方。法官提醒说这笔钱是用于抚养男方的儿子,而不是一个陌生人;她还提到他的儿子已经13岁了,这笔抚养费用不算高,因为他只需要支付到儿子18岁为止;她甚至还质疑男子工资的真实性,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收入是计算孩子抚养费的基数;她劝说男方,抚养儿子是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从我们的研究角度看,最值得深思的是,法官从未提及家庭暴力。
根据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难道男方不应该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吗?难道这不足以促使男方接受额外支出100元抚养费吗?
上述策略不是特例。在女销售员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法官成功证实了家庭暴力的存在。然而,在调解环节中,法官尝试在充满怨忿、对峙的夫妻间进行“调解”,从未提起家庭暴力。在巫若枝描述的另一个案例中,妻子不断提出家庭暴力问题,出具警察报告证明她受了轻伤,但丈夫否认这些伤是自己造成的。
在调解中,妻子私下对法官说:“我不敢向家庭以外的人透露任何事情。有时我被打得很惨,全身青紫。但当别人问我怎么会有伤时,我说是自己摔倒了。我也不敢告诉我父母真相。”法官回答道:“如果双方可以谈妥,我会让你们签署一份调解协议。如果不能,法庭会进行判决。我们会尽力。调解到这里结束了。”
这些对话表明法官不想触及妻子提到的家庭暴力问题。正如调解这个词语的含义,双方在调解中尽力达成合意。法官作为调解者,需要跳出过错和违法行为的审判框架。为了取得调解结果,法官很小心地保持一种较和谐的氛围。过多指责家庭暴力会招致男方的否认或抗拒,从而削弱调解的效果。换言之,为达成调解,法官应避免使用谴责性的话语。
法官以结案为主导的思维在发现犯罪行为的离婚诉讼中体现得也很明显。法官没有报告刑事违法行为,而是将犯罪作为达成协议的筹码。
在另一个案件中,卡车司机第二次起诉离婚,他声称25岁的妻子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回家。丈夫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需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昂贵的手术。她还很懒惰,不做家务。夫妻双方同意离婚,但对抚养权和财产分割存有争议。女子坚称她有权分割80,000元土地拆迁补偿款,但丈夫一家只同意补偿10,000元,并坚持要孩子的抚养权。
和大部分离婚案件中的妻子不同,这名女子精力充沛,她身材矮小但很结实,有一张健康棕褐色的圆脸。很难想象她会像丈夫所说的懒惰。这位妇女私下告诉法官,她的公公曾经两次试图强奸她,这是她坚持自己诉求的原因。法官和丈夫的诉讼代理人讨论了这个问题。丈夫的家人马上妥协并达成协议:丈夫一家同意支付40,000元,但没有对孩子的抚养权作出决定。
法官仍然只关心结案。被配偶以外的家庭成员强奸,无论成功与否,都是极其恶劣的犯罪。至少,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它是一种家庭暴力行为。然而,法官并不想去证实这一行为。她的公公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但从家庭成员总是询问他的意见来看,他应是一个身强体壮且很强势的男人。但是,强奸仅仅是法官用于迫使男方改变主意的筹码。
很多夫妻愿意接受法官主导的调解,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坐下来谈,而是法官促使他们调解,他们之间还有很多可讨价还价的地方。调解过程通常关注孩子抚养权和婚姻财产分割,但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暴力无可避免地被忽视。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涉及诸如离婚的家庭纠纷法庭程序和早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试点中,法官迫于压力需要“视而不见和轻描淡写”配偶的虐待,从而促使司法调解。法院对调解方法的广泛使用遭到许多批评,因为调解无法确定责任和惩罚施暴者,从而导致中国女性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持续存在。
3.法官的逻辑
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法庭调查中已经提出、讨论并确立了家庭暴力事实的存在,最终都会被遗忘,在法庭调解环节中尤其常被忽略。当法庭调查环节审查家庭暴力行为时,双方当事人会激烈对峙,当事人之间相互指控、侮辱和否认是常事。如果法官仍然纠缠在家庭暴力问题上,可能会损害和解的氛围而无法成功达成协议。
从法庭调查到法庭调解的演变过程,科布(Cobb)称为“转型”(transformation)过程。法庭调查阶段适用法律性规则,关注的是权利和义务,以现有证据为依据;但法庭调解阶段适用调解性规则,关注的是当事人的需求。
在调解环节,调解性规则迅速占据主导,扩张其权威性和管辖范围,将法律权利和道德指责排挤出去。科布指出,“调解的目标是达成协议,实现当事人的需要,而不是实现一条道德准则。事实上,调解的目的在于调和相互冲突的道德标准:没有绝对‘正确’的道德,除非能够认可和强化相对性”。
家庭暴力调查中的权利导向(rights-based focused)在调解过程中被需求导向(need-based focus)所取代。同时,法恩曼(Fineman)在分析抚养调解时指出,由于对话由“最佳利益说”所主导,父母的权利在子女的需求面前坍塌。
因为调解的目标是达成合意,它必须满足个人需求,因此它的话语总体上是务实的。事实上,正如希尔贝(Silbey)和萨拉特(Sarat)所说的,调解通过区分权利和需求的实践而正当化:权利话语适用于以等级和权力主导的正式场景中;需求话语适用于以参与性而非权力主导的调解程序。调解程序为纠纷双方提供了一个架构,允许双方以平等的社会、法律身份共同参与到纠纷解决中。
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尤其是因缺乏证据和模糊法律规定而导致的纠纷,都必须让位于维护关系和经济安全,最终不断被边缘化,直至消失。
国际实践中,是否对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纠纷案件进行调解,长期存在争议,这是因为调解会威胁受害人安全。学者普遍担忧,调解没有考虑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以及在施暴关系中经常出现的造成受害者恐惧和战栗的胁迫问题。
西方学者研究表明,社区内的调解程序经常边缘化家庭暴力问题。格雷特巴奇(Greatbatch)和丁沃尔(Dingwall)认为“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指的是家庭暴力的指控被“忽略或淡化”,暴力事件被表述为“关系性的而非犯罪性的”。在法院主导的调解程序中,情况并没有更好。正如特林德(Trinder)等人对英国制度的研究发现的,家事审判人员一直在边缘化家庭暴力的指控,有些案件甚至对坚持指控这一问题的妇女实施惩罚。
中国的情况更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由于调解由法官主导,法官有权以更多介入的方式边缘化家庭暴力的指控。相较于边缘化或驯化,我国家庭暴力的忽略更具强制性;部分原因是法官和纠纷当事人的权力悬殊明显。在营造调解的氛围中,法官积极且强势;相较之下,社区调解员显得更隐晦些,主要是因为司法调解是在审判架构中进行的。选择调解结案的受害者以为自己得到了法律救济,但实际上他们在达成调解协议时也不知不觉放弃了自己的法定权利。
第二,当他们选择司法调解时,他们也穷尽了所有的法律救济,再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择。政府最终意识到家庭暴力作为一项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司法机关受制于效率和保护社会弱者的冲突目标中,很难从体制上系统和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
审判对证据的不认可
对家庭暴力低确认率和低赔偿率的一个普遍解释是受害者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然而,张剑源发现,47%的受害者提供了证据。正如前面提到的,只有10%的家庭暴力申诉得到认定,只有17.3%提交的证据得到承认。受到家庭暴力的陈述是最普遍的证据形式,但法官大多不理会,因为它们是单方证据,对方当事人也经常否认。下一个问题是,法院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标准是什么?
一般来讲,“谁主张,谁举证”,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在原告(《民事诉讼法》第63条)。法律规则是,只要提出诉讼请求,就应当提供证据。然而,就家庭暴力而言,《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规定,受害人的陈述比被告的陈述更可信(第41条)。当原告提供受伤害的证据,并主张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至被告(第40条)。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是由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下属的非司法机构——颁布的。从法律上看,审理指南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至多算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属机构的一个指引。它不是法律,因此法官不必遵守,有些法官说他们甚至不允许在判决文书中引用。根据现行的证据规则,如果受害者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如医疗伤害鉴定或警察报告),便不符合指控施暴丈夫的举证责任要求。在这些案件中,大部分法院没有办法,只能不去理会家庭暴力的存在。
无论如何,法官对此享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并没有明确“多严重的虐待”是家庭暴力。所有轻伤都是家庭暴力吗?打一下是吗?如果不是,多少次才是足够的?打多长时间?法律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而是留给法官自由裁量权。另外,法官就是否亲自收集证据也有自由裁量权。《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需要对其诉讼请求提供证据,但是法官在认为需要时可以依职权收集证据。尽管如此,法官很少走出法庭收集证据。
法官在自由裁量权下如何判决家庭暴力的诉讼请求?以下事件是发生在反家庭暴力的试点地区珠江三角洲的一次审判。妻子指控丈夫在很多场合打了她。她出示了警察的到访记录、医疗报告和伤痕照片。然而,她的丈夫是一位大学老师,决心反驳每一项指控。他也出示了医疗报告和自己的伤痕照片,声称是妻子打了他。当法官问起事件的细节时,女方说:
……他抱怨我关门太大声,可能会弄坏门。为此我们吵了一架。他对着我的头指过来,这是打我的前兆。我躲过了他的手,跑到客厅。他追着我,揍了我五次。接着,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头往地上撞。我的前额肿了,我申请人身保护令时向法官展示过。接着我举起凳子向他反击,直到小区保安到达。
男方回复道,“是的,当我指着她时,她拿书砸我。我一直在猛低头。紧接着她抓起东西就向我砸过来。我试图阻止她,然后她举起了凳子。”
当法官问他,女方头上和额头上的伤是哪里来的,他首先说他不知道,接着说,“是她抓我和伤我的。我有照片为证。我没有打她。我有可能在自卫时伤到了她。”
在这段对话中,尽管女方提供了详细的陈述,男方仍把自己说成是受害人。他避开了女方提到的“他追着我,揍了我五次”,他说,“她拿书砸我”,“紧接着她抓起东西就向我砸过来”,以及“她举起了凳子”。他不承认女方的所有伤害指控,尽管他可能无法解释她前额和头部伤痕的原因。他提到在自卫时可能伤到了她。
法官并没有引导男方承认实施家庭暴力。当法官问他关于原告的每一处伤痕时,他说“我不知道”或者“我没有看到”。显而易见,这个男人很狡猾且难以对付。另外,他很有经验地保留了前臂、胸口和手指上被抓咬的淤青和划伤的医疗报告。
尽管如此,妻子提供的证据更具说服力。记录显示,妻子在被丈夫打后报警,她的头肿得比较厉害。她的医疗报告表明她右腿、左膝和左眼青紫,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她左手拇指有伤,头上有肿块,大部分伤痕是撞击和殴打形成的;而丈夫的伤痕更像是妻子自卫留下的。
此外,法官在证据上更倾向于相信女方。和上一代的离婚法官一样,她没有详细调查夫妻的邻居或单位,但是她有五份当事人和儿子的证言。这些证言表明抚养权和家庭暴力的问题。以下是法官和11岁的当事人儿子的对话片断:
法官:你妈妈之前受伤过吗?
儿子:是的。一般我爸爸会把她推倒在地,
然后踢她。我妈妈的头受伤了。
法官:你父母打你吗?
儿子:有的,两个人都有。
法官:他们怎么打你的?
儿子:我妈一般用筷子打我的手,我爸甩我
巴掌。
法官:打得厉害吗?
儿子:我爸爸打我打得严重。他把我的头撞到墙上。
法官:你爸爸多久像这样打你?
儿子:不常这样。但另外一次,他把我的头撞到地上。
法官很专业:她的问题包含是否存在殴打、如何发生、频率和谁更暴力一些。总体而言,儿子的证言表明他的父亲比母亲更暴力。他“把她推倒在地,然后踢她”。同样地,他也打自己的儿子,把他的头撞到墙上和地上,而母亲只是“用筷子打我的手”。
实际上,另一个录制于两个月前的证言表明,当丈夫知道儿子选择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丈夫打儿子并强迫他录制视频,让他说想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证据并不绝对有利于女方。男方有自卫的伤痕记录,从而抵消了女方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然而,丈夫更可能实施家庭暴力:他身强体壮;女方的重伤很难用自卫来解释;儿子的证言也表明“我爸爸打我打得严重”。由于儿子是中立方,他的证言更有说服力,如果不是被逼或引导,他没有说谎的动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指南,这类证据应当认定为“重要证据”。即使根据民事审判的证明责任规定,这样的证据程度也足以支持女方的请求。
最终,法官勇敢地判决准予离婚并将抚养权判给妻子,虽然这是第一次离婚诉讼。法官同情妻子和儿子,希望他们尽快摆脱暴力的家庭环境。然而,法官并没有认定存在家庭暴力。法官告诉我们她的想法:
简单说,不认定家庭暴力是因为这个丈夫麻烦、难对付。我们通常称这种需要给予特殊关注的人为“贵宾”。我想,离婚和孩子抚养权能够帮助妻子和儿子脱离暴力环境。我希望在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情况下,丈夫不用戴着施暴者的帽子,比较容易接受这些决定,也会愿意放妻子和孩子走。
这个故事说明法官经常使用平衡术。她已经支持了妻子两个主张一离婚和抚养权,也应该让男方在家庭暴力问题上有所得。她希望男方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要上诉。如果输掉所有,精明且暴力的他肯定会上诉。这是一个有成效的妥协,因为妻子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离开男方和儿子更平稳地生活。如果法官认定家庭暴力并且支持女方的全部请求,男方可能会用各种诉讼技巧拖延程序,对妻子来说结果可能会更糟糕。这样的考虑不是没有依据的。
事实上,男方仍然不满意抚养权的结果而选择上诉。二审法官撤销原判,改判抚养权给他。虽然在抚养权问题上有不同判决,两级法官对家庭暴力的相同策略是:安抚男方;双方能够接受的决定比家庭暴力的法律标准更重要。因此,社会效果取代法律效果一法律规则服从于法官的制度约束。
该审判发生在反家庭暴力的试点地区,绝不是个别做法。就家庭暴力的认定而言,其他地区的处理方式更不利于女方。一位陕西法官告诉我,她只处理那些发生在庭审中或庭审后的家庭暴力。审判前发生的暴力事件只是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一个因素。一旦原告撤诉,有些法官会把纠纷当作没有发生。张剑源发现法官不愿意认定家庭暴力,即使受害人已经提供大量证据。判决文书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4曰,原、被告双方发生矛盾,在双方推搡过程中,被告汪某甲对原告肖某右脸庞部击打一下,致原告肖某右脸庞部青肿。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肖某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仅证明被告汪某甲仅有一次殴打行为,又未造成一定后果,属于原、被告夫妻之间的日常吵闹、偶尔打闹且尚未造成后果的家庭纠纷,故不能认定为家庭暴力。
张剑源评论道:“‘一次’是法官不予认定家庭暴力的重要标准,即便这“一次”打的后果是‘右脸庞部青肿’。试问,脸被打得青肿,这后果算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呢?”46张剑源在另一个案件中进一步发现,法院认为司法鉴定机构评定“轻伤”不足以成立家庭暴力,因为“它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即使伤痕已经符合刑事责任的标准。
在另一案件中,法官不顾警察发布的“家庭暴力警告信”,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不足。他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法官并不重视受害者陈述。此外,在13%的家庭暴力诉讼请求中,法官很少关注受害者提供的其他有力证据。
在这样一个案件中,原告指控丈夫经常“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尤其是2014年5月28日那一次,她的丈夫把她往死里打,之后她打“110”报案,第二天向妇联求助。她继续指控2014年7月8日被告差点把她掐死,当她打他的手时,他才放开。她提交医疗记录作为支持其家庭暴力指控的证据。被告质疑证据无法证明是他造成的伤害,是她先把食物泼他脸上让他看不见的。
即便如此,法院仍不准许离婚。虽然该片断没有明确提及法院是否认定家庭暴力,但可视为“没有认定”,因为家庭暴力是离婚的法定理由,
没有离婚意味着没有家庭暴力。尽管有“几乎把她掐死”的陈述和警察与妇联记录的“医疗文件”,法院还是做出了决定。
罕见的“成功”
我在田野调查时收集的所有案件中,只有一例认定家庭暴力的案件,至少是在一审。这类案件的罕见,已经说明法院认定家庭暴力的困难。即使在这个案件中,我还必须给“成功”加上引号,这是因为二审法院最终撤销了一审支持受害者的判决。虽然在特定环境下,受害人有机会成功,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这个案件表明法院无法通过执行法律保障妇女权益。
38岁的原告起诉和鱼贩丈夫离婚,主要是因为“他打了我无数次”(鱼贩案件)。本次婚姻之前,她曾和一名吸毒者结婚,有一儿一女。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女儿和原被告同住,现在的这段婚姻两人育有一子。庭审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家庭暴力。原告说:
从孩子出生那个月起他就打我。他用铁管打我。他说我是个离婚女人,没有人要我,无处可去。他娶我是因为他同情我。所以他想什么时候打我就什么时候打……我们因小事争吵,然后他开始打我。他用很大一根铁管打我的腰,用砖头敲我脑袋。
被告回答,“原告要打我,我逃跑。她便在街上追我,踩到一块香蕉皮摔倒了”。此外,被告在离婚诉讼答辩书中提到,“原告脾气火爆,她用啤酒瓶打我。在我几乎失去意识时,她拿刀来追我。后来邻居把她制止了”。
原告提交了医疗报告和警察所准备的协议:原告支付给被告1500元后,被告便从他们的公寓中搬出去了。在警察的建议下,她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事实上夫妻两人已经分居超过四年,四年间被告多次打原告。
法官的判决有利于原告:
原告指控被告向其实施家庭暴力并提供医疗报告和警察准备的协议。从医疗报告中看,原告头部后面有两厘米伤口,头皮上的皮肤擦伤,肋骨断了,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这些伤痕不可能像被告所说是因摔倒造成。相反,这些伤痕与她指控被告用大管子打她腰部和用砖头打她的头是吻合的。被告声称原告打他,但他没有提供证据。被告在身形上比原告大。原告不太可能攻击到被告。作为一个成年人,被告应当知道打别人头的严重后果。用砖头打原告的头表明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这构成了严重的个人安全威胁。因此我们支持家庭暴力的存在。
由于家庭暴力成立,尽管这只是第一次起诉,法官准予原告离婚。她还把15岁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母亲,因为家庭暴力实施者不适合养孩子。尽管如此,法官没有判予任何金钱补偿,显然是为了平衡诉讼双方当事人。如果另一方已经获得抚养权,就不能再要求抚养费。
这是家庭暴力得到承认并写在判决书中的少数案件,这样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原因。
第一,受害人的强有力证据:医疗报告,详细的伤痕情况,与受害人陈述吻合;警察准备的和解协议;以及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其他面对家庭暴力指控的男方一样,他不承认所有的指控,但是他的辩护不够聪明。他说原告踩着香蕉皮滑倒了,这和医疗报告上显示的原告腰上、背上的伤情不符。他声称女方用啤酒瓶和刀等暴力工具打了他,但他没有提供任何伤情或其他可以支持指控的证据。
第二,法官想要帮助受害人。法官年轻、有性别意识、有能力以及专业,她同情女方,希望把她从暴力丈夫那里解救出来。她引用了详细的医疗报告证明那些伤是由殴打形成的,不可能是摔倒形成的。她还提出尖锐的分析:男方体形上有优势,女方不可能攻击得到他。正如贺欣和吴贵亨已经发现的,法官收集证据的技巧和意愿对保障家庭暴力受害者至关重要。
但是到了最后,原告这个罕见的胜利仅维持了很短时间。被告上诉后,尽管二审法院同意一审发现的事实,为安全起见,法官还是判决驳回了离婚请求。“在这个案件中女方是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双方已经在一起生活了10年,还育有一子,再加上女方上一段婚姻带来的女儿,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定程度的感情基础。上诉期间,男方拒绝离婚且要求法院调解和解。因此我们认为双方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
不准予离婚的上诉判决驳回了一审法院的家庭暴力认定,它说明离婚案件的日常实践很难被改变:大多数一审案件判决不准予离婚,即使是已经实施严重家庭暴力的案件。二审法官的行为很容易理解:不准予离婚,为什么还要去探究家庭暴力的问题?
案件被驳回后,一审法官之后是否改变她的策略?换言之,如果二审法院并不支持她的判决,为什么她要支持女方?她所在法院的院长告诉我,他们对法官们在这类案件中被二审法院驳回的情况比较宽容。然而,在大多数其他法院,案件被驳回会影响法官考核,为什么法官要冒险呢?如果这个案件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其他法院保障妇女权益的情况只会更差。法官更多考虑自我保护,不太愿意收集家庭暴力的证据,或者激怒施暴者。
在很多其他案件中,受害人没有这么幸运。
一位北京的男法官说:“我知道女方提到的家庭暴力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她没有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我便不能支持她。为什么法官必须要收集证据?首先,我太忙,无法收集;其次,这不公平。法律明确提到谁主张谁举证。”对这个法官来说,保持公平是无动于衷的借口。
一位北京女法官的观点更有代表性:“除非证据非常强有力,否则我会在第一次起诉时判决不准予离婚。毕竟,我必须要考虑二审法院的意见。即便准予离婚的理由很充分,二审法院很少推翻我们不准予离婚的判决。但是,他们对判决离婚的观点不同。当案件上诉后,二审法官很紧张,他们不擅长处理那些麻烦的人,于是就推翻我们的判决。”
对二审法官来说,推翻一审法院的意见可能会招致一审法官的不满,但是不安抚麻烦的当事人可能会对职业前景和工作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点上,法院无法认定家庭暴力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一位特立独行的法官不可能改变总体情况。
大部分法官没有在判决中提到家庭暴力,是因为考虑到效率和社会稳定。尤其是对二审法院推翻判决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家庭暴力的认定。这些法官受到上级法院的严格审查,不想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判决。
制度环境使法官们选择一条安全的路:忽视家庭暴力的存在。法官小心处理这类案件情有可原,自我保护可能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下一级法官长期受到上诉率的困扰。由于错误判决,年轻法官可能受到纪律处分或其他压力。例如,1999年,约50%的案件上诉。在这些判决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26.6%)的案件维持原判。
拖延判决中的延续暴力
如果上述论述已经反映出因调解和判决所生成的暴力,那么处理案件的过程也会产生暴力。
如前所述,尽管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拒绝首次提出的离婚申请是法院处理离婚案件时一种固有做法。事实上,对于任何争议很大的案件,即使当事人不是首次提出离婚,拖延裁决也是法院普遍会采取的一种策略。多项研究表明,53即使家庭暴力已经被承认或确立,一些法院仍拒绝判决离婚。法院的判决忽略了这一部分,直接判决驳回;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更多讨论将无可避免地降低驳回判决的合法性,甚至与之相矛盾。
这种表面中立的拖延做法,会在受到家庭暴力威胁或已经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妇女中加剧两性不平等。只要不准予离婚,婚姻仍然完整。在人身保护令制度之前,法院对家庭暴力的指控不做任何有效处理。一些法官可能会进行形式化的口头警告或劝说。更多的情况是,没有警告,也没有补偿,什么都没有。这是令人反感的官僚主义。不准予离婚的判决似乎支持了那些拒绝离婚的男人的请求。
男性对女性的仇恨和报复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家庭暴力得到释放。许多人向他们的妻子吹嘘说:“你想和我离婚?连法院也对我无能为力,它站在我这一边。你还能做什么?”因此,一些被告可能会因为原告提起离婚诉讼而对原告进行报复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为了离婚,女方可能会使冲突升级,以便为下一次起诉收集更多证据。虽然案件各有不同,但都具有同一种模式:家庭暴力持续存在,并在某些案件中加剧。俗话说得好,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大量访谈材料、法庭文件,甚至是法庭判决,都可以看到不准予离婚的可怕后果。一份第二次起诉书中写道:
如果上次离婚申请得到批准,就不会发生下面这些事情:2000年12月28日,我不在家时,另一方(丈夫)的情人来到我的公寓。当他们发生性关系时,他们把我女儿锁在了公寓外面,那是在寒冷的冬夜,我们仍是夫妻。当我第二天在他的工作单位指责他的这些行为时,他用木棒打了我。我的脖子、腰和脊柱都受了重伤,甚至站不起来。即使花了2万元到3万元接受各种治疗,我仍然几乎瘫痪。结果,我丧失了工作能力。我现在只想离婚。
一份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中写道:“在法院驳回了第一次提出的离婚申请后,被告仍不思悔改。相反,情况变得更糟。他威胁我,诅咒我,打我。即使现在,我的身体和头部仍然有伤疤。”
陕西一位保护令申请者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说道:“有一天我失去了知觉,住进了医院。我怀疑他给我吃了过量的安眠药。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可能试图在我失去意识后和我发生性关系。但我没有证据证明,法院驳回了我的离婚申请。我回到娘家,他说,只要法院不批准离婚,我就仍是他的妻子,我必须和他一起回家;否则,他会在我娘家闹事。有一天,当他用力抓住我时,我妈妈挡在他前面。他把我妈妈推倒了。”
这名女性的经历再次表明,拖延判决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它把受害者置于危险之中。由于无法提供安眠药的证据,这名女性的离婚申请被驳回。与偶尔有暴力行为的丈夫待在一起意味着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她可能会被强奸。这个男人更加自信了,甚至吹嘘他会打他的岳母。
另一位因首次判决驳回离婚申请而提起上诉的陕西妇女告诉我:“我害怕回家,因为他每次喝醉都会打我。现在我住在出租房里,做临时工,很难养活自己。他拒绝离婚,因为他听说一旦离婚,一大笔土地补偿费将归我所有。法院驳回了我的离婚申请。我提起上诉,但是将近6个月过去,我没有从上诉法院得到任何消息。我给上诉法官打电话,但只有他的书记员接了电话。书记员说我应该等等,因为安排庭审需要时间。在我打了四次电话后,书记员变得不耐烦,挂断了我之后的电话。”
目前还不清楚为何在该案上诉6个月后法官仍未安排庭审。面对麻烦的诉讼当事人,法官只会拖延庭审,延长判决时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法官甚至不接原告电话的原因,结果是这位妇女一直不敢回家。
很难知道这些事件的发生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不适当的驳回裁决。然而,对于许多案件,法官们第一眼就知道,仅仅通过给予6个月的冷静期不能使双方和解。尽管如此,只要有证据表明这对夫妇仍然可以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们就会做出不准予离婚的裁决。虽然这类法庭判决偶尔会挽救一段破裂的婚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判决只会进一步恶化夫妻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而且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升级。
毕竟,当原告决定向法院提起离婚时,他们一定已经争论了多次。当他们最终克服了犹豫,决定在法庭上与另一半对簿公堂时,挽救这段婚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田野调查显示,在被判决驳回离婚请求后,原告对另一半的信心会进一步下降。
拖延策略与性别有关。由于提出明显虐待指控的原告中有90%是女性,她们因这种拖延做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约70%的原告是女性,她们的诉讼请求更有可能被拖延。
人身保护令的有限作用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于2016年3月1日起生效。
我有十位受访者已经从陕西法院和珠三角法院获得了这样的保护令,她们认为人身保护令是有效的。她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得谨慎小心、脆弱且无助。有些人能幸运地回到她们的娘家,其他人则不那么幸运。男人会在她们的工作场所骚扰她们,一些人因此失去了工作。
对所有这些受害者来说,法院的人身保护令是她们的救命稻草。一位申请人说:“保护令下达后,他就不再骚扰我的娘家人了。”另一个说:“他被法庭传唤去谈话后,就不再在我上班路上拦截我了。他也不会在我的工作场所闹事。”还有一个说:“他不再给我发辱骂和威胁的短信,我们也不用住在一起。”
一名广东法官告诉我,人身保护令限制男方回家。显然,他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人身保护令只是禁止男方接近起诉人,并不一定禁止男方回到自己的家。撇开误解不谈,这个故事揭示了人身保护令的威力。法官们认为,人身安全保护是有作用的,甚至对那些认为自己有充分权利殴打妻子和拒不改变自己行为的男人也是有效的。
这样的积极评价并不能掩盖整体上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上的惨淡:统计数据和我的田野调查表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和批准数量极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过去5年期间,全国法院仅发布2154条保护令,而受理的离婚案件有850万件。考虑到中国有3000多家法院,这意味着在过去5年里每家法院平均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到一项。另一份报告估计,从2016年3月到2017年6月,全国法院只发布了1284条保护令。
同样,在16个月的时间里,每家法院平均只发布了半个人身保护令。陈苇和段伟伟发现,重庆市地方法院在过去三年里只发布了两项人身保护令。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所有法院中,发布人身保护令的情况很少见。早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之前,珠三角法院就已是这一措施的试点法院。尽管接收了500多起离婚案件,但珠三角法院每年只下达三份人身安全保护令。陕西省法院被誉为实施该机制的典范,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下达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才不到10份。
数量如此之少的一个原因是受害者对该保护令缺乏了解。例如,在鱼贩案中,直到警方介入,女方才了解到这种机制。在过量服安眠药妇女案中,法院驳回她的离婚申请,男方一直跟踪她到娘家,之后她才从邻居那里了解到这个机制。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有关这一制度的信息可以在各种媒体上找到,许多政府大楼和办公室都悬挂着反家庭暴力的海报。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法院的激励机制不利于发布这样的命令:发布这样的命令为法官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降低他们的效率。下达保护令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件,这是离婚案件的一部分。
然而,发出和执行这类命令的工作量并不亚于处理另一宗没有这类问题的离婚案件。为了批准这样的请求,法官必须进行调查,口头警告被指控的施虐者,并另外向所有相关方传达命令。为了决定是否批准,法官必须评估家庭暴力的证据。更麻烦的是执行过程。
与财产执行不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涉及人身权,人身权是流动的,法官通常没有能力监督这一过程,必须寻求警察和街道或村/居委会的帮助。虽然村/居委会接到命令没有什么问题,但警方更抵触:似乎法院在给警察下命令,这与他们在三大政法机关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太一致。
无论如何,这是警方不愿承担的额外任务。警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作为是有据可查的。—位法官告诉我,根据相关规定,警方和居委会也要向法院反馈执行人身保护令的情况,但她从未收到过警方的任何反馈。
这些问题都让法官头疼,因此,法官会劝申请人不要提交申请,或者法官会以家庭暴力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批准。《反家庭暴力法》第27条规定,该保护令在两种情况下发布:一种情况是发生家庭暴力时,一些法官对“是否有家庭暴力证据”的要求比在诉讼过程中更高;另一种情况是“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这个定义很不明确。
法官经常利用这个模糊的定义,说服申请人撤回他们的申请。他们这样回应女方的请求:“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你们不能再在一起待几个月呢?”,或者是“你们就要离婚了,你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人身保护令?”
事实上,许多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受害者本应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知有这一制度,但法官没有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告诉他们。正如那位服药过量的女性所述,她是通过她娘家的邻居,而不是通过法官,知道这个制度的。
总之,一旦批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有效的。如果不是法官考虑效率问题,这一机制本应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更早的批准。尽管如此,考核指标和法官的考量损害了一个本意良好的制度的有效性。法官不愿下达这样的命令,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布数量有限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论
我们很难说法官们没有遵守法律。毕竟,他们确实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因此,家庭暴力的证据被驳回。当他们采取调解并允许消除家庭暴力问题时,他们的决定是正当的,因为法律允许调解,而诉讼各方包括受害者,已经同意了这点。
当他们劝说潜在的受害者放弃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受害者不管情愿与否,都会接受他们的劝说。家庭暴力很少与是否同意离婚、监护权之争或财产分割的决定有关,仅仅因为法官裁定双方的感情没有破裂到不可挽回地步。迈克逊(Michelson)甚至认为:“法院最好的情况是视而不见,最差的情况是滥用法律驳回女方离婚申请。”
我也许不完全同意迈克逊的观点。但是,法官确实没有足够努力保护受害者的利益,结果是家庭暴力被淡化,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履行。他们可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们为什么不呢?答案就在问题的反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动力这样做?
如前所述,他们的目标是以一种安全、高效的方式解决这些案件。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家庭暴力只是婚姻是否应该继续的一个边缘证据。如果受害人提出有力的证据,他们可能接受。如果没有,法官们很少做出特别的努力。为家庭暴力取证只会增加法官的工作量。
未被充分应用的保护令只是一个例子。这意味着只有具有两性平等意识、有能力和负责任的法官才会为家庭暴力收集证据,鱼贩案中的法官是例外而非常例。只要案件能够和平、安全地结束,一些证据注定永远被埋葬。当离婚申请被驳回时,就没有必要调查家庭暴力问题。肯定要离婚时,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主要的问题是确定监护权和财产分割,为什么法官还要关注家庭暴力?当双方都接受离婚,他们为什么还要纠缠于家庭暴力问题?
此外,许多施暴者性情恶劣、精神不稳定或有暴力倾向,他们的仇恨可能会从妻子身上转移到法官身上,法官为什么要引火上身呢?因此,若想加强法庭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力度,未来或许需要对法官身处的考核机制进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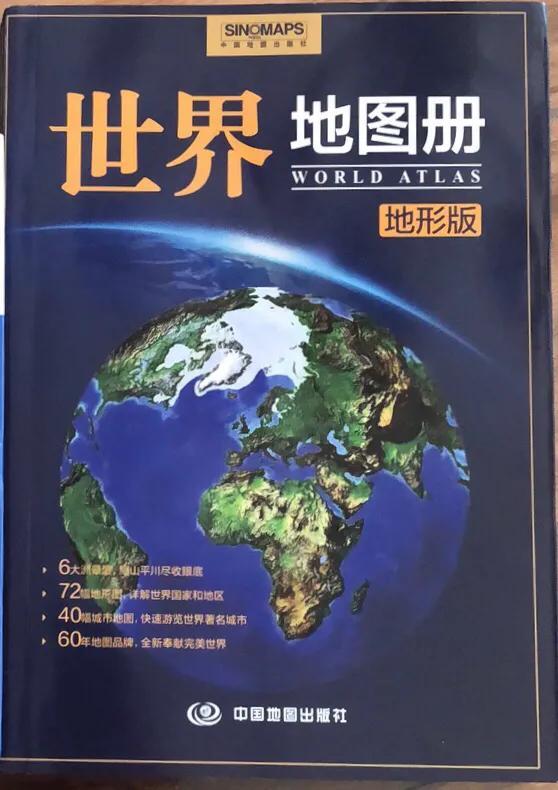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