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物”到“通物”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白辉洪
提要:“异类具存”是王弼论证“无”之必要性的重要依据,即经由无而生成万物,充满差异的万物由此被统合起来以建立整体的秩序;这一点也历来受到重视和讨论。然而在王弼看来,“统物”只是论证无的必要条件且有着局限。实际上,除了统物,“通物”也是王弼所揭示的无的另一层面。而且通物居于无与统物之间,具体指明了无如何统物,是连接两者的实质性环节,从而是王弼讨论无的更为充分和根本的路径。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和廓清王弼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为在新的问题视域中阅读王弼著作和理解其哲学提供路途。
关键词:王弼/无/统物/通物
一般以为,《老子》发现了“无”,而直到“王弼系统论证了一个‘以无为本’的思想体系”(参见王博),无才淬炼为一个完备意义上的独立哲学概念而越居道之上。王弼关于无的讨论,一方面明确指出和强调其与“有”之间的差别,所谓无形无名者与有形有名者;另一方面又借助此两者之间的关联来揭示无的具体义涵。在诸多关联当中,“统物”与“通物”是最为核心的,是由有形之域的物上升到形上之域的无的基本路径。
一、“统物”之必要性及其局限
王弼哲学的现代典范性研究始于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自其以来,相对于《周易注》,其《老子注》无疑受到了更多关注,以至于成为理解王弼哲学思想的核心依据。此种状况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直观看来,相对于《老子注》关于无的高度哲学思辨,《周易注》更多的是具体甚至于零碎的道德教导、行动指南,哲学思想的意味似乎要淡薄很多。而对于《老子注》,核心的关切点落在无对于物的“包统”上:因自身缺乏任何的规定,无形无名之无也就能接纳任何的有形有名之有。对此,王弼在《老子指略》的开头有如下的经典性论述: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楼宇烈,第195页)
如此一段深具思辨的文字以简洁明快的方式强有力地论证了万物之宗主必须是“无形无名者”,从而为所有讨论王弼哲学的研究者所重视和征引。既然任何的规定都意味着对其他规定的排斥,例如温的规定就不能是凉的规定,宫调的规定就不能是商调的规定,并在思维上落入语言的二分模式中,因此有着任何规定的万物之宗都意味着对非己者的拒斥,从而意味着对整体世界的分析与割裂;而只有依据于不落入言筌的无形无名者,万物才能有共同的宗主,世界的整体秩序才得以建立起来。王弼严格区分无与有物,但此两者绝非断然无关,故王弼又试图阐明其间的联系并借此来理解无。这一联系的具体内涵,在自汤用彤先生以来的研究中,基本被理解为无对于万物的包统。这在王弼那里当然有着坚实的依据,除了《老子指略》,表达包统之义的文句在《老子注》中时常可见,例如:
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哉。(瓦格纳,第424页)
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楼宇烈,第27页)
不炎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同上,第88页)
以上所举,都是在不同层面上表达包统之义,如五章言仁者不能无为而有仁恩举动,最终导致对物的去取,这是政治哲学层面;三十五章言“大象”因其无形而使四时行而百物生,这是形上学层面;十一章以车毂这一具体物件为例,指出车毂的中间虚空无物以容受辐条:这些论述无一例外地与无、无为、无形无名相关联。王弼言道是“取乎万物之所由”(同上,第196页),即万物都经由道而无遗失;又言“道,称之大者也”(同上,第198页),言此称谓的广阔悉备:这些都是在强调道之囊括万物的普遍义。故包统确实构成了王弼讨论无的理论支点。而这在汤用彤先生那里就受到极大的关注,如其叙述王弼之本无时言“万有归于一本”,又借助易学语言描述云“王氏之所谓本体,盖为至健之秩序……由其本身言,则谓为其性分(或德)。由始成言之,则谓为所以然之理”。(汤用彤,第49、93页)①这是汤用彤先生在佛学乃至理学的影响下,试图以性理概念为主干,以体用范畴为架构来理解无对于万物的包统之义。
在汤用彤先生的基础上,冯友兰和汤一介先生更加注重从纯粹概念思辨上来理解无的包统之义;二位分别说道:
在理论上说“有”这个名的外延最大,可以说是“至大无外”,它的内涵就越少,少至等于零……这也就是无。《老子》和玄学贵无派把“道”相当于“无”,所以强调“道”是“无名”。(冯友兰,第343页)
天下所有的事物排除了其特性,所谓的“本体”只能是无规定性的“无”……任何有规定性的事物都不可能统一其他事物,只有无规定性的“无”(本体)才可以统一任何事物……(汤一介,第103页)
汤、冯两位先生都在探究在思想概念中无是如何被发现的。冯先生借用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关系,汤先生直接就“统一”来讨论。两位先生的具体论述虽有所不同,其实都借用一般与特殊的架构来分析王弼所谓无,即不断地对概念或事物进行抽象,去掉其中具体内涵或规定性,以至于所有的内涵或规定性都被抽象、去除之后,就获得了无;而这样的无由于没有任何的内涵和规定性,也就能够在概念上容纳所有的外延、规定性也就是所有的事物。此与汤用彤先生的讲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围绕无的包统万物之义上建立各自的阐释体系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此种阐释路径的问题在于,经由无可以推导出对于万物的包统,但颠倒过来,仅仅根据包统是否足以反推到王弼之无?事实上,正如汤、冯二先生所言,如此理解的无,“在思辨中它也可以说是‘纯有’”(汤一介,第104页),“抽象的有就是无”(冯友兰,第343页)。这也就是说,仅就包统之义而言,“纯有”或最高类的“有”就已经足够了,无不过是对“有”的说明。②换句话说,就概念思辨而言,抽象过程的最后虽然可以得到无,但此无只不过是对于有之无内涵、无规定性的描述,从而是“有”的一部分,成为附属于“有”的一般描述性语词而非哲学概念。如此一来,其后果即使不是取消了概念无,也使得概念无被边缘化了;而这显然不符合于王弼的哲学思想。
冯、汤二先生还在实在论或本体论上讨论无,但有的研究直接降低无的哲学意义。例如葛瑞汉(A.C.Graham)以《老子》第二、十一章为依据,认为包括王弼在内的道家都将无理解为任何物质形式的缺乏,并作为道的虚无性而与有相互依赖。(cf.Graham,pp.344-346)此种理解或许合于《老子》,但与王弼大相径庭。所以然者,对于二章“有无相生”,王弼仅言“此六者”而将其与其他五者等同视之,可见此无仅是形名层次上与有相对而与道无涉,如恶与美相对;对于十一章,王弼言“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是明言无对于有的优先性与根据义。③新加坡学者陈金樑(Alan K.Chan)以为王弼之无仅是道的本性(the nature of Tao),是对道之无形无名的描述,而反对从本体论上来理解王弼之无,因此他将无对译为non-being而非Nonbeing。(cf.Chan,pp.47-52)这种理解的前提是以道而非无作为万物之宗主和王弼哲学的核心概念。④然而王弼《指略》言“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道所传达的“所由”实际上是万物由无以生以成。这意味着与玄、大等一样,道也从属于无而指称无的某一面相;陈金樑却将两者关系颠倒过来。但即使如此,无形无名之道如何作为万物本源的问题仍未获解答。⑤
葛瑞汉与陈金樑的方案都将无理解为形容性语词(无形无名),从而将焦点从无转移到有无相生之道或理上。但王弼锲而不舍地讲有生于无、无为万物之宗,使得此种方案难免于回避实质问题的嫌疑。不过正如陈金樑所言,如果只停留于否定性的表达,那么无确实将成为从属性的形容语词而丧失其独立意义。(ibid,pp.51、57)也正是因为未能从其否定性中推论出更多的义涵,冯、汤二先生所论之无也最终沦为对抽象的有、纯有的描述。这意味着此种阐释王弼无的方式有着内在的困境。实际上,王弼在《老子注》中就已经指出,如果仅是着眼于包统之义,无并非是必要的。例如:
无以为者,无所偏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至于无以为,极下德之量,上仁是也。足及于无以为,而犹为之焉。(三十八章注)
这是对《老子》本文“上仁为之而无以为”的解释。王弼将“无以为”理解为“无所偏为”,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偏向而包统万物;很明显,无为的上德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王弼又以为,虽然下德总体上是“有以为”,但是归属于下德的有为之上仁如果能够极其量,也能够跟上德一样做到“无以为”。这就是说,上德与下德的区别标准严格地是在于无为与有为,而非无以为与有以为。虽然上德自然而然就能做到无以为而下德极其难以做到,但仅凭无以为与有以为仍然无法彻底判别无为与有为,其缘由在于无以为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无为才是所以然者。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只是着眼于包统之义,无或无为就并非是必须的,因为极其量的上仁可以达到。换句话说,由无为可以推导至无以为,但由无以为并不能完全反推至无为。因此如果只是注重无以为或包统,那么无为就并非是必须的。与此类似,王弼在四章注文中也表达了这一意思:
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满以造实,实来则溢,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
这段注文解释的是《老子》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在王弼看来,执一家一国之量者,虽然穷尽其力量能够包统,但最终不能保全家国;就如极其量的上仁只能一时半会地无以为,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之前终将跌落到不得不辨别是非曲直的义的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仅着眼于包统,不仅无变得不必要,甚至连包统本身也难以得到保证。这暗示着无与包统之间存在着其他因素,从而提供了越出单纯的包统之义而重新理解无的契机,即必须有超过包统的“量”才能一方面达到无,一方面真正实现和保证包统,而这就是所谓“冲而用之”。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王弼之无才是必要的。
进一步地,单纯的包统可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无任何规定的无自然能够包统万物,允许任何规定的存在,但能否保证整体秩序的建立?或者说,如何能使王弼的思想不是如他所批评的杂家那样,只是将众物纂集起来,但缺乏裁断而最终导致秽乱(参见楼宇烈,第196页)?在现有的研究中,一个可能的回答是黄老学方案。事实上,魏晋玄学常被视作黄老学或其替代,如唐长孺先生在描述玄学兴起时,就认为出于历史或政治的原因,黄老学不可采用,故以玄学作为替代性的政治思想方案。(参见《唐长孺文存》,第168页)又如王晓毅以为荆州学派中有黄老学的因素,而王弼哲学与荆州学派又有着承继关系。(王晓毅,1996年,第178-180页)⑥而将王弼之学与黄老学关联起来,早在汤用彤先生那里就已有端倪:“《人物志》言君德中庸,仅用为知人任官之本,《老子注》言君德无为,乃证解其形上学说,故邵以名家见知,而弼则为玄学之秀也。”(汤用彤,第23页)这实际上是认为虽然在论述层面上有异,但在“有名—无名”这一思想结构上,刘邵与王弼是相同的,甚至可以说王弼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论证刘邵的思想,或者说刘邵的思想是王弼的形而上学在政治层面的落实。而汤用彤先生以刘邵为名家,乃是因为《隋书·经籍志》将《人物志》一书归入名家类,但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述,《人物志》杂糅儒道名法各家,主张君主无名无为,而以形名来考察、选任人才并使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事实上颇具黄老学的色彩。由此,具有相同思想结构的王弼,自然也会有黄老学的特征,至少不会排斥黄老学。而且,汤用彤先生将汉魏的形名之学作为玄学的思想来源之一,更加说明王弼与黄老学之间的相似性。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黄老学,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述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即是以无为来任用形名之术;无论是因循万物之性还是具体的历史时势、习俗,实际上都是以形名的方式得以具体展开的。⑦而将王弼的政治思想理解成某种意义上的黄老学,也就等于说王弼承认以形名之术作为政治治理的方案,但这却是与王弼对于形名的批评直接相冲突:“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楼宇烈,第196页)这一批评意味着王弼的思想不是对众家的综合,而是在对汉魏之际各家思想的严厉批判和拒绝的基础上,以寻求超越各家的“圣人之意”的形式产生的。⑧因此,将王弼与黄老学关联起来,是在直接违背王弼的本意。
实际上,以包统为基础的阐释与黄老学方案,都以形名或性理为视角来考察王弼思想;在当时的语境中,性理与形名之间有着无法割离的意义关联。⑨而形名意味着静态地看待万物,以获取其静态本质。在此下,包统及由此建立的秩序,就意味着万物静态地各安其分、各居其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拒绝变动,而是静态更为基础,变动则为第二位。此种形名及静态式理解,构成了现有研究的内核。但很明显的是,王弼始终在克服此种理解方式:形名不仅不足以把握无形无名者,也不足以真正理解万物,反而最终会招致竞争、虚伪、狡诈:这不仅是理论推导,也是历史事实。
返回去再看《老子指略》开头的经典论述的话,可以发现着眼于“统物”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不温不凉”以下的文字展开的。此种讨论无疑是忽略了王弼所设立的“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这一最基本的语境,以至于以静态的方式来理解王弼哲学。实际上,王弼在《老子注》中引入终始、生成的图示⑩,正是试图以此来摆脱形名对万物的束缚,而将万物置于生成变化之境中,并由此来理解万物以及进而探究无形无名者;这意味着物之性理与统物本身需要在动态语境中进行理解。王弼思想的这一路经,由“通物”具体地表达出来。王弼说道:
唯此复,乃能包通万物,无所不容。(十六章注)
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二十九章注)
动皆之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瓦格纳,第566页)
上述所引,十六章注文直接言包通,即万物复归虚静而得性命之常,从整体上看是包、通万物,这表明“包”与“通”构成了在无之下万物所呈现的两种素朴而真实的总体面相;四十章注文单言通,即事物若反其形名而动则是合于道,从而得以通畅自身;二十九章注文在与“执”、“造”等有为的举动相对比中,指出万物之性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加以把持、固定,而必须在无之中无所滞碍地畅达自身。由此可以看到,不仅是包,事实上通也构成了王弼在《老子注》中理解无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且相对于包,通所表达的万物无所滞碍地生成变化之意义,更加需要在关联性的动态语境中才能得到实现和理解。而《老子注》中所采用的终始—生成的图示,显然与通的关系更为紧密。在这个基础上回顾四章注文的“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以及三十八章注文的“极下德之量,上仁是也”,就能很容易地知道,仅着眼于包统之义不仅不需要无,甚至连包统本身最终也难以得到保证,其原因正在于通的缺失:穷力与极量在理论推演上可以达至包统之义,但由于并未给物的变化提供“空间”、留下余地,将事物固定在分位之上而使物不得通畅,因此最终至于坏乱、失败。而通意味着需要超出于物的力、量,从而能够“冲而用之”,如此一来无就变成必须的;并且通既然意味着万物的自然舒展、变化与呈现,那么事实上也在造就着整体性秩序,由此包统之义的实现也就能够得到保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通不只是与包相并列以描述在无之下万物的存在状态,而且是作为包的前提与根据:通比包更为接近于无,因而也更为基础和重要。这一点也体现在王弼对“玄”的理解中。有意思的是,王弼说道:“玄,谓之深者也”(楼宇烈,第197页),玄与深在字义上皆言恍惚不明。在《老子》本文中,“深”字时有出现,但总体上只是一般的描述性语词,并不具有“玄”那般的思想意义。然而王弼对“深”却颇有属意,如其说道“言道之深大”(三十五章注)、“唯深也,故知之者希也”(七十章注),以及“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楼宇烈,第196页),这是将“深”与道紧密关联起来,突出和抬高其思想意义。而“唯深也”的表达,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系辞》的“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探赜”一词更是直接取自《系辞》。如此一来,玄与深的语义关联也意味着玄与通之间存在着某种思想上的连接。而且玄、深与形名之明相对,不正是意味着经由无之幽隐以葆物之真、朴,从而使物得以通达?
同样的观点在《周易注》中也能看到。最为明显的可以算得上《大有》卦,其卦辞云“大有,元亨”。对于“大有”,王弼注云“体无二阴以分其应,上下应之,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如此理解的大有完全可以对应于《老子注》中的统物之义,其间毫无二差。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王弼对《大有》卦辞的整体解释:“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则必元亨矣。”王弼的注解方式与诸家有所不同。如孔疏云:“既能大有,则其物大得亨通”(《周易注疏》卷四)(11),这是说由于大有而得元亨。又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云:“犹大臣有圣明之德,代君为政,处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长群臣以善,使嘉会礼通”(卷四),六五以阴爻居尊位,故郑康成解为有圣德的大臣代君统率群臣而得亨通。这两种注解虽然方式不同,但都是沿着由大有而得元亨的思路展开的。然而王弼正与此相反,是由元亨而得大有,将元亨视作大有的因由、根据。事实上,这不仅与其他注解不同,也与王弼注解卦辞的一般方式有异:卦名所表达的卦时作为背景或前提,而卦辞的其他文字描述卦时之下的具体情势。如《需》卦卦辞云:“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是说在需时之下,如果有孚信以对待事物,则可以获大通而吉,且可以共同涉险渡难。而王弼对《大有》卦辞的理解与此一般方式正相反:以元亨为前提而得大有。当然,其注文又云“大有,则必元亨矣”,既然元亨为大有的根据和实质性内涵,那么在大有之时必有元亨之情势以保全大有:这也可以算作是重归一般的解释方式。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萃》卦。王弼在卦辞注中云“聚乃通也”,似乎是以聚在通之前;然而其《彖传》注云:“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这是以情同、气合作为聚群的前提,故关键在于“何由得聚”:“顺说而以刚为主,主刚而履中,履中以应,故得聚也”(《周易·萃·彖传》注)。有顺说、刚中之德,才能广应众物而群聚之。广应众物意味着使众物能够畅通无碍地表达自身,从而能够有感应,在此基础上也就能够群聚万物:这是仍然以通在聚前。至于言“聚乃通也”,一方面大概与《大有》卦一样,萃聚由通物而成,故萃聚必然要求通物;一方面也是指出通物不是仅就孤零零的自身而言,而是必须处于群类当中,面对众物。
王弼之无以通物而统物,事实上表达了其对于物以及有无关系的独特理解。显而易见的是,物有形有名从而有别于无,然而王弼并不认为物与形名之间可以划等号。一个最为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是王弼对于“玄德“的注解:
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十章注,又参见五十一章注)
《老子注》中的德除了德行、德目之义外,最为重要的是“德者,得也”(三十八章注)、“德者,物之所得也”(五十一章注),德是指物由无、道而所得者,因此可以理解成得于道或无在物上的落实。《老子》之玄德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本义为道对于物之玄冥不可言说的生养亭毒之德行、功用。然而考察王弼注文,可以发现前两句的主语是道或无,合于本义;但第三句的主语突然滑转为物,如此玄德是就物而言。这种注解既保证了德概念的统一,更是指出了与无一样,物之德也是“玄”的。所以如此者,如一章注所言,无之始成万物是玄同不可名的;反过来从物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物之始成变化在本根上也是玄冥幽深:此即所谓玄德。由此可以说,王弼之无是物之生成变化的根本机制、结构,而由乎无的玄德而非形名是王弼对于物的根本洞见。与玄类似,王弼也将“常”同时用以描述道与物。如三十二章“道常无名”,王弼注云“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这不是将常理解为经常、常常之义的一般语词,而是视作概念。王弼言:“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十六章注),其基本义涵是无形不可名。由此,道或无必定是常,而凡是可形名之道皆非“常道”。如果说玄意味着道之幽深不可见,那么常意味着道之贯通古今而永存。对于物,王弼有“性命之常”(十六章注)、“常性”(二十九章注)的表达,这首先意味着物之为物所有的恒常之性,拒斥外在的干涉、损益;更为重要的,是指示了物之性命与道之间的本源关联。三十八章注中王弼以得释德,随即言“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同样这里的“常”也须读为概念而非一般语词,如此“得”才会有落实之处而免于单纯的语义说明之嫌疑。(参见杨立华,第225-226页)这其实意味着,物性之常乃本于道之常,而王弼对于性命概念的理解与其说是在于规定性、限制性,毋宁说是在于所由以存续、变化的本源性。事实上,除了玄与常,朴、真等概念也有类似的特征、义涵。在此基础上,王弼拒斥形名的原因就不仅是高高在上的道或无,也具体地落实到物上,即物在本根上也反形名,即由于无而不可形名的生成变化而非形名才是物之本真存在:这意味着从根本上斩断了形名之术对于物的定固、裁制。而所谓通物也直接植根于玄德、常性以及进一步的无当中,即物经由无以得其玄德,从而能够朴素、真实而没有滞碍地生成变化,并因于作为万物共同本根之无而实现统物。王弼所谓“由无乃一”(12)(四十二章注),是以通物这一环节来具体完成的。
王弼在《老子注》与《周易注》中表达了关于包、通的相同看法,这当然证明了两者的一致性。不过,其差别也是明显的:通在《老子注》中的表达是很有限的,并且与生成—终始紧密相关,内容上比较单薄;而《周易注》中不仅有大量的表达,更有丰富的讨论。从解释学上看,这当然是因为《老子》本文中通一类的字眼就很少,《周易》中“亨”字则几乎随处可见。更进一步的原因,则是既然通意谓着变化,那么关于通的讨论需要在变化之境中才能有所展开;但《老子注》局限于以终始—生成来描述变化,《周易注》则直接有着丰富详细的变化之境作为基础,这直接决定了在通的问题上,《周易注》会比《老子注》有着更为详细、丰富乃至深入的讨论,也可能更为重要。实际上,在王弼看来,《周易》就是为讨论通而写作的。对于《论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王弼注云:“《易》以几、神为教。颜渊庶几有过而改,然则穷神研几,可以无过”(楼宇烈,第624页)。这段注文完全本于《系辞》,如“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等。而言“《易》以几、神为教”,显然是本于《系辞》的“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王弼在上引注文中仅言几、神,乃是以“深”为最后的目标,即《易》以几、神为教导、指引,最终归于“深”而“通”这一目标。《系辞》有云:“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易道在于开启和成就万事万物以统御天下,而圣人经由此道来通达百姓之心志,建立、成就德业,因此通是圣人制作《周易》的固有目标。而这可以在王弼《周易注》中获得证明,对于《同人·彖传》“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王注云“君子以文明为德”,所谓文明之德乃是“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周易·同人·彖传》注)。而在王弼《周易注》中,“文明”与“不犯”、“通”等字眼关联在一起,如“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周易·坤·六五》注),“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周易·大有·彖传》注)等。而《同人·彖传》王注直接言“君子以文明为德”,是将“文明”与“通”关联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弼直接以文明之德来理解君子,或者说在《周易注》中,王弼以文明而非其他的德目作为君子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在王弼看来,“文明”与“通”是《周易》对于君子的核心定位。而在《论语释疑》中,王弼言“德足君物,皆称君子”(楼宇烈,第624页),这是注重“君”的统领之义。如果将《周易注》与《论语释疑》关于君子的理解合观,那么可以知道的是,“君”与“通”乃君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并且所以“君”者在于“通”。
进一步地,王弼也明确地讲到,“通物”与“时”有着紧密的关联,例如其注解《大有·彖传》以及《随·彖传》云:
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
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故大通利贞,乃得无咎也。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
这两段注文皆论述通与时之间的紧密关联:《大有》卦言大有在于元亨,而元亨在于应天时行;《随》卦言要使万物云行景从,不能以利诱惑而必以正道导之,使物得以亨通,而所以如此者在于得时,得时则得随。此外,如《蒙·彖传》注云:“时之所愿,唯愿亨也”,是言亨通乃时境的内在要求;《遁·彖传》注云:“遁不否亢,能与时行也”,是言即使在不得不逃遁之时,如果能够时行,也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通达。无论王弼的具体解释是如何展开的,“通”与“时”的关联是显著和明确的:时行或得时,才可以得通。也就是说,通是在“时”中展开的,也只有在“时”中才能获得理解,甚至可以说通的实质在于时行。另一方面,王弼对《周易》中具体时境之下各种行动的解释,很多与《老子注》中的“无为”相关连,如《乾》之上九、《坤》之六二、《大有》六五、《益》之九五等注。这意味着相对于《老子注》而言,《周易注》为具体讨论无为的行动结构提供了新的契机。而由此也可以说,王弼思想中时与无之间有着紧密关联,或者说《周易注》对无之通物、统物以及圣人之体无的更为细致、丰富的理解。
思想具体展开的过程往往同时是深入掘发的过程。物之生成变化总是意味着“时”;与《老子注》所言的物之终始—生成之时相比,《周易注》之时是由众多的事物和变动交织而成的具体而丰富的时境。这一显著的差别决定了《周易注》的独特意义。前文说过,王弼之无可以理解成物之变化的根本机制,这在《老子指略》中表达为“反”。请看如下两段文字: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楼宇烈,第195页)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克,乃反其名。(同上,第197页)
前一段屡被征引、讨论,后一段则少有关注。但两者其义一也,而且后者提供了理解无的新视野:无形无名即反其形、反其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反是相反之反而非返归之返,接在其后的一段本于《系辞》的存亡安危之说是为确证。而“其”指自身,如存需反于存自身之形名才得以保其存,由此反即为“自反”之义。自反不是如《老子》二章所言的形名之反,而是一种行动,如王弼注“反者道之动”云:“动皆之其所无”,之即去、往之义,道之反乃是朝向自身所不是、无有而行动。由此自反既是无形无名,也同时避免了无形无名的囫囵一团,摆脱了沦为形容性语词的厄运,而具备了可供分析的内部结构,提供了淬炼为哲学概念的可能。而王弼以四十章的“反者道之动”概括二十八章的雌雄、黑白、荣辱之说,也就将自反与“正言若反”勾连起来,如此则自反在《老子注》中更为常见的表达是“不自”。(13)此义在《周易注》中也有表达,例如《乾·彖传》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天所以能够成其覆物之形名或功能,在于不依赖于此形名的乾健之德;又如《乾·用九》“无首”注云:“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所不与也”,这是诫告刚健之德若是自居自恃,则亦将沦为形名而招致败坏,故需自反而无首、谦退。对于《坤》卦中的柔顺、永贞,王弼注义亦是如此。然则虽皆言自反,《老子注》中的自反基本上只有“自己”在场,“他者”隐没不见。但王弼言由通物而统物,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先行设定的秩序以待于实现,任何秩序都是在生成变化过程中所造就的,这也必然要求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交往、关联。由此《老子注》的问题是,他者如何显现,或者说异类如何俱存以建立整体性秩序?对此,《老子注》只能单纯地诉诸本根之无而未能直接从通物中推演出来,这将给深入分析无及其通、统之义造成困难。但易学语境恰恰可以成为对治。一般而言,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最坏的时境不是六爻皆不当位且无有所成的未济,而是断绝了相互交通往来的否卦。在《屯》卦卦辞注中,王弼言虽然刚柔始交之时会有屯难,但不可畏葸不前,因为只有立足于刚与柔、物与物之间的交往,才能至于盈满而安宁;“不交则否”,虽可免于屯难,但也断绝了一切的可能而陷入分裂、僵死之中。这意味着在《周易注》的语境中,亨通从来不是自通而已,同时也是通物;己物皆通,也就意味着和谐共处。由此,安贞的秩序是在物与物相交往的变化中所造就的,即是由通物而统物。以《讼》卦为例,争讼意味着有冤屈而不通,故需裁断枉直以通之。对于卦辞“中吉,终凶”,王弼注云:“唯有信而见塞惧者,乃可以得吉也。犹复不可终,中乃吉也”,这是说解决争讼不仅要使受冤屈的一方得到伸张,同时也要考虑另一方,如此才可得吉;不可得理不饶人、死磕到底而落入自居、自恃理直当中,否则将招致凶咎。因此断讼需使得双方都能接受而皆通,故王弼以“断不失中”的九二为“善听之主”。又如《随》卦之上六,天下皆已随从而己独最处于后,乃是鄙固不从之人。对此,王弼注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为不从,王之所讨也,故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也”。对于上六这样的不从者不是弃置不问、不相往来,而是即使是武力征讨也要打通西山所象征的阻隔。所以如此者,不在于权力所带来的欲望膨胀,而在于物与物之间的普遍关联及其整体,其所引《诗·北山》也正是此意。同样,对于《老子》中所设想的“小国寡民”状态,王弼认为仅是“举小国而言也”(八十章注),只是举例的方便说法,最终是要归结于大国、天下,不会真的赞同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可以说,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来往不仅是《周易注》之时境的显著特征,事实上也是王弼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周易注》中的无暂时表达为“共在的自反”。
据此,可以说只有进入《周易注》中,发掘出其易学的独特哲学意义,才能真正和全面地理解王弼之无及其通、统之义。而要清楚地揭示其义涵,就必须对《周易注》之时以及各卦各爻具体、纷繁的行动进行哲学的分析、概括、淬炼,以易学语言为基础来建立哲学概念与命题体系,但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本文的目标只在探求理解王弼之无的新进路和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方向。
注释:
①这种论述也被理解为“一多”关系。(参见汤用彤,第69-70、149页)
②二位先生的理解方式有其先声,如《荀子·正名》:“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言“物”是剥除了所有的差异而遍举万有的大共名。而这种理解是在名言概念层面展开的,是对认识活动的描述,但王弼之无是存在论层面的,两者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不对等。
③葛瑞汉的观点大概源于这样一个误解:无所缺乏的只是物质形式或具体事物。(cf.Graham,p.345)但老子与王弼都认为美、善、仁等也是形名,这意味实体(entity)也是无所缺乏的,由此构成了不同于以实体为核心的哲学进路。
④毋庸讳言,王弼确实也讲道为宗主,如一章、四章、三十四章注等。所以,一方面是王弼既注《老子》,就须自觉地依经为文,但在可以自由行文的《指略》中,王弼明言以无为宗主;另一方面,王弼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二十五章注),道这一称谓取于无之无物不由,也就从无那里获得了宗主之义。
⑤陈金樑沿着钱穆先生的路径,将“理”引入进来作为对道的肯定性表述,以与无作为否定性表述相对,来论述道与物的具体关联或者一多问题。(cf.Chan,pp.52-61)然而问题是,王弼的理都是就物而言,且所谓吉凶(四十二章注)、“所以然之理”(《周易·乾·文言》注)表明理是事物变动的具体条理,严格说来还不是哲学概念;“至理”(四十二章注)、“理有大致”(四十七章注)与“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周易略例·明彖》)是一义,言差别之理可以统合起来,但宗元只是理的统合而非理。事实上,汤用彤先生即已使用性理概念来讲论王弼哲学,并由此将宗极概括为“至健之秩序”。(汤用彤,第93页)此种解读进路事实上将重点转移到理概念上,但为何此秩序是无,或者说理最终可以归结于无,汤用彤及陈金樑都未给出论证。宋明道学以理为核心的讨论,不正是要论证本体并非虚无而是切实的“天理”?
⑥不过其以扬雄的《太玄》及当时的《太玄》学作为论据,由于文献的不足,恐怕缺乏说服力。又,作者近些年明确认为王弼思想中有黄老学的因素。(参见王晓毅,2015年)
⑦关于政治哲学的黄老学,可参见文后“参考文献”中陈鼓应、李零等条;关于汉初黄老之治,可参见陈苏镇,第107-111页。
⑧余敦康先生认为《老子指略》中既有对各家之短的批评,也指出了各家之所长,故王弼要在《老子》之学的基础上综合各家之长。(参见余敦康,第138-139页)这大概是对王弼的误解,实际上除了对各家的批评,王弼有对各家学说的简要描述和各家基于自身立场对《老子》的解读,并无所谓的诸子之所长。且“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的评价意味着,在王弼看来诸子之学完全不足取。
⑨汤一介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以“辨名析理”作为玄学的方法,极为鲜明地表达出这一意义。
⑩此频见于《老子注》,例如一、十、十六、二十一、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五十一、五十二等章注文。
(11)对于王注,伊川先生批评道:“此不识卦义。离、乾成大有之义,非大有之义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二程集》,第768页)这是认为王弼由大有而得元亨,但很明显,这是误以孔疏为王弼之意。
(12)在现有的研究中,“一”往往在“一多”问题之下与无等同。相关的论据有不少,其中征引最多的是《明彖》篇及“大衍义”。然而《明彖》篇中从未出现道或无,将其中的宗、元、主、一与道或无关联起来,缺乏有效的证据;“大衍义”中的一之为太极与其是因为“一”,不如说是在于一之“不用”。而在《老子注》中,一不等同于无的证据倒有不少,如四十二章注及三十九章注“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既然已是在数、物层面上,就不可再与无等同。当然,三十九章注中“为功之母”的表述,倒容易让人认为一即无。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更多地从秩序整体的视角来理解一,但王弼之一的义涵要更为丰富,需要另文加以专门讨论。
(13)由此,王弼之无与黑格尔的自否定概念颇为相近,不过其间的差别也很显著。如黑格尔以有为开端而以无为有的中介环节,并由此建立起目的论的哲学;王弼的自反以无为本或开端而走向有,其哲学是非目的论的,世界和变化永不终结和停息,由此“功不可取,常处其母也”(二十八章注)。
原文参考文献:
[1]古籍:《老子注》(武英殿本)《荀子》《周易集解》(嘉靖本)《周易略例》《周易注》《周易注疏》(足利本)等.
[2]陈鼓应,2007年:《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3]陈苏镇,2011年:《〈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
[4]《二程集》,2004年,中华书局.
[5]冯友兰,2007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
[6]李零,1998年:《说“黄老”》,《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楼宇烈,1980年:《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
[8]《唐长孺文存》,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9]汤一介,2009年:《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0]汤用彤,2009年:《魏晋玄学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瓦格纳,2009年:《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2]王博,2011年:《无的发现与确立——附论道家的形上学与政治哲学》,载《哲学门》第2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3]王晓毅,1996年:《王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黄老“因循”哲学与王弼〈周易注〉》,载《周易研究》第6期.
[14]杨立华,2010年:《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5]余敦康,2016年:《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6]Chan,Alan.K.,1991,Two Visions of the Way:A Study of the Wang Pi and the Ho-shang Kung Commentaries on the Lao-Tzu,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来源: 《哲学研究》第2020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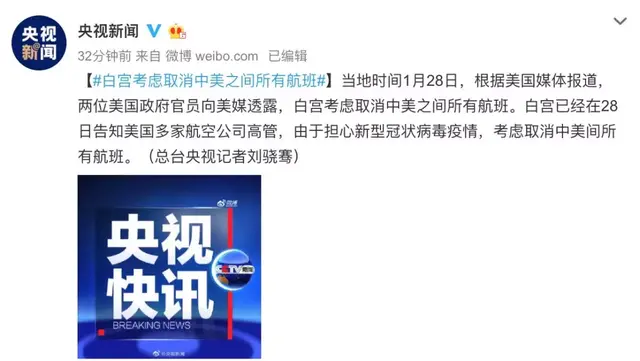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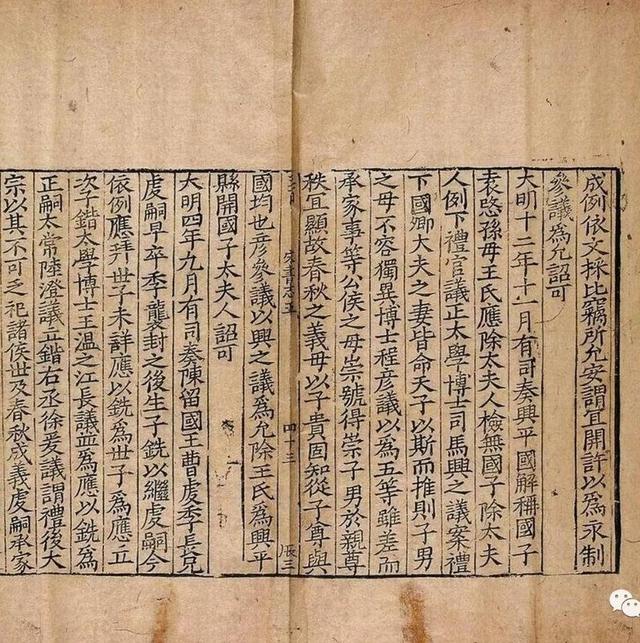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