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钧德的“星洲缘”

上海油画家陈钧德(1937-2019)长期以来是一位画坛“隐士”,他不自我炒作、不迎合市场、不巴结权贵,只顾埋头作画,生前任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也是一位美术教育家。
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画家进入新加坡市场,最著名的就是吴冠中。中国画家以各种渠道打入新马市场,二十年前,陈钧德也与新加坡画廊结缘了,这个缘分不同于其他画家的操作方式,可以说是老天的安排。2001年,陈钧德夫妇以游客的身份到新加坡旅行,他们逛乌节路累了,进入百丽宫的兴艺画廊(Heng Artland),主人谢声远对远方来客一向热情接待,请他们夫妇坐下来喝杯茶。边喝边聊,非常愉快。儒雅的客人留下名片,谢声远才知道对方是一位上海油画家。从此,谢声远一家和陈钧德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和合作关系。第二年即2002年,谢声远和女儿谢书慧访问上海,拜访了陈钧德夫妇,谢声远后来在文章里写道:“主人的情谊、上海的美食、朱家角的景致,至今记忆犹新。”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约定了首次合作,2002年12月在新加坡举办画展《生命的律动:陈钧德油画展》。接下来的十多年,“兴艺”又为陈钧德举办了三次个展和一次联展。
谢声远和陈钧德都很重视纸本画,2007年专门展示纸本画,2010年也是纸本画和油画一同展出。很多画家在户外画速写是作为画室里的画稿,陈钧德不同,他把速写视为纸本画。他采用不同媒介,从铅笔、炭笔、自来水笔到油画棒,他的速写不仅仅是为创作而做的准备,速写本身就是一幅完成的作品。通过这些速写,可以看到陈钧德扎实的基本功。毕加索曾说:“就绘画而言,再没有什么更胜于最初的速写了。”2007年陈钧德在新加坡的纸本画展,是他第一次公开展出“旅游系列”的速写。谢声远的公子谢宇婴在画册撰文指出:“如同他的油画那样,陈钧德的纸本画也是以印象主义为源,表现主义为魂。”又说:“许多人未曾见过陈钧德的另一面,就是他画起写实作品,技巧上简直无懈可击,完全可以和一流老画家媲美。尽管如此,他还是偏爱表现主义。对他而言,最佳的表现主义作品是介于照相式真实与超然抽象之间,朦胧而神秘。”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2005年陈钧德在新加坡的画展。谢声远的女儿书慧,很有艺术天赋,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和得力助手,她策划了2002年陈钧德在狮城的首次画展,又继续帮助父亲筹备2005年陈钧德画展,在和陈钧德夫妇交往的过程中,聪慧善良的书慧给画家夫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然而,天妒英才,2005年3月13日,书慧病逝,对于谢家简直如晴天霹雳,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原计划7月初的画展,还是遵从书慧生前的意愿,按时举办了,这期间,陈钧德一直关心谢先生的情绪状况,对书慧的去世深表痛惜,他写道:“(书慧)其英姿、其才貌,均历历在目,其语音不绝于耳……我们实难忍悲痛,深致哀悼。” 2005年,陈钧德为书慧画了一幅肖像,以玫瑰色为主,将书慧的形象永远留住。陈钧德多绘风景画和静物画,除了几张自画像,他很少替人画肖像,这幅书慧的肖像,不仅对谢家弥足珍贵,对研究陈钧德的艺术生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年,陈钧德在马来西亚期间,谢声远还和他们夫妇游马六甲古城和槟城海滩,朋友的陪伴暂时减轻了谢家的丧女之痛。
谢声远告诉我,陈钧德给他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真!他的画也是一片真趣和真情,在交往的过程中,他有时像个天真的孩子。
陈钧德曾告诉谢声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私下携画登门向林风眠讨教,林风眠很欣赏这些画,叫他把这些作品收藏好,不要给外人看。言下之意就是,这些画是纯粹的艺术品,不符合当时的审美主流,怕给陈钧德带来麻烦。多亏长辈的提醒,陈钧德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林风眠画过一些偏重结构的画,但终究没有进一步朝着抽象的方向走。林风眠曾对作家木心说过:“我画我懂得的,不懂,我不画。”(见木心《双重悲悼》)林风眠的这个观念,一定也影响着陈钧德,陈钧德由具象到抽象的探索,总是适可而止,在他“懂得的”范围内,不懂,他也不画。他晚年的一些抽象油画譬如“山林云水图系列”,分寸感把握得极准,类似中国画的大写意,既没有抽象到不知所云,也没有落到实处,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对于抽象画的实践,他走的不是赵无极、朱德群的路子,他是在林风眠的基础上往前继续探索。海派,是陈钧德的一个标签,他的艺术创作、情感寄托和灵魂栖居都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但“海派”二字不能将他全部容纳,他也有超越海派的地方。
陈钧德五来狮城办展,在新期间,偶尔也外出写生,创作了一些油画和素描,为新加坡留下了美丽倩影。
谢声远是一位儒雅的画商,也是一位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人,早年供职于《星洲日报》,担任电讯翻译;1984年创办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现在是《怡和世纪》杂志的主编。他和陈钧德之间,超越了画商和艺术家的关系,他们是朋友,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老一辈文人的交往,非常单纯美好,令人向往。(何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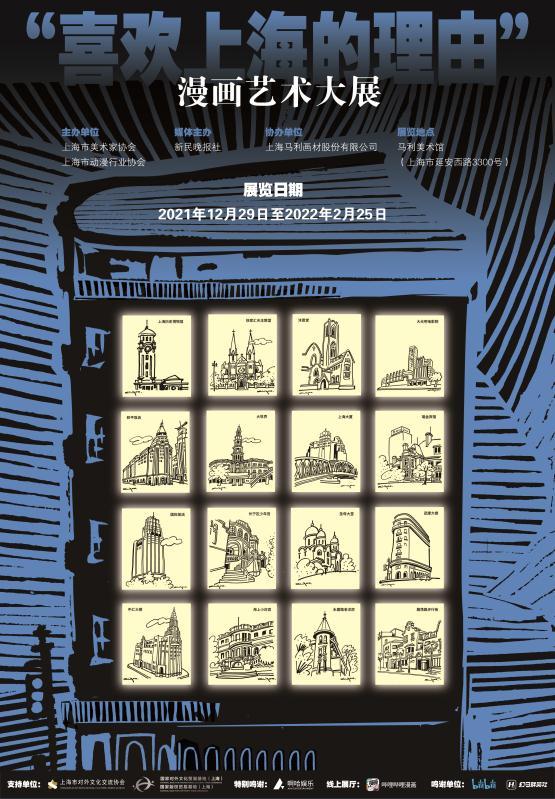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