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与福山辩论的十二个问题

2011年前后, “阿拉伯之春”爆发,迅速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当时,西方媒体一片欢呼声,宣布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的春天来临了。与此相反,我的判断截然不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现在考证下来,我是全世界最早作出这个预测的学者,至今引以为豪。英文维基百科在“阿拉伯之冬”词条下是这样表述的: 2011年6月,中国的张维为教授与("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进行了一场辩论,福山当时认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蔓延到中国,而张维为教授则率先预见了(“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体现了人们好像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四次。20年前开罗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五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叫"中东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的冬天。严格地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会看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 “阿拉伯之春”很快就变成了血雨腥风的“阿拉伯之冬”:埃及的全面动荡、叙利亚的全面内战、利比亚的全面失控、也门的全面厮杀。我想“阿拉伯之冬”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全世界第一个作出准确的预测,这既是对自己国家的尽责,也是对世界的尽责。我经常跟国内的朋友说,当时不少国人被来势汹汹的“阿拉伯之春”吓倒了,认为中国制度也岌岌可危,哪里还敢向西方政治话语亮剑?我经常跟欧洲人说,如果当初你们能够听取像我们这样中国学者的预判,你们也许就可以避免今天席卷欧洲的难民危机了,但现在已经晚了,你们只能自己去承担这场危机所带来的一切。我也经常对美国人说,不要再到处放火,一会儿“颜色革命",一会儿“阿拉伯之春”,这叫害人害已,结果将一个比个糟糕,你们驻利比亚的大使都惨死于“阿拉伯之冬”,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今天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雄心壮志。我们要通过自己对中国和世界扎扎实实的研究,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千万不要满足于给西方学术当打工仔。我们应该花大功夫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世界,了解西方话语,进入西方话语,但进去之后一定要出来,否则是没有出息的,而走出西方话语就是海阔天空。总之,我们尊重西方,但绝不迷信西方,绝不迷信西方的智库,绝不迷信西方创造的指标体系。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创性的研究,绝不人云亦云,西方的东西只能是参考。以我比较熟悉的中国政治研究为例,多少西方政治学者,多少西方的智库,对中国政治作过准确的预测?我几乎找不到,我怎么尊重他们所做的学问?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提出能够影响中国和世界的观点和理论,中国学者和中国智库应该自信起来!
让我们回到那场“世纪之辩”。这场辩论发生在2011年6月,距今正好八年。我们可以简单回顾这场辩论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还在影响我们今天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它所涉及的一系列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民主还是专制问题、问责制问题、中国和美国制度的未来问题、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问题、西方民主的未来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世界文化会不会趋同等问题,将会长期地影响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
这场辩论的地点在上海文广大厦。福山先生是西方自由主义大家,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The End of the Historyand the Last Man)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西方式的为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当时《文汇报》和上海春秋研究院邀请他来,希望他谈谈国际秩序中新型经济体的作用,并和我进行一场对话。但他到了文广大厦休息室后对大家说,他要谈谈中国模式。坦率地说,我们有点儿惊讶,这跟我们原来给他的题目不完全吻合。这些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话语的渗透非常之深,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在与福山先生辩论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国学者与他的对话和讨论,恕我直言,那不是对话,而更像是“汇报工作”。我们一些学者关心的是中国哪一天才能达到美国民主和法治水平。这种弱者心态使许多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如入“无人之览”,所向披靡,在任何问题上都被看作专家,观点被广泛转载和引用。这种局面该走向终结了。我对在场的《文汇报》负责人轻轻地说了一句, “给他一点儿中国震撼吧”,当然,双方都保持了礼貌和互相尊重,但我们的观点分歧很大,辩论激烈但不失理性,应该说这场辩论已经成了中西方学者,就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进行理性对话和正面交锋的一个经典。
让我简单回顾一下那次辩论涉及的12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刚才已经讨论过的,中国是否会经历“阿拉伯之春”,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未来,这里就不重复了。
第二个问题同样尖锐,福山说他研究中国历史,觉得中国模式实际上是这样的:碰上个好皇帝这个朝代繁荣昌盛,碰上个坏皇帝这个朝代一蹶不振,他叫“坏皇帝问题”。我的回应是,即使退一万步,中国历史可以被简化为“好皇帝、坏皇帝问题”,那么中国至少有七个朝代的寿命都在250年以上,比美国历史都长,谁也不能保证美国和西方的制度能够持续下去。然后我说,中国已经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解决了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中国领导人大都担任过两三任省委书记,治理过至少一亿人口。而且中国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像美国小布什当政后,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中国制度,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不会产生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第三个问题是“小布什问题”。我接过福山的“坏皇帝问题”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所谓中国的“坏皇帝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步,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的产物,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我担心美国今后选出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小布什。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非常认同我的这个预测, 2017年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一点,下面掌声一片。
第四个是问责制问题。福山理解的间责制就是西方那样的每四年进行一次的大选。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我说我长期在西方生活,熟悉西方这种问责制,现在看来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真正的问责。我跟他说:中国现在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治制度。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超越了西方模式,因为西方模式有太多的问题,无法做到真正的问责。中国进行的政治试验,包括政治问责、经济问责、社会问责、法律问责等,比西方这个问责制的面要宽得多。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点在上海市静安区,这个区不久前有一栋民居着火了,造成了不少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实际上这是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一个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出了事故。我们实行了同责制,有关的官员、有关公司的负责人都受到处理,被绳之以法。我说相比之下,美国金融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我们这场辩论是2011年,整整三年过去了,现在又八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被问责,一笔糊涂账。而就因这笔糊涂账美国老百姓的财富平均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法治的。福山说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法治。我说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高质量的法治社会,也一直在学习西方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中国的眼光超出了西方法治模式。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造成金融危机的那些金融大鳄,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将他们绳之以法,还以法治的名义给予他们上亿美元的奖金。为什么?因为这些华尔街大鳄几乎都签过合同,英文叫"golden handshake"-“黄金股的握手”,以吸引人才的名义,就是不管盈利不盈利,我离开你这个公司的时候这笔奖金都是要给的。这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公愤,但他们还是心安理得,奖金照拿。我告诉福山,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叫“天”,中国文化“敬天”。这个概念如果翻译成现代的政治话语, “天”就是民心向背,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核心的利益。我说我认为我们99.9%的情况是严格照法律来办,但我们一定保留一个小小的空间,在涉及民心向背的大问题上,在涉及人民整体与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会在不违反法治精神的前提下,作出政治决定,否则就可能是“法条主义”,治理中国这么一个100个欧洲普通国家规模之和的“文明型国家", “法条主义”会出大问题。换言之,中国法治建设一定是要超越西方模式的,美国今天的“法治” (rule of law)几乎已变成“律师治” (rule of lawyers),律师是按市场收费的,这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而且律师在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使美国国家治理的成本奇高,使许多必要的改革寸步难行。
第六个问题是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在这个问题上我给他讲了“文明型国家”的观点, “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大周期,中国现在还处在这个大周期的上升阶段。西方学者和深受西方话语影响的人,预测中国老是出错误,就是因为他不懂“文明型国家”的大周期。我说,历史上,中国一个好的朝代怎么都持续250年、3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今天不能用朝代来形容,但中国人讲势,势一旦形成,即使有相反的浪花,相反的力量,也扭转不了这个大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中国今天还在自己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第七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福山对毛泽东主席有颇多微词。我说你一定要了解中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至今对毛泽东主席仍然非常尊重,这一定是因为毛主席做对了很多事情。我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毛主席统,了这么大一个国家;二是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国的农民今天是有土地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三是妇女解放,中国妇女地位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第八个是腐败问题。我说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历史眼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在崛起的时候,也就是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时候都经历过腐败增多的问题,因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监管,后来都是通过补短板,把监管这一块做上去,这就是中国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且力度非常之大。福山认为只有西方模式才能遏制腐败,我说历史经验不能证明这一点。以“亚洲四小龙”为例,“亚洲四小龙”在初步完成现代化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采用了美式政治制度,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还是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来的模式。结果在治理腐败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要成功得多。我还讲了美国的第二代腐败。美国金融危机,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那是严重的金融腐败造成的。美国的监管公司搞“监管套利",把许多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评定为最好的3A产品,向全世界兜售,害得全世界多少老百姓包括许多美国人倾家荡产。但美国不把这个叫作金融腐败,而是简单地称为"moral hazard"(道德风险),美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九个问题是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问题。福山认为中产阶层崛起必定带来民主化,因为中产阶层要求问责制,要求发表自己的声音,要求参政。我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实际上是最支持中国稳定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稳定和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
第十个问题是所谓的“文化趋同论”。福山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世界文化将越来越趋同,我说可能不是这样的。我提及了当时中国的一首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中国人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在这首歌里都找到了感觉,觉得不管你多么忙,也要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歌在美国不会流行,因为中国人为家所愿意付出的远远超过美国人。我还说,中国的文化像八大菜系,美国的文化有点儿像麦当劳。麦当劳文化有其长处,值得中国借鉴,但不可能是八大菜系融入麦当劳,而是八大菜系怎么收编麦当劳的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涉及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明确表示,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难以解决“低智商民粹主义”问题,美国的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福山当时是这样回应的:“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有一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对于美国这样一种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人民有自由的言论权、评论权。从长期角度来说,人们最终还是会作出正确的抉择。”我当时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想:这个福山呀,有一点“简单天真”啊。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您很乐观,认为美国会吸取经验教训,不被民粹主义左右。但我自己觉得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制问题。”从2016年英国脱欧的公民投票和美国特朗普上台这些黑天鹅现象来看,西方民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金钱的卷入,新媒体的卷入,最终西方这种“低智商民粹主义”可能会毁掉西方的未来。至于林肯的表述,在哲学层面是对的,语言也是诗一般的,但现实很骨感,政治有许多维度,比方说,政治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还有成本维度。就好像说,你今天丢了手机,我可以宽慰你:没关系,你的手机一定还在这个地球上。
第十二个问题就是讨论关于“历史终结论”本身。我讲了一个很大的观点,我说从历史长河来看,我认为西方现在这种民主制度,即所谓“多党制+一人一票”,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县花一现。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两千四五百年前在古希腊有些很小的城邦,那里的男性公民有一人一票。最后这个所谓雅典民主也被斯巴达给打败了。之后的2000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中一直是贬义词,相当于暴民政治,直到西方国家完成了现代化之后,一人一票才开始成为主流,美国是1965年才开始的一人一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开始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就差十几年,我们可以竞争的。我直白地对福山说,我认为不是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我想到了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1793年的时候派特使到中国,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会见了英国特使,乾隆皇帝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好的制度了,你们英国送一些雕虫小技的东西,我们大清帝国不屑一顾。后来历史证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运急剧下滑了。我说我觉得恐怕西方现在有点儿像中国的乾隆时期,正在明显地走下坡路。
以上12点,就是我们当时辩论的主要内容,八年过去了,大家可以作出初步的评判,谁的判断和预测更为靠谱。一些问题再等一些时间下定论也无妨,但我相信我的判断和预测是准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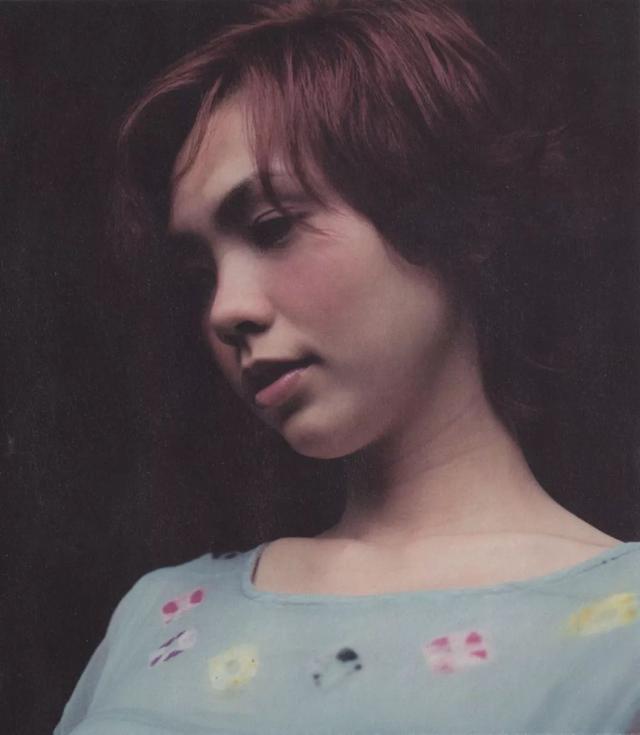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