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越界招惹了野味病毒

2020年1月23日,有着1100多万常住人口的武汉封闭了对外交通,这是阻止疫情扩散的关键手段——尽可能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移动散播。
最早被该病毒感染者,多是华南海鲜市场西区的商贩及其家人。这个市场里售卖各种野味肉类,而且最新的研究已经追踪到病毒可能来自华南常见的野生动物,就像2002年的非典(SARS)病毒最早也是从菊头蝠传播到果子狸,然后被嗜食野味的客人吃下肚。
人们越来越熟悉这样的情节,故事总是从接触某种野生动物开始,然后人类在病床前以及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展开斗争。而在现代生活的边缘地带,是农牧民、盗猎者、伐林者进袭丛林——无论是在武汉黄陂、广西玉林的山区,还是在刚果(金)的郊野,或亚马孙、苏门答腊的热带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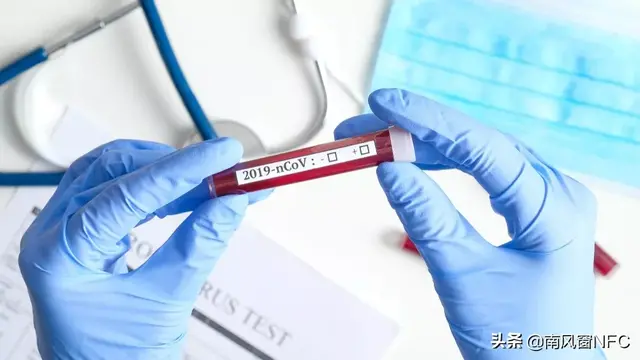
当病毒从边缘地带进入城市后,就开始跟着高密度人口的流动快速扩散,各种严重的症状使一般人无力抵御。也只能感谢现代医学同样善于扩张知识的边界,深入剖析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基因构造,努力控制病情。
然而,倘若边缘地带的生计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便只能持续对生态造成压力。
病毒散播的捷径
武汉新型肺炎肆虐之际,在非洲中部的刚果(金)北基伍省,致死率高达60%以上的埃博拉(Ebola)病毒仍然持续每周发生许多新病例;在沙特和卡塔尔,到2019年年底一直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冠状病毒的传播;在东非的苏丹与乌干达等地有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在尼日利亚有猴痘病毒(Monkeypox)病例,2019年还一度散播到了新加坡。
这些疾病的特色,就是能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它们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原本在自然环境中很少接触的人、家畜与野生动物,在密集共处中发生交集。
像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流感病毒这类RNA病毒的特性是,突变的速率非常快;即使原本只限于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也可能演变出能适应家畜或是人体的病毒。医学研究显示,跨物种范围越广的病毒种类,在人当中散播的能力也倾向于更强。

2013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疫情后,研究人员进入最早发现病例的几内亚村落调查。在这个贫穷的村落,他们找到一个曾经栖息许多蝙蝠的树桩,一个名叫埃米尔的两岁小男孩经常在那里玩耍。小男孩首先成了病毒的牺牲品,然后病毒感染了他的家人和村民,蔓延到广大的地区。
如果说埃博拉的传染可能来自小男孩与蝙蝠的直接接触,那么,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播是先由蝙蝠传给了骆驼或羊等牲畜,再感染了牲畜的主人;1994年在澳洲爆发的亨德拉病毒,则是马匹吃了狐蝠吃过的食物或接触了狐蝠幼仔,再感染了赛马场管理者。

在很多地区,农民垦伐森林把土地转变为果园,这些果园常见的现象就是吸引果蝠前来觅食。假使农民也一并饲养牲畜或其他动物,就可能成就病毒散播的捷径。SARS传播的路径也可能是这样来的,不仅野生的果子狸喜欢进入果园觅食,果园的主人也可能兼营果子狸的养殖。蝙蝠、果子狸与人类就这样有了密切交集,促进了病毒向人类扩散。
吃野味的后果
经过严重疫情的爆发与媒体传播之后,如今人们越来越知道蝙蝠、果子狸等动物可能传染疾病。例如,SARS期间各地就扑杀了大量果子狸,而澳洲、毛里求斯等国也曾有扑杀蝙蝠的行为。
看来,蝙蝠似乎是集齐各种危险病毒于一身的动物,果园的主人也早已视之为眼中钉。事实上,蝙蝠会在野味市场占一席之地,部分原因也在于农人本就十分讨厌来觅食的蝙蝠。

果蝠
然而,扑杀蝙蝠并不是真正正确的方案。蝙蝠不仅难以有效扑杀,而且在生态系统里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传播种子、传粉、捕食害虫等。蝙蝠本身不是病毒,就像其他传播人畜共通疾病的猴、骆驼甚至猫狗一样,与其说这些动物本身有危险之处,倒不如说它们的角色只是一种桥梁;如果没有多种动物与人类密集接触的条件,病毒也不会那么容易演化出传染给人的形态。
在疫情危急或农作物受损的时刻,人们宁可寻找简单的怪罪对象,但是更有用的方式,或许是尝试改善边缘地带社会与生态的互动状态。
如果人们试着仔细检视这些边缘地带发生了什么,会看到贫困与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这些疾病生成的关键脉络。这里用“生成”来形容这些新疾病,是因为根本上这些疾病并不是原本就在那里,也不是主动来寻找人类,而是在人类开发野外环境或利用野生动物的过程中,因病毒跨物种迁徙才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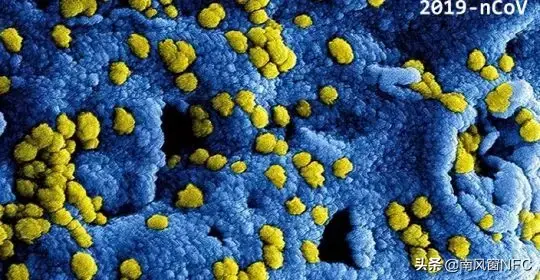
在西非埃博拉大流行之后,很多地方的野味市场不再受到欢迎,但许多西非城市里仍然有大量的贩卖野味交易。2019年对金沙萨和布拉柴维尔的调查就显示,接近1/5到1/2的市场和餐馆里还能找到野味肉类。
许多调查推估,西非和巴西每年的野味消费量可能高达600万吨,甚至有的资料认为光是刚果盆地就能接近这个数字,这只比全欧盟每年的牛肉产量少一点,即使数字打点折扣还是很惊人。
从西非野味摊位上怒目圆睁的大猩猩头颅,到东南亚餐馆里的狰狞蝙蝠汤,事实上在野味市场里几乎没有不可吃的动物,不管是各种啮齿类、猿猴、两栖动物、爬行动物,一概都能果腹。网上流传的武汉野味产品标价表,也印证了这一点。许多论者也都指出,野味消费背后往往是炫耀性消费、猎奇或者迷信思维。

在西非市场贩卖的野生动物肉品,还可以是巫术的材料,用于宣扬诸如用兔脚做的钥匙圈能带来好运,用秃鹰的脑、眼睛或骨架来驱邪或增强个人力量,等等。
这些貌似遵循传统信仰的方式,在古代并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太大危害,但是在现代城市化人口增加,打猎工具从刀变成猎枪或电网的情形下,事实上生态效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其背后的驱动力不再只是部族的小范围习俗互动,而是城市化令人惴惴不安的焦虑生活,或是展示经济地位的欲望。

消费的另一端是杀戮,猎人可能仅仅是乡村的贫困居民,或是因失业而难以谋生的青年。杀戮的绝境,往往来自生活的绝境。因自然灾害发生粮食短缺的时期,通常也是该地区捕杀野味的高峰期。很多难民营或受战争破坏地区的人们,更常在野生动物中寻求食物与生计,例如埃博拉肆虐的刚果(金)北基伍省就是如此。
生态和平的未来
相较于刚果(金)难以遏制的野味消费状态,国内即使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贩卖,也是极小规模的。刚果(金)的生态资源极其丰富,如果在正常维护的情况下,其实有机会像邻国卢旺达一样发展良好的生态旅游项目。
在巴西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猎捕,往往与伐林破坏同时进行。伐林公司配有武装人员,在伐林的同时猎杀动物。猎捕野生动物的暴力,也与其他性质的暴力相连结,例如各种走私犯罪,甚至是杀害动物保护人士与森林原住民的恶行。这种在盗猎中伤人伤己的危险行为,在非洲也屡见不鲜。

(巴西国家太空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巴西亚马逊雨林已有多达8934平方公里被砍伐,面积约相当于8个中国香港)
对边缘地带的生态破坏,通常可追溯到当地人在高度贫困的压力、经济发展与谋生的需要下所形成的暴力情境。这种危险情境,附带卷起了病原体的流动传播和演化。这种可怕的病原体,就如同我们盲目施加于自然的暴力,会反扑到我们身上,人类最终将以经济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来偿还。
病毒不断提醒着我们要更好地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找到与生态平衡共处的生活方式。
作者 | 邓晨
特约编辑 | 姜雯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唐俊霏,STA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