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价值和意义
作品鉴赏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7]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7]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8]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8]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前者用以比喻形体,后者用以比喻感情之变化。[8]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觉喻感觉;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如《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东方诸侯国之百姓对西周王朝贵族窃据高位、不恤百姓的愤怒(皆有名无实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开口挹取,指出西人对东人的剥削。实际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8]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师尹地位之显赫、重要,此以具体物之高,喻抽象的地位之显赫。
《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以山冈之永恒,河水之不断,日月之长在,松柏之茂盛比喻君福祚之不可限量。[8]
《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喻人之盛怒,以自然现象喻人情绪之变化,是通感之比。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8]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对赋、比、兴概念的解释十分明确,但他将《诗经》每章表现手法都一一标出,其所言的类型和对诗的解释中,就显示了矛盾。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标:“兴也。”但他在具体解释此章时又说:“雎鸠,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烈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串讲全章时又云:“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合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则又成了“比”。[8]
再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卷耳》、《黍离》、《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8]
三、赋。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8]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8]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前人用赋、比、兴来概括《诗经》的表现手法,十分精到。但对《诗经》“赋”这种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在兴和赋、比的关系上也一直未能划分清楚。再就是将比、兴看作诗的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将《诗经》中的“比兴”和后代的“比兴”混同之故。其实,对《诗经》中赋法的研究,应是探讨《诗经》艺术手法的重要方面,这同古代文论史上探讨“比兴”概念的流变是两回事。[8]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8]
重章叠句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8]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国风》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诗经·国风》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语言风格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8]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8]
皆有曲调
诗与乐的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乐律全书》说:“《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诗与乐的这种关系在上博简《采风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证实。马承源先生认为:“简文是乐官依据五声为次序并按着不同的乐调类别整理采风资料中众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时可依此类别定出腔调,如《诗经》那样,而简文所记约是楚地流行的音乐。”[9]
5学术研究编辑
历史考据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10]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现代研究
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
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
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
民国时期《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
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
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
研究发现
2019年2月3日,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初步释读工作完成,海昏简本《诗经》现存竹简1200余枚。简文内容分为篇目与诗文,可以见到“《诗经》三百〇五篇”“《颂》丗篇”“《大雅》卅一篇”“《国》百六十篇”等记载篇目数量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海昏简本《诗经》的总章数记载为“凡千七十六章”(1076章),与今本1142章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海昏简本《诗经》的发现,不仅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更提供了汉代《鲁诗》的可能面貌。[11]
6价值影响编辑
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诗经价值
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宝贵的民俗材料。
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12]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12]。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12]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

步元诗经八卷(宋)朱熹集传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日本当代学者于二十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诗经嫏嬛体注大全八卷·清嘉庆己卯年刊本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开始于公元16世纪,通过来华的传教士译介给欧洲读者。19世纪初叶起,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诗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欧洲的主要语种都有了全译本,而且趋向雅致和精确。关于是散译还是韵译,曾形成韵律派和散译派之争。韦理的译本可作为西译追求“雅”的典型,把原著译成优美的抒情诗,为了体现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打乱原来的体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内容分类,附录又将《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代表与欧洲诗歌比较研究。高本汉的译本可作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语言学家,在训诂、方言、古韵、古文献考证诸方面都倾注功力。这两部译著在西方产生几十年的影响。
北美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诗经》译介。单篇译文大量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重要译本有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E·Pound,1885~1972)的选译本《孔子颂诗集典》(1954),海陶玮(J·R·Hightower)的全译本、麦克诺顿(Wenaughton)的全译本。庞德的英译曾引起热烈讨论,他向美国读者特别推崇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
沙俄时期原已有15种《诗经》译本(选译和全译),5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文化交往大有进展,从事译介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图金院士、费德林通迅院士的影响最大。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也都有《诗经》译本。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后迅速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巴次大陆都正在传播《诗经》。越南社会科学院列《诗经》越文全译为国家项目,蒙古文全译也即将完成。《诗经》正以几十种语文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诗经学是世界汉学的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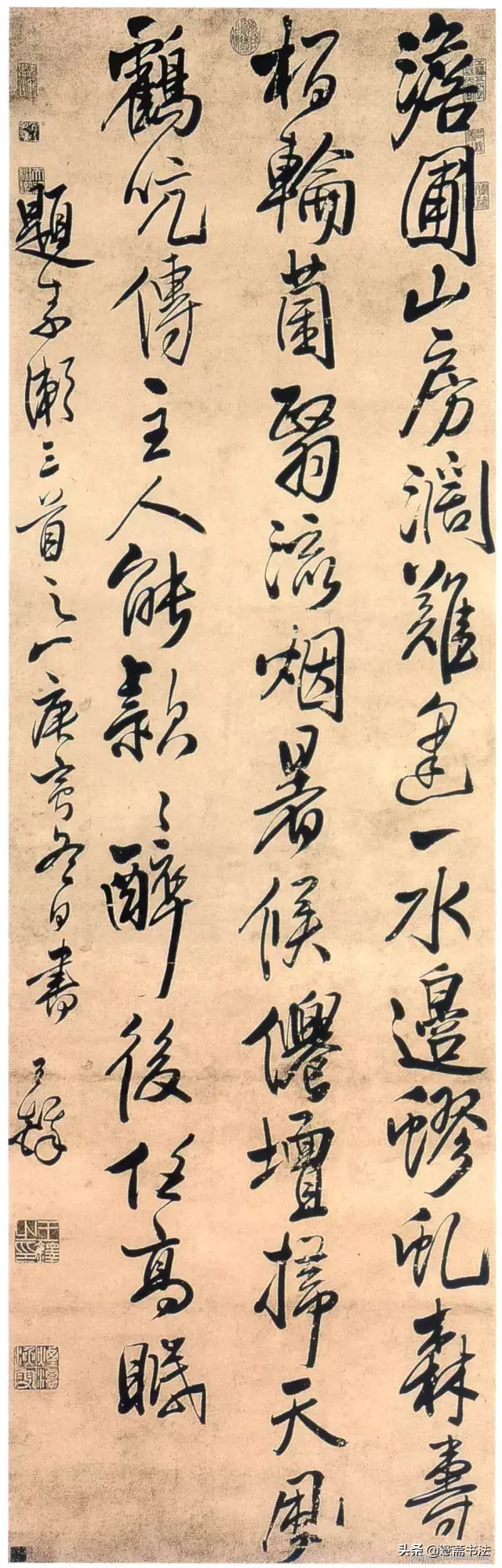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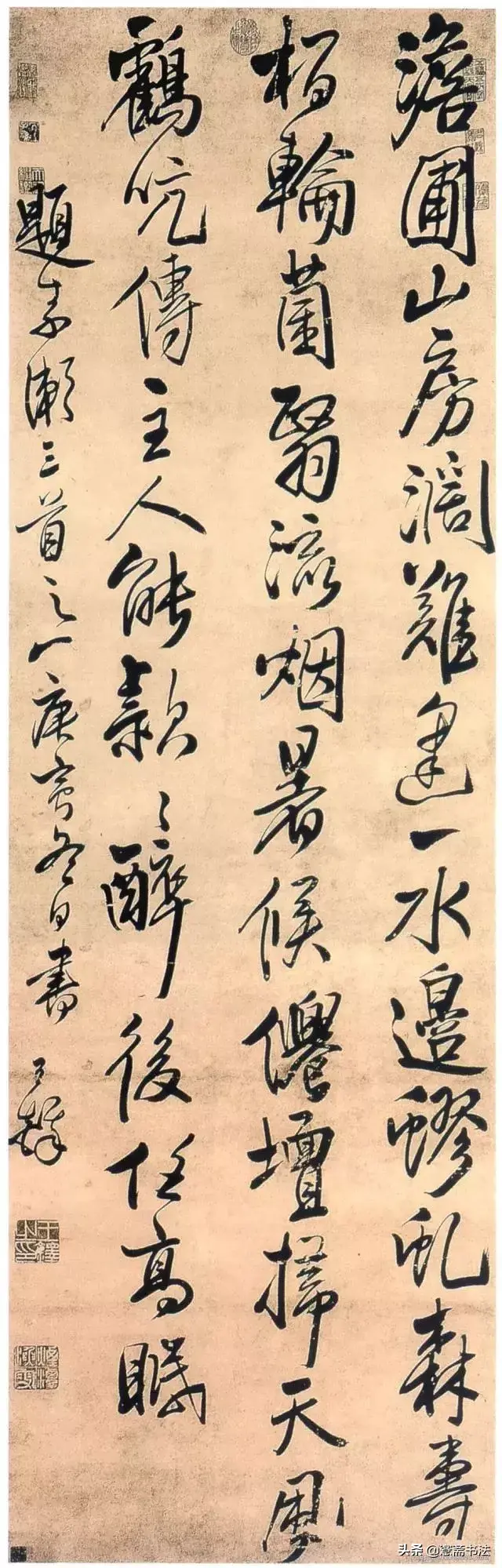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