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和蒲风一起编诗的客家诗人野曼走了
本篇为客名君好友河心月作品。感谢河心月搜索大量资料,精心撰写。

————————————————————野曼(1921.8-2018.1)——————————————————————
野曼,曾任《华夏诗报》总编辑(1985-2015),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国际诗人笔会创会主席。
2018年1月4日,97岁高龄的野曼驾鹤仙去,这位客家诗人的诗歌人生却凝结在一首首诗里。野曼(1921-2018),广东蕉岭县新铺狮山乡人。野曼的父亲在蕉岭县故乡是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尤其擅长画兰,因此给野曼出生时取名赖观兰(后改为赖澜)。在家庭的熏陶下,早慧的野曼从小喜好古典诗文,并喜欢普希金、惠特曼等外国诗人的诗,读初一时,就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作品。

————————————————————— 在东山中学与诗歌结缘 —————————————————————
1938年,时年17岁的赖观兰在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与后来成为东山中学第十八任校长的李泉隆先生是同班共室、志趣相投的同学兼诗友。赖观兰读高中时因酷爱新诗,经常创作爱国诗歌,彼时便取《诗经》“野有蔓草”之“野蔓”作为笔名,后又改为“野曼”。从此,野曼一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是这样写的:“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野曼就读的梅县东山中学由叶菊年、叶剑英、丘燮亭等创立于1913年春天,立校之初在东山书院创立了“私立东山中学”。那时,抗日救亡运动已扩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广大青年学生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梅县东山中学的学生爱国运动搞得轰轰热烈。17岁的野曼血气方刚、爱国热情高涨,激发了追求民主、进步和自由的理想;正如野曼在2003年8月26日《中国诗人》“野曼访谈录”(采访人:张大为)中所说:“我真正爱上了新诗,还是1938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的时候开始的。这是一所地下党领导的学校,救亡抗日的洪流在那里涛飞浪卷。”
那时,野曼是一位新诗的狂热追求者,是一位“走路在做诗,做梦也在做诗”的“诗迷”。野曼在“访谈录”中还说到:“当我写下‘第一句’和‘第一个标点’叫做诗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风狂雨骤、内忧外患的年代……在这国家民族和个人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新诗挺身而出,高度发挥了‘炸弹和旗帜’的功能,它如狂风似炸雷,在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歌颂抗击日寇的英雄战士……时时刻刻在冲击着我的心灵,为那‘炸弹’和‘旗帜’所震撼、所激励。”
————————————————————— 与蒲风一起编爱国诗 —————————————————————

1940年夏蒲风夫妇(前排)与江洪及野曼(后排)合影于松口
就读高中期间,野曼有幸与蒲风一起主编了爱国进步诗刊——《中国诗坛岭东刊》。蒲风、陈残云、雷石榆、芦荻等诗人常为之撰稿,使这株诗歌奇葩在岭东大放异彩。蒲风也是梅州人,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是新诗歌运动的最热心组织者和推动者。

蒲风(1935年摄于东京)
彼时野曼还主编了《孩子纵队》,宣传发表东江纵队小鬼队的事迹,大受读者欢迎,后来,《孩子纵队》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特务查封,《中国诗坛岭东刊》第二卷第六期送检的稿件也被检查所扣留。山雨欲来风满楼,梅县的形势一片严峻,人心惶惶。地下党发现在邮局检查的异党分子信件中,野曼的名字赫然在目。于是,蒲风决定到桂林文化城去,并相约野曼“于桂林《救亡日报》聚首”。1940年野曼参加了全国抗敌文艺协会桂林分会。
—————————————————————— “枪边的梦” ————————————————————————
后来,日本军队开始南北夹击,向桂林推进,国民党也将在桂林下手,形势陡然紧张。野曼在桂林也呆不下去了。
1942年野曼就读于粤北中山大学文学院,在那里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短笛》。1942年,野曼与诗友芜军一同创办了《诗站》;后来还组织了萌芽文学丛书,发表彭燕郊等人作品。1943年,芜军前往桂林,不幸遇难。野曼面临内忧外患,悲愤交加,在《诗站》第三期发表了他的著名诗篇《枪边的梦》。这首诗最初被《浙江日报》转载,后来又被上海崔万秋主编的《笔》杂志(1946年)第一期转载,2005年7月《诗刊》第7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经典名篇回顾”中,又把这篇诗与戴望舒、巴金、艾青、臧克家、胡风、魏巍、贺敬之、郭小川等22个人的诗,列为“经典名篇”。
今日,我们将《枪边的梦》细细读来,仿佛仍能触摸到作者滚烫的心、悲愤的怒火、火热的激情和那个时代的精神:枪/多么响亮的名字啊/昨夜/我梦到枕边的枪失踪了/我发现这支心爱的枪/被握在一个喝血者的手里/向着我年老的母亲/向着我的弟弟和妹妹/瞄准着……/我哭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多的泪水/我看见我那经不起恐吓的/衰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弟妹/都跪在枪的面前号哭/他们都比我哭得更加的悲伤……/妈呀,不要哭,不要再提起/我们是什么胜利国的公民/生活在这痛苦的日子里呀/我曾经看到了/无数的人都像一条小牲口/那样地生活着,劳碌着/把繁花似锦的日子/埋葬在阴暗的田野里/每逢收获的季节来了/喝血者却嚎笑着走来/从他们的手里抢去了/最后一把生锈的镰刀……
—————————————————————— 中国诗坛长青树 ——————————————————————
在现当代中国,从上世纪的1938年夏开始诗歌创作、与蒲风创办、主编《中国诗坛岭东刊》到95岁高龄仍在主编中国唯一一张全国公开发行的诗歌大报《华夏诗报》, 野曼当是中国第一或唯一编龄最长的著名诗人、编辑家了。

1946年野曼在广州与黄宁婴主编《中国诗坛》,同时与于逢、易巩主编《文艺世纪》;1949年10月,参加接管国民党的《大光报》《建国日报》。建国后,长期主持《广州日报》副刊“珠江”与《羊城晚报》副刊 “花地”;1985年创办《华夏诗报》(艾青题写报名)并任总编辑至2015年。

建国后,野曼于1955年受胡风冤案株连被审查。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后,野曼被批判押送粤北山区黄陂劳动改造,受到不公正待遇;1973年,野曼从黄陂被调了出来。1980年胡风案平反;1981年,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的野曼终于得到解放。野曼先生文革前虽也不时有作品问世,但直到新时期后,才真正焕发诗的青春,发表了大量的诗文。野曼在新时期的诗歌中经常写到爱,包括《爱的潜流》、《爱着是美丽的》、《妻爱》等,从这些诗中可以感到一颗炽热的心在跳动。
野曼一生诗作颇丰,甚至年逾花甲仍笔耕不辍,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诗歌、散文与评论,出版、主编诗集、散文集、诗论集几十部, 数以百计的名篇佳作如《枪边的梦》、《积雪期》、《秋旅情思》及散文《妻爱》等上百首、篇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卷》、《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新中国50年诗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1949--2009中国诗歌名篇珍藏版》及外国多个国家出版的《中国诗选》、《亚洲现代诗集》等两百余种权威选本。

野曼《关于时间》
野曼还出版了专著诗集《短笛》(1942年)、《爱的潜流》(1982年)、《迷你情思》(1987年)、《花的诱惑》(1992年)、《女性的光环》(1991年)、《浪漫的风》(1991年)、《风流的云》(1999年);散文集《妻爱》(1984年),诗论集《诗,美的使者》(1991年)以及《野曼作品选萃》(1998年)等;还有散文集《缪斯的爱》、诗论集《中国新诗正喧腾于一片辉煌的空间》等。
其中诗与散文等已被选入80多种选本中,且被译成英、日、韩、德以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在各国出版发行。野曼先后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30届世界作家会议、南斯拉夫24届诗歌节,以及应邀访问罗马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同时参加泰国及日本举行的第10届、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
野曼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诗人笔会创会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号称中国诗坛长青树。2003年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野曼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7年,野曼获得“宝玉陈杯·百年新诗贡献奖”之“编辑贡献奖”。
———————————————————————— “诗=生命” ———————————————————————
野曼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了新诗,新诗融入了他的骨和血。诗在野曼的人生历程中相喜、相悲、相慰、相爱、相随,用野曼自己的话来说:“我曾经写下了一个公式‘诗=生命’。还写下了‘生命宣言’:诗,是生命的喧哗,生命的追寻,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而生命又是属于人民的,它为追求而献身。为了这一追求,我将终生奋发,鞠躬尽瘁!”
晚年的野曼也时刻关注着中国诗坛的发展,面对上世纪末中国诗坛出现的一些歪风邪气, 他仗义执言,敢于批评。关于这一点,笔者查证到野曼先生2003年8月26日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文章“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其时野曼先生已82岁高龄,仍思辨清晰、引经据典、逻辑缜密,分析了当时诗界存在的一些对新诗艺术传统的认识误区、甚至是全盘否定新诗传统的问题。

野曼在文中指出,“新诗的艺术传统,它既不同程度承接了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血脉 , 又体现了自由诗的艺术特点。它在艺术上的操守, 包括形和音两个方面。所谓形, 即诗的体式建构,如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楼梯体、散文诗、民歌体,等等 ,它和古典诗歌一样 , 都是多元的格局。所谓音,也就是诗的音乐美 ,音乐性形态 ,主要是节奏和韵律”。
野曼先生是一名经历了抗日救亡战火考验的爱国诗人,其骨子里流淌着不可磨灭的爱国情怀。1996年8月,野曼先生到日本参加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期间安排一天旅游,他忽然发现旅游车开到了靖国神社丛林外,便立即要求下车,愤而拒绝参观;同时下车的还有他的夫人林紫群和上海女诗人陆萍。
当晚,他在下榻的东京银座宾馆写下《杀手们的墓》——“那死了多年的头号杀手/已悄悄爬出了棺椁/他们浑身浸透/中国死难者淋漓的鲜血/手里还紧握着/从未睡眠的屠刀/墓里死了的又活了/墓外活着的却死了/他们彼此疯狂拥抱/眼里燃烧着/帝国贪婪的火/夜夜失眠的导弹/正在墓门外等候。”
生命誓言
無疑,我會老去
我那挺直的脊椎
便是我的碑
Naturally,I’ll be old
My upright backbone
Will be my tabl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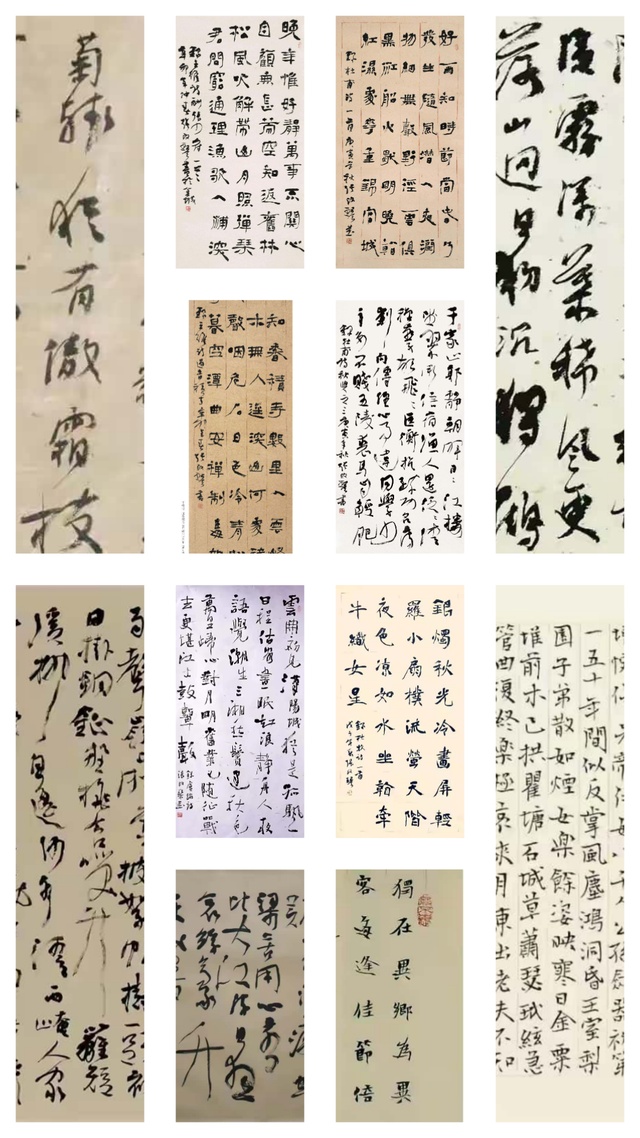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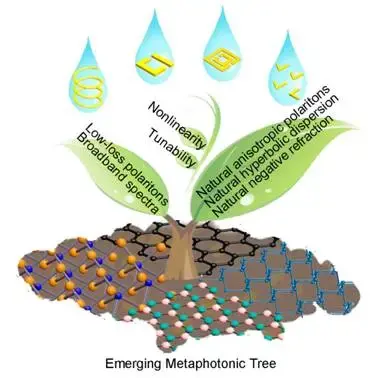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