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燕生|追忆:马克瑞与日本禅史研究传统
提起禅宗,许多中国学者会有某种“自家宝物”的错觉,似乎只有中国人才能把握禅的精髓,相应地,只有中国学者才能“美善”和“地道”地研究禅的思想和历史,这几乎可算是某种带有反讽色彩的“汉话汉说”。且不说禅之思在历史上流经东亚多个国家,生长出中国禅(Chan)、日本禅(Zen)、朝鲜禅(Sŏn)、越南禅(Thiên)、欧美禅(ZEN)等多类“花种”,就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禅史研究而言,实也起源于胡适、铃木大拙、金九经等现代中日韩学者的密切协作,并且是与敦煌学这类世界性学问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说,中国禅宗史研究从来就是一项国际性学术。
然而勀实而言,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学人范围里似乎仅胡适真正在国际交流平台上参与禅史的核心讨论,这当然与他广泛的影响力和流利的英文表达相关,许多时候我们阅读胡适的论著,感觉他就是在用英语思维写作。胡适的绝响让人感叹,因为在特定背景下,国内学者在近半个世纪内无法有效和深入地参与国际同行间的对话。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胡适的影响力毕竟是全世界的,他的事业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柳田圣山这样的禅宗史大家的研究方法,并且经由柳田圣山的宣介,更进一步影响至今天的日本和欧美禅史研究。本文所谈及的马克瑞(John R. McRae)先生,就是承接了日本和欧美禅宗史研究传统的一位世界级学者。于胡适先生而言,马克瑞既传承了他大胆假设和勇于质疑的精神,又严肃批评其基于世俗启蒙主义的反宗教叙事策略,及历史还原主义意识支配下的、蓄含目的论色彩的禅宗史考证思路。然而天不假年,这位一直予人们以意气风发印象的学者竟已早逝了,生命之轮停留在六十五岁。
若干年之后,每当面对国际禅史领域内风平浪静或稍有微澜起灭的状况,笔者常不由己地想起神采焕奕的马克瑞,以及他那些充满灵感和激情,同时又极富批判解析力的禅史撰述。每一次重新稽阅他备具典范意味的著作,字里行间的琳琅文思和不竭才情似乎有自主延伸的力量,仿佛他的溘然急逝并未带来书写的辍然终止。毕竟,这位友人故去而造成这个领域缺憾不断增加,是许多国家学者群体的共同感受。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再也没有看到类似于《北宗与初期禅的形成》和《中国禅宗史:虚构之上的真实》这样兼具深邃洞察和粲然逸兴的著作了。

马克瑞(John R. McRae, 1947-2011)
与许多其他最后走向禅宗研究的学者一样,作为本土美国人的马克瑞之所以对禅产生浓厚的兴趣,其实要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风靡西方世界的“禅学热”。作为诸多“边缘思想”之一,禅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毫无预兆地投入那个令人目眩和困扰的年代,转而成为治疗那个魔幻时代的精神修炼指南。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此时西方世界接受的禅学,乃是经由日本文化浸染后的思想。实际上,从二十世纪初始,日本学者在禅精神的阐发、禅艺术的研究和禅史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这些成就经由各种途径折射给西方知识界和大众社会。青年学生马克瑞无意外地耽迷于此,并自此开始长达数十年的禅修生涯。这种“半佛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被马克瑞幽默地“自损”为,“在自传式的吹嘘里,我通常加上如下一句:是一位长期然而‘无常性’的佛教修行者”。禅在西方世界蔚为风潮是与不少禅学的传播者相联系的,例如铃木大拙、海瑞格(Eugene Herrigel)、瓦茨(Alan Watts)。在当时,“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也多有研习禅的经历,我们可以提及一系列灿若繁星的名字:《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垮掉派”代表诗人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斯奈德(Gary Snyder)。
禅的生命兴趣自然将马克瑞诱导至禅学研究旅程上,这就是他的耶鲁大学研究生涯。马克瑞的导师是当时全美最为知名的东亚佛教研究者之一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他的研究领域与稍早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接近,后者撰有《中国佛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和《中国史里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威斯坦因撰有《唐代佛教》(Buddhism Under the T'ang),并曾远赴日本禅宗曹洞宗驹泽大学交流,马克瑞从导师那里获得许多建议和建设性批评。在研习禅宗史的过程中,马克瑞还受到另外一位美国禅宗史研究大家扬波斯基(Philip Yampolsky)的学术接引。扬波斯基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他基于敦煌写本的《坛经》英译被誉为英文《坛经》定本(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he Tex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 with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Notes),在该文本的许多英语翻译中居于首选地位。正是扬波斯基将青年马克瑞介绍给了日本禅宗史宗匠性人物柳田圣山先生。
谈及禅的历史研究,柳田圣山(1922-2006)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禅史研究的中心人物。实际上,这五十余年的禅史研究,其实也是以来自东瀛的贡献为主。就柳田圣山而言,这种中心性尤其反映在如下值得注意的事件上:许多当今西方重要禅史学者都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初留学日本京都,并在柳田圣山的禅史典籍研讨班上接受培训。在这群外国留学生中,最为知名且贡献最大的要数马克瑞,以及目前美国佛教学领军性学者、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法籍学者佛尔(Bernard Faure)两人。
马克瑞是1973年至1975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留学的。在这个时段里,柳田圣山是花园大学教授、禅文化研究所所长,后于1976年起才开始担任京都大学教授,并于1985-1986年任京都大学历史学“京都学派”重镇之地,即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因此,马克瑞在京都大学留学的那三年,柳田尚未调任至该校。然而,据入矢义高以及柳田圣山二人的回忆,柳田圣山于1960年代末开始应入矢义高的邀请,同时在入矢义高执教的京都大学兼课,并且成立了“禅语录读书会”,一起研读禅语录。因此,马克瑞师从柳田圣山应该是在“禅语录读书会”这些场合,地点同时包括花园大学。
柳田圣山在《禅の文化》“绪言”中回忆说:“作为(读书会的)班长,我期待的是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理工学等不同领域的方法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讨禅的主题,而这其实也是为了顾及外国进修生们的问题兴趣。”可以想见,当时参与柳田圣山主持的禅语录读书会的“外国进修人员”,不仅仅是以禅的研究作为专业的学者,也有其他人文科学乃至理工科的学者。
柳田圣山同时强调指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一个传统,就是重视“文献研究,每一次的发言,都要以底本作为问题”。因此,马克瑞在柳田圣山门下应该是以“禅语录读书会”的方式学习禅宗研究的,而“重视文献研究”“以底本作为问题”的研究风格,也应该被马克瑞所继承。当时“禅语录读书会”阅读的语录有《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等唐五代禅僧语录。“读书会”一般是逐字逐句地读,对不懂的词汇以及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书名等专业术语,除查找各类词典外,还要对照相关的文献书籍,佛教之外的典籍也在查找之列,而以历史文献最为优先。查找出来的结果,一般用注释的形式予以记录,而最后一道手续是将原文翻译成现代日语。这种做法既可以训练初学者阅读古典禅文献的能力,同时更可以提醒他们,说话应该做到“言之有据”,不能凭空想象。
那么,马克瑞先生禅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是如何继承柳田圣山的?其间类似或相同点何在?在中国禅文本材料里,“灯史”(lamp history)类文献是最为重要的一项。“灯史”,严格意义上说,并非记载着史实,其记载的重心主要放在禅宗内部的传承上。所以,与同时代的《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记载相比,“灯史”的信赖程度,往往遭到质疑。胡适基本上采取摒弃的态度。柳田所持的研究态度相对客观一些,并未采取完全摒弃的极端做法。这是因为他认为,“灯史”之类的书籍,决不单单只是记载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宗教信仰传承的表达;与其说它们是被人写出来的,倒不如说它们是历史形成的产物。
因此,“在认真地研究这些被虚构的每一个记录的过程中,我们反而可以对那些虚构者们的历史社会的宗教本质得到明确的了解;与所谓的史实完全相异的另一层面的史实,难道就不可以从历史中洗涤出来吗?”柳田《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认为,灯史的虚构,“毕竟是灯史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方便和表达的偶然”。柳田对待“禅语录”,也是持这样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否定。柳田的这种方法论为马克瑞所继承。马克瑞在《中国禅宗史:虚构之上的真实》里所强调的“正因为是虚构,所以很重要”的所谓“马克瑞法则”,应该正是受到柳田圣山的影响,它们之间,可以说非常相似。
让我们先回到《北宗与初期禅的形成》(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这部马克瑞的博士论文。该书出版于1986年,以“北宗”(Northern School)为研究对象,以“初期禅”(Early Chan)作为审察时间段,从而与佛尔1984年出版的、探讨北宗的法文博士论文(该书以1997英译版最为学界熟知,名为《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一时构成禅史研究里的“北宗双壁”,倒转了被传统宗门灯史所扭曲的唐代禅宗发展面貌,在长达千余年历史里被“污名化”、被视为低劣和道德上有缺陷的北宗和神秀,经由佛尔和马克瑞这两位西方学人的努力,终于恢复了他们在禅宗学术里的应有地位。他们的工作可谓开创了禅宗史领域内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马克瑞:《北宗与初期禅的形成》(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
在这场颠覆性的学术努力里,马克瑞提出了许多意蕴深刻而负载巨大冲击性的命题。例如,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学者应该区分四种类型的禅宗材料:历史、传说、禅法和宣传,它们每一项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然而,如果我们混淆了它们的类型和性质,将会给我们的禅宗史理解带来严重扭曲,从而误将传说当成历史,将宣传性口号当作禅法思想的真实表达。此外,该书还彻底质疑了传统宗门里“南宗/北宗”“南顿/北渐”“《金刚经》/《楞伽经》”等固化命题,就北宗与顿悟思想的密切联系作了令人信服的证明。对《坛经》的作者,马克瑞也提出迥异时贤的看法,并对神秀和慧能的“呈心偈”作了饶有兴味的别解。当然,该书对北宗文献也进行了充分的整理,对学界贡献良多。关于《北宗与初期禅的形成》的学术影响力,凡此种种,汉语佛教学界已多有了解。马克瑞先生北宗研究余音颇密,该篇博士论文里还有不少崭新然而未及深论的命题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撰述里,尤其反映于其总结性杰作《中国禅宗史:虚构之上的真实》。因此之故,笔者在此想着重讨论这部总结性作品的创新之处,及其在日文、中文相关禅史研究里的地位和影响,供学界同行和读者们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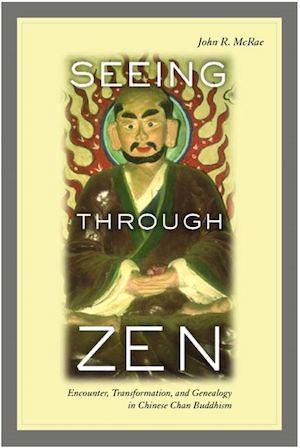
马克瑞:《中国禅宗史:虚构之上的真实》(Seeing Through Zen)
第一,新颖的禅宗史观。《中国禅宗史:虚构之上的真实》对中国禅宗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即原型禅、初期禅、中期禅和宋代禅,这种方法是以前未曾见到的。特别是,马克瑞并不像以前那样持“唐盛宋衰”的佛教史观,而恰恰相反,认为宋代禅是禅宗的成熟时期。这应该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的叙述重点是第四章至第六章,即放在了唐末至宋代的禅宗发展的形态上,作者认为,这个时期正是禅的形态开始确立的重要时期,而以前的研究对这一段时期的关注恰恰甚少。该书虽然没有直接批判柳田的观点,但对杜默林(Heinrich Dumoulin)在其禅史著作里过分理想化唐代禅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其实,柳田圣山“重唐轻宋”的态度更为明显。这也是马克瑞不同于柳田的地方。因此,本书的出版,对我们重新评价宋代禅将会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从经济史的角度注意唐末至宋初禅宗的发展情况。作者并不像前人那样特别重视《祖堂集》在唐末宋初时期禅宗史中的重要性,这也是本书的独到之处。作者这一观点主要反映在第五章中。柳田圣山重视《祖堂集》,是因为《祖堂集》为我们了解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禅宗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柳田忽略了《祖堂集》作为政府公认的文献的一面,即“禅法系谱”的官方性。马克瑞指出《祖堂集》成立的“官方性”背景,意在对目前国际禅学界重视《祖堂集》的倾向提出批评。
第三,“马克瑞法则”的重要性。特别是以下四点对我们研究禅史非常重要,时刻警醒我们切勿盲目地对待文献。这四条的具体内容是:因其非事实,反而更为重要;家系声明愈强烈,距离事实愈远;详尽意味着不透明;浪漫情怀孕育义愤精神。该书在国际禅史研究界产生的震撼效应最初是来自这四条旗帜性的颠覆命题,以至于人们一提到马克瑞乃至一提及禅史研究,就会想起“马克瑞禅学研究四法则”。用平常心来看待,这四条法则其实不过是对自胡适、柳田圣山迄今近百年来数代严肃禅史学者的研究,从方法论、理论命题和论述精神等层面加以提升、凝炼的结果。这四条原则贯穿于本书撰写的全过程,且对更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马克瑞自己的寄托更加高远,我们从序言中了解到,他认为本书撰写目的之一是“描述人类行为进程的类型”,那么这四条法则又可以视为“某种人类行为进程类型的法则”了。对这一点,读者当细心品味。
下面介绍一下本书日本版翻译出版的相关情况。在本书英文本出版九年后,日文版在马克瑞教授逝世后翌年(2012年)5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书名《虚構ゆえの真実—新中国禅宗史》,由东京大藏出版社出版。据日译版代表小川隆教授介绍,日文版的翻译比较特殊,当时马克瑞教授在东京大学讲学,时任该校教授的末木文美士先生在研究生课堂上以这本书作为教材,进行讲读,其实是让学生们翻译,同时请马克瑞教授参与指导,讲课过程中顺带将其译成日文。日文版就是这样在作者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译著,背景比较特殊。而且,一起参与翻译的,既有当时一起听课的研究生,也有像小川隆教授和前川亨教授(专修大学)这样的禅学专家。据小川隆教授说,这就是日文版未署译者名字的原因之所在。综合翻译任务分工,小川隆主译前三章和第五章,柳干康译第四章,前川亨译第六章,注释由前、柳二人负责,最后由小川隆担任统校任务。小川隆还特为撰写长篇《解说》作为日译版序言置于书首。在《解说》里,他对本书的学术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对未能赶在马克瑞教授在世时出版,表示遗憾和由衷的歉意。此外,小川隆先生还介绍了他与马克瑞教授关于本书出版前后的一些往来电子邮件,读来非常感人,从中也不难看出小川隆教授与马克瑞教授之间的深厚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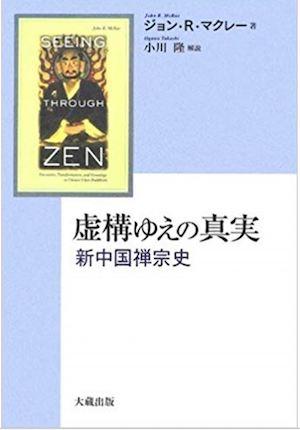
马克瑞:《虚構ゆえの真実――新中国禅宗史》,小川隆等译,大藏出版株式会社,2012年
日文版出版后,末木文美士教授撰写《唐宋禅研究への大胆な提言》的书评,该文除回顾日文版翻译的缘起外,还介绍了马克瑞在学生时代跟随耶鲁大学资深佛教学者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和柳田圣山学习佛学的经历,指出作者尽管在生活中贯彻其美国嬉皮士派性格,看上去比较自由、浪漫,但在学术上秉承的是严谨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和强烈的批判意识。末木教授还对各章的精彩内容进行介绍,认为该书是作者禅学研究的“一大总结”,是名副其实的收山之作,因此该书日文版的出版也是日本学术界的一大喜事。与此同时,末木也直言不讳指出,日文翻译中使用的一些词汇似欠考虑。末木教授还对日文版书名提出疑问,认为用“虚構ゆえの真実”(“虚构故真实”)来表达本书中所强调的“因其非事实,反而更为重要”的“马克瑞法则”过于严重了一点,似乎并未客观和恰当地表达马克瑞的观点,故而日文版书名值得商榷。我本人以为:与小川隆教授相比,末木教授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学术阅历上都与作者较为接近,对其观点的理解似乎更显理性。中文版译者将汉语书名定为《中国禅宗史:虚构之上的真实》,其实更切合马克瑞所欲表达的思想。
我与马克瑞教授第一次见面,具体是哪一年,已无从记起,不过回想起来,大约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当时马克瑞教授与其夫人那体慧(Jan Nattier)已经举家离开美国移居日本。马克瑞自己在东京大学和驹泽大学授课,那体慧是国际著名佛教文献学名家,时任创价大学的特聘教授,夫妇二人在日本拥有一份颇令人羡慕的安定生活。我们见面的地点大多是在东京,一般都是利用读书会和开会的机会。记忆中,我们一起参加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祖堂集》读书会”,一起多次参加过在日本和中国举行的各种学术研讨会;每次我去东京开会,会后我们一般都要与几位好友一起聚餐,举杯畅谈;我个人还曾受邀到东京八王子他的家里做客,等等。
马克瑞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典型的美国嬉皮士派性格,自由而不拘小节,领带多半是大红色,而且总是半系的状态。见到我,他有时总要用手指轻轻地弹一下我的肚子,告知我最近又胖了。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用中文做自我介绍,说自己的中文名字叫“马克瑞”,“马”是“马克思”的“马”,也是“马祖道一”的“马”,把我和站在旁边几位懂中文的日本学者逗得都捧腹大笑。附带提及的是,日本的同行学者平常都称马克瑞教授为“马老师”。“幽默而又和蔼可亲”这句话用在马克瑞教授身上是最贴切不过了。以我个人平常对马克瑞教授的观察,马克瑞教授似乎是一位一直与理想为伴的学者。追求自由,追逐理想,似乎是马克瑞教授对待人生的一贯态度。当初他为了陪同夫人,毅然放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终身教职,来到日本,似乎并不是为了一块面包。马克瑞教授对待人生的这种态度,令我望尘莫及,由衷地敬佩。

2010年5月5日摄于台北·政治大学后山某间茶屋。迎面左起:何燕生、马克瑞、那体慧
旧事历历萦绕心头,令我最为感怀的是我们在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期间的来往。记得地震发生的前几天,葛兆光教授应邀来东京大学举行学术演讲,我也去听了那次演讲。当晚,好友小川隆教授留我在他家住宿,他让我看了自己为本书日译本撰写的长篇《解说》,我则表达了将他刚出版并赠送与我的《语录的思想史》翻译为中文的想法,小川隆教授欣然同意。在3月12日与马克瑞教授的一封信中,我把此次东京之行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当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先生在信中诚恳地请我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并风趣地说道:“小川先生好像是负责日文版翻译的编修工作,以这种身份,他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序文。他一边表扬我的书,一边批评我的观点,他有不可思议的才能啊!”
收到马克瑞教授的信后,我感到既惊喜又惶恐不安。惊喜的是,他夸奖我将小川隆教授《语录的思想史》译成中文,并且邀请我担任他自己的书的译者之职,能够得到这位世界级学者的信任,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然而当时我已经承担了小川隆教授的《语录的思想史》的翻译工作,加上自己的英语水平有限,在时间上恐难得到保证,所以又感到不安。接到信后,我马上给他回了信,一来对他给予我的信任表达谢意,二来强调在时间上可能要拖延一段时日。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信,认为我是最理想的译者人选,并说道:“因为你有作为中国人的汉语能力,同时又通晓日本的禅学研究。如果你能承担下来,我将终生难忘,会感激你的!” 马克瑞教授对自己著作的爱护,从学问角度对我的信任,都令我对他更加敬佩,同时也打消了我的顾虑。
正当我准备给他回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同时正式向他表示愿意承担其大作的翻译工作时,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核泄露事故,我不得不离开福岛,举家避难。在之后的一段岁月里,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对自己的工作和家人充满担忧。即使后来局势趋稳,因为搬家及心理恢复原因,也无法正常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此时马克瑞教授已携夫人离开日本到泰国定居,却不幸被诊断出癌症。在此后的通信中,我们彼此安慰,却都没有心情提及译事。
始料不及的是,2011年10月23日那天,我同时收到几位友人的电子邮件,告知马克瑞教授逝世的消息。当时有如晴天霹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尽管我知道他得的是癌症,但没有想到死神来得如此之快。当时我正在国内参加“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非常巧合的是,此前一天有位来自新加坡的学生在车上向我请教一本英文的禅学著作,接过一看正是此书。在禅宗的发祥地听到这位禅学大家逝世的噩耗,而且在他逝世的之日,又让我重温他的这本大作,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然而与此同时,愧疚之感也油然而生:迄今未能践行所应允的翻译之责,而因此带来的自责和后悔之情一直持续到今天。
欣喜的是,他的这本收山之作目前已由禅宗史领域内优秀学者译成中文,并将于近期出版,从而可以告慰马克瑞教授的在天之灵。我相信这部由国外学者独立撰写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禅宗史》,将会给汉语学界带来全新的视角和学术上具有颠覆意义的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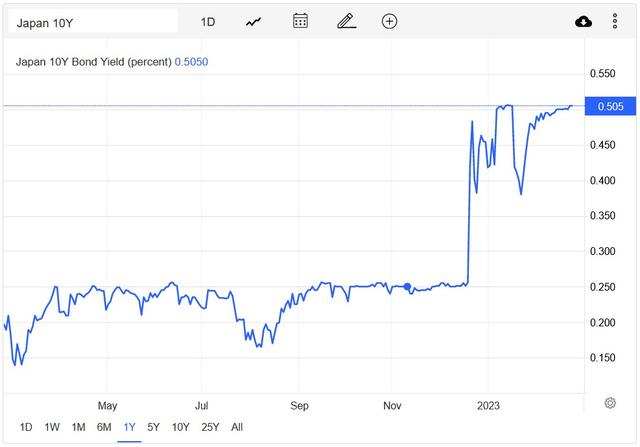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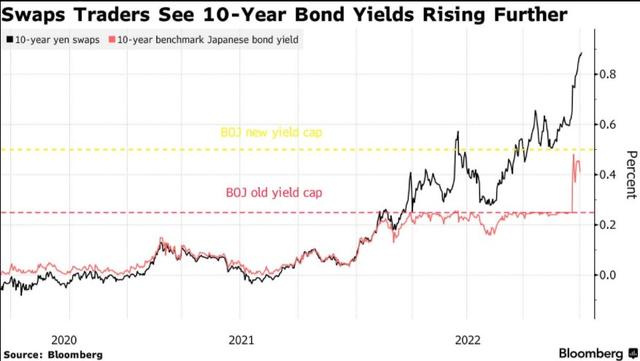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