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育儿,让我们面临什么
【专家视角】
作者:谢爱磊(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7月至8月,中央和各地方一系列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相继出台。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放开“三孩”的消息出来后,话题热度数月不减。参与讨论的年轻人都在问,到底“生不生”呢?生几个呢?

甘肃省昆仑幼儿园在儿童节成为一片热闹欢腾的海洋。侯崇慧摄/光明图片
低生育率让多国面临挑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显示,年轻父母们肯定还是生少了,统计显示,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总数的指标为1.3,而一般来讲,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不过,这在全球并不是个别现象。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回应——有效性如何?》的工作论文指出,全球的年轻人都生得比较少:在过去30年,世界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普遍下降,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越来越多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南欧、东南欧、东欧以及东亚的部分国家,生育率则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世界银行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为韩国(0.9),有八个国家或地区这一指标在1.2及以下,其中四个国家或地区在亚洲——除韩国外,还有我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新加坡。
研究人员指出总和生育率的极低(低于1.5)或超低(低于1.3)现象是全球生育率转型进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担心其会给公共财政、养老金体系、社会保障和卫生事业带来巨大压力。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生育率低的挑战,但“生不生”的确不只是个人“偏好”。年轻的父母们做出生育决定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影响。例如: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程度:个体往往视经济方面的安全、工作上的稳定为为人父母的重要先决条件;
社会危机:危机容易导致个体选择推迟婚育,导致生育率下降;
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
性别不平等:妇女仍然承担着大量家务,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容易导致低生育意愿;
买不起房:房价和供应情况影响着生育能力和意愿;
年青一代的家庭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宏观和微观因素有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存在的,但为何会在当代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深刻影响呢?这就牵涉年轻人在育儿观念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父辈们不同,现在的年轻人追求高质量育儿,而落实具体行动,就演化成一场高强度育儿。高质量与高强度的叠加,使育儿成为为人父母者的一件“艰巨任务”,使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2021年5月28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一家书店,家长与孩子们一起阅读图书。殷潮摄/光明图片摄
“父母决定论”与高强度育儿
在当代,“做父母”的社会意义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这代家长在观念层面大约比此前任何年代的家长都更加坚信“父母决定论”的观点——孩子所接受的养育的质量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生活面貌。各类家庭教育政策文本、无处不在的商业营销、耳提面命的老师和同样焦虑的其他家长也好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怎么养育孩子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在实践层面,一项数据更是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在美国,父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增长了两倍,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当然多了更多——她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仍是父亲的两倍。但请不要忘了,从世界范围看,女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刚刚获得稍平等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短短40年,新的育儿精神又在重新召唤着她们重返家庭的“战场”。研究指出,而今全职工作的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与上世纪70年代的全职妈妈几乎一样。另一项针对西方十一个富裕国家的比较研究甚至显示,2012年时,母亲们教孩子的平均时间较1965年长了一个小时。两项研究的共同指向是——全职工作的老母亲,既要主外又要主内。
高强度育儿已是我们这个年代主导的育儿模式。在过去,对于孩子能否在学业上获得成功,我们要么信奉个体决定论要么相信社会经济地位的力量。但在父母决定论的话语体系之下,一切转向子女的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养育质量意味着什么呢?花更长时间给孩子以高质量陪伴,最好能够与他们一起游戏、一起学习;还要把握机会系统地引导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要花时间与孩子讲道理,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投入金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必不可少,目的是创造机会学习课外知识;在学业的重要阶段,购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和购买专家咨询则是上佳选择。研究人员测算,在美国,从2000年至2010年,每个家庭花在孩子上的平均成本上升了40%之多;2015年,从呱呱坠地到17岁,每个美国家庭养育单个孩子的平均成本为233610美元——这还没有加上大学学费。按照澎湃新闻的报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口所发布的一份关于上海市中小学成绩变化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该市静安区,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每个家庭的总投入接近84万元,其中教育投入超过51万元,在闵行区,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6万元和52万元。
大约可以把当代父母育儿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做得好,那就做到了“高强度育儿”,做不好,那就是低强度育儿。父母都需立志成为最好的儿童发展专家,哪怕需要自学儿童心理发展知识,抑或再学一遍数理化。
目前的总体趋势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接受父母决定论,这是对儿童发展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转变——从社会学的解释过渡到道德的解释。道德解释的内在含义使我们认定,父母是否称职的依据变成了孩子发展得好与不好,对养育行为有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力争做全能的父母和为孩子创造美好的童年成了“好父母”的标准。英国广播公司曾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标题耸动:《坏父母的能力差距在扩大》。言下之意,父母质量如何影响着孩子的学习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儿童发展的道德解释和父母决定论显然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儿童福祉和生活机会的影响。儿童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发展受到许多结构性因素的(例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制约。
生还是不生?竞争性养育与低生育意愿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提及,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对育儿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它影响着父母们定义什么才是合适的养育方式。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亦指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开始并加剧。而在赢者通吃的社会,父母总是担心子女落后于人,希望孩子在很小时便赢得人生的主动权,为在社会上立足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研究指出,父母尤其是中上产阶层父母已然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社会学家埃伦瑞奇在《担心失败》一书中指出,中产的立身之本在于自身的专业化工作。但其不同于金钱和资产的占有,无法构成有效且有力社会排斥手段,除了投资教育,不断加码外,似乎别无他途。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后果之一便是中产阶层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过度关注,对他们的教育机会和成功变得高度紧张。
一言以蔽之,经济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群体的养育文化,正是逐步加深的经济不平等、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以及学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时代的养育实践为何更加“高强度”。假如教育系统高度分层且选拔性强,那么这个系统就更容易引发“育儿战争”。在一个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中,父母会更侧重教育帮助子女实现个人提升、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流动的功用,他们往往视子女教育为自己不可避免的责任,尽力想办法提供给子女适当的教育资源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取竞争力——即便资源投入和竞争力远超实际所需。
韩国的“教育热”现象曾被美国宾州大学的安德森(Anderson)和康乐(Konler)深入研究。他们指出由于韩国年轻人所处的经济环境在总体上竞争更加激烈,要获得一份高薪有保障的工作,进入韩国最负盛名的精英“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韩国大学和延世大学)变得至关重要。为了将孩子送进这三所高校,韩国的父母们也是百般武艺都用上,一般都会在孩子们正常上课时间后再安排他们参加课外补习,接受数学、写作、音乐、科学、英语等科目的额外培训。按照赛思(Seth)在《教育热:韩国的社会、政治以及教育追求》一书中的提法,送孩子参加课外培训已经成为韩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按照统计,到2009年时,就已经有超过75%的韩国儿童有过上课外补习班的经历。未能送子女上这些额外课程的父母甚至要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据说在韩国,说英语不单是一个别致的地位象征,更是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因此,“英语热”现象一直困扰着韩国,越来越多的韩国父亲将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送到英语国家学习,而自己则留在韩国工作,通常选择每年拜访妻子和儿女,自己则被称为候鸟父亲(goosefather),按照有关资料的统计,目前韩国总共有大约20万候鸟父亲。
在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下,父母通常认为孩子的成功反映的是父母而非孩子的努力程度,所以争相投入,让他们参加最好的补习班、英语课程或日托中心,对每个家庭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毕竟,孩子越多,能够给每个孩子的经济资源就越少,如此,孩子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安德森和康乐也留意到东亚剧烈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现象,并指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与欧洲地区不太一样,欧洲地区统计学意义上的生育率下降多是由青年人推迟婚育的行为所致,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其在他们婚育后还可得到部分弥补,但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一般无法挽回。在研究韩国个案时,他们使用韩国私立教育调查数据开展分析并验证了父母的教育负担与生育愿望,发现课外补习上的教育支出的确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关联,亦即前者的增加与后者的减少有关,花费更多的家庭倾向于要更少的孩子。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的工作报告也指出,在双职工家庭模式不断扩张,经济确定性低的情况下,“高强度育儿”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此,深入推进收入公平,降低教育系统的选拔和竞争性,通过减税等形式教育补贴,建设均衡高质量的公立教育系统支持儿童发展便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2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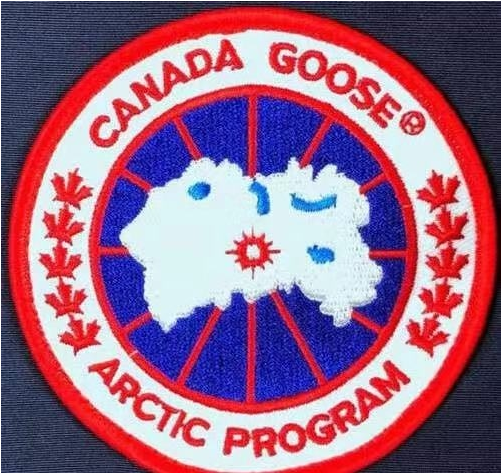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