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没有墙,但香港人有一堵心墙
作者 | 刘侃昱
编者按:格隆汇曾经分享过一个在香港工作了7年,最后放弃永久身份回国的会员张恒的原创文章,那篇文章被美国外交家杂志全文转载。这次是又一个略显悲伤的故事——在香港中环工作了近6年的格隆汇会员刘侃昱,把自己孩子重新转回内地读书。孩子代表未来,孩子回去了,他自己未来会不会留在香港,不得而知。但他对香港的分析、阐述,明显更接地气,更理性、客观,我们强烈推荐此文。
1
昨晚和太太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今年9月把儿子转回内地读书。
做这个决定不容易。因为不断转换环境,对孩子的适应和成长都是一种挑战。我和太太都在香港工作,但我们都是内地高考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尽管我们都很幸运地考上了一流的大学,但对内地那套填鸭式的应试教育体系并不认同。我们的理解,这种体制下教育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眼光与性格都是存有天然瑕疵的。所以在两年前儿子小学毕业时,我们把儿子从北京转到了香港。
儿子是个天生的阳光男孩,心地善良,帅气开朗,酷爱运动。在我们看来,这种性格的孩子,到哪里都会是受欢迎的对象,再加上儿子有很好的语言天赋,粤语很短时间就能日常表达和对话,从小练就的一口顺溜的美式英语更是让我们都自愧不如,所以我们从没有担心儿子融入的问题,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教学模式完全改变以后,他的成绩能不能跟得上。
但,恰恰是我们最不担心的融入问题,出了大问题。
这个问题,我和太太此前都遇到过。我们曾经在诸多场合遭受过不加掩饰的排斥与没来由的白眼,比如公司的香港同事、街上的出租车司机、百佳超市的收款员,甚至吉野家、美心、镛记的服务员,而原因只是因为我和太太都说普通话。我们尝试过学习粤语,但天资不够,对这种有9个音调的语言实在学不来。
香港这些年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再加上政治摩擦,媒体误导,香港人的心情并不愉快,整个社会徘徊停滞,戾气集聚,族群撕裂对峙,甚至盲目排外,逢中必反——这个“外”,这个“中”,明显包括了不会说粤语,只会说普通话和英语的我,虽然我一年缴的个税远远超过绝大多数港人,虽然再过两年我就是香港永久居民。
好在我是一个成年人,走过多个国家,经历过各种人和事,我有很好的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来适应这种“排斥”,所以我并不抱怨,哪怕大陆朋友聚会是经常批评香港在自己“作死”,我也都是莞尔一笑,勤勉解释:大一统的迷思(myth)要不得,要允许多元社会中少部分人对国家民族的不同理解。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多一个能说话的香港,不是坏事。
2
但我完全无法接受一个社会对一个11岁孩子的排斥。
他太小了,小到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分辨社会的善恶真假,更无法保护自己。这个社会展现在他眼里的一切,将对他未来的成长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如果社会是温暖的怀抱,这个孩子未来大概率也充满爱心。如果目光所及,皆是冷眼与排斥,这个孩子的内心能生长的,会是仇恨,还是迷惘?
我一直以为,“划界”、“排斥”只是成人世界的游戏,小孩家家的学校,断不可能如此,直到我亲身感受到。儿子是他们班里唯一的“大陆”学生,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那种“非我族类”的冷漠对待,来自老师明显的故意刁难,也来自同龄同学的集体排斥。这种自动划分界线的迷惑与苦恼,让原本开朗活泼的儿子一度变得敏感、沉闷甚至内向。儿子的连续倾诉与抱怨,我不以为然,并想当然以为只是换了环境后的不适应,因此我让他要做得足够谦虚,足够热情,主动去打成一片,主动去参加各类活动。
半年后,情况貌似有所好转,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儿子参加了Drama班,年级的足球班,积极承担班上的各类“辛苦活”,脸上的笑容也慢慢多了起来。但直到后来我亲自接触几件事后,我才明白,儿子脸上越来越少出现的偶尔笑容,那只是儿子迅速长大了,在努力自我调节,但环境其实并未改变,他一点也不快乐。
儿子酷爱足球,在北京也受过相当系统的训练,技术算有模有样。去香港后,足球班的各种训练,他从不拉下一节。我一直以为这个运动集体里,他融入是绝不会有问题的。直到有一次他们足球队踢训练赛,我突然好奇,陪着他去看看。在接近球场的时候,遇到一个胖胖的香港小孩,也与父亲一起过去。儿子说这是他们的队长,并非常热情地与对方打招呼。
我一直没能忘记那个香港小孩的反应和眼神:他异常冷淡地看了一眼儿子,根本不搭理,像没看见一样,满脸不屑地扭过头和自己的父亲说话,并一路不回头地走向球场。
儿子尴尬地冲我笑了笑。
我内心瞬间冲起一股凉凉的寒意:这个所谓的足球队长,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啊,他哪来那么大的仇恨啊?
到了球场,我能看得出儿子在努力“融入”:主动凑上前,和队员沟通,和教练沟通。但我也能清楚看得出其他队员看待儿子的异样眼神。他们基本都是看一眼,然后扭头自己一群凑一起说话,把儿子撇在一边——撇开的距离也许只有一米,但却无比清晰、刺眼。
儿子仍然积极参加了训练。及至开赛,被特意通知来参赛的儿子却被教练叫下了场——儿子很失落地一个人坐在了场边。中场休息,教练训话,儿子跳起来凑过去认真听着。下半场开赛,儿子依然不能上场。
这次,他异常落寞地坐在场边,不和我说话,并把脚上那双珍爱的红色足球鞋脱了下来。
那次直到终场,儿子也没有机会上场。我终于知道了儿子过去的抱怨不是年少矫情。
我和太太后来都很小心翼翼,不太敢直接问儿子有没有上场。这个周末我和太太回了北京,儿子则早早出发,独自去参加足球队的训练与比赛。晚上太太电话过香港,很隐晦地说,儿子你今天踢球辛苦了,自己早点睡吧。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憋住,很小声回答:妈妈,我今天还是没能上场。
我的眼泪一瞬间就下来了。
我陆续问了很多类似我们这样“内地生”的父母,他们也几乎都面临着相同的苦恼,也都在后悔把孩子转到香港就读。及至儿子的地理老师考试时因为莫须有的理由给了全班唯一一个孩子,也就是儿子,近乎羞辱性的10分的时候(我检查了试卷,卷面至少可得85分以上),我知道儿子面前横着的这堵墙,儿子自己是没有能力推掉的了。
是时候让他回北京了。我不需要高大上的所谓“国际视野”,我需要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孩子,立着一堵厚厚的墙的香港,给不了。
3
世上本没有墙,砌墙的人多了,墙也就起来了。
香港人经常自得于大陆很多墙,这不能说,那不能讲,还不能上Facebook,不能上Twitter,但他们没有发现,可怕不是有形的墙,而是无形的心墙。大陆人这不能说,那不能讲,但心里其实明镜一样的,而且他们会翻阅所有的墙,去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
而在香港这么多年,我能明显感受到,香港没有墙,但香港人自己有一堵厚厚的心墙。
过去一年多,环球经济过冬,中美还贸易摩擦,各主要股市表现都一般,都没太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周期现象而已,怎么去的,还会怎么回来。
但过去一段时间的各种冲击甚至骚乱,以及几大高校学生会就此事发表声明,“永远站在反抗者一方”,甚至网上传递香港国护照贴纸的做法,以及一些港独的发声,则真的让我感到了阵阵寒意。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突破所有家国底线的“为反而反”,当你把国家、民族的界线,与自己的所谓理念,甚至一时的心情好坏混为一谈的时候,这已经不是在排斥别人了,而是在放逐自己。
我在新加坡、台湾、大陆等几个主要的华人文化圈都呆过,都能适应。唯独香港,我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成人,都难以融入,都能时刻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固步自封与冰冷。
最近几年,我经常去深圳。香港和深圳实际上是一座城。所谓罗湖桥,就是一座不到100米的小桥,深港之间,很多地方就是一条小河沟,但被两边的铁丝网隔离。我见识过很多香港人,包括我在中环高级写字楼的高级白领,他们甚至从没有去过深圳,但对深圳(实际代表着内地)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和鄙视,说深圳社会治安多么坏,多么脏乱差。香港的普通旅馆不会有凤凰卫视台,香港报摊一般不发行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因为这些都是所谓的“大陆媒体”。
香港人在选择性地视听。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本没有墙,但很明显,香港人自己在砌一堵墙。
砌墙容易,推倒就很难。1961年修建的柏林墙,到30年后的1990年才拆除。即使拆除了,那堵墙留在历史和人们心头的阴影,可能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消除。
4
结语
最近网上看到一篇好文章,题目是《香港证监会,请收回发给老千公司的那把枪—兼与李小加商榷》,说的是香港证监当局不作为,放任老千公司横行。
文章是好文章,但很明显,作者在香港资本圈混的时间并不够长,或者说与香港证监会那帮人打的交道不够多,所以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子。
根子还是那堵无形的心墙,只是这次是傲慢自大的心墙。
李小加只是港交所的行政总裁,他定不了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香港证监会定的。李小加是内地背景,他还是很与时俱进和锐意进取的,问题的根子在香港证监会的那帮港英时期过渡来的“精英”。这帮所谓精英,都是港英时期过渡过来的,他们不是没看到问题,也不是不能作为,而是不愿作为,甚至故意不作为,这源于他们骨子里的那股傲慢,自大,以及对内地的歧视看不起。
他们觉得港英时期制定的规矩都是好的,回归后对这些做任何改变,都是向内地的示弱与妥协,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一种刻意对抗的刻意不作为,以把抱怨和屎盆都扣在回归的头上。这不是我故意耸人听闻,你去香港呆几年就懂了。在香港,说是法律完善,但法院法官八成以上是英国人,所以在香港有条不成文规则,打官司必须请英国律师,否则你的官司大概率会输。
所以,对老千股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不是小修小补,也不是没收老千公司手中的枪,而是拆墙:接管金融话事权和定价权。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今年春节期间,香港中环海滨没有墙遮挡的长廊上,绽放了25000朵LED白玫瑰花灯,在情人节到来之际点亮维港,营造浪漫温馨气氛——这样一个充满爱,没有墙的香港,或许,才是香港的本来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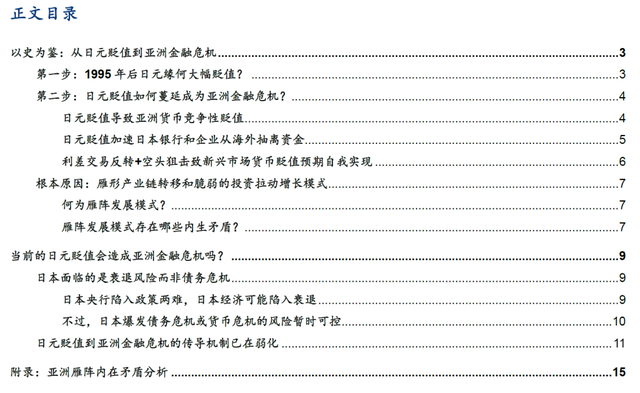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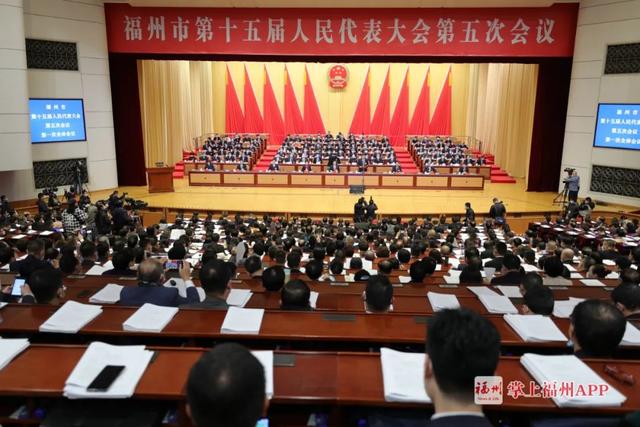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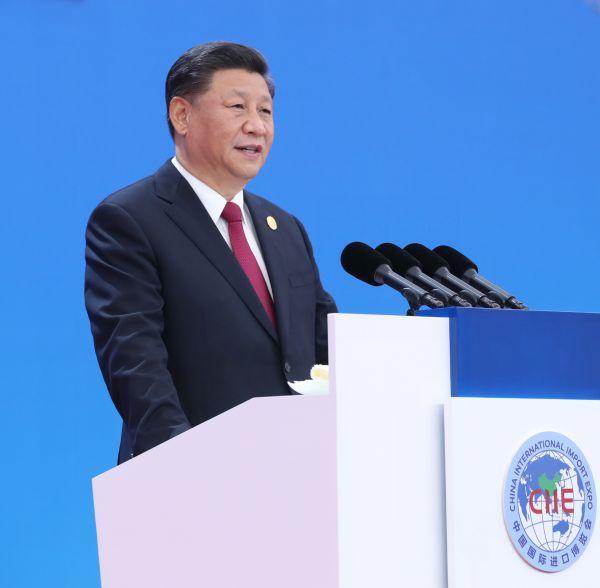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