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包弼德、邓小南、艾朗诺:中国“中古”研究意味着什么
3月8日,包弼德(Peter Bol)、邓小南、艾朗诺(Ronald Egan)三位中国“中古”研究专家齐聚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在中文系王昌伟教授主持的“中国‘中古’时期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展望中英文圆桌论坛”中进行对话。他们根据自己的专长,从史学、文学角度就中国中古时期研究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论坛伊始,王昌伟教授首先指出“中古”(Middle Period History)是一个近十年内才逐渐使用起来的概念,一般指从中晚唐到14世纪约6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学者一般将这6个世纪的中国史视为比较连贯的历程。对此,王昌伟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古史”意味着什么?把这段历史当作“连贯的历程”有意义吗?我们能从这段“连贯的历程”中得到什么益处?
包弼德:“始于唐宋变革的中古史何时结束?我不知道!”
包弼德教授指出,对于历史分期而言,朝代变化往往只能反映上层政治精英的变化,而思想、宗教、科技、社会结构、经济却未必同步变化,因此以朝代划分历史是存在不足的。一些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学者常常试图寻找哪一项变化可以代表中国的转变,而他关注的则是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包弼德认为,要从两个维度看待唐宋时代的历史:时间上朝代更替;空间上发生了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时空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持续发展,在南方建国的“十国”第一次使中国南方出现了多个区域中心。这一时期南方人口也愈发稠密,而南方密布的水路极大降低了商贸往来的成本。伴随经济成长,这一时期货币供应量成长了30倍、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地方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分离、税制也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也发生很大变化,科举制度使得知识取代出身成为支持向上流动的因素,以及道学取代佛学占据社会思潮主流等。
在包弼德看来,这些彼此相关的诸多因素使得中国“中古”史有别于前一时期,但中国中古史的下限为何?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

会议现场(严诗喆 摄)
邓小南:“中古史”与“中叶史”
邓小南教授首先谈及自己对“中古”一词的认识,她指出,西方学界对于“Middle Period”一词含括时段的理解有很大分歧。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中将其定义为750至1550年;2014年哈佛大学、2017年莱顿大学有关“Middle Period”的学术会议将其定义为800至1400年;而耶鲁大学明年将要举办的“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学术会议”中则将“Middle Period”定义为220年至1600年。在中国,有学者将Middle Period翻译为“中叶史”,不过很少有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放在“中叶史”的框架之下。但大家早已意识到依据朝代划分历史断限会阻碍对很多问题的深入理解,应该尽量从更长的时段去研究历史问题。
邓小南接下来简要介绍了近年中国“中古”研究议题的情况。宏观而论,该时段议题丰富,集中的关注点一方面在于“变动”,例如唐宋变革、宋元变革、元明变革;另一方面在于“秩序”,即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持、重构,历史人类学对于国家渗透下的社会、社会中的国家,有许多切实的讨论。在新议题方面,近年来,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相当重视历史书写、史料批判,因此出现了诸如《制造汉武帝》《制造“夷狄”》等著述;基于史料辨析的辽金史的再探,尤其对于契丹王朝早期政治史的研究,尽管观点不同,整体上有明显推进。民族史、环境史、疾病史、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等等也有相当多的讨论。除了新议题之外,有很多关于政治、制度等传统议题的再认识,例如日常政务运行、礼制、士人网络等等,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交叉互动,深化了相关讨论。近来的一些热门话题如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中央地方关系等,与当代全球化进程、国际格局、国家治理相关,使得一些过去有积累的领域蓬勃发展。而全球化更刺激了学者对“中国”概念进行研究,试图理解中古时期的人们如何认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
在邓小南看来,近年史籍资料整理有相当成果,如重新点校出版《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整理《全宋文》《全宋笔记》《宋会要辑稿》,分析《全宋诗》,而对于王安石、朱熹等人的著作、年谱也有新的整理研究。而郑振满、丁荷生整理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则是地方文献整理的代表。考古成果也对历史研究带来很大帮助,如对唐长安、辽上京、元上都的考古工作,对辽代帝陵、南宋六陵、吕祖谦等家族墓群的考察等,丰富了我们对于时代面貌的感知。考古发现的《徐谓礼文书》等出土文献以及墓志、家谱乃至图像资料等,都更加充分地运用到中古史的研究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青年学者对藏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等古老民族语言,以及梵文、佉卢文、波斯文等语文的学习与掌握,有效拓宽了研究视域,对历史研究的长远发展有根本性的帮助。
最后,邓小南指出,学界近年引入了《哈佛中国史》、日本《讲谈社中国史》等普及性的学术读物,提升了讨论交流的热度。而在各类机缘促进下,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开始关注宋代,《三联生活周刊》有关宋代的议题成为“爆款”,也是有趣的文化现象。
艾朗诺:“宋代的诗文书画是不应被分割的整体。”
站在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艾朗诺教授探讨来唐宋文学、艺术之间的异同,以及他对宋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艾朗诺指出,宋代出现了一个人擅长多种文学、艺术的现象,这在唐代是没有的——比如唐代诗人李白、杜甫、书法家颜真卿、怀素、画家阎立本、吴道子都只在自己的领域成就极高,但并不擅长其他文学、艺术形式。而在宋代,根据苏东坡的《书吴道子画后》可以看出:在他观念中诗、文、书、画有相当的关联,而这四种形式在唐代分别已经达到高峰,必须综合它们才能和唐人竞争。这种观念在宋代影响很大,当时许多人都把诗歌、书法、绘画甚至音乐放在一起看待。
在艾朗诺看来,宋代所出现的文学、艺术的“综合”在当今没有得到适当回应,今天的学者往往针对文学、艺术中的各领域分别研究,从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的整体性。他将此归类为两个原因:第一是研究方法不灵活、保守,“分门别类”的研究适用于不同文学、艺术种类距离较远的唐代,但应用到宋代时却没有及时调整;第二是现代学术专业划分导致学者为自己的领域限制,但如今诗学、词学、散文学、书画学的分类却不符合宋代文化产品的情况。
最后,艾朗诺还提及,宋代文人最有创造性的作品不是诗、文等地位较高的文体,而是地位比较低的笔记、题跋、书简、尺牍、杂文等等。但当今的文学选本、文学史书写都未对这些地位较低的文体予以足够的关注——这恰恰体现宋代人很灵活,我们现代人却很死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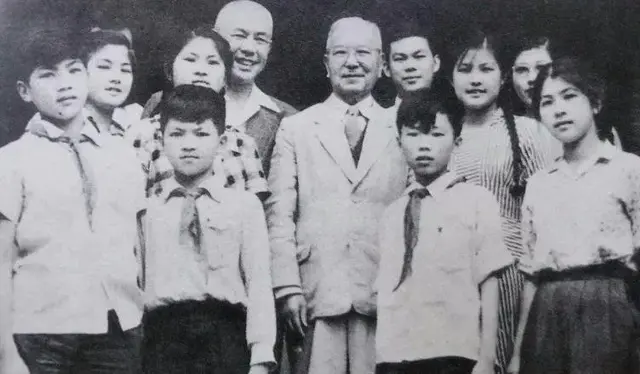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