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仲伟民:既除旧,且布新,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崔庆贺 整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特色的讨论越来越多。中国现代化是如何开始的?从什么时间开始的?经历了哪些曲折与进步?学界虽有不少研究,然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仍然认为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与必要。
近期,仲伟民教授在河南大学做了一场讲座,围绕上述问题,仲教授进行了精彩而细致的讲述,与河南大学师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本次讲座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翁有为教授主持。
仲伟民教授首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世界现代化有没有共性问题?第二,中国现代化有没有特殊性问题?仲教授认为,世界现代化大部分都是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世界现代化的共性,只有少数国家如新加坡例外。中国现代化也是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在具体发展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纵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仲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化过程被严重延误了。
关于延误,仲教授根据前人研究,发出了三个感叹。
第一个感叹来自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被延误的问题,罗氏归纳了学术界提出的两大观点,第一是外因论,即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教科书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基本分析框架。第二是内因论,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弱点,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传统—现代性”的对立是这种解释的分析框架。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第二个感叹来自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蒋氏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鸦片战争后“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现代化进程第一次被延误了。蒋氏说:“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第三个感叹来自李鸿章。李鸿章在1872年的《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仲教授问道:“李鸿章说的‘变局’到底是什么?”他的理解是:“变局”主要是指中西冲突发生后,原来的“天下观”彻底崩塌,即具象(天圆地方)和抽象(华夏中心)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易言之,意识形态的崩溃与文化自信的丧失。

李鸿章与日本明治首相伊藤博文
仲教授指出,直到甲午海战后,才陆续有人重新产生了类似李鸿章这样的看法,可是时间又过去了20多年!
言到此处,仲教授总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几次延误。
一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毫无知觉(比日本起步晚20年);
二误:洋务运动学习皮毛,成效甚微(比日本再晚10-20年);
三误:甲午战后激进维新,葬送改革(比日本再晚5-10年);
四误:清末新政有所改进,无力回天(比日本再晚5-10年);
五误:日军侵华,阻断中国和平发展(比日本再晚10年);
六误:……
中日比对,仲教授痛陈:中国现代化不仅被延误,而且被大大延误。
仲教授认为,现代化进程也是世界各国竞争的历史,如何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不断进步,是关键问题。他引用郭廷以《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之论述:要顺利进行现代化,首先是对环境与时代有正确的、深刻的认识。
由此,仲教授问,中国现代化进程被延误的主因是内因还是外因?他认为,外因论主要受到激进史学的影响,以“侵略—被侵略”为解释框架。内因论起源于马克斯·韦伯儒学有碍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费正清“挑战—应战”说直到当下的现代化理论是这一理论脉络。此派以“传统—现代性”对立为分析框架。

[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费正清、邓嗣禹著,陈少卿译:《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仲教授说,虽然外因论仍占主流,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内因更为关键,其解释框架更具合理性。
那么,造成中国现代化一误再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仲教授认为是中国知识的落伍,制度的落后,对世界局势认识的缺乏。
具体而言,中国直到19世纪关于世界的知识、科学的知识十分匮乏,更严重的是还盲目自信。仲教授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只有传统地理观(天圆地方、天下主义),而没有现代地理概念(七大洲、四大洋,地球是圆),他的知识与视野,决定其不可能参与地理大发现,不可能带领中国参与到波澜壮阔的15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制造万国来朝、我皇圣明的盛况,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到了清初,汤若望与杨光先关于历法的争论更说明中国科学知识、地理知识的匮乏。汤若望坚持以西方天文、地理知识制定新历法。杨光先则“无理气壮”,声言若大地是圆的,你们岂不是倒挂于墙壁,根本就不是人。
杨光先《不得已》云:“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种野蛮的自信与莫名的闭目塞听给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巨大障碍。
汤、杨二人的争论,被鳌拜干预,引发“康熙历狱”,汤若望、南怀仁被处分,与汤、南合作的中国人李祖白甚至被处死。鳌拜倒台后,南怀仁重算历法,“所言悉应”,而受到杨光先支持的吴明烜“所言悉不应”。杨光先因此被处分。
这反映出自宋代后,中国的天文、地理知识大大退步,至清朝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
仲教授回顾晚明历史,指出万历年间,利玛窦已经为中国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与徐光启
令仲教授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知识,却无人理解,更无人接受。“中国居天下之中”观念控制着中国人的大脑,利玛窦因此严厉批评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相比,中国传统的地理书基本上都以九州版图为限。但唯独王圻(1530-1615)《三才图会》中的《山海舆地全图》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绘制的唯一的一副比较准确的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地理卷先世界而亚洲,亚洲而中国,然后具体到各省、各府县,很接近近现代地理顺序。一般认为该图是依照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翻刻的,至少是受其影响的。

山海舆地全图
仲教授通过中日两国历史的对比,指出《坤舆万国全图》在江户幕府(1603—1867)前期被介绍到日本,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日本传统的“慕夏”观念发生根本动摇,不再崇拜中国。该图对日本的地理学也产生重要影响,后来日本发明的北极、南极、日本海、地中海等词也源于该图。
回溯“地圆说”的历史,该说于公元前6世纪由古希腊科学家提出,至15世纪欧洲人已坚信此说,并且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了环球航行的能力。大航海除了有传教、发财等追求外,证明“地圆学说”也是其内在动力。
反观郑和下西洋,还是以天下体系为观念,还是以万国来朝为目的。
东方航海以政治为目的,西方航海以科学为背景,以经济、探险为目的,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仲教授总结道:“大航海及其贸易、殖民的作用巨大,不仅把欧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而且把全世界联成一体,开启了真正全球化的时代。”
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国在知识与科学方面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中国人不仅对“中国中心论”的落后毫无知觉,即便在鸦片战争惨败之后,仍然毫无反思。因此,对世界形势毫无认识,不肯向西方学习。
对此,孟森批评:“至鸦片一案,则为清运告终之萌芽。盖是役也,为中国科学落后之试验,为中国无世界知识之试验,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才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
孟森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两三百年间,西方因地理大发现、经济大发展、科学大进步,已经确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与之相较,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则是假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而论,鸦片战争其实是这两种世界体系的冲突。
从16世纪到19世纪,支配中国人(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的仍是“天下国家观”“夷夏之大防”的理论或称思维定式。
在此情况下,即使到西方商人、传教士、外国使节频频东来叩击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人仍然视之为“藩属”,采取鄙视的态度和抚绥的策略。这迫使传教士不得不“自我中国化”,而后传教。
仲教授指出,造成中国现代化一再延误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中缺乏鼓励创新的机制。
仲教授在此引用蒋廷黻之言:“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仲教授说,蒋廷黻这里说的文化就是制度,是中国传统制度缺乏创新机制。
仲教授举洋务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郭嵩焘、李鸿章为例,说明此点。
郭嵩焘说:“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

郭嵩焘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认识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据仲教授分析,郭、李想表达的是,中国学习西方不只要学习坚船利炮,而且要改变守旧因循的制度,以制度创新催动技术创新,而非仅仅着眼于器物上的“师夷长技”。
顺此思路,李鸿章在戊戌变法中对改革派给予支持,且在康梁出逃海外时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梁启超1896年发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此文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后,总结道:“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然而,戊戌变法由于措施激进,瞬间失败,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与成效,算不上是一场现代化运动。
几年之后开始的清末新政虽有成效,然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仲教授如此分析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的历史:“从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20世纪初期的清末新政,守旧派之顽固,改革派之艰难,表面上是保守与开放问题,是人的观念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从本质上看,这是体制问题、文化问题,关键时刻成为现代化难以逾越的障碍。”
仲教授认为,正是由于传统体制与文化的问题,造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如奕䜣、郭嵩焘、李鸿章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
最后,仲教授总结道:“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证明,除旧而不布新,或布新而不除旧,都是行不通的;必须既除旧,且布新,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仲教授此讲座之部分观点,已表达于《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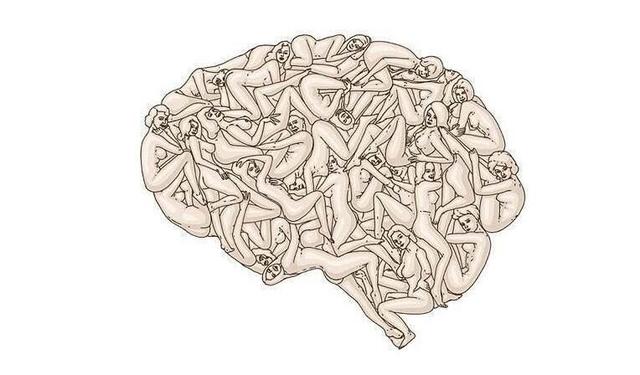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