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专访|殷正声:设计师引领部门合作的日本模式值得借鉴

殷正声教授,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后就职于日本东芝公司设计中心,1992年赴同济大学任教至今,从事艺术设计学专业,专长于工业设计、环境设计、城市设计等领域。殷正声教授还兼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业设计委员会、日本设计学会会员、原上海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先后担任过德国博朗工业设计竞赛、日本大阪国际设计竞赛、中国设计红星奖、中国十大青年设计师评选等大型赛事评委;主持过上海电动概念车、南京东路步行街、上海科技馆室内设计展示、上海世博会规划及场馆设计、上海轨道交通车站标识设计、杭州城市印象识别系统设计等重大项目。
作为“中日科技交流”项目、湖南大学工业设计研究班的第一期学员,殷正声教授回忆了当年参加研究班的过程,分享了参加研究班之Emden工作经历和后期赴日本进修的经历,指出在教育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素质教育基础上展开专业教育,是我们可以从日本教育中借鉴的东西。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许多日本大企业不仅有庞大的设计队伍,而且在公司战略层面上让设计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是让他受到很大启发。
《设计》:请您谈谈对研究班的回忆。
殷正声:在谈1982年日本吉岡道隆老师来湖大举办工业设计研究班之前,必须讲一讲这次活动产生的背景。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全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出访德国,他看到德国工业产品都设计得非常有品味,无论是造型、色彩、材料都震撼到了这位部长。他询问德方接待人员得知,德国企业拥有专职的工业设计师,这些设计师都受过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培训。他们自豪地说起世界工业设计教育得摇篮——包豪斯学校就产生在德国。它是由几位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所创建。回国后,主管教学的孙部长就开始筹建这个专业,当时大部分院校归各个部所辖,教育部管辖的学校只有师范类学校。孙部长查看了华中科技大学、哈工大、湖大等学校,认为湖南建筑较强,机械、材料、化工都齐全,因此决定在湖南筹建这个从未有过的新专业。
由于部里的决定和财经支持,1979年湖大成立了以建筑系五、六位老师为主,加上机械系、化工系以及引进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已在长沙轻学学校任职的老师与当时浙江美院等校的毕业生等组成了“机械产品造型设计研究室”,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系。
1979年,一机部发红头文件给下属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西安、重庆、长沙、武汉等地方仪表局从事产品开发的技术人员,每局分配到1~2个名额到湖南大学参加首届“仪表造型研究班”。学习班从198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我即当时的第一期学员之一。
由于是新办专业,课程基本上是美术、技术、表现、设计等各自为政的大杂烩。鉴于急需了解国际工业设计的现状,以及工业设计教学的课程体系。一机部孙部长通过科技部向邻国日本科技部提出了邀请日方专家来华授课的愿望。由政府对接,日本国际协力团(JICA)承办的“中日科技交流”项目于1982年正式启动,日方派遣了由筑波大学教授吉罔道隆和千叶大学讲师永田乔等组成的师资赴湖南大学合作举办工业设计研究班。
这次研究班主要是面向一机部所属学校的师资培训而办的,一开始我并不在其中,是与我一直有往来的湖大老师们打电话给我,要我赶快到长沙听日本专家的课,于是我特地请假,自费赴湖大插班听课。在学习中不仅认识了吉罔老师,还有幸结实了吉罔老师的太太,他俩对我的作品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并鼓励我到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后,我马上打了辞职报告,无奈那个年代,辞职非常困难,特别是工作努力、专业能力强的。经过三年多的不断游说与努力,终于在1986年得到单位同意。拿到盖有红色公章的辞职信后,我赶快附上吉冈老师的太太帮我申请到的赴日留学许可书和签有吉岡道隆老师大名的担保书,才得以用自费公派(由于我被破格评为工程师,讲师以上人员哪怕自费也必须公派)的形式,继很多学校公费派出访问学者后,以留学生身份在日本攻读工业设计专业的研究生。
《设计》:您在进入研究班之前是在从事什么工作?
殷正声:参加研究班之前,我已经是一名工业设计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当时中国仪表行业数一、数二的大型国企——上海电表厂的设计科从事新产品的结构与外型设计。
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城市。1843年,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正式开埠,外国列强在上海划定租界;设立码头,搞贸易;开发城市,搞建设;建立工厂,搞工业;建设街道,搞商业;开办银行,搞金融⋯⋯。三十年代时,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现代设计也应运而生,领先亚洲。张光宇曾在这里设计家具,庞薰琹曾在这里设计广告⋯⋯解放以后,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上海的花布、床单等纺织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轻工业品;收音机、唱片机等家用电器;日用生活用品等都是全国追捧的产品,一票难求。所以这些民用产品生产厂商里一直有专业设计师的存在。
《设计》:研究班的学习经历对您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殷正声:从研究班回上海不久,我被仪表局—— 一个十万人规模的大型国企管理局借调到科技处工作,工作内容一是主持上海工业展览会中仪表局的各种展示策划与设计及落实,二是领导仪表局里跨厂的工业设计小组的活动。
研究班回来不久,我就邀请湖南大学工业设计系到上海来,为仪表局辖下各个工厂的设计师们举办短训班,由于局长的支持,学习班开办很顺利。当时参加短训班的有蜚声全国的“飞跃”、“凯歌”等品牌电视机生产厂家的设计师,有一票难求的“红灯”、“海燕”等品牌收音机生产厂家的设计师,有新兴的半导体收录机生产厂家的设计师等。不仅有民用产品生产厂家的人员,更有计算机、医疗器械,电子产品等新兴企业的有关外型与结构的设计师们的参加。
研究班对我最大的影响当数促成我赴日留学。无论在千叶大学的学习和毕业后在日本东芝设计中心的工作,我都受到吉岡道隆恩师的介绍与关照。我也一直以我学到的设计方法和在实战中掌握的设计能力让日本共事的设计师刮目相看。回国后,更让我在同济大学设计学专业大展拳脚,对学校设计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设计》:在您的留日经历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地方?
殷正声:日本的素质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初到日本,繁华的商业、车水马龙的交通,外观漂亮的产品都给了我震撼的感觉。今天,随着我国硬件的发展,这些记忆慢慢淡去,唯有日本人的“软件”——素质教育仍让我感叹!不同于新加坡的法制建设,日本人从小养成不乱扔垃圾的习惯,在银座、新宿等大马路上你几乎找不到垃圾桶,人们习惯带个小塑料袋收纳自己的垃圾带回家处理。乘地铁,人一多时即自动排队,从不抢座,从不在车厢吃东西及喧哗。读小学、中学每人一样的制服,冬天里,男孩短裤,女孩短裙;普遍喜欢各种运动。学生中,大家有各自的爱好,没有人会因为数、理论、英语好而傲视大家。我在千叶大学读书时发现,设计系的学生,考前就非常了解设计,有些人从小喜欢设计。上大学时,设计概论、设计史类的课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更专业一点而已。
教育普及是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日本,我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学校,无论是大都市东京、大阪还是冲绳、北海道等小地方,学校的教学质量都差不多,学校里的审美教育、品味教育课程很多,如日本有“家政大学”、“女子学院”和众多时尚、素质培养的专门学院;还有大学里设有“教养专业”、“文化修养”专业等可见一斑。成人后,女孩的打扮、男孩的穿着都彰显了日本大众的品味。审美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换,简单而有内涵,价廉但有品味,小型环保而又不浪费的价值观是日本大众的追求,“优衣库”、“无印良品”等无不是这些理念的体现。这些非高科技类的服务设计却创造了高于科技类产业的产值。
我国的设计教育,湖大、清华、同济等在全球的排位都不低,水平确实也很高,但国内的设计教育两极分化严重,一些学校离国际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在教育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素质教育基础上展开专业教育,这是我们可以从日本教育中借鉴的东西。
《设计》:日本设计教育体系是否也经历了学习西方,以为自用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中国最应该从日本学习哪些方面?
殷正声:日本的设计教育始于明治维新(1868)年,距今一百五十年之前就有留学生到海外学习,也邀请了一些外国设计师到日本讲课。但日本现代设计的正式发展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著名建筑大师除丹下健之外,桢文彦、隈研吾,黑川纪章等都曾在美国留学,安藤忠雄在欧洲留学七年后成才。东京的近代美术馆是请柯布西耶作的设计,东京帝国饭店从建筑到室内设计都是请赖特设计的,今天在横滨保存和移建了很多近现代西洋式建筑,被称为“明治村”。在工业设计方面,1982年在湖大演讲的吉岡道隆教授就是战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课程,毕业后回日本千叶大学任教的。吉冈老师1962年成为千叶大学的教授,由于当时千叶大学的工业设计专业在日本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很多学生或在企业担任要职,或在日本各大学成为骨干。吉冈先生还多次应欧、美、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邀请讲学而蜚声国内外。
在日本的城市规划、建筑、工业、商业都能发现设计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许多大企业不仅有庞大的设计队伍,而且在公司战略层面上让设计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在日本信息产业省(相当中国的信息产业部)专门设置了“工业设计课”用来制定和指导工业设计的产业政策;丰田、日产的大企业的副总都是学设计出身而又学习了管理的人担任;很多大企业的生活研究、战略设计由社长直接领导,凌驾于技术部门之上。交通、城市建筑往往是采取以设计师为引领,技术工程、材料等部门一起合作的模式,这是我国必须学习的。因为技术、工程等是手段,设计是为了“不忘初心”,是为了目的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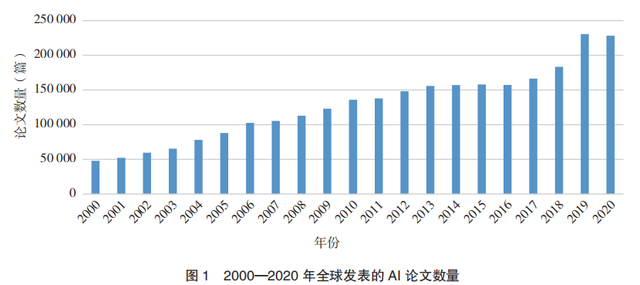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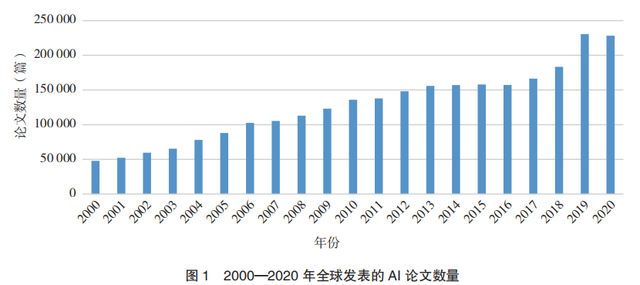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