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炳坤:跨境破产中的司法协助与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破产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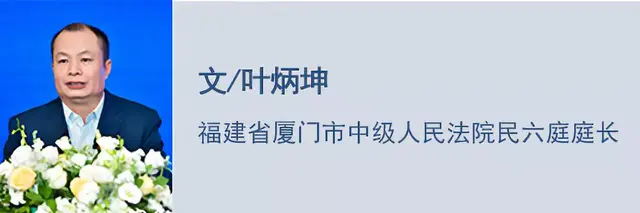
注:原文发表于李曙光、刘延岭主编《破产法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为方便阅读略有删改。
本文共计22,559字,建议阅读时间45分钟
一、问题的提出:本国债权人保护问题在跨境破产中的地位、现象与成因
跨境企业破产[1]中,本国债权人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一国法院裁量、决定是否给予某一外国破产程序必要司法协助的过程中往往起到关键和决定作用,也因此往往成为对抗、拒绝对外国破产程序提供司法协助的主要理由和借口。历史上,跨境破产的司法协助问题曾长期难以获得进展,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即在于各国法院难以平衡对待和处理本国债权人与境外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跨境破产中,承认债务人在外国启动的破产程序在本国的效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为外国破产程序提供冻结债务人在本国的财产、停止(中止)通过对债务人的诉讼、执行进等各种司法协助,无疑将阻却本国债权人对债务人实现个别求偿;而将破产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移交给外国破产程序、归入境外破产程序中进行处置和分配,则意味着这些财产完全脱离本国法律、法院的控制,本国债权人的债权将完全置于外国破产程序和外国破产法律的管领之下。因此,这些司法协助措施的给予与否,均紧密攸关本国债权人的利益。出于保护本国债权人权益、节约本国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成本等目的和对外国破产程序、制度能否公平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的顾虑,各国对为外国破产程序提供司法协助,特别是将破产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这一“手中之鸟”[2]移交予境外管理人控制、处置并由其在所有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或用于外国债务人企业的重整拯救一直心存芥蒂[3]。这也成了阻碍跨境破产案件及时获得相关外国、地区法院司法协助的主要障碍。可以说,如果没了本国债权人保护问题,跨境破产就不会面临这么多复杂问题,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在其发展中也不必经历如此多的障碍和坎坷。
跨境破产司法协助中本国债权人保护的成因主要有经济和法律两方面:1.经济上,债务人企业财产和负债在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分布不均衡。伴随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发展,同一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存有财产、业务或为拓展经营、便于管理甚至避税需要而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形十分普遍。由于企业在各个国家、地区的业务经营情况各不相同、其设立分支机构的目的亦均不尽相同,因此,企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保有的财产、业务、分支机构财产价值与其在当地所负债务也存在普遍的不均衡现象。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这一财产与负债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位于各个国家、地区的债权人从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业务中受偿几率和比例的不平均。2.各国家、地区间破产和相关法律制度仍存在差异。各国家、地区的破产法律与本国的历史法律传统、经济发展、社会情况等客观因素密不可分,直接造成各国破产制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如破产重整制度的有无、破产清算与重整制度在具体制度上的差异、破产债权清偿顺位差异、担保债权的优先保护程度、破产具体制度如抵销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等均可直接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比例造成重大影响。3.国际上对跨境破产的司法协助规则尚不一致。迄今为止,除欧盟制定了统一的跨境破产协助规则外,对外国破产程序的司法协助问题,仍属于各国国内法范畴。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法律传统、历史发展、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所处的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对跨境破产的司法协助的态度、原则和制度均存在一定差异。理论上,主要存在地域主义(Territorialism,又称属地主义)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主要区分,并由此衍生出合作的地域主义(Corporative Territorialism)、有限普遍主义(Modified Universalism)等。普遍主义则由于其在“一个债务人、一个程序”下倡导各国对跨境破产程序几乎无条件、无保留的承认与协助,在全球破产制度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基于对本国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目前实践中没有任何国家采取这一原则。
本国债权人保护之所以成为各国法院为外国破产程序提供司法协助的主要考量因素,主要出于本国债权人在外国破产程序中存在的法律、经济与费用、信息和机会等诸多方面成本的不平衡:1.法律成本。首先,单一破产程序下,各国破产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本国债权人无法在外国破产程序中获得与本国法律下等同的待遇和保护,其在本国法律下本能够获得保护的权益可能遭受损害。这点在税收、劳动、担保债权等较为明显。此外,一些国家破产法律制度中存在对本国与外国债权人的差别性、歧视性规定,则更直接损害本国债权人的利益。其次,跨境破产重整程序中,外国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业务可能被在外国重整程序出售并以所得资金用于向所有债权人进行清偿或直接用于债务人在境外的继续经营所需资金。相较于依照本国破产法对债务人进行清算,本国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和数额大幅降低,甚至落空。第三,平行破产程序下,各国对本国破产程序下分配顺位、分配原则、担保权利的保护等差异可能导致彼此程序中的分配比例不一致,在国际社会尚未建立一个统一的分配限制原则的情况下,本国债权人也可能蒙受利益上的损失。2.经济上,本国债权人在外国程序中将不得不付出多余的“客场成本”,不得不增加相关的法律、财务服务等费用,甚至由于对外国破产及相关法律的不了解而丧失本可获得保护的部分权益。3.信息方面,本国债权人对在外国进行的破产程序所能获得的信息与破产程序的当地债权人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不得不由于这种信息不充分、不对称而付出远高于后者的成本。4.法律、信息上的劣势也迫使本国债权人不得不承担更多机会成本。本国债权人在外国破产程序的参与机会和获取的信息造成其在外国破产程序中的判断和表决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情形做出的,这种在不够充分的条件下作出的判断和表决直接降低了其在外国破产程序中获取与债务人、管理人、债权人的交易机会,增加了其成本,损害了其利益。
二、跨境破产司法协助中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措施与努力
为在跨境破产中尽可能保护本国债权人,各国均尽可能通过在国内法上建立适当的制度、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将债务人在本国的财产留于本国控制之下、适用本国法律、清偿本国债权。但是,过度强调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而忽略对外国破产程序的司法礼让与协作,无疑将导致国际社会间彼此的司法报复。而各国在这一领域内均采取与邻为壑、相互报复的最终结果,是伤害国际投资、贸易、金融领域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并因此妨碍国际投资、贸易的发展。因此,在跨境破产发展中,两方面的努力贯穿其始终:一方面,国际社会始终努力寻求为跨境破产建立一个能获得广泛接受的、可行的司法协作制度;另一方面,各国则均力求尽可能地在跨境破产中维护、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两者之间的博弈和彼此消长最终的结果是,有限普遍原则跨境破产司法协作逐渐得到接受,而各国亦逐渐将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限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限度内。
(一)国内法的解决路径。
为在跨境破产中维护本国债权人利益,各国在国内法中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1.采用严格的地域主义原则,排斥所有外国破产程序在本国的效力。
地域主义原则主张,破产程序的效力仅及于该程序所在国家内的财产[4]。因此,其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在本国的效力,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只能用于向本国债权人进行清偿,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保护本国债权人的做法[5]。破产法发展史上,在国际投资、贸易尚不发达、国际破产司法协作需求尚不那么迫切时,曾有不少国家、地区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采取这一做法。但是,这一做法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地域主义原则在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在本国效力的同时,也限制了本国破产程序在外国的效力,本国债权人也将丧失针对债务人在境外的财产进行求偿的机会;二是直接导致了本国债权人与外国债权人之间的不平等[6],并因此招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等报复,导致本国债权人在境外的债权无法获得保护;三是在整体上降低了对债务人企业的破产清算效率,并消除了跨境重整的可能性[7]。四是直接影响和降低了本国对境外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的吸引力。
基于上述原因,目前,大多数国家已逐渐摒弃这一原则。一些国家在坚持地域主义的基础上,揉入对跨境破产较为积极的协作态度,允许针对同一债权人在各个国家、地区间启动的各个破产程序通过条约、公约等方式进行协助和协作[8],即“合作的地域主义原则”。但是,由于这一做法仍以地域主义为其前提和基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域主义存在的上述问题和弊端[9],尤其是对本国债权人过度、极端的保护而带来的不公平保护和影响跨境破产效率、消除跨境重整可能性等问题,其成效仍十分有限[10]。
2.在本国法律中制定“围栅条款”(Ring Fence Articles)或规定本国与外国债权人在本国破产程序中的差别待遇。
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债权人的利益,在国内公司法、破产法等相关法律中规定,外国公司位于本国的财产,必须先行清偿其在本国所负债务,只有在全部清偿后仍有剩余的,才可用于对国外债权人的债务或移交外国破产程序进行处置、清偿,即所谓“围栅条款”。这一做法目前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等[11]仍继续存在。我国《公司法》第197条[12]中对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规定虽未涉及破产制度,但也影绰可见这一思维。有的国家则干脆直接在其破产法律中规定对本国债权人与外国债权人的差别待遇,对外国债权人采取歧视性、差异性待遇。很明显,这种做法也极易招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等报复,其破产程序难以在其他国家、地区获得必要的协助与协作。
3.扩大本国法院对外国公司的破产管辖权,以本国债权人的利益作为行使对外国公司破产管辖权的依据。
与地域主义消极对待外国破产程序不同,一些国家反其道而行、采取积极措施,以本国债权人利益为标准设定本国法院对外国公司的破产管辖权,将存在本国债权人利益因素的外国公司破产案件置于本国法院管辖之下以维护本国债权人利益。在这点上,以英格兰及其具有相同普通法渊源的国家和地区较为典型。他们主张,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并不意味着本国法院放弃对同一债务人启动、继续平行破产清算程序的权力,本国法院仍有权按本国破产法律启动、推动这一程序并控制债务人在本国的财产[13]。其主要做法是:在成文法授予法院对外国公司(Unregistered Company)享有破产管辖权的基础上,由法院在普通法中设定其对外国公司行使破产管辖权的三个条件:(1)该公司与法院地存在适当联系[14],这一联系并不仅限于该债务人在法院地存在财产[15];(2)启动本国破产程序对债权人而言具有合理的可能利益[16];(3)法院对一个或若干在财产分配中具有权益的人享有管辖权[17]。显而易见,上述管辖权基本上建立在对本国债权人保护的基础上。
4.允许本国法院对外国债务人启动从属程序,就债务人在本国的财产、债务进行清理、清偿。
无限制地以本国债权人利益为依据扩张本国法院对外国公司的破产管辖权,无疑将引起各国法院的管辖权竞赛,司法管辖权和破产程序之间的纷争将导致跨境破产无法在国际私法领域建立一个较为一致的管辖权规则,直接破坏各国对企业破产管辖的基础规则,司法礼让和协作更无从谈起。为避免上述问题,一些国家退而求其次,在认可公司破产的注册地或“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COMI)管辖标准的基础上,允许本国法院依据申请启动从属破产程序(Ancillary Insolvency Proceeding)对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业务、分支机构和债权进行清理。以英国为例,尽管该国允许法院行使对外国公司的宽泛管辖权,在国际传统规则上,则对在公司注册地启动的外国破产程序及破产程序代表(如管理人等)的权力予以承认[18]。然而,这一承认并不妨碍法院对同一债务人启动破产程序[19],只是,这一破产程序被限制为外国主要程序的从属程序,该程序中指定的管理人权力也仅限于外国公司在本国范围内的财产、证据和债权等[20],且只能为清算程序。尽管这一做法自1880年起即已产生,但普通法学者仍认为,这一领域实际上是完全依赖由法院对个案情形做出的自由裁量构成的判例法,很难对其作出准确的界定和归纳[21]。
从效果上说,从属程序在有利于充分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之外,对跨境破产程序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在欠缺统一的普遍协助原则的现实条件下,一国的破产程序并不必然为外国所承认。通过在债务人存在财产、业务和分支机构的国家和地区启动从属破产程序,有利于及时中止在这一国家和地区针对债务人的诉讼和针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和执行,尽快将债务人的财产、业务等及时置于从属程序指定的管理人控制之下;其次,从属程序中法院一般指定本国破产执业人员担任从属程序的管理人,其对本国破产法律及相关法律较为熟悉、了解,也有利于及时处理相关法律问题,提升破产效率;第三,在本国从属程序管理人的努力下,债务人可能与本国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重组等,解决债务人位于本国的债务问题。正由于此,欧盟在制定破产规则时,对从属破产程序这一做法予以了保留,但对其适用条件、效力范围、程序种类及其与主破产程序之间的协作配合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是,从属程序的根本出发点毕竟仍在于保护本国债权人,其不可避免在诸多方面与主程序存在一定冲突:首先,两者在利益上存在根本冲突:从主破产程序的角度来说,其在利益上是尽可能维护公司的财产、业务的整体性以维持破产企业价值的整体效应,以求最大化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对从属程序而言,其目的则在于尽快实现本国债权人的债权,停止债务人在本国的营业、处置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财产和业务,以维护本国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因此,尽管在许多国家均要求从属程序应当尽可能地与主程序保持和谐[22],这一冲突始终无法避免,特别是在一些大规模的跨境企业重整案件案件中,主、从程序之间的上述矛盾和协调往往增加了重整的复杂程度,给企业的整体重整造成极大障碍,甚至导致重整失败[23]。其次,从属破产程序只能是清算程序,难以满足跨境企业重整的需要。对此,有学者指出,由于在英国和欧盟法中从属程序只能是清算程序,导致该程序中的管理人根本无法满足重整程序中维系企业经营的需要[24],通过司法协助的方式才是有利于跨境重整的最佳措施之一[25]。 第三,各国法院在启动从属破产程序时往往存在大量裁量性因素,这也给从属破产程序带来不确定性。以英国为例,普通法上,是否对一家外国公司启动从属破产程序,其管辖依据与启动对外国公司的破产程序并无差异[26],这一决定完全有赖于法官对个案情形的自由裁量。而且,即使在上述要求均满足的情况下,法院仍有权决定不启动从属破产程序[27]。因此,迄今为止,学界仍几乎无法为这一程序的启动归纳出具体、明确的考量因素和标准[28]。此外,英国法院还认为,如果它认为英国比外国法院更为适宜管辖债务人企业的破产案件[29]或者外国破产程序中对英国债权人存在歧视性待遇[30],其有权决定在这一破产程序不再从属于外国破产程序[31]而成为主程序,并在英国法下享有全球性效力[32],则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第四,从属破产程序将引致更多的法律冲突问题。一般认为,从属程序在破产法和实体法律上均应适用法院地法[33]。由于各国对破产撤销权[34]、优先权等方面存在的法律差异,无疑将造成主程序与从属程序在适用法律上的冲突,从而有利于本国债权人而不利于外国债权人。第五,从属程序将增加破产成本。特别是在一些破产管理费用较高的国家,从属破产程序产生的破产费用甚至常高于主程序的费用,加之主、从程序间管理人的冲突、沟通和协调造成的时间和成本浪费[35],将极大增加破产的效率和金钱成本。最后,由于管辖规则的差异,将造成从属程序“从属于谁”难以确定的问题。在企业破产主程序的管辖和认定规则上,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以公司注册地为标准的传统管辖规则和以公司主要利益中心地(COMI)为标准的现代管辖规则,还有一些国家则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管辖规则:如英国,对欧盟国家采用后者,而对欧盟之外的国家在普通法上则仍采纳前者[36]。一旦公司的注册地与其主要利益中心分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并且在上述两者均已启动对企业的破产程序,从属程序究竟应当从属、配合于哪一程序,则将成为一个法律难题。实际上,基于管理、避税等方面的需要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个企业的注册地与其实际管理中心所在地相脱离的现象如今已十分普遍,这一问题也日益成为从属破产程序中不断发生争议的问题之一。
5.以本国债权人利益为主要衡量因素审查确定是否给予外国破产程序司法协助。
除了在本国法内基于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而尽量扩充本国对外国企业的破产管辖权、允许本国法院启动对外国企业程序控制之下,更好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之外,在决定是否给予外国破产程序所请求的司法协助中,各国也均将本国债权人的保护置于决定性的地位。当然,基于在本国启动的破产程序也将可能面临在他国的协助问题,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往往需要为本国债权人利益采取一个较为隐蔽和正当的“外壳”,以尽量使其符合国际礼让原则和要求。
一般来说,对外国破产程序提供司法协助以本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为前提。国际上,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通常要求外国程序至少必须符合三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启动破产程序的外国法院具有相应的管辖权;二是外国破产程序不得违反本国公共政策;三是外国程序是一个适格的“破产程序”。在外国法院管辖权的问题上,由于对外国法院的管辖认定在国际私法及破产管辖两方面的规则中已经较为明确,因此,基于这一问题产生的对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及其不确定性空间也较小。公共政策问题则涉及各国法院对公共政策范围的理解与认识,其范围大小客观上往往也影响了其对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范围。对此,下文中将有较为详细的讨论。国际破产司法协助实践中,与本国债权人保护相关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三方面,即外国程序的适格性问题。由于各国在破产法律上至少存在三方面差异:一是范围差异,各国对破产程序的概念和范围存在不同理解。有的国家将公司清算也视为破产程序的种类之一;有的国家则将破产程序的范围严格限制于因资不抵债或丧失清偿能力而启动的公司清算、重整等程序;此外,还一些国家存在一些独特的程序,如英国法上的管理清收(Administrative Receivership)、债权和解制度(Scheme of Arrangement)[37]等,是否可以被归入“破产程序”,均存在一定争议。二是法律体系差异,各国的破产程序和法律制度并不完全规定于单行的破产法中。如,有的国家为破产制定了单行的破产法典;有的国家将公司破产、清算等制度区别于个人破产制度,规定于公司法中;有的国家甚至并不制定单行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破产制度散见于公司法和其他法律中。三是具体破产制度和程序的差异,各国对企业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有些国家至今尚未建立企业重整制度。即使在重整制度下,也存在美国的债务人管理(DIP)模式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管理人管理(AIP)模式和混合管理模式的差异。同时,各国在破产保护期间(Moratoriums)、破产管理(Administration)等具体破产制度上也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各国在破产法律制度上存在的上述差异,在判定一个外国程序是否是一个“适格的破产程序”时,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因素就往往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以本国法律制度为衡量标准,不仅有利于本国债权人对法律更为了解,还可以摈除由于破产法律制度的差异所可能给本国债权人带来的潜在危害。为此,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本国破产法律制度为标准衡量外国程序是否是一个适格的破产程序,并据此确定是否给予承认和协助。较为典型者如英国普通法认为,外国法院除了依据“破产法”享有与英国法院相似的管辖权外[38],请求的事项还必须是与“破产法”有关[39]。至于所谓“破产法”的范围,该国在Hughes[40]一案中则直接做出了十分狭隘的限定,即仅指该国的《破产法》(当时是1986年《破产法》)[41]。严格据此,不仅美国的破产重整程序难以被认定为“适格破产程序”(其时1986年英国《破产法》尚未规定破产重整程序),即便是如与规定于该国公司法中的债权和解程序(Scheme of Arrangement)相类似、广泛存在于英国为首的普通法系国家中的程序也难以被认定为适格破产程序而获得承认和协助[42]。
即便外国程序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得以进入是否给予司法协助的下一阶段具体审查,本国债权人的保护在这一裁量过程中也往往仍具有决定性作用。将外国破产程序能否对本国债权人提供充分、平等保护作为对来自外国破产程序请求提供必要的司法协助的条件,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传统上,这一考量常以本国法和本国债权人在个案中的具体待遇作为主要标准和依据。这一做法的结果是,除因外国破产法律中存在的歧视性差别待遇外,外国破产程序还常因请求国和本国在破产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差异而被给予负面评判,这一情形明显不利于跨境破产协作的开展。如,英国普通法的早期案例中,以个案检视为基础,完全由法官根据个案中本国债权人的利益裁量确定是否给外国破产程序予请求的协助[43],导致这一裁量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及不可预见性[44],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跨境破产程序的复杂程度、造成了成本浪费。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第一起涉及对美国破产重整程序司法协助问题的Felixstowe[45]案。该案中,被告是一家在美国进行破产重整的公司,美国破产法院依据《破产法典》,在该公司申请的当日签发了一份在全球范围内自动停止对该公司进行诉讼的命令。依据该公司的重整计划,公司停止在欧洲的业务,并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在欧洲的财产和业务均出售,以所得资金维持其在北美地区的业务。一个英国债权人则向英国法院起诉并申请获得了一份禁令,禁止该公司将财产转移出英国。被告遂向英国法院申请解除该禁令,但其申请被法院驳回。在其判决中,赫斯特法官认为,尽管英国法院原则上非常愿意为其他“友好国家”破产程序中作出的裁判提供所有合适的协助[46],但是,是否给予协助、给予何种协助,则应当由法院根据具体的问题、英国法的规定及案件的整体情况作出决定[47]。该案中,按照重整计划,被告位于英国的所有财产和业务都将被出售并用于该公司在北美地区的经营,英国债权人将无法获得清偿,其利益在重整程序中被边缘化,这构成对英国债权人的歧视性待遇,据此,不应为美国的破产重整程序提供相应的司法协助。该判决作出后,长期被指责为是欠缺司法礼让的典型案例之一[48],并认为将给跨境重整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49]。在此后的一系列涉及外国重整程序与本国诉讼禁令的案件中,英国法院力图依据司法礼让原则解除本国禁令以给予外国破产程序必要的协助[50]或者拒绝本国债权人提出的禁令申请[51],甚至声称将为发生任一国家和地区的破产程序的撤销之诉或追究董事责任诉讼签发诉讼禁令,予以协助[52]。有学者认为,这一情形表明,除非外国破产程序中存在对英国债权人的明显歧视,否则,英国法院将基于司法礼让原则给予协助[53]。但是,基于个案、逐一分析本国债权人在外国破产程序中所受的具体待遇和实际利益所受的影响等因素这一衡量方法,则仍在普通法中延续并导致跨境破产的司法协助问题继续受制于本国债权人在个案中的具体利益[54],并因此极为欠缺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与英国普通法相比,美国在接受《示范法》前的《破产法典》(现美国《破产法典》第十五章)第304条中则相对较为明确,规定将美国债权人在外国破产程序中的待遇是否将低于本国(美国)法律规定[55]及外国破产程序是否欠缺与美国破产法的一致性[56]作为拒绝给予协助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国际破产司法协助的早期司法实践中,对上述因素的判断也采取与英国相同的逐一个案实际考量的方法[57]。但最迟自2000年初开始,则已逐渐转向对外国破产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的整体衡量[58],并且其标准也逐渐降低为只要“不严重违背美国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即可”[59]。
(二)国际上的解决方法
1.制定统一的国际破产法律与规则。
造成各国基于债权人保护的需要而拒绝、限制对外国破产程序在法律上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破产法律、规则与相关法律上的差异。因此,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路径在于实现各国在破产等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一致。为此,有学者建议,在国际上对跨境破产建立一个特殊的一致法律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包括统一的跨境破产程序、法律适用规则和相对一致的实体规定[60]。尽管实践中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也不断进行努力,但基于各国经济地位、经济条件、法律传统与历史、社会等条件的差异,这一路径在可见的未来仍无法实现。
2.缔结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
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以平等保护本国债权人为条件互相提供司法协助,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在这一方面,如欧盟破产规则、北美破产条约等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展开详细介绍。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首先,这些条约一般均在经济条件、在世界经济地图中地位较为相近,并且具有较为共同的政治因素或法律传统的国家间缔结。不同于国际贸易等国际民事诉讼,跨境破产由于涉及的本国金融、投资、贸易等债权人的利益十分重大,各国破产法律制度差异仍十分明显,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十分微妙复杂,各国在缔结跨境破产司法协助条约时也均十分慎重。在民商事司法协助双边条约中也往往将破产协助问题排除在外。
3.建立或形成特殊的司法协助“国家(地区)群”。
部分国家与地区之间基于共同的法律传统和相近的破产法律制度,形成跨境破产司法协助群小“圈子”。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接受《示范法》之前依据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426条[61]、澳大利亚《公司法》第581条第(2)款[62]而给予具有共同法律渊源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更为便捷的协助程序。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法院的司法协助请求,除非存在违反本国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系因执行外国税法而为,一般均能直接获得所需的司法协助。基于这些国家之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普通法渊源和传统,本国债权人保护问题较少成为司法协助的考量因素。
在这些国家相继接受《示范法》后,近年来也仍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加强彼此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协作,如近年由新加坡发起推行的JIN(Judicial Insolvency Network)[63]、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ALI原则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他们之间的合作领域已经不断拓宽,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承认彼此之间的破产程序、提供所请求的司法协助措施等,而逐步拓宽到共同审理(Co-hearing)破产案件等更为紧密的层次和领域。
4.建立一致的司法协助原则、条件、措施和规则。
在这一领域,《示范法》自1997年制订颁布后,已经先后为20余个国家的接受并融入本国法律体系中[64]。虽然这些国家就数量而言并不庞大,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却十分重要。他们中既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传统英美法系国家,也包括了日本、韩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希腊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目前,在亚洲,泰国、菲律宾等国依据《示范法》制订的法律草案也已经先后进入了立法程序。
《示范法》在跨境破产司法协助领域带来的最主要变革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两方面:一是突破了地域性限制。依照该法的要求,接受并通过该示范法的国家和地区对请求予以司法协助的国家和地区不应存在地域上的限制,即其应对来自任何其他国家、地区的请求均依照该法的规定予以协助。而在此前有关跨境破产司法协助的条约、公约或规则中,均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地理区域、法域条件或法系传统的局限。如欧盟破产规则仅适用于欧盟国家之间,对来自欧盟之外的国家的司法协助请求,仍由各成员国依据本国法律进行处理;英国原1986年《破产法》第426条中的跨境破产协助,也仅给予与其具有高度法系沿袭性的部分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对其他国家则其适用十分苛刻的普通法。因此,这些司法协助体制在适用范围上都存在一定地域性局限,对某些跨越了这些地域限制的跨境破产、重整案件而言,成效十分有限。二是建立了有限普惠原则。《示范法》在允许保留的前提下,首次采用有限普遍原则,将普惠、开放式的司法协助体系引入了跨境破产领域。而此前有关跨境破产的司法协作机制,无论是双边或者多边,一般均以各参加国之间彼此的互惠为前提条件。《示范法》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跨境破产司法协助问题的限制,极大地便利了跨境破产案件在其他国家中及时获得必要的司法协助,是国际社会多年努力的结果,迄今为止代表了这一领域引领性成就与意义。
三、有限普遍原则下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对《示范法》下相关司法实践的一次检视:现状与趋势
为跨境破产的司法协助问题,《示范法》从司法礼让的基本原则出发,寻求建立一个较为中肯、可行、并较易为各国所接受的开放性协助体系,在承认外国法院破产程序和管理人的身份、职权、财产移交、财产分配等诸多方面设定了若干较为正当、合理的条件。接受《示范法》的各国法院在最近的司法实践中,在理解和适用这些规定时也尽量秉持司法礼让,适当地克制对本国债权人过度保护的倾向,有效地提高了跨境破产案件在其他国家获得司法协助的可能性,节约了跨境破产及重整的成本,提高了跨境破产的效率,并在立法、司法理念和技术上为建立外国法院与破产有关裁判的承认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5]。这些相关司法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一)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条件与标准。
《示范法》中,除临时救济措施外,对外国破产程序提供司法协助的前提是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特别是移交财产,《示范法》将其列为承认后的司法协助措施之一。在这一意义上,《示范法》中有关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条件和规定就成了法院保护本国债权人的第一道防线。根据《示范法》的相关规定和有关国家的司法实践,对外国破产程序不予承认的情形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1.外国程序不是一个适格的破产程序。
根据《示范法》第2条的规定,依照该法申请承认并寻求司法协助的外国程序必须是一种破产程序。依据该条中定义,所谓“破产程序”,必须同时具备如下三个要素:首先,这一程序是一种对债务人财产和债务的集中处理的司法或行政程序;其次,这一程序必须遵循与破产有关的法律;第三、在这一程序之下,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和行为均应当受外国法院的控制或监督;最后,这一程序的目的在于重整或清算。与前述普通法做法相比,其标准趋于明确、其范围也明显兼顾、包容了各国在破产法律制度上的差异。
司法实践中,尽管各国法院对上述要素的理解仍存在一定差异,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他们对上述条件的解释和把控逐渐趋于宽松。例如,就外国程序是否符合“对债务人财产和债务的集中处理”这一特性,2010年,英格兰上诉法院在斯坦福国际银行案中认为,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美国法院签发的对该银行的收集令是依据单一债权人的申请而签发的、而且其法律依据并非破产法,故不符合上述前两项要素的要求[66],并据此拒绝予以承认和协助。但两年后,美国德克萨斯北区法院针对同一案件却认为,该案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这一收集令的目的在于维护所有该银行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这一程序应当被视为符合上述条件[67]。关于“与破产有关的法律”,司法实践中也逐渐不再要求这些法律必须严格局限在据以启动程序的法律必须以“破产法”或“清算法”为名。美国法院在Betcor案[68]和ABC Learning Centres案[69]、澳大利亚法院在Chow Cho Poon[70]公司案中均认为,虽然上述程序系依照所在国的公司法规定启动的,但仍应当被认为依据的是“与破产有关的法律”,而无须考虑这一程序的目的是在于清算并注销公司或是为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类似于Chow Cho Poon案中新加坡法院基于衡平法原则、直接按公司法的规定签发的清算令,尽管并非依据破产法做出,但也被认为符合上述“与破产有关的法律”这一要求。关于对上述要素的裁量方法,英格兰上诉法院在斯坦福国际银行案件中则指出,法院在这一审查中,应当综合上述各要素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综合考量后做出结论,而不是严格地按上述要素逐一进行单独审查并分别作出判断,以其中的某一要素未能满足认定外国程序不是一个适格的破产程序,这一做法也明显区别于前述传统普通法上的裁量方法。
2.公共政策例外。
公共政策例外是跨境司法协助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示范法》第6条的规定,被请求国法院得以违反本国公共政策为由,拒绝对外国破产程序予以承认及提供司法协助。这一规定是《示范法》以明文方式规定的被请求国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唯一事由,体现了《示范法》“可能对国际破产司法协助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将至最低并予以明确”,以增加确定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原则。
司法实践中,公共政策是被告抗辩法院对外国破产裁判予以承认中最重要、最常见的抗辩事由。由于《示范法》并未对公共政策作出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实践中,受请求法院只能依据本国的国内法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涵进行认识和理解。由于外国破产法律、破产程序或多或少与本国法律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各国都依据本国国内法意义上的“公共政策”概念对这一名词作出广义的理解,显而易见,仅有极少数外国程序能够获得承认。归纳而言,目前在各相关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被纳入公共政策例外的范畴:
(1)违反本国法律基本原则或程序公平原则。在一个开放的跨境破产法律体系内,对公共政策例外的范围应当依据司法礼让原则给予适当限制,即它只能针对那些违反了被请求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宪法性原则的情形。以美国为例,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以外国破产程序违背了本国法律规定、未对担保债权提供优先保护等理由认定外国程序违反本国公共政策,并据此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拒绝提供司法协助将财产移交外国管理人的案例[71],在最近的案例中,该国法院对公共政策例外范围的理解日趋严格。近年的相关案例中,仅有如下因素被认为有违公共政策:外国程序的公平和中立性(Ephedra[72],案)、外国程序是否符合破产法上诉讼自动中止的目的(Gold & Honey[73]案)、管理人拥有的权限超越了美国的法律传统或法律规定(Toft[74])等。但是,其他接纳了《示范法》的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则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认识,特别是上述因素中的后两者,将本国法律作为评判、衡量外国法律、程序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司法礼让原则的要求。例如,英国法院在对Toft案做出的裁决中,则认为该案中管理人拥有的权限超越了本国法律传统或法律规定这一因素不构成违反英国的公共政策,并因此给予了承认和执行。2013年,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ABC Learning Centres Ltd案中进一步明确,《示范法》中所指的公共政策例外仅指外国破产程序中的实体和程序不符合正当性保护的要求[75]。
(2)滥用破产程序。虽然《示范法》中并未直接规定受请求国法院应当将这一因素纳入其是否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考量中,但是,目前大部分国家均认为,对破产程序的滥用,如破产欺诈,应当被认定为直接违反了破产法的基本法律原则并纳入公共政策例外的范畴内而拒绝予以承认。至于何种行为构成对破产程序的滥用,则由被请求国法院依据本国国内法的规定进行鉴别和认定。
(3)选购法院(Forum Shopping)。某种程度上,单纯基于法院选购的目的而在某一国家申请启动的破产程序也可以视为是滥用破产程序的情形之一,并因此被认定为违背了公共政策。同时,由于选购法院导致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形成对债权人不公平,或可能便于债务人规避、从事某种违反被请求国法律的行为,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因选购法院申请启动的破产程序被认定为违反了被请求国的公共政策而被其他国家拒绝承认。2009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最高法院在一起涉及斯坦福国际银行破产案的案件中,直接以在安提瓜进行的破产程序是一种法院选购行为而拒绝对该程序予以承认[76]。同时,由于基于法院选购而申请启动的破产程序往往难以表明破产债务人与法院国之间存在适当的关联性,这种程序也难以依照《示范法》第17条的规定被认定为主程序或从属程序并因此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例如,在Bear Stearns[77]一案中,虽然破产企业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也在开曼群岛申请并进入破产程序,但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认为,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的主要利益中心位于开曼群岛、或者该公司在开曼群岛存在永久性的行为,开曼群岛进行的这一破产程序不符合上述两种程序中的任何一种,不应按照《示范法》的规定予以承认。依据这一原则,对那些既非在企业的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或者企业设置了某些经营设施的国家或地区启动的破产程序而言,譬如只有企业财产,很有可能在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示范法》所规定的承认和协助。
另一方面,在被请求国与破产债务人不存在实质性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对债务人的外国破产程序也可能被拒绝承认。最近,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即主张,在没有证据表明破产债务人在美国具有住所、经营场所或者财产的情况下,对该债务人的外国破产程序拒绝予以承认[78]。
(二) 基于“充分保护”的审查与判断。
《示范法》对获得承认的外国破产程序提供的司法协助措施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第20条规定的对外国主破产程序的自动司法协助措施,即对已经获得承认的外国主破产程序,被请求国法院应自动给予如下协助:中止对债务人的诉讼、执行等单独程序、禁止债务人对其财产的转让、处分或其他对财产设定负担的行为。2.裁量性司法协助措施。依据《示范法》第21条的规定,外国破产程序一旦获得承认,不论其是被承认为主程序或从属程序,被请求国法院可以依照外国破产程序管理人的申请,裁量给予任何适当的协助,包括:调查、取证或者获取并递交相关信息、移交债务人的财产、延长临时性救济措施及本国法律所规定的其他协助措施。同时,依据《示范法》第21条的规定,在法院认为必要的情况下,第20条规定的协助措施也可以给予已经获得承认的外国从属破产程序。3.第19条规定的承认前的临时性协助措施。
显而易见,在上述三种协助措施中,裁量性司法协助措施的给予必须符合下列条件:首先,它必须在外国管理人提出申请后才能作出;其次,由于该条项下的调查、取证或者获取并递交相关信息、移交财产等对本国债权人利益均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法院在批准采取这一司法协助措施前必须进行适当裁量。为保障这一裁量符合正当性的要求,并避免对本国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示范法》规定了一系列考量因素和要求:1.本国债权人的利益在该外国破产程序中得到充分保护,见于该法第21条第2款,即对承认后的司法协助措施的规定中;2.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包括债务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见于该法第22条第1款,该条件同时适用于临时性协助措施和承认后的司法协助措施;3.除上述两方面的考量因素外,被请求法院在其认为必要时,还有权对其批准的这些司法协助措施设定一定条件,见该法第22条第2款。同时,对外国从属破产程序提出的移交财产这一司法协助,还必须满足一个特殊的条件,即:依据被请求国法律的规定,这些财产必须交由外国破产程序进行管理或者涉及该程序中必需的相关信息。
从上述分析可见,《示范法》下,在审查确定是否给予上述司法协助措施的过程中,外国破产程序是否给予本国债权人、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充分保护”是一项具有决定性异议的考量因素。这一规定曾被批评为是该法的重要缺陷之一[79]。有学者曾指出,《示范法》将这一司法协助措施建立在对上述如此不确定性因素裁量的基础上,将导致被请求法院只将个案中具体、个别的法律和事实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并因此做出极其狭隘的理解和裁判[80],不利于对外国破产程序的司法协助。在传统的英国普通法中,法院基于某一个别的本国或外国债权人的利益将在外国破产程序中受损,或者外国破产程序中某一个具体的行为将可能影响本国或外国债权人的利益,直接拒绝对其提供司法协助的案例并不鲜见[81]。
但是,各国在《示范法》下最近的司法实践则体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法院在这一裁量过程中已经逐步摆脱个案中上述具体因素的影响,转而以请求国的破产法律和原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例如,2009年,在Atlas Shipping[82]一案中,债务人公司存放在美国银行中的资金因海事诉讼保全而已被冻结,美国法院纽约南区破产法院对丹麦破产法进行分析后认为,丹麦破产法中并不存在对该案债权人的歧视和差别待遇的规定,将该笔款项移交基予丹麦破产程序管理人并不会造成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对该案中债权人提出的其个案将蒙受损失的主张不予考量,裁定将该笔款项移交丹麦的破产管理人。2011年,佛罗里达南区破产法院在SNP Boat Service[83]一案中则更进一步,拒绝对某一个别债权人在法国破产法中是否能得到充分保护的问题进行考量,认为:“任何破产法院均无权对某一个别债权人的利益在外国破产程序中是否得到充分保护进行裁量”[84]。在HIH Casualty and General Insurance Ltd[85]一案中,按照请求国即澳大利亚法律的规定,债务人的财产在被用于向所有债权人进行清偿前,必须先行清偿某一保险合同项下的赔偿债务,这一规定不仅有悖英国破产法,而且在个案中无疑将导致英国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充分受偿。一审中,英国高等法院以此为由拒绝将债务人的财产移交予澳大利亚破产管理人,二审予以维持。澳大利亚管理人再次提起上诉后,英国上议院推翻了上述裁判并批准了这一司法协助措施。虽然参加审理的五位法官对裁判结果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彼此的理由却各不相同。他们各自考量的内容虽涉及公共政策、原英国《破产法》第426条及其立法理由等诸多因素,但在考量方法上则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对澳大利亚破产法的整体做出考量和评价,而非针对个案中债权人权利是否受到损害等具体事实和法律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示范法》第22条的要求,被请求法院在这一“充分保护”的裁量中,除了应当考虑传统普通法内对本国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之外,还应考虑外国破产程序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因此,《示范法》的这一裁量是建立在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正当性和公平性的考虑之上的。如在前述SNP Boat Service[86]案中,美国破产法院即认为,虽然它在决定是否批准给予外国破产程序司法协助措施中不应考虑个别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只有在确信外国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在该破产程序中获得充分保护,它才会提供协助,按照外国管理人的申请将财产移交给后者。
(三)平行破产程序中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对财产分配比例的限制。
在接受平行破产程序的情况下,《示范法》第32条专门针对平行破产程序中债权清偿制定了一个特殊规则。按照该条的规定,在不存在对担保债权和物权请求权优先保护的歧视的情况下任何已经在外国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的债权人,在针对同一债务人的本国破产程序中,在同一清偿顺序的债权人获得与其在国外已经获得的相同比例的清偿前,不得针对同一债权再行接受清偿和分配,即比例原则(Hotchpot)。这一规定尽管并未直接对司法协助问题做出规定,但是,在外国破产程序不存在这一法律规定或违背这一规则的情况下,请求国法院可依据“充分保护”的要求,在判定该程序未能为本国和外国债权人提供平等、充分保护的基础上,拒绝提供司法协助。因此,这一问题实际上和司法协助及本国债权人保护均紧密相关。
依照《示范法》上述规定:首先,这一规则必须遵循各国国内法对担保债权和物权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这一条款的目的仅在于为同一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提供平等受偿的待遇,其前提是担保债权和物权已经获得全部受偿。至于担保债权和物权在何种程度下可以认定已经获得全部受偿,则取决于破产程序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但是,对哪些权利足以被认定为担保债权或物权,尽管《示范法》在其《立法和解释指南》中允许各国根据本国法律的规定采用其他词语进行表述,由于各国法律存在的差异,具体案件中的法律冲突问题仍不可避免。例如,某一债权人对位于本国国内的一位债务人拥有一项为本国法律规定的担保债权,但这一担保债权在针对同一债务人启动了破产程序的另一个国家法律中,却并不被列为担保债权,或者恰恰相反,某一在外国破产程序中持有的对同一破产债务人的担保债权在本国法律中并不属于担保债权。此时,本国法院无疑将面临一个选择:对其应当适用本国法律或者该外国破产程序所在国的法律。两种结果的差异显而易见。对此,我们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根据该条款中规定的对上述权利“不得歧视”的原则,对担保债权或物权的范围属于本国法律规定的范畴,对该债权人的优先受偿地位应当予以保护;在后一种情形下,为提高跨境破产司法协调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则应按本国国际私法规则确定其适用的法律。
其次,该条款的计算依据是债权清偿的比例而非数额,并且,在存在多个平行程序的情况下,这一比例的是债权人在各个程序中获得清偿的总和。例如,普通债权人A在B国进行的针对债权人C的破产程序中已经获得了5%比例的清偿、在针对同一债权人在D国进行的破产程序中已经获得了10%的清偿,此时,如本国破产程序中对普通债权的清偿超为14%,则该债权人仍不应受到清偿;反之,如果本国破产程序对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达到16%,则该债权人即依据这一条款的规定,仍可以获得1%比例的清偿。
最后,虽然没有在该条款中作出明确规定,适用该条款进行分配仍需由本国法院作出裁决。因此,只有在确认担保债权和物权已经依照本国法律获得无歧视的完全受偿后,法院才可以裁定依照该规则进行财产分配。
这一规定的初始目的在于防止同一债权人针对同一债权在不同国家的平行破产程序中获得优于其他债权人的待遇,平等保护各国债权人利益。但是,客观上它确实有利于促进各国法院放弃基于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目的而拒绝对跨境破产程序提供司法协助,有利于促进各国对外国破产程序提供更为开放、有效的司法协助。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整体上,各国在《示范法》下的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实践中,在涉及本国债权人保护的裁量方面,主要存在如下趋势:1.裁量标准上,从个案裁量(ad hoc Discretion)到整体衡量(Balancing the Insolvency Law and Principles of the Jurisdiction As A Whole)。即从考量本国债权人在个案中面临的具体待遇和问题转向对外国破产法律、原则和制度的整体的评估。2.裁量依据上,从本国法到外国法。即从依据本国破产法律制度对外国破产程序进行考量到主要依据破产程序所在国的法律制度进行衡量。3.裁量对象上,从单一对象到多元对象,即从仅考虑本国债权人利益是否在外国破产程序中得到平等、充分保护转向综合考虑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在外国破产程序中是否得到公平、足够的保护。
四、对我国《企业破产法》跨境破产制度的反思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有关跨境破产的内容仅见于该法第5条第2款。该款规定: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财产,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承认和执行。
上述规定存在的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1.基本原则及其问题。
《企业破产法》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对跨境破产司法协助采用互惠原则。提供司法协助的前提以提出申请的国家、地区与我国之间存在条约或互惠为前提。由于迄今为止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基本上均未涉及跨境破产领域,更未专门针对为对方国家内破产程序的协助问题做出特别的规定,目前主要依据互惠原则解决跨境破产的司法协助问题。但是,《企业破产法》上述规定未就互惠范围作出规定,即互惠是否仅限于破产领域,将来可能给这一领域的司法实践造成一定困扰。由于破产程序与一般民商事程序在各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对这一领域不做适当限制,如外国法院在其他民商事领域(如离婚)等方面存在的对我国判决、裁定不予认可、协助的情形下,我国法院即因适用互惠原则而拒绝予以提供协助,显然不利于这一领域的国际协作和礼让的基本发展趋势。为此,从促进国际协作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将这一互惠领域限制于破产领域。
2.适用对象及其问题。
《企业破产法》上述规定中,将跨境破产司法协助限制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这一做法忽略了符合破产程序的特点和需求,实际上将破产程序的司法协助等同于其他民商事程序的司法协助,存在诸多问题。概要而言主要有三:一是未规定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及其效力。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在本国的效力并依据程序所在地法院的法律规定在本国产生中止对债务人的诉讼、执行等以阻却债权人个别求偿,并采取适当协助措施以确保上述效力的实现,即所谓“开门即全进”(One Comes, All Come),是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在跨境破产司法协助中通行的做法。传统国际私法上,承认一个在公司注册地启动的外国破产程序,即意味着两方面的意义:(1)该破产程序依据其启动国的法律产生相应的效力,当与本国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本国法律优先适用;(2)该外国程序代表享有依据该程序启动国法律所规定的权力,但不得与本国法律冲突或超出本国法律规定的范畴[87]。我国《企业破产法》上述规定回避对外国破产程序效力的承认问题,而仅规定对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承认与执行,不仅无法解决由于外国破产程序启动而产生的一系列效力、后果和相应的协助措施问题,而且将给司法实践带来对外国启动破产程序的判决、裁定所涉效力范围的争议和困扰。同时,这一局限客观上还将造成司法协助无法一次性解决的问题,当事人或外国程序代表不得不针对不同的司法协助措施多次申请,造成时间上的延误和成本的浪费。
二是未规定对外国破产程序的具体协助与救济措施。跨境破产程序涉及的司法协助措施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涉及诸多方面、十分具体的救济措施。其中任一救济措施的缺失或拖延,都将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不利后果。以《示范法》为参照,其规定的司法协助措施按时间划分包括临时性救济、承认后对主要程序的救济;以性质分又可分为必须给予的救济和裁量提供的救济;以外国程序特征划分又可分为对主要程序和对非主要程序的救济等。我国《企业破产法》在救济与协助措施方面存在的立法空白,特别是承认前临时性救济的缺失,显然不利于及时控制债务人的财产、业务,造成了债务人财产流失的空间。
三是未能区分外国法院在破产程序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与裁定,未明确后者是否属于该条的适用对象。该条中笼统以“破产案件”规定其适用对象,但未对“破产案件”的内涵或外延作出明确规定。国际上,各国破产制度及其对“破产案件”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诸如外国在破产程序进展中所需作出的程序内裁判之外,法院在破产程序中或破产程序外作出的、直接产生于破产程序或与之紧密关联、涉及破产财产的判决与裁定,是否得适用上述规定,亦不无疑问。基于上述问题,联合国贸法委已就该类判决与裁定的承认与执行问题进行多轮研讨,并已于2017年初步形成《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示范法草案》[88],值得学习、吸收和借鉴。《企业破产法》该条在适用对象上不仅存在未与国际接轨、造成理解和适用上的困惑,客观上还将增加寻求司法协助的成本,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和浪费。
3.公共政策问题。
按《企业破产法》上述规定,请求协助的外国破产判决、裁定必须还应满足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我国领域内的债权人合法权益等公共政策这一条件。但是,在该法及其他法律中,我国仍未对社会公共利益等概念及其内涵做出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对跨境破产司法协助中的“公共政策”应当将其放置在国际环境下进行审查,即仅指违背了本国宪法、法律尤其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违背程序公正的正当性基本原则,如未给予债权人适当的通知、未能获得参与外国程序、向外国法院表述意见的机会和权利[89]等。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例中所持的意见体现,它对公共政策保留所持的态度是符合国际要求的狭义解释,即只有当存在违反我国社会根本利益、法律基本原则和公序良俗的情形下,才应当认定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90]。据此,仅因外国程序违背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不足以构成公共政策例外的事由。这一理解完全符合国际上的上述观点与做法。但是,上述意见是否得适用于跨境破产领域,则尚不明确。
4.管辖规则及其问题。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仅依住所地原则规定了国内破产管辖权归属原则,未对跨境破产管辖权问题做出规定,更未规定我国法院对外国企业的破产管辖权。这一立法欠缺,将使我国法院无法行使对虽注册于国外、但其主要财产、业务及债权人均位于国内的企业行使破产管辖权,在国际破产管辖权争夺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国际上,“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COMI, Center of Main Interests)这一概念在被《示范法》及《欧盟破产规则》(The EC Regulation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91]接受后,目前已经被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广泛接纳作为行使对跨国企业的主要破产程序管辖权及确定破产主要破产程序所在地的依据,有逐步替代传统企业注册地原则的趋势。我国在《企业破产法》立法时未适当吸纳这一成果,规定其概念并作为跨境企业破产管辖依据,无疑将给未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在涉及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的管辖权冲突带来极大不便与困惑。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不断发展、已逐步从单一的投资目的国转变为主要对外投资国之一;同时,大量国内企业出于避税、境外上市等需求,虽采取在BVI、开曼、百慕大群岛或美国特拉华等便利地区注册相关企业,但其财产、业务和主要债权人均居于我国;此外,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则使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中心与其主要财产、业务相分离成为日益常见的现象,上述诸多现实情况之下,这一立法上的瑕疵无疑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5.从属程序问题
从属程序(Ancillary Proceeding or, Secondary Proceeding)的具体制度及其优劣,前文已作详细论述。目前,不论在欧盟破产规则、联合国贸法委《示范法》或英美等普通法中,从属破产程序的做法均为法律和司法实践所认可和接受。在国内意义上,当债务人在外国进入主要程序的同时,在国内启动针对同一债务人的从属程序,对破产债务人在本国的财产、业务和所负债务依据本国法律进行管理、处置和分配,无疑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本国债权人利益。在国际意义上,当不同国家针对同一债务人启动平行破产程序、相关法院均向我国提出司法协助请求时,法院可根据从属破产程序的相关规定识别外国程序的主从属性,并分别给予不同的司法协助措施。我国《企业破产法》未对此作出规定,不仅不利于及时将外国债务人在我国国内的财产置于我国法院或法院指定的管理人管控之下、适用我国破产法律,在影响了跨境破产效率的同时不利于对本国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将来在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平行破产程序的司法协助请求的处理中,还将处于不知所措和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6.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标准问题
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同,我国把外国破产程序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作为裁量是否提供司法协助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作出了规定。但是,该条中“不损害我国领域内的债权人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裁量依据不明确。“债权人合法权益”所指,系债权人依据本国破产法律规定享有的权益、或依据请求国法律享有的权益,抑或依据国际私法规则适用的法律所享有的权益?均未明确。在不同国家在破产法上存在清偿顺位、优先权范畴差异、在担保制度上也存在诸多差异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不仅攸关本国债权人的利益,也是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中无从回避,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跨境破产的法律冲突与适用所涉问题十分复杂,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详细讨论。一般来说,在司法协助的审查中,大体依据国际私法规则,对程序性问题适用法院地法律,对跨境契约性债权、担保债权等则按国际私法规则确定的适用法律,但有几点需要特别说明:(1)承认外国破产程序、以外国破产程序所在国的法律作为是否给予司法协助的审查对象,并不意味法院放弃适用本国法律的权力。相反,法院有权决定适用本国法律或外国程序所在国家的法律[92],特别是在涉及本国债权人重大利益如担保物权的保护等问题上,本国法院仍有权适用本国法律;(2)本国破产法的原则性和强制性规定,如破产撤销制度等,必须予以适用;(3)本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必须得以适用。
二是裁量方法不明确。如前详述,在跨境破产司法协助中涉及本国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存在个案衡量与整体衡量两种不同的裁量方法。法院在面对涉及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的争议时,应当如何进行衡量、依据那些因素进行衡量,是依据个案中本国债权人在外国破产程序中的具体待遇和利益是否受损进行考量,抑或应当仅对请求国的破产法律原则、规定是否存在对本国债权人的歧视性、不平等待遇进行整体衡量,在立法中均未给出答案,无疑都将给未来的司法实践带来困扰和疑问。
7.平行破产程序的比例规则问题。
《企业破产法》未规定平行破产程序下外国债权人参与本国财产分配或本国债权人参与外国破产程序分配的比例规则,并将此作为提供司法协助、移交债务人在本国财产的条件之一,也是其缺陷之一。虽这一问题可归入“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中进行理解和处理,但这一立法缺失也不免给平行破产程序下相关司法协助措施和财产移交、分配等带来一定问题。
结语
在一个相互之间的经济关联日趋紧密的世界里,过度强调对本国或本国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无疑只能招致其他国家的抵制和报复,最终必将反受其害。跨境破产中有关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发展和趋势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启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以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宽阔的胸襟融入到其中,才是正确的做法。对我国而言,在国际合作、对外投资日益增长的今天,如果在跨境破产司法协助事项中继续坚持孤立于世界之外,最终受伤的,仍将是自己。是为结语。
注释:
[1]鉴于我国目前仅有企业破产法律制度,除非必要并明确指明,否则本文的讨论均以跨境企业破产为限。跨境个人破产所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所要考虑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因素更多,篇幅所限,难以在本文中一一详论。
[2]“relinquish their holds over the “bird in hand”,See Felixstowe Dock and Railway Co. v U.S. Lines Inc. [1989] QB 360.
[3]E.B. Leonard and C.W. Besant, “New Frontiers in Canadian Cross-border Insolvencies”, in E.B. Leonard and C.W. Besant (eds.), Current Issue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Reorganisations, Graham & Tortman and IBA 1994, at 116.
[4]I.Fletcher, Law of Insolvency, 3rd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2, p.13-14.
[5]See J.L. Westbrook, “The Case for Cooperative Territoriality i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2000) 98 Mich.L.Rev.2216, at 2218; F. Tung, “Fear of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2001)33 Geo.Was.Int’I L.Rev.555, at 561; J.J.Chung, “The New Chapter 15 of the Bankruptcy Code: A Step Toward Eros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2007)27 Nw.Int’IL. & Bus89, at 93.
[6]I. Mevorach, Insolvency With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rou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t 72.
[7]See J.L. Westbrook, “A Global Solution to Multinational Default”, 2000 98 Mich. L. Rev. 2276, at 2309-2310.
[8] See L.M. Loppucki,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A Post-Universalist Approach”, (1999) 84 Cornell L.Rev. 696, at 702.
[9]See L.M. Loppucki, “Universalism Unravels” 79 Am.Bankr.L.J. 143; Also L.M. Loppucki, “Global and Out of Control”, (2005)79 Am.Bankr.L.J.79.
[10]见注8,J.L. Westbrook, at 2302.
[11]新加坡公司法中原也存在这一规定,但在2016年已通过立法程序予以废除。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外国公司撤销其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时,必须依法清偿债务,依照本法有关公司清算程序的规定进行清算。未清偿债务之前,不得将其分支机构的财产移至中国境外。
[13]Re English, Scottish and Australian Chartered Bank[1893] 3 Ch.385, at 394.
[14]Re A Company (No. 00359 of 1987) [1988] Ch.210.
[15]Guaranty Trust Company of New York v Hannay [1915] 2 KB 536, Garthwaite v Garthwaite [1964] P 356. 香港地区案例见:Re Chime Corp Ltd (2004) 7 HKCFAR 546, Joint and Several Liquidators of Kong Wah Holdings Ltd v Grande Holdings Ltd (2006) 9 HKCFAR 766,Re China Medical Technologies Inc [2014] 2 HKLRD 997 applied; Re Yung KeeHoldings Ltd[2014] 2 HKLRD 313 (CA) considered).
[16]同上。
[17]R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1991] BCLC 210, Knox J. at 217.
[18]See L. Collins(eds.),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0, Rule152-(1), p.1101 andRule158, p.1141.
[19]Re Thulin [1995] 1 WLR 165.
[20]Subject to a reservation of funds for theclaims of English preferential creditors, Re Hibernian Merchants Ltd [1958] Ch.76.
[21]I. Fletcher and H. Anderson, “The Insolvency Issues” in M. Bridge and R. Stevens (eds.)Cross-border Securityand Insolven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65.
[22]Felixstowe Dock and Railway Co. v U.S. LinesInc. [1989] QB 360, p.379.
[23]例如,在早期的跨境重整案例中,由于德国(主程序)与英国(从程序)管理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最终导致了Boss旗下Lancer Boss/Stein Beck Boss的重整失败,见 (1994) ICCLR C-146。
[24]See P. J. Omar, “Co-operation Between Courts: The Common Law Legacy”, (2003) Insolvency Lawyer 74.
[25]See P. Smart, "Administration Orders and Foreign Companies" (1997) 13 I.L. & P.186S. Also G. Moss, “Administration Orders for Foreign Companies”, (1993) Insolvency Intelligence 19.
[26]见前文。
[27]Re Wallace Smith Group Ltd [1992] BCLC 989.
[28]See S. Shandro, “Ancillary Winding-up and Winding-up of Foreign Companies”, (2000) CFILR 197.
[29]See C.K. Grierson, “Issues in Concurrent Insolvency Jurisdiction: English Perspectives” in S. Ziegel (eds.) Curren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rporate Insolvency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4, p.580.
[30]Re Matheson Bros Ltd [1884] 27 Ch.D.225.
[31]See H. Hanishch, “‘Universality’ versus Secondary Bankruptcy: An European Debate”, (1993) 2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 151, p.158.
[32]IA 1986 s.144. Also Millett J., Re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1987] Ch. 419, p.446.
[33]Re BCCI (No.10) [1996] 4 All ER796.
[34]Paramount Airways [1992] 2 WLR 690.
[35]P.J. Omar,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olvencies: British and French Rules Compared”, (1996) 4 ICCLR 152, p.153.
[36]Re Vocation (Foreign) Ltd [1932] 2 Ch.196, Maugham J., p.207.
[37]作为英国破产法体系下最重要的企业拯救手段,有关Schemes of arrangement 的介绍详见V. Finch, Corporate Insolvency Law: Perspective and Princi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24 to 326.
[38]Subsection4.
[39]Subsection5, See J.W. Wolniecki,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Insolvencies: Recent United Kingdom Legislation”, (1986) ICLQ 644, p.650. Also K. Anderson, “Statutor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Cross-border Insolvenc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2000) CFILR 44, p.50.
[40]Hughes v Hannover Ruckversicherungs-Aktiengesellschaft [1997]1 BCLC 497.
[41]Subsection10(d).
[42]C.K. Grierson, “Issues in Concurrent Insolvency Jurisdiction: English Perspectives” in S. Ziegel(eds.) Curren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rporate Insolvency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4, at 598. See also P. Smart, Cross-border Insolvency, 2nded. Butterworths 1998, p.414-415.
[43]I. Fletcher, Insolvenc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9, at 187.
[44]I. Fletcher, The Law of Insolvency, 3rded.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2, at 737.
[45][1989] QB 360.
[46][1989] QB 376.
[47]同上.
[48]See Millett LJ, “Cross-border Insolvency: The Judicial Approach”, (1997) 6 IIR 99. Opposition see Lord Hoffmann, the 6th Denning Lecture and n.20 above; M. Crystal, “The Company Lawyer Lecture 1997-Judicial Attitudes to Insolvency Law”, (1998) Company Lawyer 49.
[49]C. Morris and M. Kirschner, “Cross-border Rescue and Asset Recovery-problems and Solutions”, (1994) 10 Insolvency Law & Practice 42, p.44.
[50]Banque Indosuez S.A. v Ferromet Resources Inc [1993] BCLC 112. Rowland v Gulpac Ltd (No.1)/ Inoco plc v. Gulf USA Corp (No.1) [1999] Lloyd's Rep. Bank. 86, including an indemnity action (Rowland v Gulpac Ltd), and a declaratory action, Inoco plc v. Gulf USA Corp.
[51]Barclays Bank v Homan [1993] BCLC 680. See also Look Chan Ho, “Anti-suit Injunction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 Restatement”, (2003) 52 ICLQ 697.
[52]The 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Act 1982 (Interim Relief) Order 1997, See P. Smart,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nd the 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 Act 1982”, (1998) Civil Justice Quarterly 149. The Order has been amended by the 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 Order 2001 but relevant provisions were reserved.
[53]See P. Smart,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Judicial Discretion”, (1999) Insolvency Lawyer 12.
[54]See K. Anderson, “Statutor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Cross-border Insolvenc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2000) CFILR 44, p.71. See also I. Fletcher, (2004) Insolvency Intelligence 89 (casenotes of a U.S. case).
[55]s.304(c)(2).
[56]s.304(c)(4).
[57]Re Toga Manufacturing Ltd (1983) 28 BR 165.
[58]Re Caldas 274 BR 583 (Bank. S.D.N.Y.2002); Re Avila, 296 BR95, at 112 (Bank. S.D.N.Y. 2003),at 107-108; Re Board of Directors of Multicanal S.A., No. 04-10280 (ALG) (Bank. S.D.N.Y. March 12, 2004).
[59]Re Bullmore, 2004 Bankr. Lexis 230, at 18 (B.A.P. 8th Cir. 2004).
[60]E.J.Janger,“Universal Proceduralism”, (2007) 32 Brook. J.Int’IL.1, at 9.
[61]《1986年破产法院协作令(指定的相关国家和地区)》(Co-operation on Insolvency Courts (Designation of Relevant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Order 1986),包括安圭拉岛、澳大利亚、巴哈马、百慕大、博茨瓦纳、加拿大、开曼群岛、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香港、爱尔兰、蒙特色拉、新西兰、圣海伦那、土耳其凯科斯群岛、图瓦卢、维京群岛;《1996年破产法院协作令(指定的相关国家和地区)》 The Co-operation of Insolvency Courts (Designation of Relevant Country) Order 1998)增加了马来西亚、南非;《1998年破产法院协作令(指定的相关国家和地区)》(The Co-operation of Insolvency Courts (Designation of Relevant Country) Order 1998)增加了文莱。
[62]《破产法》附表五(Schedule5 of the Bankruptcy Act),包括: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泽西岛、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斯威士兰、美国。
[63]如,已获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联邦法院)、百慕大群岛、不列颠维京群岛、加拿大(渥太华)、开曼群岛、英格兰和威尔士、新加坡、美国(特拉华和纽约南区)等国家和地区加入。
[64]数字截至2013年12月1日,以立法机关通过为准。包括:澳大利亚 (2008),英属维京群岛(2003)、加拿大 (2005),哥伦比亚 (2006),厄立特里亚 (1998),大不列颠 (2006),希腊 (2010),日本 (2000),毛里求斯 (2009),墨西哥(2000),黑山 (2002),新西兰(2006),波兰 (2003), 韩国 (2006),罗马尼亚 (2002),塞尔维亚 (2004), 斯洛文尼亚 (2007),南非(2000),乌干达 (2011) 和美国 (2005)。最近,新加坡于2017年接受示范法。
[65]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示范法草案》,2017年12月18日至22日,维也纳。
[66]Stanford International Bank [2010] EWCA Civ. 137.
[67]Stanford International Bank, District Court, Northen District of Texas 2012.
[68]In re Betcorp Ltd ( in liquidation) 400 B.R. 266 (Bankr. D. Nev.2009).
[69]In re ABC Learning Centres Limited 445 B.R. 318 (Bankr.D.Del 2010).
[70]Re Chow Cho Poon (Private) Limited (2011)NSWSC 300 (15 April 2011).
[71]In re Treco, 240 F3d. 148 2nd Cir. 2001. (refusing to turn over assets to a Bahamian liquidation proceeding because it prioritize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ver secured creditors, and summarizing other cases denying turnover because the foreign proceeding failed to sufficiently protect prioritized secured interests).
[72]In re Ephedra Product Liablity Litigation 349 B.R. 333 (S.D.N.Y. 2006).
[73]In RE Gold & Honey, Ltd 410 B.R.357 (Bankr. EDNY 2009).
[74]In re Dr Juergen Toft 453 B.R. 186 (Bankr. S.D.N.Y. 2011).
[75]In re ABC Learning Centres Ltd., 728 F. 3d 301 (3d Cir. 2013), at 309.
[76]In the case of the Bankruptcy of Stanford International Bank, 11 September 2009, Superior Court, Districtof Montreal, Quebec,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quidators, para. 59.
[77]Bear Stearns High-Grade Structured Credit Strategies Master Fund, Ltd (In re), First instance: 374 B.R. 122 (Bankr S.D.N.Y. 2007) [CLOUT case no.760]; on appeal: 389 B.R. 325 (S.D.N.Y. 2008) [CLOUT case no. 794].
[78]Drawbridge Special Opportunities Fund LP v. Barnet (In re Barnet), 2013 BL 341634 (2d Cir. Dec. 11, 2013).
[79]See S. Isham, “UNCITRAL'S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 Workable Protection for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at Last”, (2001)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77, p.1204.
[80]See K. Anderson, “Statutor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Cross-border Insolvenc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2000) CFILR 44, p.71. See also I. Fletcher, (2004) Insolvency Intelligence 89 (casenotes of a U.S. case).
[81]Felixstowe Dock and Railway Co. v U.S. Lines Inc. [1989] QB 360;Rowland v Gulpac Ltd (No.1)/ Inoco plc v.Gulf USA Corp (No.1) [1999] Lloyd's Rep. Bank. 86.
[82]Atlas Shipping A/S (In re) 404 B.R. 726 (Bankr. S.D.N.Y.2009) [CLOUT case no. 1277]
[83]SNP Boat Service, S.A. v. Hotel le St. James, First instance: 435 B.R. 446 (Bankr.S.D. Fla. 2011); on appeal: 483 B.R. 776 (S.D. Fla. 2012) [CLOUT case no. 1314]
[84]同上, pp.783-784.
[85]HIH Casualty and General Insurance Ltd (Re), [2005] EWHC 2125; first appeal [2006] EWCA Civ 732; second appeal: McGrath v Riddle [2008] UKHL 21
[86]前注20
[87]A. Dickinson, D. McClean and P. McEleavy, Dicy, Morris & Collin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3rd ed. Sweet & Maxwell 2010, r.197.
[88]A/CN9/WG.V/W.P.150, 2017年9月17日。
[89]R.Good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Insolvency Law, 4th ed. Sweet & Maxwell, 2011, at 811. Also, Re Eurofood IFSC Ltd [2004] B.C.C. 383.
[9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海口中院不予承认和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请示的复函(2005年7月13日[2001]民四他字第12号).
[91]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46/2000.
[92]Re 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SA [1993] B.C.C. 787。该案主要涉及对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426条的处理,但对这一问题也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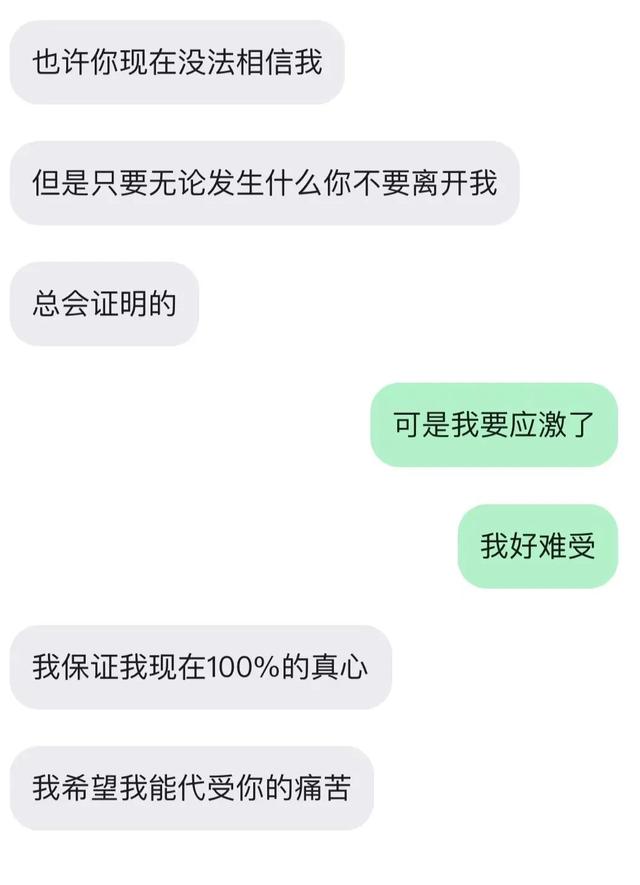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