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庆与鲁迅的“尊孔反孔之争”
鲁迅的大名在中国无人不知,其在中国文学史和政治史上的地位也不言而喻,民国时期名士才子如过江之鲫,谁不对鲁迅的名字竖起拇指?那么林文庆何许人也,竟然也敢与鲁迅叫板?
他是新加坡第一名医,人称其“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又是第一个获得英皇奖学金的中国人;他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又创办了英皇爱德华医院;他是孙中山的随行秘书兼私人医生,还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南洋橡胶之父;他是《离骚》的英文版译者,也是通晓五种语言的语言天才……

他就是林文庆。在大陆也许他默默无闻,但在当时的新加坡的文教政商各界,林文庆都一马当先,有圣人之称。
那时候,每个男人心底都有一个齐家治国的大梦等着实现。1920年,陈嘉庚有意在厦门开设一所高等学府,次年进入实质性办学阶段,林文庆是最适合的校长人选。接到陈嘉庚的电报后,林文庆没有迟疑,立即启程回国。
也正是在厦门,前五十年中一帆风顺的“新加坡圣人”与鲁迅先生针锋相对又惊天动地地展开了一场“尊孔反孔之争”。
一、打造东南最高学府
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时,林文庆已经52岁高龄了。
笔架山顶,一座二层的欧式建筑成了林文庆在厦门的家,在它的对面,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正引领着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体系。二楼平台就对着鼓浪屿的碧海兰天如诗美景,每天晨昏,林文庆都会从卧室来到平台上,散步、品茶、接谈,此后的十六年时间里,他就在这里操劳。
为了发展厦大,林文庆不但接受了陈嘉庚大量的资金支持,还自掏腰包,扩建校舍、广开言路,甚至开出了当时中国教育界价码最高的薪金,用以吸引最著名的学者任教厦大。
当时的鲁迅怎样呢?又是如何与林文庆相遇从而发生了此后一系列的恩怨呢?动荡的中国,学者们正过着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中国真的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连鲁迅这等堪称伟大的学者也过得捉襟见肘朝不保夕。
鲁迅《发薪记》一文中记载,1926年上半年他只领到了190块大洋的薪水,此前教育部共拖欠他薪水近万元。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因支持学生反对教育专政,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罢免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相当于失业。
就在这时,7月28日,厦门大学寄来一纸聘书和预支的车旅费共计500元,同时允诺予以高薪重酬。失了业的鲁迅抵不住高薪的诱惑,也有离开事非之地“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于是他打点行囊,在八月末离开北京南下,于九月四日抵达厦门。
在这里,他将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的课程,并任国学院研究教授。
做为文化投枪手的鲁迅,显然并不把教书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他更喜欢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经历了女师大风潮之后,他把厦门之行当做一次养精蓄锐的休整,而厦大的高薪也正好满足了他失业之后的囊中羞涩。
但是显然,厦门大学是让他失望的。
初来厦门,鲁迅见到了市中心的洋房阔宅,而普通百姓的住处则荒草高过人,乱坟如蚁。他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写信,信中夹着一张自己端坐在坟场中的照片,并声称厦门大学“硬是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不仅是学校的选址让鲁迅不满,办学需要钱,林文庆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商场上,这让鲁迅很是鄙视。同时,为文者的高傲也让鲁迅很难容忍他人的白眼和忽视,这几乎是所有学者的通病。
但是林文庆是办学者,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不可能不把金钱看得重要。在来厦大的第一天,林文庆就规定了教授的薪水是当时国内其他院校教授的两倍之多。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土地卖掉,用来支持陈嘉庚和厦大,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不仅变卖自己的资产,而且不领取厦大的薪水,直到后来经济危机时才不得不领取校长工资;他是医家出身,在笔架山的别墅里他开门诊,给政商显要治病,所得酬金全部交给厦大;他在江南各省游说,为厦大筹措资金,他三次到马六甲、新加坡募捐。五六十岁的老人每每登门拜访自己当年在商界的同仁甚至是晚辈,说些客气话,求得些捐款。而这一切,都让鲁迅感到可悲和可笑。
但也正因如此,林文庆在十六年的时间里,把厦门大学办成了“南方之强”,也被外国教育界称做“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国民政府授予其“东南最高学府”之称。对于厦大,林文庆功不可没,甚至说“没有林文庆就没有厦大”也不为过。
二、“我也有发言权”
来自北京的鲁迅是习惯穿长衫的,但是厦门大学的学者,更多的是西装革履的模样。而瘦小枯干的鲁迅,不仅其貌不扬,胡子还常常乱得吓人,脸色又缺少富贵气,自然遭到不少白眼。
厦大的工资是由总务处开出支票,由教授本人去银行领取。鲁迅第一次领薪水,就让银行的小职员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那职员看着面有菜色、衣衫草草的鲁迅居然拿出一张巨额的支票,很是怀疑这支票的来路,反复核实验证,这让鲁迅忍无可忍。虽然最后银行还是一文不少地兑现了这张支票,但却让鲁迅心里极是不爽,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大概是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也常见。’”
但是高薪还是让鲁迅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他在厦大的时候不仅每周要上四节课,更支持进步学生创办了“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学社团以及《波艇》、《鼓浪》月刊。同时完成了《汉文学史纲要》的大部分以及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名篇。
即便是这样,还是无法阻止鲁迅不喜欢这里。
最主要的是,鲁迅是反孔的,而林文庆校长却是尊孔的,不仅尊孔,还尊得五体投地。林文庆虽然常年在南洋生活,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成为不折不扣的孔家学说的代言人,无论经商还是办学,他都离不开孔子的教诲。
他把《大学》中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做为校训,处处以孔教为办学之“纲”,大力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们在主课之外背古书,写古文,并身体力行的以孔学为第一要务展开大讨论。
正在如火如荼地经历着新文化运动的学生们,则更多的喜欢接受新鲜新奇的西方学术理论和观念,很多在厦大任教的老师们也多是留洋学者,他们接受了先进的西方哲学并在厦大中大谈西学,反对孔学。鲁迅虽然穿着长衫,但骨子里却实在是个彻底的新文化运动者,他虽然并不是彻底的反孔派,但对孔学家派的一些封建糟粕深恶痛极,并对一切以尊孔为纲的林文庆的办学思想并不满意甚至是抵触的。
其实在鲁迅来厦大之前,厦门大学就已经因为太过尊孔出过大事了。1924年4月6日,林文庆在厦大三周年校庆上发表演说,号召师生尊孔学理。新派学生在欧元怀等教授的带领下掀起了一次驱逐林文庆的学潮运动,最终因为陈嘉庚的插手,此次驱林运动以学生的失败告终,但却致使九名教授带着二百余名学生出走上海,成立了大夏大学。
此次胜利使得林文庆对尊孔更加炙热。随着鲁迅、林语堂等“半个北大师资力量”的加入,林文庆愈发想以孔子的仁人学说治校,并规定每周四都要开全校的纪念周会,而鲁迅做为国学院的教授,自然不仅要出席尊孔周会,更应该发表演说才对。
对于林文庆的邀请,鲁迅拒绝了好几次,最终还是“给校长一个面子。”在一次周会上做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
演讲中鲁迅建议学生少在书本间浪费时间,而应该主动和热情地加入到国事的讨论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之中去,这显然与尊孔的理念背道而驰,孔老先生是教导学生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的。几天之后,《厦大周刊》上刊登了鲁迅的演讲稿,但是稿子却被林文庆删改得支离破碎。
从此鲁迅再不出席这种周会了。这次演讲加深了鲁迅对厦大的反感,也加深了与林文庆校长的矛盾。而在林文庆看来,鲁迅是国学院教授,拿着全国最高的薪水,却公开反对国学,与厦大的尊孔之说公然为敌,哪有这样的道理?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公开化也白热化。
另一方面,林文庆以经商手法经营学校也让鲁迅很看不上。林文庆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大力提高教授收入,扩建校舍,而这一切都要动用大量的资金,与银行自然也要搞好关系。如此林文庆经常在接待银行要员时请厦大的知名教授作陪,也曾多次请鲁迅出席。鲁迅很瞧不上这种处处以钱为主的作派,多次当着那些银行家的面呵斥“请我来是林校长给你们贴金呢还是污辱我周树人呢?要知道,古话说道不同不想为谋!”搞得林文庆很是下不来台。
有一次,林文庆托人带了请帖,烦请鲁迅出席一个宴会,鲁迅在请帖上写了个“知”字让带信人送回去,自己并未出席。事后林文庆问他,“既然知道了怎么还是不去捧场呢?”鲁迅回答说,“知之一字,意为不去可知矣 (意即我不会去的,你应该知道) 。”
那年冬天,学校因办学经费紧张,开会讨论准备压缩国学院的编制,与国学院的教授们展开激烈的辩论,期间做为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也大力反对。辩到急处,林文庆有些发火,不点名地批评道:“国学院不是大力反对我搞尊孔吗?孔学是国学,你们既然不尊孔,怎么还要出任国学院教授呢?怎么还要反对压缩国学院呢?你们应该建议取消国学才对。”
此话有些偏执,却也看得出只是一时气话。但就是这一番话,彻底惹怒了国学院的教授们,而那些凭口才吃饭的教授们又人多势众,驳得林文庆面红耳赤,急极败坏之下,他说:“老夫虽不才,却是尊孔前辈,更是在商言商,办学办教育,也是商界一部分。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只有校董,才有发言权。”
鲁迅一听大怒,掏出两个银角拍到桌上:“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于是胡颉刚、黄坚等教授便一同向鲁迅发难,后者是介绍鲁迅来厦大的林语堂的秘书。这让鲁迅更加的忍无可忍。

三、“重的是钱,何曾重过学问”
当时的厦大分为两派,一派是本就与鲁迅等人有间隙的“现代评论派”的宿敌,还有一派就是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认为自己现在是背字连篇,委屈在厦大只是虎落平阳,本就不安心于教书匠的工作,一遇挫折委屈自然不肯屈服。
黄坚曾是北京女师大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在厦门大学则出任林语堂的私人秘书,在北师大时黄坚便与鲁迅矛盾重重;而林语堂是鲁迅来厦门大学作者的介绍人,与鲁迅的关系本来还算融洽,但鲁迅对林语堂“信任黄坚这类小人”的作法实在做不到无视,而林语堂又与顾颉刚等鲁迅的宿敌来往密切,林文庆为了稳定这些厦大的俊杰,不得不左右调停,偶尔便会在这些人中间说上几句让鲁迅如鲠在喉的言辞,久而久之,鲁迅便连带着林语堂一并恨上了,很多次公开场合与林语堂对骂,便也夹枪带棒地捎上林文庆。在鲁迅看来,这些人都是林校长的走狗和打手,“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甚至还翻出了1924年厦大学潮的事指责林文庆。
1924年6月,林文庆正在海外奔走为厦大募捐,因为厦门地处闽南,有很多当地的教授与外省教授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烈,校长又不在,校方慌了手脚,由建筑部主任陈彦廷雇了数百工人对学生们的暴动以暴制暴,据说还死了人。这件事史称“六一流血惨剧”。鲁迅就常拿这件事对当时毫不知情的林文庆大加责骂,而林文庆一介儒生,怎么会是字笔如刀的鲁迅的对手,数番指责之后也恼羞成怒,甚至用手杖追打鲁迅,风度尽失,一时成为笑谈。
而另一方面,林文庆的商界头脑与纯学术的教授们显然也有人生观上的差距,于是摩擦就势不可免。
林文庆不仅大力提高教授工资,用以吸引最著名的学者来学校任教,更大力鼓励教授们著书立说。仅鲁迅就被林文庆催过多次,要他把已经初稿脱稿的《古小说钩沉》稿子交上来在厦大出版,但“放了大约至多十几天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也让治学严谨的鲁迅极其反感。随后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无法与此辈共事的。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
此后与许广平每次书信联系中鲁迅都要义愤填膺地提到厦大和它的校长,“学校以金钱为中心,常是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记得刚入校时,就烦厌不迭地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像养奶牛每日挤奶一样。可见厦大重的是钱,何曾重过学问。”
四、椅子事件
厦大本是侧重理科的,理学院的比重在厦大初期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强,林文庆注重国学,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学院并投入大量资金给国学院,这让理学院的教授们有些怒气,特别是理学部主任刘树杞更是有怒却不敢言,也就将气发在鲁迅等国学院的教授头上。他指使后勤处逼迫鲁迅搬家,且是越搬越小,最后竟将鲁迅逼到了地下室里住。鲁迅在地下室居住时因为光线不够,晚上会点上两盏灯,但后勤处却以浪费能源为由强令鲁迅摘下其中一个灯泡,此事被刘树杞等人巧舌如簧的粉饰得不露一点痕迹,而鲁迅却把这笔账算在了校长林文庆头上,认为是自己的倔强惹怒了林文庆,后半生常常在写到厦大经历的时候就此事以笔做刀,对林文庆“捎带一枪”。
还有几件事经常让林文庆背着黑锅。一是“椅子事件”,有一天,黄坚来到鲁迅居处说是要搬走一把椅子,因为“学校门房缺一把椅子。”鲁迅当即说,“难道门房缺把椅子,就要让厦大的教授坐在地板上吗?”后来鲁迅多次明里暗里说到此事并言之凿凿地声称是林文庆主使。
不久之后国学院要开一个展览会,鲁迅因为手边有不少上古拓片,正好可以充实展品,于是就着手准备,并亲到展馆悬挂拓片。鲁迅的学生孙伏园看鲁迅一个人辛苦忙碌便赶过来帮忙,却不巧被黄坚叫走。鲁迅也认定这是林文庆指使黄坚这么干的。
后人有说当初在厦大,有一个“驱赶鲁迅的流氓集团”,其首脑便是林文庆。其实想想林文庆身为校长,当初重金相请,现在即便要赶走鲁迅不必如此多费手段,只需一纸辞退信便省时省力坦坦荡荡名正言顺还君子得多,大可不必如此在小事上使绊子。
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已经渐渐升级到见面就吵的程度了,林文庆多次安抚,并找人说和都无效果,鲁迅每次上课第一句话准是“这可能是我在厦大的最后一节课了。”一些学生听说鲁迅要走,搞了个不大不小的学潮,要求驱逐林语堂黄坚等一干与鲁迅不睦的人,林文庆当然还是好言相劝左右调停,但这些教授们平时都眼高于顶同行相轻,怎么会在这样的事情面前轻易让步?最终忍无可忍林文庆当众对着鲁迅大吼。“我请你来是讲课的,难道是来捣乱放火的吗?”
即使是与鲁迅搞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林文庆对其也是极力容忍。1926年底,中山大学邀请鲁迅担任文学系教授(后出任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遂于12月31日向厦大提出辞呈。林文庆多次写信挽留,并四方求人,央求鲁迅的友人和同乡甚至是学生向鲁迅表达自己的挽留之情。后来见鲁迅去意已决,又多次设宴饯行,宴会之上又再次致聘书再次挽留,鲁迅对此只付以一笑并不应允。
1927年1月15日下午,鲁迅带着三个国学院的学生离开厦门去中山大学任教,这三个学生仰慕鲁迅,甘愿一同转学去中山大学,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明确说明,此次负气走出的原因是厦大的“校长和几个教授”。
从此,在厦大便有了一桩下不了定论的公案:鞠躬尽瘁十六年的林文庆赶走了任职四个月的鲁迅。
五、“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吗”
1937年夏,日军虎视眈眈,由于南洋经济萧条,陈嘉庚决定将厦门大学出让给国家,当年7月1日完成交接手续。陈嘉庚本来建议林文庆继续任国立厦门大学的校长,但是当局以其任内两次学潮为污点否决,随即任命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博士为首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笔架山的别墅里,林文庆制定了厦大的校训章程;也是在这里,把一所尚显幼稚的大学办成了文、理、法学、教育、商学五个学院21个系的民国时最成熟最知名的高等学府;还是在这里,他完成了《离骚》的英译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翻译的《离骚》英文版是由著名诗人泰戈尔做序的,是《离骚》最早的英译本),并出版了《东方生活的悲剧》、《新的中国》等著作。这是他在大陆的唯一一块净土。别墅里本来是有架钢琴的。每当落日时分,林文庆会坐在琴边,在涛声之中弹些散淡的曲子。据说林文庆最后弹奏的是一曲《忘离伤》,家人建议把钢琴带回新加坡,老人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我连一整个大学都丢在大陆了,不差一台琴。鲁迅当时不是说,中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吗?留着这琴,还可经给这坟场里添些艺术味道。”
而鲁迅临走也真的似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离开一潭污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吗?”在鲁迅眼里,厦大就是不干净的,而罪魁祸首,就是林文庆。

纵观林文庆与鲁迅之间数月之久的敌对和恩怨,从相互敬仰到互为公敌,从相敬如宾到不共戴天,其间透露出的正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左右摇摆和左右为难。
林文庆尊崇儒学,却又是十足的基督徒;他信奉圣母,却又是南洋孔教会的会长,孔子儒学在南洋的唯一传人,他并非反时代逆行的“独尊儒术”,也不盲目的全盘西化;而鲁迅则坚定地以中国传统文化做思想的最终指引又对民国时西方的先进哲学体系有着兼容和吸纳,对于遵孔还是反孔,二人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抵触的相对观念。
文化与理论之争永远没有对错。在这一点上,历史是公平的,厦大也是公平的,厦门大学里时至今日仍处处可见鲁迅的痕迹,甚至从鲁迅的手迹中找到厦门大学这四个字做出校额;而在2006年,厦门大学又建成了文庆亭。
这座纪念林文庆的亭子简简单单的朴素,跟华丽或是风雅似乎不沾边。其亭联曰:“十六载耿耿乎礼门义路,千百年熙熙矣时雨春风”,横批:“唯有文庆”。陪着它不声不响的是一尊塑像,天亭饱满,一付儒雅风采的胡子。《文庆亭记》铭文记载:林文庆校长,“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前驱。”

走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你时时可见一些历史文化遗韵,或碑或亭,或诗或文,或人或景,让人时不时感叹一声:在1900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里,那些时之俊杰,国之伟人,是怎样的风雅又尖锐、迷茫又执著、固执又可爱。
(本文已纸媒发表,转载及约稿请留言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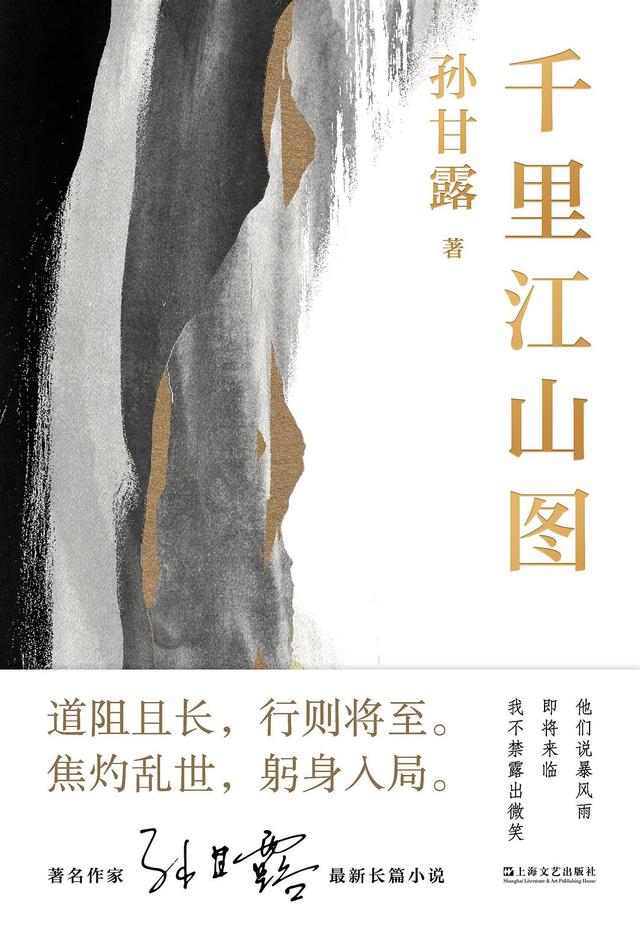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