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汶︱上海摩登的南移:刘以鬯1950年代的南洋足迹

刘以鬯(1918-2018),图为传记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1918》剧照。
起先,淳于白没有注意到那幅画;偶然的一瞥,使他觉得这幅画的题材相当熟悉。那是“巴刹”的一角。印度的熟食档边有人在吃羊肉汤——热带鱼贩在换水——水果摊上的榴梿——提着菜篮眼望蔬菜的老太婆——斗鸡——湿漉漉的地——凌乱中显示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新加坡的“巴刹”。淳于白曾经在新加坡住过。
对于新加坡读者,刘以鬯《对倒》(1972年)的男主角淳于白透过眼前的画作回忆起自己的南洋经历,是一段既亲切又饶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借助淳于白的视角,小说以蒙太奇式的描述手法,将一幕幕充满“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南洋场景展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回顾刘以鬯五十年代所写的南洋小说,这些作品也如同《对倒》中的这幅画一样,可以成为我们审视其时新马文学、文化、政治的重要途径。

刘以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照(左),及九十五岁生日照(右)。
刘以鬯1952至1957年间旅居新马编报。五十年代末,他在新马、香港的报章和通俗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南洋背景的小说。不过,相对于他的上海身份,及其香港经典作品如《酒徒》《对倒》,刘以鬯的南洋小说与编报经历鲜少为人关注。但不论是他笔下的小说人物不时流露的南洋记忆片段,抑或是他后来主编《香港文学》时推动新马华文文学,都证明了南洋经验在刘氏文学生涯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1950年代的南洋,正逢新马独立运动与东南亚冷战的关键时刻,报业与文坛成了各种意识形态角逐的重要场域。刘以鬯拥有“报人”“作家”双重身份,其南洋书写,不但能让我们了解一位来自上海的南来文人如何参与五十年代末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运动,同时也展现了由故国情怀与旅居经历交织而成的摩登南洋图景。
刘以鬯下南洋
早在1948年,刘以鬯就已产生面向海外华人读者群的愿景。他离开上海到香港闯荡,原先希望延续其怀正文化社的理想,发展以海外华人为对象的出版生意,但后来因资源问题作罢,随即加入了《香港时报》《星岛晚报》等报纸的编辑行列。

1952年,刘以鬯只身来到新马编华文报纸。
1952年,刘以鬯接受刘益之的邀请,来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的副刊主编。《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是当时的四大报刊之一。新加坡《益世报》的创刊不但得到于斌主教的支持,还成功聘请到当时香港报界的“五虎将”——刘以鬯、刘文渠、张冰之、钟文苓、赵世洵——前往当地办报。不过,纵使创刊时声势浩大,该报后来却因为资金与管理问题在四个月后迅速倒闭。《益世报》的昙花一现似乎预示了刘以鬯南洋事业的坎坷。
四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报业兴盛,需要大量有经验的报人主持大局,因此吸引了许多文人南下。但由于行内竞争激烈,加上后来新马政府着力打压黄色与政治立场偏激的新闻内容,许多报纸的寿命也十分短暂。《益世报》倒闭后,刘以鬯曾出任马来亚吉隆坡《联邦日报》的总编辑,但该报也在几个月后停刊。不久,他又回到新加坡加入《中兴日报》。其后,刘以鬯辗转于不同的新马报刊如《新力报》《钢报》《狮报》《铁报》《锋报》担任总编辑或主笔,不过这些小报常常面临资源不足或销路不佳的问题,而他在各报的任职时间也不长(郑文辉:《小报的兴衰》,《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新马出版社,1973年,76-80页)。
相比起刘以鬯早期在重庆与香港的办报经验,他在新马的事业可谓不尽顺心。然而,尽管南洋报业沉浮郁郁不得志,刘以鬯的南洋编报经历却给予了他深入了解五十年代新马文学与社会的契机。这,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刘以鬯的第一本书,上海桐叶书屋1948年10月初版。
南下新马时,刘以鬯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除了参与当地的文学活动鼓励年轻作家外,他也经常以“刘以鬯”“令狐冷”“葛里哥”(该笔名受启发于他喜欢的美国好莱坞演员Gregory Peck)等笔名在南洋报纸的副刊发表作品:不论是《南方晚报》,《益世报》的《语林》与《别墅》,还是《新力报·新草》《锋报·芒刺》《铁报·副叶》,都有他活跃的身影。刘以鬯旅居新马期间正式出版的小说有三部:《第二春》《龙女》《雪晴》(后两部曾连载于新加坡的《南方晚报》),但它们皆非以南洋为背景。他另外两部关于南洋的中篇小说《星嘉坡故事》《蕉风椰雨》(原名《椰树下之欲》)则应该是在回港后完成的作品——首先刊登于有美国驻港总领馆新闻处(简称“美新处”)背景的香港虹霓出版社发行的小说杂志《小说报》,后来才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王梅香:《隐蔽权力:美元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0-1962)》,第五章“译书计划下的‘共同创作’(collaboration)”,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286页)。
刘以鬯1957年返回港后仍继续为新加坡的副刊供稿。1958年至1959年期间,他应《南洋商报》总编辑李微尘之邀,写了一系列南洋色彩丰富的短篇小说,发表于该报副刊《商余》。这些小说经由刘以鬯太太罗佩云女士的整理后,收录于2010年香港获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热带风雨》。

《椰树下之欲》

刘以鬯的小说
“马来亚华文文学”本土化运动
马来西亚作家马汉回忆起刘以鬯五十年代刊登在《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时表示:刘以鬯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读者,主要是因为他晓得如何准确使用当地的语言与读者熟悉的主题,反映马来亚人民的生活,这构成了其小说的“南洋色彩”(马汉:《刘以鬯印象记》,《文学因缘》,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1995年),第8页)。虽然这些作品主要刊登在面向南洋大众读者的副刊,或许会被视为具有商业考量的“娱人”作品,但我们也应该从战后新马华文文学本土化的脉络,考虑其中“南洋色彩”的经营。
二战结束以后,新马的华族社群逐渐把居住地视为家乡,自五十年代中期,新加坡与马来亚政府也开始与英殖民政府展开 “默迪卡”(马来文的merdeka的译文,意指独立)谈判。1957年,新加坡与英国政府达成了允许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协议,而马来亚联合邦也在同年成功正式脱离英国独立。为配合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新马文坛的作品逐渐从面向中国的“侨民文艺”,转型为着眼本土的“马来亚华文文学”。


刘以鬯在《南洋商报·商余》发表的短篇小说
与此同时,新马也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Malayan Emergency,1948-1960年),当局为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颁布了不同法令。像1958年的禁书令就造成了新马市面上中文读物严重短缺,促使当地书商必须另辟中国以外的货源,并且自行为新马读者出版书籍,而这也间接造就了新马与香港文化界、出版业之间的紧密关系。面对中文读物短缺,政府呼吁本地作者放眼本土,配合自治与独立建国的趋势,努力生产属于马来亚人的马来亚文学,以建立起马来亚族群想象的共同体。对当时的执政者而言,培养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尤其重要,这将有助于减少华人族群认同祖国——中国的意愿,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与传播。
这股本土化趋势当然不限于文学。南洋市场的三大电影巨头邵氏兄弟、光艺、国泰电懋也在这一时期积极筹拍有关新马题材的电影,迎合当地观众的口味。值得注意的是,刘以鬯的短篇“电影小说”《热带风雨》(1959年)便刊登于邵氏杂志《南国电影》的文学栏目。这是一个凄美的异族恋爱故事,主人公分别是来自新加坡的华族城市少年“我”与马来少女苏里玛。小说的场景被设立在远离新加坡都市的马来亚“甘榜”(马来文Kampung的译文,意指乡村),全篇亦包含了对于马来婚礼传统、马来舞蹈音乐、回教习俗、娘惹(即土生华人)生活习惯,以及南洋独特建筑如“奎笼”(即建在水面的屋子)的类似民族志(ethnography)的详细描写,叙事的手法极具电影画面感。

1959年10月的第二十期《南国电影》里署名“葛里哥”写的《热带风雨》。
异族婚恋
类似《热带风雨》中的异族恋爱,是刘以鬯南洋小说经常出现的主题。五十年代,许多新马作家开始通过异族恋爱或异族友谊的故事,探讨当地华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以表示对各族齐心建设多元文化的独立马来亚的憧憬。不过,刘以鬯创作此类小说,似乎更有意探索新马华人社群通过异族婚恋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早期“过番”(闽粤方言,即下南洋)的华人以男性居多,刘以鬯或许是为了呼应这段新马华人社群的集体记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即是漂泊在南洋的离散华族男性:像是以自身经验为原型的苦闷南来文人、南下谋生的“新客”(泛指十八世纪末以后移民到南洋的中国人),或是常年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男性。这些男子经常与当地的马来女性谱出恋曲,后者往往被刻画为沉默被动的“他者”。
例如《巴生河边》(1958年),虽然讲述的是马来少女莎乐玛在巴生河边耐心等候华族男友郑亚瓜归来的恋爱故事,但整篇小说却以郑亚瓜与顺风车司机间的对话为叙事结构,读者仅能从对话中拼凑出莎乐玛的形象,想象郑亚瓜口中的莎乐玛那单纯与沉默的性格。直到结尾,莎乐玛才出场,但读者也只能通过两个男人的视角,遥望静静伫立在巴生河边的莎乐玛和她怀中的孩子。
换言之,刘以鬯异族婚恋小说中这些穿着传统服饰甲峇耶(马来文kebaya的译文)或爪哇沙笼(马来文Javanese sarong的译文)的马来女性,不仅仅是“南洋色彩”的载体,她们在固定地点守候、等待男人归来的身体,也给予了这些漂泊南洋的华族男性建立家庭、落地生根的可能性。进一步推论,我们或许也能把刘以鬯南洋小说中的异族恋爱,视为这一时期马来亚文学建构主体性与本土性的隐喻。小说里的马来女性形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南来文人东方主义式的南洋想象(Nanyang Orientalism),却也呈现出马来亚文学本土性,与新马华人的离散经验、性别政治、文化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甚者,如是女性形象,还关涉刘以鬯对于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叙事策略的继承与改写。新感觉派小说擅以男女关系反映社会化历史经验,即利用行踪捉摸不定、喜爱速度的摩登女性身体,象征三十年代的现代都市——上海对男主角的诱惑与疏离。刘以鬯的南洋小说倒转了这一性别权力关系:在其时“南洋侨民”向“马来亚国民”身份转型的社会现实下,刘氏以位置固定的马来女性身体,意指漂泊南洋的男性主角落地生根的希冀,协助读者树立对于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上海摩登”南移

梁秉钧等编:《刘以鬯与香港现代主义》
也斯说,刘以鬯早年的上海洋场经验,使他比别的南来作家更晓得如何在作品中把握都市脉搏(也斯:《从〈迷楼〉到〈酒徒〉——刘以鬯上海到香港的现代小说》,梁秉钧等编:《刘以鬯与香港现代主义》,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刘以鬯本人亦曾以早期作品《露薏莎》为例,坦言自己受了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影响,喜欢大城市人的生活。或许,南下以后的刘以鬯就如同《对倒》里的淳于白,“将回忆当作燃料”推动自己的生命力,他小说的都市描写所散发的浓郁 “上海” 摩登气息,仿佛是对故国回忆的文学投射与想象延伸。刊于《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丝丝》(1959年)写道:
之后我常常见到丝丝。在武吉智马的马场,她挽着一个红毛老头的手臂。在快乐舞厅的舞池中,她同一个印度年轻人跳森巴。在莱佛士酒店的餐室内,她与一个马来商人同席对杯。在水仙门的服装公司门口,她独自一个人看橱窗。在厦门街的街边,她有说有笑的吃虾面。
刘以鬯的笔锋,宛若电影镜头,透过男主角的凝视,捕捉摩登女郎丝丝的行踪。新加坡都市场景的切换,仿佛蒙太奇,暗示了紧凑的现代都市步伐。小说中的摩登女郎,亦如新感觉派小说摩登女郎的副本,呈现为歌台红星、上班族、舞女的不同形象,偕同不同族裔的男人,游走在歌台、酒吧、酒店、咖啡室、百货公司、电影院、赛马场、舞厅等娱乐空间。她们不仅是男主角凝视的对象,也是展现南洋都市现代性、消费娱乐、多元文化的重要媒介。
在刘以鬯罗列的众多南洋娱乐项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南洋歌台文化的刻画。歌台主要设立在新加坡著名的三大游艺场——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之内,曾深受新马华人欢迎,在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当时许多香港艺人、歌星纷纷前往新马登台演出。刘以鬯任编辑的小报如《新力报》《锋报》亦经常报道歌台与艺人的新闻。可以说,歌台仰赖小报宣传明星活动,而小报须靠歌星的新闻促进销量,二者相辅相成。刘以鬯南洋办报,游走在歌台的幕前幕后,结识了五十年代的南洋“歌舞皇后”庄雪芳,南洋歌手潘秀琼,在新马登台演出的香港女歌星顾媚,以及后来成为其太太的现代舞蹈家罗佩云等艺人,这使他深谙歌台文化,更间接促成了其南洋小说的相关侧写。

刘以鬯与罗佩云结婚照
中篇小说《星嘉坡故事》(1957年)讲述了由港抵埠的报人张盘铭与南洋当红歌台明星白玲的恋爱悲剧。刘以鬯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对歌台文化的观察。比如张盘铭初次到新世界观看歌台表演时,透露出这样的偏见:
我对于听歌并不如一般华侨那么热心,记得我刚到星嘉坡的第一天晚上,同事们就邀我去听歌……我不懂这一种在其他中国城市并不普遍的娱乐事业,怎么会在星嘉坡发展的如此畸形,后来才知道上歌台除了“吃”与“听”之外,最主要的享受是“看”——看花枝招展的歌女们站在麦克风前的装腔作势。
但是,歌台却是他认识女主角白玲的重要地点。在新感觉派小说里,舞厅是彰显男女关系与摩登文化的关键场景,于是,刘以鬯南洋小说的歌台文化便可视为上海舞厅文化的南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后者的改写。除了歌台,《星嘉坡故事》的笔触还伸向了首都戏院、国泰戏院、加东海边等娱乐场所,它们一起组成了繁荣的热带都市景象。刘以鬯2013年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时表示,自己对新加坡的加东海边、康乐亭、红灯码头难以忘怀,这些地方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南洋小说。

《星嘉坡故事》
概言之,造就刘以鬯文学观,及其作品独有面貌的,除了他自学生时代吸收的西方文学资源,更有这么一条“上海—南洋—香港”的离散路线。而有别于刘以鬯用以“娱己”的现代主义与实验性作品,他“娱人”的南洋通俗小说则呈现出了现代性的另一面向。他小说中由充满热带风情的马来女人、都市娱乐消费文化构成的南洋文学景观,与其时新马左翼写实主义文学作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可以说,刘以鬯以个人的上海视角与回忆,在小说中重构本土女性、摩登女郎与都市空间,仿若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南洋延伸,给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运动带来了别有韵味的“新感觉”。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香港文化资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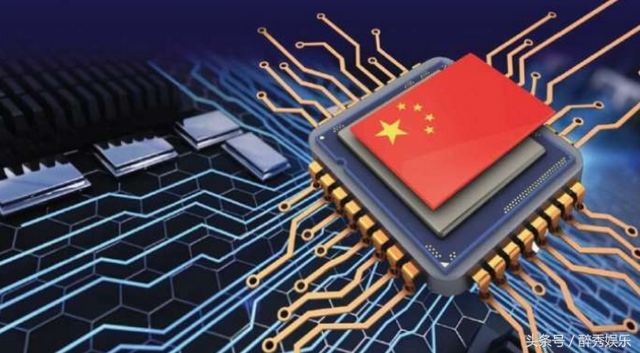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