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高 玉:汉字简化思想:百年历程及其反省
本文来源:南国学术
·时代问题论争·
汉字简化思想:百年历程及其反省
高 玉

[作者简介]
高玉,1987年在湖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在武汉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2012年起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7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从“话语”视角论中国文学》《艺术起源怀疑论》等。
摘 要
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后,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简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现的,1950年代制定并推行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古已有之的简化字一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如今强行废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汉字的六书原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强行“转正”为印刷字、正字是有违其本性的。作为“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但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化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重新思考恢复繁体字的时候了。
关键词
汉字 繁体字 简化字 汉字改革
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改革又是汉语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汉字简化对汉字改革、汉语变革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语言学界的思考特别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识人(包括一些语言学工作者)主张恢复繁体字,但为什么要恢复?其深层的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是什么?也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达;至于如何恢复?恢复到什么状况?学术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设计。鉴于此,笔者试对清末至今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背景、理论、推行方式以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检讨,希冀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汉字、汉语自产生之后就一直在变化着。汉字起源于图画,从形体上经历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的过程,在手书的意义上还有行书和草书。总体上看,汉字的变化是一种从图画到符号、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杂芜和枝叶的东西不断地脱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东西;但是,汉字的数量和书写则呈相反的变化,字数越来越多,异体字越来越多。汉语的变化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书面语来源于口语,口语不断简练而雅化,再加上文人们不断丰富和创造,使它越来越远离口语;另一方面,口语不断变化,也不断丰富,自行发展,越来越远离书面语。除了秦朝的“书同文”以外,中国古代不论是汉字的变化还是汉语的变化,都是自然流变,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强力所为,所以变化速度缓慢——汉字“体”的变化比较大,但结构变化不大。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提出汉字、汉语改革的问题;但自清末以来,汉字、汉语改革却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并最终导致汉字、汉语发生巨变:在汉字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简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化、拼音方案、读音统一等;在汉语方面,语言体系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变成现代汉语,与此相关的语法、词汇、词义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末以来汉字汉语变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开始交流以来就时有冲突,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落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则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势,中国一方面是抵御、自保,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进而痛苦地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反思的路向和进程可以说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开始时认为器物不如西方,后来又认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后认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国民素质不高等,于是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和文化就此发生了现代转型,于是有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清末汉字汉语改革就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发生的。当时接受了西学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不发达,国民素质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和汉语——汉字繁难(难识,难写,难记),汉语文言不一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掌握运用,而民众大多数是文盲,不能读书看报,不能进行书面表达,甚至于最简单的记账都很困难。
汉字复杂难学,可以说是清末语言学界普遍的观点。例如,卢戆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林辂存说:“我国文字,最为繁重艰深……中国字学,原取象形,最为繁难。”陈虬说:“字又着实难识得很……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沈凤楼说:“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杨琼、李文治说:汉字“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马体干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因此认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态度和具体方案。
清末兴起的汉字改革有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三种方案。一是最激进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的李石曾和吴稚晖。他们认为,西文优质,与其学习、模仿西文,对西文进行改头换面的汉化,或者汉语西文化,还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由于民族自尊的原因,这种主张在清末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还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后却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中不少人认为汉字终当废除,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都持这种观点;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废除汉字是困难的,所以主张用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汉字,但废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态度和方案,以刘师培、潘籍郛、卢戆章、蔡锡勇、王照、劳乃宣等人为代表,主张不否定汉字、汉语、文言文,但在汉字以外另创造一种简字、快字、合声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语、官话等构成的汉语书面语,也即宽泛意义上的白话,前者供知识分子使用,后者供大众使用。这种态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态度和方案。据倪海曙统计,从光绪十八年(1892)卢戆章提出中国第一套汉语切音字方案,到宣统二年(1910)郑东湖提出汉字笔画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时间共产生了二十八种新汉字方案,所创造的新汉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汉字笔画切音字、速记符号、自造符号、数目代字等,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实施,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书,但最终都成为了历史;不过,它们对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电报数码、速记等有很大影响。三是保守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对繁体字进行改造、简化或者简便。这是一种思路很不清晰的态度,当时缺乏深入的讨论,提出的方案并不多,也不具体,但却是本文最为关注的。
简化字可以说古已有之,符号化就是一种简化。秦隶之后,汉字结构大致固定,之后的汉字变化主要是减省笔画,或者变化笔画。中国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体在汉字的形体上相对规范,但仍有一定的随意性;大量的文书则是手写,而手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特别是流布范围比较小的文书如日记、书信、账目、收据、借据、文告等,书写更是随意,大量使用别字、错字(例如,偏旁错误,笔画错误)、简笔字、破体字、草书楷化字、符号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们称这些字为“俗字”。最初这些字具有私人性,书写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随着文书流布范围的扩大,这些字慢慢流行开来,越来越被认同、模仿,于是,错误变成了正确,别字变成了通假字,简笔字变成了异体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这是事实上的汉字简化。
清末最早提倡简化字的是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说:“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而其代言语之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我国文字,义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欲求读书识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简字之法所由创也。故简字与旧有文字,相去太远,一时不能冀其通行。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语。如‘體’作‘体’,‘燈’作‘灯’,‘歸’作‘归’,‘萬’作‘万’,‘蠶’作‘蚕’之类,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张此议,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文章发表后,有读者致函提出疑问,陆费逵又作答文说:“采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简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创造更难,就俗字而采用之,不过略减正体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记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采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体代之也。”他认为,使用俗体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处极多,而苦笔画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笔字,不知不觉,转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体字。以其易写易记,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极易,虽功令悬为厉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体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这里所说的“简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卢戆章等所说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简化字,后来称之为“减笔字”“简体字”。陆费逵主张用已有的、已经广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简化字,并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简化,这与后来的简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陆费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简化汉字设想和思路,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回应,当时汉字改革的主流还是切音字、简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问题才再次被提了出来。
二
语言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白话文就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与清末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不同,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更关注的是汉语而不是汉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但同时又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存废问题搁置起来,专注于汉语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话文,否定并废用文言文。对于吴稚晖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广泛的“汉字革命”主张,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也是有响应的,概括起来就是提倡简化字。
翻阅《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阵营最早提出简化汉字的人是钱玄同,但其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前夕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长文的时候,他是赞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又转而赞成吴稚晖已经放弃的“万国新语”的观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世界语与文学》《答陶履恭论Esperanto》《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答孙国璋论Esperanto》《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汉文改革之讨论》《答姚寄人论Esperanto》《答胡天月论Esperanto》《答区声白论Esperanto》《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Esperanto与现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张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与胡适、陈独秀等人主要思考语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既思考语言改革,也思考汉字改革,他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汉字、汉语反思基础上的。民国初期到“五四”前后,学术界一些人发现,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不能准确表达西文的思想文化。钱玄同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语言上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不同,钱玄同主张废除汉语,改用世界语,或者在汉语之外增加世界语:“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好?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五四”初期的钱玄同很激进,不仅反对文言文,也反对白话,反对汉字,反对汉语拼音化。他说:“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汉语不能拼音化的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讲得更明确:“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汉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汉字、汉语,改用世界语,“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至少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在通行汉字汉语的同时推广世界语。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为一种统治性的语言大势已去,白话文一统中国不可逆转,钱玄同主张世界语的文章就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所以,对于在中国推行世界语取代汉语——不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话文,钱玄同自己也没有信心。特别是白话文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为“新国语”之后,钱玄同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语言上转而支持“国语罗马字”。1923年,他提议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两年后又说:“说到制造中国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现在也主张用罗马字母。以前《国语月刊》出‘汉字改革号’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倾向于罗马字母了。不过彼时被音理所囿,以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够用与发音密合一点的,所以又想试用标准音符(国际音标)。但是不久就觉得这个意思是错误的。”而在文字上则主张,改造汉字即减省汉字笔画。钱玄同对于汉字的态度可以说由“汉字革命”转变为“汉字改良”。
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这是中国自汉语产生以来首次系统地提出的汉字简化字方案。他说:“前几天,独秀先生对我说:‘表中国国语的文字,非废去汉字、改用拼音不可。’这个意思,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制成以后,恐怕还要经过许多波折,费上无数口舌,才能通行。我以为我们就使讲‘一厢情愿’的话,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如此,则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汉字的声音难识,形体难写,这是大家知道的;今后社会上一切事业发展,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处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其补救的办法就是减省汉字的笔画。这是一个妥协、无奈、暂且的办法,但却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现实性的办法。钱玄同提出的汉字简化的八种方法,都为19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
到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一期“汉字改革号”,其中有胡适、黎锦熙、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赵元任等人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对于改革汉字达成了共识,差别只是简化汉字与国语罗马字的方案。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选了《简体字谱》;在此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8月21日发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但却遭遇强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废止《第一批简体字表》,这对于汉字简化之路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1936年后钱玄同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于1939年逝世,简化字研究、倡导以及推行虽然不乏来者,但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强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声音所淹没。
1949年始,汉字简化之路峰回路转。这年5月,黎锦熙联合当时北平各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写信给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动文字改革。吴玉章先请示刘少奇,又写信给毛泽东,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吴玉章为主席,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成员既有学者也有官员,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于之前在请示刘少奇时,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化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因此,简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项内容。之后,在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的大力推动下,汉字简化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简化字方案从酝酿到出台到最后推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汉字难识、难读、难写,是普通大众提高文化素质的瓶颈,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进行新文化建设,这正好是一个契机。二是旧中国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统的教育体制又不可能一时建立,识字特别需要“速成”,简化字为汉字识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与国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设不一样,新民主主义文化更强调大众文化建设,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大众识字问题,汉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该机构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范文澜为副主任。
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并于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
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全文。
国务院“决议”的公布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发表,标志着清末以来汉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后,汉字简化运动还发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汉字简化方案”小组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修订,发布《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同时编辑出版《简化字总表》。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征求意见,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用;但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止这个方案,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2009年,教育部新研制出《通用规范汉字表》,网上公布以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设计对44个汉字进行“整形”,但遭到广泛的质疑,2013年国务院最终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时,没有采纳汉字整形方案。与1986年《简化字总表》相比,《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了226个类推简化字,如“闫”等。而对于“整形”字,研制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个说明:“鉴于字形调整目前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对印刷宋体字的字形规范,也不应该只着眼于宋体字本身,还应该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几个关系的协调问题,如各种主用字体之间的协调、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协调、已定规范汉字与大字符之间的协调等。如此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让《通用规范汉字表》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做出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汉字“整形”方案虽然“失败”了,但可以肯定,汉字简化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三
反思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各种方案、历程以及理论,需要检讨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初期,语言学界对于简化汉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汉字改革的暂且办法。1955年,毛泽东还说:“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但1960年代之后,简化字被当作了汉字的终极形态,汉字简化被误作为汉字改良的主导方向。如果说清末、民国的简化汉字是“汉字病”之“止痛”的话,那么1950年代汉字简化则是“汉字病”之“根治”了。
陆费逵最早提倡简化汉字,但他同时又明确说简化汉字不是汉字改良的“正法”。同样,钱玄同“五四”之后一直提倡简化汉字,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包括简化原则、简化方向和具体措施等,但他认为解决汉字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汉字革命”,即“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把汉字改为拼音的中国新文字,将来总有这一天”。由于汉字革命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筹备”期还不能完全脱离汉字,而简化字则是“补偏救弊的办法”:“有的主张将国语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张将现行汉字减省笔画的。……我也是持这种主张的一分子。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可见在民国时期,简体字并不是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更关注的还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国音统一等问题。
1950年代,汉字简化字运动兴起,发展成为国家行为,最终产生《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并通过行政方式大力推行,从而实现全国文字印刷简体字化,似乎简化字方向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实不然。1951年,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强调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简化不过是暂时方案,是为最终汉字拼音化做准备。吴玉章说:“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也明确说:“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由此可见,简化汉字在近百年汉字改革中不过是附属品,被当作是准备性的、过渡性的。然而,汉字一旦简化并全民运用、普及,就很难有其他可能性了。
近百年汉字简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末和民国是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另一个阶段。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个阶段总体上是学术推动,后一阶段总体上属于组织推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主要是学者探讨,提出方案,讨论基本限于学术领域,虽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钱玄同等人设计的“第一批简化字”就得到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支持,从而以教育部名义发布命令,但民国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非常软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学者、政客的反对声中宣布收回、废止。之后,《第一批简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钱玄同主持编选的《简体字谱》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国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所吸收,《汉字简化方案》和《第一批简化字表》在思路、观念和具体的方法上、具体内容上都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学术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学术背后的力量才是决定其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
而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运动是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确定各种组织机构,各种宣传,最后层级推进,从而以一种严格的行政方式推行。从相关的文献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国务院组织专家,经过反复讨论,八易其稿,才最后制定出来的;这中间又反复征求专家、学者以及普通群众的意见。这种大规模的行为,是任何一个学术团体都无法完成的。简化字方案出台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决议,国务院公布决议,教育部发布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通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分别发表“社论”,这与清末与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正是因为强大的行政推动力,所以1950年代汉字简化运动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大陆就废除了繁体字,实现了全国教育、印刷、手书的简体字化。
当然,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字改革,吴玉章等人最初设想和试图推行的还是在民国时期就思考比较成熟、并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汉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结果是,拼音文字后来被放弃了,仅只留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而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拼音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汉语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一种对汉字进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汉字,也不能替代汉字,本质上是汉字的辅助性工具,解决了汉字不能表音的问题,当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讯、编序、检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汉语拼音新文字则是反汉字的,主张废除汉字,使汉语脱离汉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有这样的话:“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办法。”由此可见汉语拼音和汉语拼音文字之间的本质差别。事实上,19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制定并推行简化汉字,选定并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的进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话是统一国音,汉语拼音则是为汉字标注国音,两者于汉字来说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简化汉字对汉字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真正改变了汉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意义和作用争议很小,简化汉字却争议很多,因为它给汉语和汉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四
由于汉语在读音上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以致同样是说汉语但地域不同的人却无法交流,但因为有汉字,才维系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假如语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国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国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曾经设计出包括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种方案,假如当时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国就不仅是语音不统一,而且文字也不统一,北京人到广州还得带翻译。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语言学领域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太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并且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国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
的确,简化字不是清末才产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简化字虽古已有之,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强行废除正字,通行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实际上是违背了汉字自然流变的规律。草书是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草书本质上是汉字快速书写的结果,快写的过程中自然有很多笔画省略,在这一意义上,草书可以称为简体字,汉字简化借鉴草书的简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书异常复杂,千变万化,有时一个字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写法,有的写法不仅与正字相距甚远,互相之间也相距甚远,没有相似性和关联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书中基本上可以写成一个字,如“成”和“来”、“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点画在草书中可以写成一样,如单人旁和双人旁在草书中都可以写成一竖,“二”“止”“工”“土”“豆”“![]() ”“匕”“丂”“䖝”“八”“人”都可以写成二横即“二字符”。正因为如此,草书的很多字不仅一般人不识,就连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的人辨识起来也不是很轻松,需要借助释文以及草书工具书。所以,简化字的草书楷化方式虽然有历史的、书写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其实是不足为据的。
”“匕”“丂”“䖝”“八”“人”都可以写成二横即“二字符”。正因为如此,草书的很多字不仅一般人不识,就连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的人辨识起来也不是很轻松,需要借助释文以及草书工具书。所以,简化字的草书楷化方式虽然有历史的、书写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其实是不足为据的。
同样,俗字、手头字包括破体字作为简化字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俗”字,是相对于“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对其作过区分,张涌泉教授的解释是:“俗字是一种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它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于平民百姓使用。颜元孙的所谓‘通者’,其实也是俗字,只不过它使用的范围更大一些,流延的时间更长一些。换句话说,‘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俗字可以变成“通字”,通过流行可以变成正字,但这个过程在自然流变中非常缓慢。汉字在唐代之后已变得相对稳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并不容易,因为正字更有优越性,更广泛地被认同和接受。
根本原因还在于,俗字也好,手头字也好,其构成很多都不符合汉字的基本规则,即不合六书原则,很多字可以说是很任意的符号,也可以说是“黑字”,有时只有书写者和特定的接受对象明白,甚至有时就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与陆费逵提倡俗字一样,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陈望道等二百余人、十五家杂志社发起手头字运动,并挑选了三百个手头字作为简体字进行推广,其中约有一半的字被后来的第一批简化字所采用,如“与”“过”“呕”“对”“尽”“怜”“卖”“战”等,还有一部分被已经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所采用。《推行手头字缘起》这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勾普及到大众。”这实际上是让正字迁就或让位于手头字,也可以说是文字下移。但手头字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第二批简化字被废止就说明了其问题。原因在于,手头字很随意,很多是破体字、别字、错字、生造字,不符合汉字规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丰子恺曾描述民间手头字的书写状况:“我家自洪杨以来,以开染坊为业,我十来岁时,每逢年假,店里忙的时候,被母亲派到店里去帮忙……因此学得了染坊账簿上所惯用的种种简笔字,例如‘三蓝’,他们写作‘三艹’,不过艹字最后一笔下面打一个弯曲。‘二厘’,他们只在‘二’字的下一画上拖一撇,其余不胜枚举。”后来,作者在上学时也写手头字,如把“青出于蓝”写作“青出于艹”,老师骂他说:“你倒不写青出于卅?”染坊里约定把“蓝”写作“艹”,“厘”写作一撇,几个人认同是没有关系的,但推广作为全民规范字却是有问题的,不能说群众使用了就是正确的。所以,俗字和手头字在生活中都限于手书,都只适用于通俗文书,主要是记账、书信、药方,便条等,通行的范围非常有限,具有约定性,如果强行“转正”作为印刷字、正字,其实是有违其本性的。
钱玄同曾归纳出八种简化字方法:“将多笔画的字就字的全体删减,粗具匡廓,略得形似”、“采用固有的草书”、“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采用古体”、“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别造一个简体字”、“假借它字”,但这每一种方法都是有问题的,都会造成混乱。例如,现代简体字中“台”“檯”“臺”“颱”四个字合并成了一个字,还有“台”作为“构件”的字,“构件”有时可以类推简化为“台”,有时又不能类推。本来,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极分明的,但简化成一个字之后,意义也合并了,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得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又如,“蒙”“濛”“矇”“懞”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为异体字;“复”“覆”“復”“複”四字不分,“覆”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干”“乾”“幹”三字不分,“干”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乾坤”不能简化为“干坤”,还有“后”和“後”简化之后不再作区分,以致书法家有“影後”之笑话。汉字是“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它希望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张书岩等人总结简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适当”,“对于偏旁的简化和类推规定得不够明确合理”,“计划性、系统性不够,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数简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笔画不适当”,“某些简化形体代替的偏旁过多”。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并且难以改正。汉字简化的“利”远小于其“弊”。
1960年代简化字推广之后,国家严格控制出版繁体字书籍,繁体字从中国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这种局面维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来,繁体字的著作越来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著录用繁体字出版,后来研究古人的现代人学术著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再后来一些与“古”有关的边缘性著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近人的著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启功丛稿·艺论卷》都是繁体字印刷的,极少数翻译著作如《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也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释是:“由于本书所研究的19世纪汉语语料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汉译本全书也使用了繁体字。”尽管解释很勉强,但可见繁体字的出版规定不断地被突破。繁体字在学术领域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有品位的象征,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古代有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已经开始恢复繁体字写作,除了时尚因素外,更多是为了准确。例如,在古人那里,“颱風”就是“颱風”,现在把它写成“台风”是错误的。
只要中国古代典籍不消灭,繁体字就不可能废除。繁体字与简体字在使用上是不对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简体字书籍可以转换用繁体字来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简体字印刷,简体字印刷古籍会造成很多错误、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国目前事实上是繁体字、简体字并行使用。一个国家是这样,国家中的许多个人也是这样。认识繁体字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素质之一,而且繁体字有越来越通行的趋势,所以中国人越来越需要学习两种字体。这有点反讽,本来当初探讨并推行简体字是为了减省汉字学习的负担,但现在不仅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增加了负担,不仅要学简体字,还要学繁体字;过去,繁体字虽然书写麻烦、费时,学习上难了一点,但那时只学习一种,现在则要学习两种字体,而且简体字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因为简体字中很多字都与字义没有关系,是硬性规定的,只能死记硬背。1950—1980年代,手书还非常普遍,应用也非常广泛,简体字在书写上的确可以节约一点时间,但这点时间相对于整体汉字汉语运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社会特别是计算机普及之后,就连这点微不足道也没有了。现代人大多都用计算机书写,不管是拼音输入法还是五笔输入法以及其他输入法,简体字和繁体字敲打键盘的次数在技术上是一样的。简体字对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台湾使用繁体字,普及教育并没有因此而落后,并没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简体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因为普通国民很多人都不认识繁体字,因而不能读繁体字印刷的古籍。
在中国内地,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来保护简体字,推行简体字,限制繁体字的通行,但它对于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华人聚集较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不具有约束力,无法改变这些地区和国家使用繁体字的现实。随着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特别是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中国内地用简体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汉语用繁体字,这是不利于文化交流的,简体字事实上越来越成为中国内地书籍向海外传播的一大障碍。同时,内地汉语用简体字,海外汉语用繁体字,会造成汉语的分裂,对汉字和汉语都是巨大的伤害。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简体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负担、一个包袱,即使现在废止简化字,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既有民族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有语言共同体,并且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在语言共同体中,汉语是重要而有影响的共同体,但简化字是不利于汉语共同体建构的。因为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但如果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体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
反省1950年代的简化字运动,简化方案从酝酿到出台用了六年时间,期间也曾反复修改和征求意见,但对于涉及千秋万代的文化大事业来说,整个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学术上的论证,很多问题没有考虑到。相反,1980年代对于汉字简化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是正确的。例如,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王码输入法被阻止进入小学语文课本,汉字整形没有获得通过等,否则,汉字将更加混乱,中国人学习汉字的负担将更重。语言越是成熟,就越是复杂,只有复杂的语言才能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汉语作为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数量的汉字作为支撑,并且汉字是需要一定笔画的,一定数量笔画的字特别是形声字反而容易识别和记忆;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笔画简单的字,如“已经”的“已”、“自己”的“己”、地支的“巳”,还有“日”“曰”等。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包括字形字义识别和记忆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更能够被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所接受。
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重新思考恢复繁体字的时候了。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第87—98页。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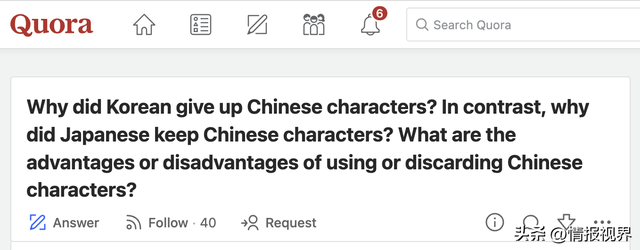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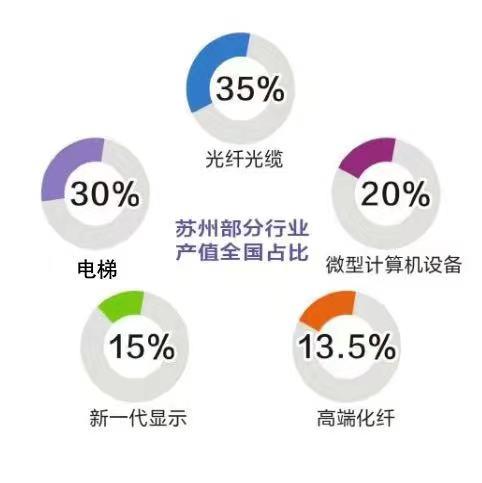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