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彧君:我不是一个着急的人

陈彧凡、陈彧君艺术装置作品《木兰溪》系列(资料图片)

第二季“重返木兰溪”艺术实践学者论坛现场林清煌 摄

陈彧君(后)坐在老乡摩托车上。林清煌 摄
人物简介:
陈彧君,1976年生于莆田,199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他以拼贴式绘画为艺术界熟知,是中国“70后”新生代艺术家中坚力量。他的艺术植根于传统宗族、区域环境和个人记忆,具有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域文化特征。从2007年以来,他以故乡的木兰溪为母题,创作了“木兰溪”“木兰溪·渡”“木兰溪·厝”“生长”系列装置及绘画作品,作品先后被国内外知名美术馆收藏。从2020年开始,陈彧君连续两年在莆田发起“重返木兰溪”艺术实践活动,探索地方文化的意义,在网上引起热议。
原乡情结,始终是陈彧君创作的母题。这两日,陈彧君一直在重庆龙美术馆布展个展《漂泊:陈彧君的多重原乡》,仍是以故乡为主题。他究竟有一个怎样的故乡?为何一次次地重返木兰溪?
“2020年,开始做‘重返木兰溪’项目。在宅家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艺术到底是什么,能做什么。疫情来临之前,我一直在工作室里创作,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封禁?这让我一下子警醒起来。于是,解封之后,我决定走进社会的现场,和我的朋友们一起重返木兰溪。”陈彧君说,因为疫情,当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旅行不再像以往一般便利时,大家会开始探索附近,重新思索地方文化的意义。
溪畔生活
莆田华亭镇园头村,位于木兰溪畔。陈彧君就住在距离溪边两百米的老厝里。即使时隔多年,他还是难以忘记这样的情景:晚暝时,山高月小,月升中天。月亮的光,银灿灿的,照在溪面上,像是母亲手里浣的白纱。他和胞兄陈彧凡跃入水中,在满是月光的水里游。他把自己伸展开来,接受水、晚风、蛙鸣给自己的一切意象。
园头村,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村子,类似一个孤岛。村里大部分的田地,种的是小麦。因为地势高,水无法大面积灌溉上来,所以,村里大部分田地是旱地,只能种一年一熟的小麦。怎么讨生活?园头的人开始外出,下南洋。他们顺着木兰溪出发,去寻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这造就了园头奇特的人口结构:三分之一在国外,三分之一在外地,只有三分之一留在村里。在外发达了,天南地北的园头人就回到老家,起大厝。起大厝的材料,靠着木兰溪上的船工,一点一点地运到园头。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建造故乡的屋顶。这是属于园头人的“重返木兰溪”。
于是,在园头村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致:南洋五颜六色的花砖旁,是毛主席语录。院子里,轰轰烈烈地长着仙人掌。房间里,红色的莆仙眠床边上,摆着家人从新加坡寄来的照片。墙角里,一株桃树绕过黄色的土墙。纸糊的灯笼,在燕尾脊下,飘飘摇摇。对联上,写着他们的祖先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史“渤海家声大,延陵世泽长”。
村子里,公示、广告、莆仙戏告示、宫庙榜文并在一起。处处都是对照,各种地方背景,时代气氛,杂糅在一起,像是马赛克拼贴,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建筑和人,不断堆叠、交缠,错落生长。陈彧君,拿着本子,在墙角边,在宫庙里,画画。他画土墙下的桃花、溪边的船工,也画宫庙的神仙、墙上的砖瓦、同学的书包,甚至画村中元宵的“福禄寿”、寿桃和仙鹤。元宵节,是莆田的大节日。村民们会用棕榈扎一顶小小的轿子,把神明请到轿子上。夜里,人们燃起篝火。穿着道士袍的男人抬着轿子,蹈火。在锣鼓声中,陈彧君画的寿桃和仙鹤,在火光里,明明灭灭。
曾经的木兰溪畔生活,就像是一场流动的盛宴。陈彧君也许没有想到,他的一生,都将与此有关。
中年叛逆
1999年,陈彧君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作为优秀毕业生,他留校任教。十五年后,他从高校辞职。那是他的一次“中年叛逆”。
2007年春节,他从杭州回到园头村。“汽车到莆田站,踩到地的时候,那种热闹、活力,那种气温和混杂着方言的喧闹,让我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陈彧君回忆道,“元宵节,大家一起聚在宫庙前,摆棕轿祈福。这种人和人、人与神深沉、稳固的关系,让我触动。这种感觉很难说清,就像植物重新回到了根脉里。”
那年元宵后,他回到杭州,选择忠于自己,开始创作关于家乡的装置作品——《木兰溪》。“我必须先自己沉进去,从空间开始。”
他用樟木、龙眼木、碎木头搭建楼梯、窗户、老厝,疏疏落落,木质斑驳,有人间味,像是在元宵节,在鞭炮齐发的烟雾中走一遭,身上还残留烟火味。
莆仙传统建筑里的燕尾脊、悬山顶,这里全没有。“我害怕具象,这会让我看不到整体。关于木兰溪,全是记忆。但记忆,不全是真实。记忆,是你和故乡的距离。我要忠实于这种距离。”
一根草绳,牵起一栋临时建筑,随时可能消失。旁边,浅棕色、深棕雕花的柜门打开,亦像是阿嬷的衣柜,深稳地存在。报纸、石块、书本、木构建筑,互相堆叠、交织,就像时间本身。2011年装置作品《木兰溪》吸引来荷兰策展人,随后《木兰溪》正式在北京的博而励画廊展出。展出不久,即被瑞士人乌里·希克收藏,后藏于香港M+美术馆。
“建筑材料的粗粝和简硬,内里是时间磨蚀带来的柔软。这批与当时流行完全不同的作品很快赢得艺术界的好评。”《南方人物周刊》评价道。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彧君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往世界各地。
此时的木兰溪,在陈彧君眼中,已成为一个象征和符号,象征着在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家在工业时代对农业文明的一种感知和怀想。他明白,这不只是怀旧。单纯的怀旧,毫无意义。在乡愁之上,生命必须再次生长。
个展“生长”
2021年,陈彧君个展“生长”在上海龙美术馆开展。
展厅入口,是一个长14米的不锈钢浴缸,金光闪闪。“经过浴缸,其实,就是刺破虚象的过程。追求的奢华、财富,很快被另外一个东西给摧毁了。最终能留下的,到底是什么?”他抛出一个思考。
往前走,“木兰溪”出现在头顶。这是一个长达22米的装置。他把木兰溪流域浓缩起来,用3D打印,再染色、雕刻、悬挂。
再往前,是他近年创作的生长系列。如果说,从前的木兰溪是建构,“生长”就像是一次解构后的重建。他把自己的作品撕下,变成一个个碎片后,并置、重组、拼贴。
正如英国作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写:“摧毁人们的,不是信息的匮乏,而是信息像洪水泛滥。”在信息化时代,面对碎片时,应该如何自处——陈彧君在探索。
在“生长”中,陈彧君笔下的植物也难以被忽视。
他画的植物,充满了原始的莽力和神秘色彩。这指认着他来自湿润、植物茂盛生长的南方。
在莆田方言中,“力气”被称为“力草”。陈彧君是个有“力草”的人,眼睛深深的,有胡茬,鼻子阔挺,棕色皮肤,花衬衫一穿,本身就像混血。
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棵龙眼树。
园头村所在的华亭镇,盛产龙眼。“夏天,龙眼成熟了。村民们在树下,用蚊帐搭起一个白色帐篷。林间帐篷是孩子们的天堂。天黑了,蛇虫出没,我和小伙伴们躲在帐篷里讲鬼故事,又害怕又激动。白天,阳光是烈的,光透过墨绿树叶照下来,一点点的。照得热了,我们就顺手采几颗龙眼吃起来,再跳入木兰溪里。”陈彧君回忆道。
在故乡,木兰溪和龙眼树,就是他的水帘洞和花果山。
重返木兰溪
直到陈彧君读高中前,园头村都没有桥。渡船,是外出的唯一通道。
村子里,只有一个渡口 ,一位船工常年撑船。他外出读书时,船工便将他摆渡出去。从2020年起,因由“重返木兰溪”项目,他再把自己摆渡回来。
2020年5月,首届“重返木兰溪”艺术实践设在园头村,陈彧君请来社会学者、艺术家、媒体人、规划师、策划人、企业家等人士。他把莆田最地道的东西端出来待客——莆仙戏、传统建筑、柴火灶煮的莆田卤面。台上,他们探讨话题;台下,是“看戏”的村民。而后,他们一起研讨、逛村,听莆仙戏、吃流水席,这种乡土和现代的对比冲突也像一出新颖的行为艺术,记录在5G直播镜头里,吸引了700多万网友观看。
《象外》杂志撰稿人阿改参加活动后,写道:“陈彧君发言,待客,诚诚恳恳,像勤勉办事的老实人。他带领大家参观老宅,同时直播介绍村里的贡生院、华侨房、戏台和曲折错落的小巷;在一场跨界的‘艺术圆桌会’和莆仙戏演出后,他还继续为‘莆田卤面’直播带货;到了晚上九十点,所有流程终于走完,酒足饭饱的宾客陆续散场,陈彧君一一话别、送客,额头冒汗,脸颊通红——他有些醉了。”
即使园头村的人去过天南地北,但这是第一次,园头村迎来这么多外乡人。
园头村里人,都唤陈彧君“阿君”。
一位村民跟他说:“阿君,活动办得很好。你要坚持住,再坚持一下,就成功了。”
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成功”是什么,但是村民的这番鼓励,让陈彧君挺感动。
第二季“重返木兰溪”,他请来碧山计划发起人欧宁、《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蒯乐昊、城市规划师潘陶等嘉宾。
蒯乐昊两次来莆田,都是因为“重返木兰溪”。在“重返木兰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论坛中,蒯乐昊说道:“我的报道侧重艺术方向。和陈彧君第一次见面,以为他想聊聊艺术,没想到,他一直拼命在讲关于改造家乡的事儿。至今已经五六年过去了,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个一时兴起、异想天开的事。他不管有戏没戏,还是隔三岔五地就要去试一试。我觉得,这就是莆田人的属性。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现在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也许你去浇一浇,说不定哪天,这个种子它就会发芽,就会冒出来。”
木兰之水,汇流入海。陈彧君希望,通过艺术家个体的艺术实践,逐步把它变成地域文化的集体创作,待越来越多人参与后,逐渐就成为一个共识,逐渐构建成木兰溪的文化池子。“我不是一个着急的人。‘木兰溪’装置做了四年,‘重返木兰溪’刚刚第三年。做事情时,我总是想把它往远处推一下,放在更大的坐标里去看。”陈彧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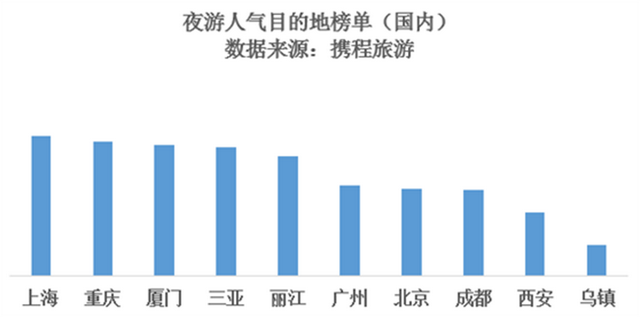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