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之泪,总督之笑:英印帝国野心下的赤裸生命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殖民时代中心威廉堡(Fort William)附近,坐落着英殖时代的诸多纪念碑建筑。这里曾是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心脏。各类纪念馆和博物馆里,至今还悬挂着殖民时代的油画供人参观。
在那些洋溢着异国情调的形形色色画作中,既能看到诗圣泰戈尔的先祖们穿着欧式服装的肖像,也会有反映英国统治者享受殖民地生活的斑斓油彩。画布上的英国人看起来常常是养尊处优:他们乘坐着印度仆人抬着的轿子或由后者牵引的大象;在炎热而漫长的南亚夏季,有仆人为他们驱动人力风扇、奉上水果;他们穿着盛装出席华丽的舞会和种种庆典,接受印度王公的问候;还有人取得了某场战争的胜利凯旋……
然而,在2015年出版的《王公之泪》作者斐迪南·芒特笔下,英印帝国的早期殖民者们是另一种形象。这些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和职业军人,与其说是站在印度人头上趾高气扬享着福的殖民统治者,不如说更像是一群亡命之徒和喘不过气的市井小民。在殖民体系下,尽管他们比他们所统治的印度人要拥有多得多的特权,但他们的生命依然脆弱而赤裸。
这本名为《王公之泪》的历史题材非虚构作品,多少有些文不对题,兴许叫做《东印度公司之泪》要来得更合适一些。毕竟,芒特笔下的故事主线,围绕着三个在19世纪上半叶参与殖民印度的苏格兰家族——洛家族、莎士比亚家族和萨克雷家族。至于印度本地王公们的故事,芒特所采引的资料也基本都来自英国人的记载。主角到底是谁也就一目了然了。

《王公之泪:印度的兵变、金钱与婚姻》,作者:(英)斐迪南·芒特,译者:陆大鹏 刘晓晖,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4月。
撰文|任其然
主角光环下的“小人物”
书的一开篇,芒特就提醒读者,他是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的亲戚。而卡梅伦和他一样,是一个在殖民时代印度经营过多年的家族——苏格兰的洛(Low)家族的后代(这也是他写作这本书的动力)。如今他们都是苏格兰出身的贵族家庭。然而回到殖民时代,他们的祖先最开始只是一个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小人物”:后来官至上将的约翰·洛最开始时只是东印度公司的公司武装中的一名基层军官。其后从后勤官一路做到地区代表,最终成为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最高级别军事顾问之一。
尽管如此,在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资深官员之前,约翰·洛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债务,越积越多无力清偿。芒特提醒人们,这才是那时候大多数殖民地英国人的状态。
与之类似,在《王公之泪》中,许多如今历史中记载的大人物都被写成了“小人物”。比如,格外有趣的是,新加坡殖民史上的英国英雄人物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在芒特笔下被以贬义口吻写成了一个充满野心和诡计的“亚洲矮化版拿破仑”。作者不吝惜任何词汇来贬损这位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开明殖民官员,甚至莱佛士的名著《爪哇史》也被芒特认为“借鉴了其他学者的成果”,以至于属于“无耻”的抄袭。莱佛士的社会改革也被贬低:“同样的对征服的渴望,同样的公共宣传的才华,同样大肆鼓吹自己扫荡了自己所征服的国家的旧弊端,同样对人道代价熟视无睹”。
德里的英国统治者梅特卡夫则被芒特描述为一个怀着皇帝梦的乡绅,竭尽全力在德里装成一个帝王的样子。更不用说那些在殖民史上一直被诟病的总督们——在阿富汗惨败的奥克兰勋爵被嘲讽为带有一种神经质般的恐惧感;而致力于将印度“英国化”、并为1857年大起义埋下伏笔的边沁信徒达尔豪西勋爵的形象,则比简明印度历史中记载得还要残酷和虚伪。

印度兵变期间,英国人在当地还是获得了一些盟友的支持,如锡克人、旁遮普人和廓尔喀人。
忠诚与贪欲:英国人的友谊值多少钱?
达尔豪西勋爵在1853年末痛失爱妻,在丧妻的十天后,他在写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信件中称妻子的去世是“全能的上帝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但他仍会“努力臣服于他的严苛意志”,然后保证除非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会按照承诺一直待到“1854年4月”。但悲痛并未让他放松权力之手。他得意于自己规划的孟买铁路、恒河运河与现代化的电报线路,因此对那些横亘在现代交通和通讯设施之间的土著邦国愈加心生不满。表面上,他指控这些土著邦国的王公阻碍了“进步”,但实质上,一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目的是吞并土地,“致力于移除这些扎眼的障碍,将地图的很大一块涂成大英帝国的粉红色。这粉红色从仰光一直延伸到旁遮普,少数例外就是若干驯顺的‘傻瓜权贵’的残余领土”。
达尔豪西勋爵在吞并奥德王国时的手段凶狠而诡诈。他刻意宣扬奥德国王统治下内政荒疏,民不聊生,对英国充满敌视,而他内心相当清楚,调查报告的结论恰恰相反:“无论是胜利之时还是灾祸之时,英国人都找不到比奥德国王更忠诚的朋友了”,奥德的内政不仅不荒疏,比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反而更加宽仁,没有一个目击证人找到证据,说奥德有走投无路的农民越境逃入英国省份,“奥德没有人憧憬英国的政府体制,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听说英国的法庭极其严酷”。达尔豪西自己也发现阻碍自己吞并欲望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土著王公的行为无可指摘,“奥德国王不肯冒犯我们,不肯与我们争吵,不管我们怎么踢他打他,他就是不肯造反。”他最终只能霸王硬上弓,采用专断的手段废黜国王,吞并其领土。当国王在卸去一切武装的宫殿里,接到达尔豪西勋爵专横的信件时,他哭泣起来,脱掉头巾交到英国军官的手上——“瓦季德·阿里·沙是最后一个看清了英国人的友谊值多少钱并为此哭泣的王公”。
早期的印度殖民确实更像是亡命之徒的事业,甚至,芒特站在当代人的角度,一直试图搞明白:为什么英国人要来到这样一个万里之外的,随时可能丧命的地方,而且一待就是许多年甚至许多代人——何况,在印度,他们随时可能死于热带疾病、死于帆船海难,又或者出席一场远征,然后在阿富汗边境的山脉中被价值十卢比的火枪击中,一枪毙命。在《王公之泪》中,除了作为主人公的约翰·洛,其他角色很少能得以善终。
卑劣与高尚:矛盾的殖民事业
在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历史上,存在着两个关键节点。一是18世纪末,在统治了孟加拉近五十年后,印度总督康瓦里斯勋爵治下的英印政府大力改革了早年公司的经营模式。如《王公之泪》一开篇所揭示的,这场改革伴随着“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观的崛起。在那以前,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是一项颇为不庄重的事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依靠腐败致富,和本地人通婚,养育欧亚混血儿,再把他们带入殖民官僚机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改革试图废除这一切,然后把整个公司官僚化和正规化。接下来的一百年间,英国人带着家眷来到印度,住在和印度人保持距离的大宅里,上喜马拉雅山疗养,和本地女性结婚不再被鼓励,混血儿则被逐出帝国机构。英国的管理模式带到次大陆,英语替代了原先在东印度公司内部通行的波斯语,英国的直接统治逐渐替代土邦国王的间接统治。
1857年则是另一个关键的节点,19世纪初以来积累的掠夺模式失效了,印度士兵掀起的大起义席卷北印度。起义最终被镇压,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也因此被伦敦终结。英国国王开始兼任印度皇帝,统治中心也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当今南亚历史的开始:印度兵的主要来源从恒河流域转移到了西北部的旁遮普;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矛盾开始被放大;分治印度的方案逐渐在英国人的推动下浮出水面。
《王公之泪》所描述的,正是这两个节点之间的半个世纪。读者跟随着芒特笔下约翰·洛在东印度公司的服役经历,得到的是一个鸟瞰视角:1800年到1857年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是如何在印度及其周边扩张征服欲望的?这其中又是哪些人哪些力量鼓动起了历史的风帆?其间,英国人输掉了在阿富汗的战事,打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攻打巴达维亚又交还给了荷兰人,在印度内部,他们一次次压制各个土邦的不满,镇压东印度公司印度士兵的小规模起义,平息军官对待遇的不满,然后不断搜刮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能够搜刮的资源。芒特书写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挖掘大量的书信、笔记和文献,他在带着读者回到历史的同时,也鲜活地呈现了这些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小人物们负债累累又常常短促的人生。
芒特作为殖民地官员家族的后裔,对殖民本身怀着矛盾理解。在一些段落中,能够看到芒特试图为英国在印度留下的政治遗产辩解几句。比如在写到约翰·洛的回国旅程时,他忍不住开始大段大段讨论起了英国在一个世纪后的最终撤离。他辩解说尽管英国的离开导致了印巴分治的悲剧,但缓慢的撤退也为印度留下了更多的治理能力;又比如,在描绘英军镇压1857年大起义时,芒特忍不住把一些高尚的溢美之词赋予了作战的英军官兵——读者读到这些地方时,也许会在心里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芒特笔下,约翰·洛成为了一个怀着高尚道德情操的主角。他同情因为待遇问题而叛变的基层军官、同情被公司和殖民地政府不断剥夺权力的印度王公。尽管他忠诚执行着各种殖民地命令,却有诸多的不情愿。相比之下,其他殖民地官僚则要么野心勃勃,要么贪欲无穷。
这多少有些过于挥霍洛家族的主角光环了,以至于显得他们和同时代的其他人物格格不入。

印度兵在进行恩菲尔德步枪使用训练。正是与这种步枪使用相关的谣言,最终引发了印度兵变。
伪善与真恶:一丘之貉
将殖民的罪恶归咎于具体的邪恶的人,而将我们的主角置身在这些恶行之外,这能说服挑剔的读者吗?而在总结1857年的淋漓鲜血时,芒特认为印度人在起义时采取了类似种族屠杀的狂热杀戮,英国人也在反击时做了类似的事情,所以是两边都错了。这样的“各打五十大板”,也让人遗憾。以至于还不如继续讨论他所引用的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的质疑:1857年大起义是一场民族革命,还是试图复辟莫卧儿体制?
读者也会发现,芒特也没有回避殖民的血腥与残暴。在英军镇压大起义的段落里,他带着厌恶的语调描述了英军如何向德里进军时一路杀戮,并且在阿富汗作战时采取过杀死全部男性,奸污遇到的妇女的焦土战术。更凶狠的也更细微的,是英国人如何夺取印度的土地和权力。这是一种礼节、虚伪和算计的混合物。芒特详细描述了东印度公司是如何在自己缺钱时向土邦王公们借钱,又在他们缺钱时鼓励他们向公司借债,最后因为他们欠债而将其土地纳入公司麾下。“多年来,不少英国历史学家喜欢说某位总督比另一位优越或者低劣。但如果你是勒克瑙的纳瓦布或哪怕仅是普通公民,你都只会觉得英国总督都是一路货色:对土地和金钱同样欲壑难填,攫取土地和金钱时同样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
对想要理解英印早期殖民时代境况的读者来说,芒特的文字是极为丰富的时代注脚。我们可以看到他详细描摹了各种各样的殖民统治技术,甚至从今天得到共鸣。在德里攻防战的章节里,他绘声绘色讲述了英军利用工兵和大炮炸开房屋侧面从而迂回包抄的“破墙战术”。人们会发现,这样的画面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在出现,并且是超级大国军队在巷战中碾压落后武装力量的某种佐证。在《剑桥印度史》中,学者C·A·贝利也提到过,著名的“铁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在19世纪初的印度和马拉塔人作战时所采取的清除丛林的战术,是1960年代美国在越南使用橙剂消灭游击队藏身之处的遥远先声。
但读者有必要留意的是,是否要跟着芒特的论断,认为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其实漏洞百出“弱不禁风”?在历史上我们要看到的是,在1841年大败于喀布尔的同时,东印度公司的舰船和军队在虎门包抄了关天培统率的广东水师与炮台,并随后北上进逼南京与清帝国的门户。英印帝国未必是成功的统治机器,却是一架残忍而高效的战争机器。而统治和战争并不是同一件事情。
芒特对东印度公司的金融本质的理解是更为贴切的:东印度公司更像是一个用战争作为债务抵押的投机商,它不断发动扩张战争。而通过这种形式,作为帝国心脏的印度并不仅仅供应原材料,它还负责帮助帝国打磨战争的刀斧,将那些在印度浸染多年没有战死并最终脱颖而出的将领输送到帝国心脏——阿瑟·韦尔斯利在迎战拿破仑之前,已经和马拉塔人、和提普苏丹的迈索尔邦国鏖战了多年,早就成为了沙场老手。毕竟,在英国人出现之前,阿克巴大帝时代的印度战争就充满了棱堡攻防和火炮对决了。反之,帝国的脆弱性并非因为其不够强大,而在于其太过扩张,对安全感和稳定感的需要变得永无止境。奥克兰勋爵对阿富汗边疆的执念和几代英国人对大博弈的痴迷,以及他们最终在阿富汗的失败,就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英印帝国的两张面孔
英印帝国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两面的形象。一方面,帝国体系里的现代化主义者们,如达尔豪西这样的人物,坚定认为只有英国人带来的文明和开化才是次大陆的未来。抱着这种心态,这些人带来现代教育、基础设施,并在印度取缔他们深恶痛绝的寡妇殉葬和活人祭祀等等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正如芒特所意识到的,这些现代化的信徒希望实践的现代理想,是以极为帝国主义的方式推动的,他们看不起“原始”的印度社会,从不关心和理解被统治者为何从心底里反对自己。“那些自称最关注农民利益的自由主义者,恰恰也是最热忱的帝国主义者。”英帝国的形象也是同样——帝国是文明的代表,追求着各种各样的高尚情操——其中许多是装点门面的,但却也有许多是真实存在的;同一时刻中,帝国又建立在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私人欲望与野心之上,而这滋生着林林总总的欺瞒、狡诈和血腥。
无穷无尽形如草芥的小人物,种族主义的血腥野蛮,然后是带着文明使命感的暴力和虚伪,混杂着一些人性的善从中偶尔露头。这就是芒特笔下的英印帝国图景。在今天,这一主题的知识与历史,及其对今天世界留下的巨大影响,常常被我们所低估了——毕竟,英帝国和美帝国是如此不同,而我们太过想当然地将它们理解为继承关系。
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王公之泪》提供的这段历史画面,也是众多出版物中所少见的。尽管书中密密麻麻的陌生人名与陌生地名构成了阅读时的必然困难,但它仍然值得读者们迎难而上。
英印帝国未必是成功的统治机器,却是一架残忍而高效的战争机器。而统治和战争并不是同一件事情。
英印帝国的脆弱性并非因为其不够强大,而在于其太过扩张,对安全感和稳定感的需要变得永无止境。
撰文|任其然
编辑|李阳、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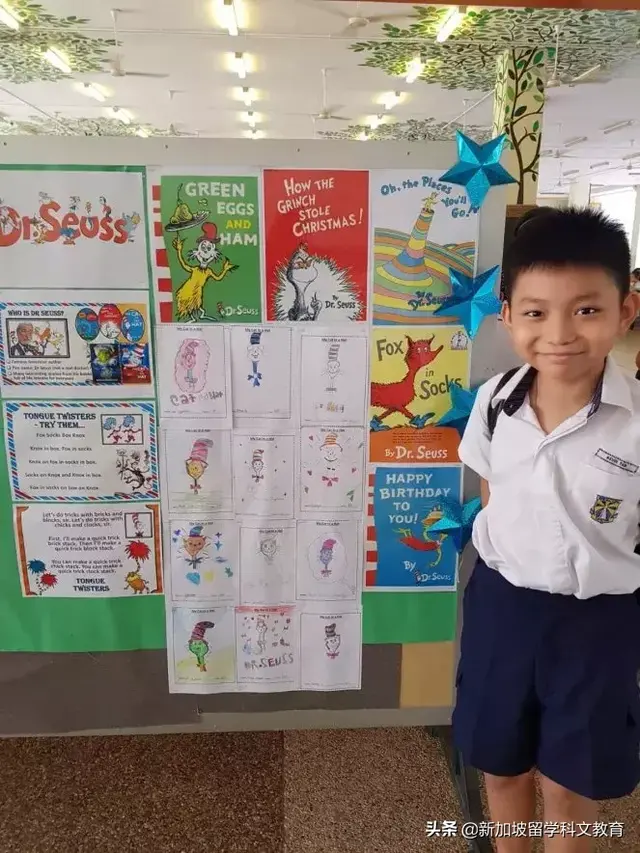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