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天于我,相当厚”:崔东明眼里的妈妈丰一吟和外公丰子恺
□张雪南
【编者按:作者张雪南现任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雪南也是桐乡人,作为“丰迷”的他与丰一吟一家素有交往。去年11月,丰一吟的女儿崔东明到桐乡参加“丰子恺星”命名仪式暨“教惟以爱”丰子恺家庭教育展,张雪南在崔东明下榻的桐乡新世纪大酒店与她作了寻缘访谈,并写下此文。今天,他通过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分享这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谨以此文纪念令人敬重的丰一吟先生。】
1945年7月,丰子恺在成都写过一首诗《寄一吟》。诗曰:
最小偏怜胜谢娘,丹青歌舞学成双。
手描金碧和渲淡,心在西皮和二黄。
刻意学成梅博士,投胎愿作马连良。
藤床笑倚初开口,不是苏三即四郎。
此诗中,丰子恺不仅对小女儿丰一吟擅画能戏的才能感到欣慰,同时表达了丰先生对幼女偏爱的情感。
丰一吟在她著的《我的爸爸丰子恺》一书中说到:
“虽然爸爸和姐姐哥哥们有说有笑,但在我看来,爸爸永远是严肃的,而且,爸爸是属于姐姐哥哥他们的。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可能或多或少体会过这种滋味。爸爸在物质上对我们没有偏爱,但在父爱上就很难说他公平了。”
其实,这是丰一吟的童年感受。丰一吟长大后,一直在爸爸身边。在丰子恺的七位子女中,作为小女儿的丰一吟,陪伴爸爸的时间最多,在艺术、翻译等方面深受爸爸的感染和教诲最多,而她对爸爸艺术和精神的研究与传承也是最多的。
很多人说,丰一吟像她的父亲丰子恺。而丰一吟在1987年儿童节写的一篇文章《我不像父亲》中曾写到:
“正如明川所说,父亲是喜欢悠悠然的。他之所以性急,正是为了早些顺利地摆脱紧张的局面,以求达到悠悠然的境界。……父亲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生活的悠情,是为了追求他所喜爱的饮酒吟诗、倚杖观景的情味。
而我呢?我却永远是那么性急,那么匆匆忙忙,被紧张的生活束缚住,不能自拔,不能超脱。
明川说对了,我不像父亲!”
在丰一吟女儿崔东明看来,虽说妈妈性急不像她的父亲,但做人做事又确实很像她的父亲,总是那么认真和勤奋,那么乐观和心善。
2020年11月21日,崔东明来桐乡参加“丰子恺星”命名仪式暨“教惟以爱”丰子恺家庭教育展。晚上,我赶去她下榻的桐乡新世纪大酒店作了寻缘访谈。
以下,为崔东明自述:
我从小对“日月楼”里的一幅对联印象很深。曾经听外公讲过,以前我们住在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后来他用了六根金条,把陕西南路长乐邨的西班牙式阳房39弄93号的整幢(一至三楼)从前房客董太太手里给顶了下来。1966年文革开始后,房管所勒令我们让出一楼,日月楼就只剩下二楼和三楼。从我有记忆起,就住在上海长乐邨的39弄93号,外公睡觉在93号二楼的内阳台上,他常常坐在床上给我讲故事,在外公身后的墙上,就是那幅有名的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我记得小时候把“界”当成“累”,把“楼”读作了“广”,家里人还常常笑我呢。
1975年8月,外公生病了,右手发展到右肘不灵活,每晚还伴有低烧。先到大华医院,后来转到了华山医院一透视才发现,肿瘤已经有拳头那么大且转移到左脑了,所以右臂才会不灵活。到了9月,外公病情恶化,记得那天我到医院,看到外公躺在观察室的病床上,脸上盖了块白手帕,妈妈示意我过去和外公告别。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听妈妈说过,就在她们准备把外公送医院时,不知道是动作幅度大了还是什么原因“日月楼中日月长”这一联从上面掉了下来。
1978年,在文化局的协调下,我们搬离了陕西南路39弄93号,离开了日月楼。我们搬到了漕溪北路,妈妈在家里挂了外公的像,旁边又挂了这副对联。睹物思人,外公总是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是一辈子的记忆和思念。
外公有一颗可爱的童心,无论是妈妈她们小时候,还是我们小时候,都是外公画画的对象和源泉。而到孩子们长大了,他就不再画了。他这一辈子,最喜欢画的就是儿童。外公跟我们小孩在一起也是很开心的,孩子们玩乐的很多场景,成了外公最有趣的漫画题材。
我对外公最深的印象是他给我讲故事。记得每天一放学,马上跑到外公所住的内阳台上听故事。那个时候没有图画书,外公总是耐心给我讲各种故事,还一边讲一边在练习本上画给我看,从不认字一直画到我上小学,竟然一共画了17本练习册!这些故事里有民间传说、有儿歌、也有谜语,当然更有外公的散文里“艺术的逃难”那一段的场景。印象很深的有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林冲发配上山等。也画了很多谜语让我猜。有很多是用桐乡话写的儿歌、顺口溜。后来我才知道,给我讲故事的日子里,外公每天5点就起床,在费心费力地画《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喜欢听故事这个习惯大概会影响我一生了,我年轻时喜欢听广播剧,现在年过半百,内容偏向了纪实和历史,还是喜欢听喜马拉雅等音频。如今,每当翻看这一本本练习册,总让我想起坐在外公身边听故事的温暖场景,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我觉得外婆的脾气很好的。有点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妇女,一心打理家务。外公那时老是说她是“四脚八色”,就是她喜欢里外张罗,家里客人来,都是她去张罗接待。这样,外公不用操心,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画画写作。外婆很会张罗一大家子的吃和穿,特别是逢年过节,外婆最忙。外婆会做各种糕点,做定胜糕是她的拿手好戏,我也很喜欢吃的。外婆自己也喜欢吃甜食,糯米做的甜食。外公倒是不太喜欢吃甜食。
外公在1975年去世后,我们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确实是个好脾气的人。年纪大了,眼睛和耳朵都不太好,记得那时候有粮票、布票等各种票据,拿来的时候当然是一整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剪票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我当时很贪玩,有时会不耐烦外婆叫我干活,有时还装作没听见,现在想想真不应该啊!尽管这样,外婆还是好脾气,她也给我讲往事,讲她年轻的时候,讲她当年出嫁时的风光。
妈妈丰一吟是丰家最小的女儿。在很多人看来,妈妈也是名人。可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普通、平常的妈妈,和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有喜怒哀乐,也会一天天老去。

丰一吟在家读漫画,摄于2018年10月
我妈妈早在1943年就在重庆国立艺专学习美术,她当时学的是应用美术。1948年毕业后没有走美术之路,而是跟外公自学俄语,曾在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室等单位,从事了三十年的翻译工作,翻译有《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还帮外公一起翻译《源氏物语》。1995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直到外公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加坡广洽法师知道妈妈学过美术,就叫我妈妈临摹父画,以满足不少丰迷和“子恺漫画”渴求者的愿望。广洽法师是外公丰子恺在新加坡的方外之交,妈妈也很尊敬他。在我生孩子的第二天,妈妈就去了泉州陪洽师。还曾陪他去过敦煌、五台山等地。妈妈尊洽师之命,重新拿起画笔,凭着她早年的美术基础和对外公画风的熟悉,不用多时,画笔有生转熟,所摹漫画广受欢迎,妈妈也总是有求必应。但她从不惑于某些鉴赏者的过誉,为了不使后人对自己的摹品与父画难于分辨,也防有些人伪充父画真迹,妈妈除了题明“丰一吟画”外,还专门请人刻了方“仿先父遗墨”印盖上。
妈妈深知人生有限,精力有限,觉得自己还有比画画写字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尽可能控制和压缩画画写字的时间,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整理外公资料、编辑外公文集画集,撰写回忆录、为海内外丰子恺研究者提供资料等。她花了很多时间来做外公的事情。

丰一吟在家读漫画,摄于2018年10月
我妈妈做事很认真。譬如她整理和研究外公的资料,考证得很仔细,每件事情都很认真。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姨妈丰陈宝和妈妈姐妹俩下决心编一套《丰子恺文集》,那时的编辑工作是很困难很辛苦的,正如妈妈在她的文章里说的:“为了一篇文章,可以追索到天涯海角,真是所谓‘升天入地求之遍’。在复印有困难时,我们就动手抄,字字句句认真校核。”我妈妈还有个习惯,坚持用卡片抄录、记录外公的资料,日积月累,集了满满的两大抽屉,总共有两万多张卡片,还有60本剪报集。如今,我们已把它捐给桐乡档案馆了。
妈妈的认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妈妈一直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几十年来坚持把每天的事细细记下来,这些都成了她晚年写书的第一手资料。1975年外公病重住院,妈妈日夜看护,她发起建立了《病中日记》,方便交接人了解外公每天病情的变化和吃药的情况。妈妈也把这本《病中日记》保存了下来。
很让我感动和佩服的是,妈妈七十多岁时下决心学电脑,不厌其烦地跟我表哥雪君和表姐朝婴学习电脑操作和拼音打字。学会后,开始用电脑写文章。那本20多万字的《我和爸爸丰子恺》,就是妈妈自己一字一字输入写成的。妈妈还将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手写的日记全部输入到电脑中。后来,妈妈还学会了使用电子邮件,收发邮件又成了她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
我对妈妈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勤!总觉得她有做不完的事情,一件事情做完了,又忙着做另一件事情,一直是挺忙的。尤其到她的晚年,好像要做的事情更多。每天匆匆吃完饭,就坐到她的工作台前,连跟我们讲话的时间也很少。记得有一次,她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只能躺或坐在床上听听收音机,而手头一大堆工作不能做了,让她心急如焚,那个很不耐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妈妈陆续写了《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我和爸爸丰子恺》《天与我相当厚》等,和我大姨妈一起编辑出版了《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漫画全集》等。妈妈曾在2008年出版的《我和爸爸丰子恺》和2014年出版的《爸爸丰子恺》两书序言中写到:“我曾说过:写完了《潇洒风神》,编好了爸爸的文集(其实几乎是全集),再编好了他的漫画全集,好比三块大石头从我身上落了下来,让我松了一口气。后来却又来了三块大石头。这第一块《我和爸爸丰子恺》已经落地,但是文(全)集和漫画全集都已收到了不少新资料,应该再作补充。以前与我‘并肩作战’的大姐早已声称要退出‘战场’,只能当我的顾问了。幸而余下的两块石头不算很大,因为毕竟已出版过,有了基础,而不是从无到有。我年事已高,可以慢慢做。做爸爸的事,我义不容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妈妈信奉佛教,心怀慈悲。1999年开始,妈妈为香港友人严宽佑所创办的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在上海主持会务,热心从事慈善事业,常常用自己画作义卖所得捐作慈善,帮助了很多偏远山区有困难的人。在助学帮困中认识了贵州的陆宗煜,一直个人出资帮助他完成大学学业,不断去信关心鼓励他注意身体健康、好好学习,不厌其烦地给他批改点评作文和书画作业。还长途跋涉专程到贵州,去看望得伤寒病住院的宗煜,鼓励他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后来又为宗煜的工作、事业操心帮忙,使他在事业和艺术方面都有了大的提升。宗煜对我妈妈很感恩,他说:“丰一吟是我的恩师。她对我的恩情,就像慈母一样关爱我,无微不至;她对我的教导,从做人到钻研艺术,无所不包。”其实,妈妈帮助过的人有很多,但她从不宣传,也很少跟人讲起这些事情。

崔东明陪妈妈丰一吟回桐乡石门,摄于2018年11月
无论是外公,还是我妈妈,都很重视家教、家风的传承。外公要每个子女背诵《崔子玉座右铭》。我妈妈自己背得很熟练的,还喜欢书写《崔子玉座右铭》送给后辈和好友。虽然是小时候背的,但我一直记得很牢。你看,现在也能背出来:“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
我小时候,妈妈把我放到了全托的幼儿所。后来,妈妈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也把我带到了干校幼儿园,劳动辛苦,带我也辛苦。好些个在干校劳动的文化人帮助送我上学,帮我拔牙。我妈妈为了送我上学,还自己学骑自行车,但最终还是没学会。
妈妈从小教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记得我在奉贤五七干校幼儿园上学时,供应并不富裕,有一天,妈妈给我的早餐是一个果酱馒头和一个花生馒头,我把果酱馒头吃掉了,把花生馒头丢在门缝里,被妈妈劳动回来后发现了。妈妈问我吃完没有,我回答说全吃了。结果穿帮了,我无话可说。我记得妈妈那天打了我,平时妈妈从来不打我的,大概这是唯一一次,这让我记忆深刻!从此我再也没有说过谎话。
我妈妈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妈妈的脾气很像外公的。我妈妈和外公一样,待人宽厚。在待人接物上,外公不仅对朋友、同事宽厚,对工人和保姆同样宽厚,和家人一样对待。外公常对家里人说:“他们离开自己的亲人,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来为我们服务,怎么可以不把他们当作自家人呢?”听妈妈讲,1970年1月,在丰家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保姆何英娥突然中风过世,全家很伤心,像自家人一样为她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妈妈对保姆同样很宽厚,保姆朱阿姨已经在我们家做了30多年,完全成了我们家里人。
外公一辈子画了很多画。虽然妈妈和外公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妈妈从未想到要外公多画一些,更未料到外公竟会在动乱之年突然离世,妈妈保存的外公遗画少得简直叫人难以相信。1981年初冬,我妈妈陪广洽法师在北京与赵朴初居士相晤,闲谈中得知朴老极喜爱子恺漫画,但还无缘珍藏过子恺漫画,觉得很遗憾。事后,广洽法师嘱咐我妈妈:“能否回上海后找一幅丰先生遗画寄赠朴老?”我妈妈当即答应。可回家后犯了难,竟然找不出一幅合适的画作送朴老。于是,妈妈找我商量,在外公画给我的几幅遗作中选了幅古诗新画《松间明月长如此》,寄赠给朴老,还附信说明是女儿小明所赠。
朴老收到赠画,很高兴,也很感动,专门赋诗一首:“明月松间照,天伦物我均。抚兹一幅画,感君三代情。”将此诗附在复信中,对赠画深表感谢,并说借观三年后当原璧奉还。妈妈得朴老复信和诗后,也很高兴。1984年,妈妈又去函朴老,求其将诗写成条幅,不料朴老回信说:诗已写成斗方,一同裱与画下。并说三年将满,画正托人带沪璧还。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已装裱成轴的画幅,朴老还在题诗后又加了一段长跋。 这件凝聚几代情谊的书画珍品,妈妈格外珍惜,由我继续珍藏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关外公的展览或纪念活动多起来,妈妈总是尽量去参加,也总是想办法多去看看外公的老朋友。妈妈八十岁以后到外面参加活动,我基本上都陪着妈妈一起去。我记得第一次陪妈妈参加活动,是去平湖参加李叔同的纪念活动。去得最多的是桐乡和杭州弘丰研究中心的活动。也曾陪妈妈去看望过牙医易昭雪,感谢他为外公拔牙、镶牙,顺便也让易老为妈妈检查治疗牙齿。我印象最深的是,易老亲手为我妈妈剥柚子,尽管年岁已高,但手劲依然很大。
外公外婆都是桐乡人,我们家里都说桐乡话,我的桐乡话就是跟外公外婆和我的妈妈学的。这是一份浓浓的乡情。外公在1939年写的《辞缘缘堂》里说:“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自从外公去世后,妈妈每年都至少回桐乡两次,一次回乡过春节,一次是清明扫墓。开始时她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我陪她回去了。今年5月11日,是母亲节,我又带了妈妈去桐乡。以前是妈妈带我去桐乡,现在是我带妈妈去桐乡。住了一个晚上,又到缘缘堂去看,那天妈妈挺“乖”的,不像平时会发点“脾气”,而是很平和、很亲切,感觉很熟悉、很喜欢这里。在石门吃饭时,妈妈还和大家一起唱起了歌,“长亭外,古道边……”,很投入、很动情。
妈妈回忆外公、写外公的很多,但写自己的很少。妈妈总是想着为外公、为别人做点事情,没想到要为自己做些事,也从没去计较级别、职称。在她的晚年,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外公的事情上。熟悉妈妈的人都说她是“劳碌命”,其实,妈妈实在没有为自己劳碌过什么。
我妈妈把外公给她题写的一幅书法——陶渊明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在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装作镜框挂在家里墙壁上,她把这个镜框看得很重,有一次我想用毛巾去擦一下,她都紧张问我:“你要干吗?”一直来,妈妈以这四句诗作为座右铭,时时督促自己。这也真是妈妈晚年生活工作的写照,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钟”。
一直到2017年4月11日,妈妈到小区锻炼时摔了一跤,医院诊断为颅内出血,因为年龄关系我们采取了保守治疗。现在,妈妈老了,还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总算能休息了。如今,妈妈每天听听李叔同歌曲、看看京剧,有时还会背唐诗宋词,真正过上了老年人应有的生活。妈妈不再是忙碌的妈妈,妈妈依然是可爱的妈妈、伟大的妈妈!

崔东明陪妈妈丰一吟参加“我自爱桐乡——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一家子合影。摄于2018年11月
访谈结束,我请东明题字留念。她写下:“天于我,相当厚”。
她说,这是外公1944年抗战期间避居重庆时作的一首词中的句子,也被妈妈选为个人自选集的书名。妈妈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她写到:“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他尚且认为‘天于我,相当厚’。而我,晚年欣逢改革开放,丰衣足食,而且身体健康,已经是‘七十古来稀’的人了,还能做这么多工作。岂不是‘天于我,相当厚’吗?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外公和妈妈都喜欢这句话,崔东明也很喜欢这句话:“天于我,相当厚”。以此豁达和感恩的心境处事待人,这何尝不是丰家的一种传承呢!
张雪南写于2020年11月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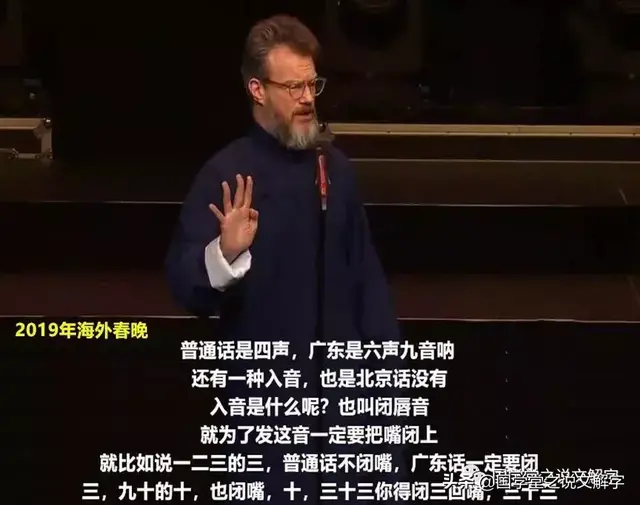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