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峪评《聂鲁达回忆录》︱坦白说谁曾活过
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 黄峪

《聂鲁达——回忆录》,[智利]聂鲁达著,李文进译,台北:盖亚文化2020年9月出版,622页,820元新台币

喜爱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聂鲁达(笔名Pablo Neruda, 原名Neftali Ricardo Reyes Basoalto,1904-1973)其人其作的读者,相信不会错过2016年上映的法国电影《追捕聂鲁达》(Neruda),也应该已经看过意大利经典名片《邮差》(Il Postino)。但如果想更了解诗人本尊,直接阅读他的自传也是一个好方法。这部收入聂鲁达个人照片集与手迹的回忆录,从2017年问世的智利版译成中文,2020年在台北出版,全书皇皇六百二十二页,厚重精装,绝对值得珍藏。此书西班牙原文标题是:Confieso que he vivido: Memorias。副标题中的Memorias是西班牙文中回忆录的复数形式,而正题这句Confieso que he vivido直译的话,意思是“I confess that I have lived”——坦白说,我曾经活过(简体中文本译为《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仔细揣摩标题句,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觉得并没有虚度。
此书智利版责编Dario Oses在序言《未曾结束的传记》中一开篇便这样介绍:“《聂鲁达回忆录——坦白说,我没有白活》是一部卷帙浩繁、手法独特的作品。聂鲁达一直到1973年9月临终前,都还在整理这部回忆录。回忆录当中有他对先前不同时期、不同出处作品的重写,也有他审视和反思个人生平之后再创作的作品。”其中收入了三份不曾出版、撰写于1954年的自传式演讲稿。根据责编介绍,这部回忆录本来计划在1974年出版,作为庆祝聂鲁达七十大寿的活动之一,但由于诗人1973年骤然离世,书虽仍按计划出版,却成了他的遗作。
聂鲁达于1973年9月23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圣玛利亚诊所逝世。仅仅在十二天前,皮诺切特将军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推行独裁统治直到1990年。作为阿连德的好友,诗人究竟是病逝,还是被谋杀,真相扑朔迷离。2013年,聂鲁达的司机阿拉亚(Manuel Araya)向媒体透露说聂鲁达曾致电给他说有人在他肚子上扎了一针。随后,智利法官卡洛萨(Mario Carroza)下令开棺验尸以查明聂鲁达的死因。他的一部分遗骸样本被送到四个国家的法医实验室化验分析。2015年,智利政府表示聂鲁达之死“很可能由第三方造成”。2016年,聂鲁达的遗骸才被重新埋葬于他的家乡,智利中部的黑岛(Isla Negra)。然而,聂鲁达的真实死因,至今仍然未能查明。
人无法选择被生下来的命运,而死亡也难以计划。可以选择的,只有爱与创作——在何时何地去爱?爱上谁?和谁相爱?用什么写作?写什么作品?为什么而写作?十多年前,为了纪念聂鲁达百年诞辰,聂鲁达诗歌重要中译者赵振江和他的学生滕威编著出版了《聂鲁达画传 1904-1973》,其中用三个关键词“爱情、诗、革命”总结诗人波澜壮阔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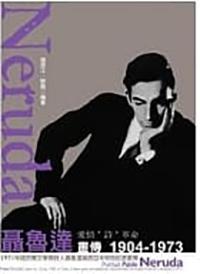
《聂鲁达画传 1904-1973》
诗歌:生存表达于此
在回忆录中,聂鲁达认真响应了自己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创作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我试着回想。在我还很小,才学会写字的时候,突然产生一股强烈的情感,然后就随便写了几行与平常说话很不一样、有点押韵的句子,就连我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我把那几句话誊写在纸上,当时我感到一股强烈的焦虑,一种在当下也说不上来的情绪,有点痛苦,又有点悲伤。那是一首献给我当时认定的母亲,也就是有如天使般温柔呵护我童年的继母。”灵感附体而全身颤抖的他把这首诗拿给父母看,却得到父亲漫不经心的“文学批评”——“你哪里抄来的?”(41页)
1923年,聂鲁达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晚霞》,题目来自他的一首诗,题为“马鲁里的晚霞”(Los crepύsculo de Maruri)描写自己居住的马鲁里街513号阳台上看到的傍晚景色。诗人敝帚自珍,如此回忆:
我的第一本书!我总是认为,作家的工作既不神秘也不可悲;相反地,至少一个用陶土捏出来的盘子,又或是技巧不成熟但很有耐心雕琢出来的一件木雕作品。不过,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手工艺匠能和诗人一样,一生仅此一次地陶醉在亲手做的第一件作品当中,而且神魂颠倒,感觉像在做梦般。这个时刻不会再出现第二次。虽然第一本书还会再出更好、更精美的版本,虽然它令人陶醉的内容会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犹如美酒倒进他的酒杯里,在世界各个角落流传、飘香;但是第一本书带着新鲜的油墨与柔软的纸张诞生的那一刻,有如小鸟飞舞、有如第一朵鲜花在被自己征服的高峰绽放时发出的声响一般,如此地令人着迷、醉心、那一刻在诗人的一生中只会出现一次。(85-86页)
爱情:阳光海洋阴影
聂鲁达一生有三位重要的女性伴侣:在爪哇寂寞难耐之时迎娶的首任妻子玛露卡(Marijke Antonieta Hagenaar Vogelzang,昵称Maruca,1900-1965)、比他年长二十岁的人生导师黛丽亚(Delia de Carril,1885-1989),陪伴他逃亡异国的灵魂伴侣玛蒂尔德(Matilde Urrutia Cerda,1912-1985)。在自传开头,聂鲁达回顾了自己少年时的初恋和相关的文学初创作,代同学写情书追求铁匠之女布兰卡·威尔森(Blanca Wilson),反而得到对方的青睐。
回忆录中第一部分“乡下的年轻人”中有两个故事很有意思,分别是“麦秆堆里的爱”和“返乡的少女”。前者描述的是少年聂鲁达的第一次性爱体验,如题所示,正发生在深夜的麦秆堆,对象是一位静静前来、激情无语的陌生女人,直到第二天中午午饭时间,刚进入青春期的他才在饭桌上依稀辨识出前一晚的秘密访客。这部自传里还收入了此次初体验几天之后发生的一段难忘插曲,关于一位“返乡的少女”。骑马回家的少年聂鲁达,马背上受他人之托,又载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女,后者的手很不安分,少年血脉贲张,但由于返程一路都找不到地方拴马,两人最终未能成其好事。五十年后,聂鲁达仍然难忘这段往事,还认为“在漫长的人生当中,那是我最挫败,最失意的其中一天”(53页)。
这种爱而不得的情绪,酝酿出聂鲁达在其满二十岁前几天出版的第二部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inte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在回忆录中,诗人总结这部诗集“是一部忧伤、具田园风格的作品,内容包含了我青少年时期最痛苦强烈情感,还混合了我祖国南方令人赞叹的大自然风光。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部作品,因为尽管它散发着浓浓的忧郁气息,但它令我享受到存在的快感”(88页)。这部诗集中的二十一首诗,分别献给三位聂鲁达深爱过却无法厮守的三位女性。在回忆录中,聂鲁达这样介绍这两位名字分别代表海洋与太阳(mar y sol)、海洋与阴影(mar y sombra)的女性:
经常有人问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二十首情诗》中的女人是谁?那部诗集中穿插了两三位女子,例如:玛莉索尔和玛丽松布拉。玛莉索尔来自夜空布满星辰的故乡,她是田园之爱的女神,黑色水汪汪的眼睛就像蝶梦谷湿润的天空。……活泼、俏丽的形象,伴随着港口的河水与海水,以及山峦间的月牙,玛莉索尔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诗篇中。玛丽松普拉则是在首都读书的女孩,她化身为灰色的贝雷帽,化身为无比温柔的双眼,也化身为时常散发出大学生用情不专气味的忍冬花香,还呈现出在大城市隐秘处激情幽会后回复平静的模样。(89页)
这部诗集中译本的译者序中,两位台湾译者陈黎与张芬龄如此考证:“聂鲁达在五十岁的时候说第 3、4、6、8、9、10、12、16、19 和 20 首是为玛莉索尔(泰瑞莎)所作;其余十首(即第 1、2、5、7、11、13、14、15、17、18 首)则是写给玛莉松布拉(阿尔贝蒂娜)的。时间会模糊或混淆记忆,聂鲁达有时候说‘灰色的贝雷帽’是玛莉松布拉的,有时又将它戴在玛莉索尔的头上。或许这两个女孩都曾戴过同样的帽子,也或许这两位青春期的恋人早在诗人心中融合为一体。六十五岁时,聂鲁达还说第十九首情诗其实是献给马莉亚·帕若蒂(Maria Parodi)——他在散发着海洋和忍冬气味的萨维德拉港所结识的另一名女子。”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出版和翻译版本最多,流传最广的聂鲁达作品集。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博士在授奖辞中如此评价这部诗集:“从他《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我们可以大体窥见聂鲁达的诗对于操其语言的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它配上乐曲,并且到处传唱,但常常并不知道作者是谁。这部诗集译本的出版更具世界性,十年前已达百万册。然而在那些充满丰腴美与阴郁美的画面里所描述的相逢,总是由彼此陌生的两个人在雾蒙蒙的冰冷的黄昏里进行。”
第二十首情诗写给玛丽索尔,其中有一句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此句来自第二十首情诗《今夜我可以写出》,开篇直抒胸臆,对自己深爱的女生告白,同时也知道这位女生对自己未必付出同样的感情: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篇。
写,譬如说,“夜缀满繁星,
那些星,灿蓝,在远处颤抖”。
晚风在天空中回旋歌唱。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篇。
我爱她,而有时候她也爱我。
开篇中提到的哀伤,来自于诗人对单恋对象的失望,因为对方无法响应自己的爱,于是写诗抒怀。但是,在此诗最后五段,诗人百感交织,复杂情绪呼之欲出:
如今我确已不再爱她,但我曾经多爱她啊。
我的声音试着藉风探触她的听觉。
别人的。她就将是别人的了。一如我过去的吻。
她的声音,她明亮的身体。她深邃的眼睛。
如今我确已不再爱她。但也许我仍爱着她。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因为在许多仿佛此刻的夜里我拥她入怀,
我的心不甘就此失去她。
即令这是她带给我的最后的痛苦,
而这些是我为她写的最后的诗篇。
从以上数段可以看出,诗人似乎已经放下自己曾经深爱,却无法拥有的女性,确认自己现在对她已经不复爱恋,但在知道对方即将出嫁之后,却仍然无法释怀,怀疑自己的嫉妒痛苦也许还是爱的表现。这首诗,是诗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也是对这二十首诗歌的一个总结。在最后一首诗“绝望的歌”里,诗人承认,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个人欲望的黑洞无法满足,对单一个体的爱欲无法持久:
哦肉,我的肉,我爱过又失去的女人,
在这潮湿的时刻,我召唤你并为你歌唱。
如同一个杯子,你盛着无尽的温柔,
而无尽的遗忘打碎你如同一个杯子。
在最后一段中,开篇中黎明的码头这一意象重复出现,被遗弃的感觉被再三强调:
像黎明的码头般被遗弃。
只剩颤抖的影子在我手中扭动。
啊,超越一切。啊,超越一切。
这是离去的时刻。哦,被遗弃者!
(以上诗歌译文引自陈黎、张芬龄译本,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10月版)
被谁遗弃?也许是被爱人,也许是被记忆,也许是被时间,也许是被命运。所谓绝望,正来自于诗人对爱情本质的参透,了解到欲望一旦实现便不复诱人,更加无法持久,只有在永恒的追寻与失落过程中,爱欲才能保持其鲜活强盛。诗歌,正为这种绝望呼告提供了表达的出口,也在万千辗转求爱的读者之间产生深刻共鸣。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革命:文学创作之根
就在聂鲁达完成《二十首情诗》之后,智利社会发生巨变,一方面,“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崛起,他们在学生和作家间寻求更多支持”,另一方面,失业潮席卷智利全国上下,工人领袖成立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圣地亚哥示威游行被警察镇压(89-90页)。由此,聂鲁达开始以文学创作投入革命的人生征程。
先后作为外交官和流亡者,诗人足迹遍布世界。1927年,二十三岁的聂鲁达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驻缅甸领事,之后的八年里他先后到过印度、中国、日本、爪哇、新加坡、阿根廷、西班牙和巴黎。这期间,聂鲁达出版了《热情的投掷手》(El honderoentusiasta)和《土地的居民》(Residencia en la tierra)。后一部诗集出版于1933年,这是三卷作品中的第一本,描述了聂鲁达在他多年的外交旅行和社会活动期间所见证的社会动荡和人类苦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作品中,Residencia是一本黑暗而阴沉的但是必不可少的书。”此部作品的第三卷“西班牙在我们的心中”(España en el corazón)对遭受内战之苦的西班牙人民表示深切同情。1936年,马德里遭到轰炸之后,聂鲁达离开此地,到巴塞罗那与妻女团聚。同年,智利驻两地领事馆关闭,聂鲁达不再获派领事职务,于是与家人经由马赛抵达蒙特卡罗,与前妻分开,随后与第二位伴侣黛丽亚赴巴黎居住,并创立编辑《世界诗人捍卫西班牙人民》杂志,筹办一系列帮助西班牙难民的活动,协助他们前往法国避难。四十年代,聂鲁达与黛丽亚访问墨西哥、美国、巴拿马等地,受到热烈欢迎。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1947年被智利政府起诉,1949年为逃避追捕前往阿根廷,辗转到达巴黎。电影《追捕聂鲁达》正是以此经历为蓝本创作。
在智利政府的追捕下,聂鲁达四海为家,写诗是他获得存在感的唯一方式。在回忆录“黑暗中的祖国”部分,聂鲁达写到关于“根”的情景:
爱伦堡一边读我的诗、翻译我的诗,一边指责我:太多“根”了,你的诗歌里太多“根”了。为什么这么多?
没错。边境的土地在我的诗歌里扎根,而且永远无法离开。我的生命长时间漂流,不停地反复奔走,但总是返回南方的树林,返回被遗忘的森林。
……
或者之后,当我骑马穿越山脉到阿根廷时,在巨树所构成的绿色穹顶底下,遇到了一个阻碍:其中一棵树的根比我们的马还要高,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好费力气还动用了斧头,才让道路畅通,那些根就像坍塌的大教堂,发现它们的巨大,也让我们了解它们可敬的地方。(278页)
在回忆录第十一章“诗是一种职业”中,聂鲁达如此写道:“在我们这个有着战争、革命、巨大社会动荡的时代中,能够顺利地写诗,将诗歌发展到不被质疑的境界,真是一种特权。一般人若不是在孤独中面对诗歌,就是在山上群众的聚会中面对;所以他们不是伤害了别人,就是被别人伤害。……当我创作最早期的孤独诗歌时,从没想过多年后会在广场上、大街上、工厂、教室、剧场和花园里朗读我的诗。”(357页)
而聂鲁达也特别说明,自己的诗歌无界,但写作的姿态,就好像树根一样,总是尽力倾向于自己深爱的,但却被黑暗笼罩的祖国:
如果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它有某种特殊、无限延伸的倾向,仿佛不甘心只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我的藩篱必须由我来超越。我不会将藩篱设限在某个遥远的文化框框里。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向我诞生的那块狭长的土地,尽力自我延伸。(370页)
1971年,聂鲁达在得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重新回顾当年骑马抵达阿根廷的那段经历:
在那无边无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葱葱茏茏和白雪皑皑的静穆中,树林、粗壮的藤蔓、沉积了千百年的腐殖土、突然倒下的变成我们前进的又一道障碍的树干,使我们每个人在行程中目不暇接。满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的大自然,又是严寒、冰天雪地以及追捕的有增无减的威胁。孤独、危险、沉寂以及我的使命的紧迫感,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聂鲁达一生之中,以创作诗歌作为在脚下土地扎根的方式,以此在流散时空中寻找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次演讲中,聂鲁达如此总结诗人的责任:
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美洲广阔土地上的作家,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召唤: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实那一大片空间。我们深知自己作为开拓者的责任——同时,在那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进行批评性交往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责任,何况那里并不因为荒无人烟,不公正、磨难和痛苦就会少些;我们也感到有义务恢复古老的梦想,这些梦想至今还是石像、毁坏了的古碑、笼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鸣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我们必须使无法表达意志的大陆的每个角落都说出自己的话语;做出这种设想并把它表达出来的任务,使我们心醉神驰。也许这只是支配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情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夸张言辞、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敲的诗句,都不过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对聂鲁达而言,因为诗歌、革命和爱情,他的一生没有白白活过。每个热爱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想必也是希望通过阅读聂鲁达诗歌汲取生命活力,体味爱情甘苦。其实,若未曾全心投入去爱,去行动,去改变至少一次,谁又可以坦言自己曾真的活过?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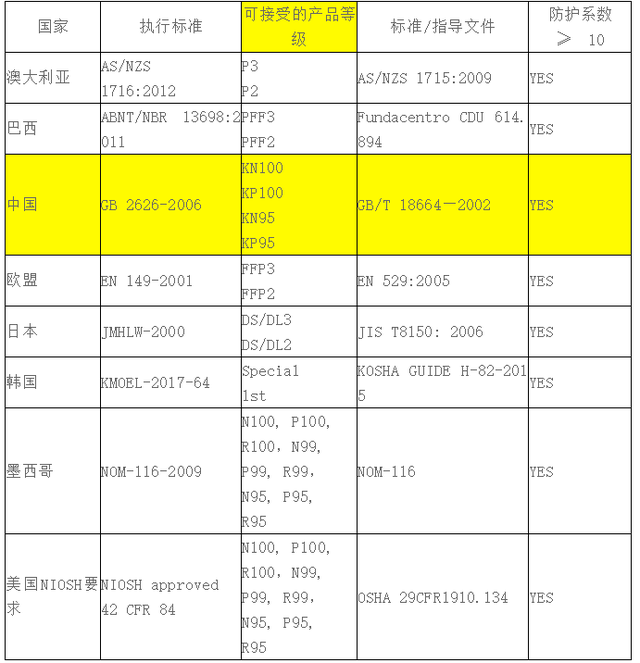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