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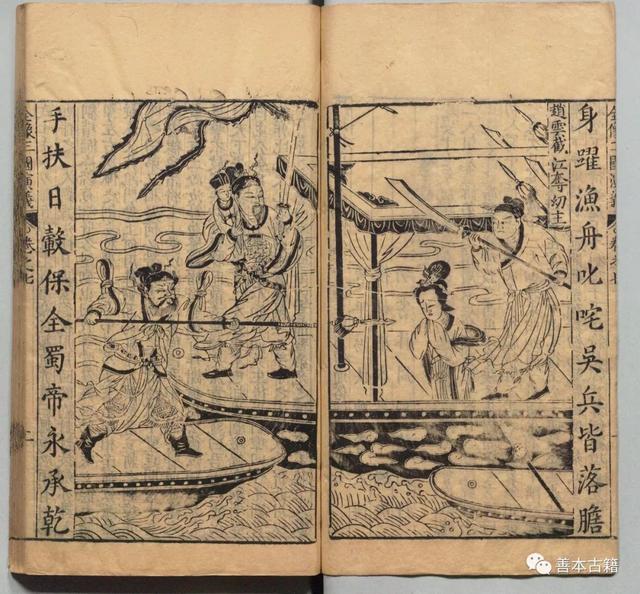
所谓域外汉籍,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经过前辈学者的辛勤收辑,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通过翻拍、影印或撰写目录等手段,多已为学术界所知见。但古代域外人士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却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域外汉籍的主体。自1992年以来,我对域外汉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多次赴日本、韩国、越南、冲绳(古代的琉球)、新加坡等地收集资料,主持或参与了国内外的若干科研项目,并在2000年成立了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我深信,随着有关文献整理工作的展开,例如目录、提要、资料汇编、文献校释等,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域外汉文学研究即将诞生。这一学科分支直接涉及到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汉字文学研究;二是东方文学研究;三是比较文学研究。本文要谈的主要是其中一个方面的研究,即汉字文学研究。汉字文学是以中国的汉语文学为主,并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的汉文学。以整体汉字文学为背景,这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学术课题。
我先来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文镜秘府论》是唐代日本来中国的空海大师(774-835)所编纂,书中汇集了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齐、梁以来至中唐的诗学资料(注:有关《文镜秘府论》材料来源的考订,可参看日本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讲谈社1953年版),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市河宽斋《半江暇笔》云:
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者,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806-809)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注:转引自池田胤《日本诗话丛书》第七卷《文镜秘府论》解题(文会堂书店1921年版,第215页)。案:林衡于文政三年(1856)所撰《市河子静墓碣铭》列其著述多种,其中有《半江暇笔》五卷。至大正乙丑(1925)市河宽斋曾孙市河三阳撰《宽斋先生著述解题》云:“先生碑文尚载《半江暇笔》五卷,诸家著述目录举若干书名,皆未得见之。”(《宽斋先生余稿》,游德园1926年版,第430页)如今在日本遍觅不得,究竟是亡轶或藏在私家,待考。)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光绪丁酉刊本)卷十三云:
此书盖为诗文声病而作,汇集沈隐侯、刘善经、刘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说。今传世唯皎然之书,余皆泯灭。按《宋书》虽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诸说,近代已不得其详。此篇中所列二十八种病,皆一一引诗,证佐分明。
四声八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问题,但八病由何人提出?其含义又是如何?在没有见到《文镜秘府论》之前,中国人的论述是不明晰的。例如,纪昀《沈氏四声考》卷下云:“按齐、梁诸史,休文但言四声、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根据《文镜秘府论》,得出沈约提出“八病”说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就被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因此,《文镜秘府论》作为一部非常重要的域外汉文学典籍,是广为人知并广为人用的。然而,这只是在极其丰富的域外汉籍宝库中的一种。
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地区和国家以很大影响,形成汉文化圈,除中国以外,主要还包括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地。后者又可称作“域外汉文化”。直到20世纪初,汉文化圈主要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知识人写作了大量的汉文作品,因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保留下大量的汉籍文献。略举如下:
1.韩国 汉籍数量惊人,仅以汉城大学奎章阁所藏韩国本为例,据1981年出版的《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达三万三千八百零八种。其中除少数如小说类中的“国文”部分,绝大多数是汉籍。韩国的汉籍中,文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韩国文集丛刊》已出版二百八十册,收文集七百多种;《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平均以一集一册计算,也达三千种。
2.日本 日本的汉籍也极为丰富,根据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及《古典籍总合目录》的著录,即使排除了其中的日文本,汉籍的数量仍然是惊人的。从文集来看,如《群书类从》和《续群书类从》的文笔部,《五山文学全集》、《五山文学新集》、《日本汉诗》等,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3.越南 根据由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于1993年合编出版的《越南汉喃遗产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nom)著录,越南的汉籍作品共有五千多种(其中包括一些喃文作品),其中集部类达一千六百多种。
4.琉球 琉球历史上尽管颇多文学之士,但文集多未刊刻。朝鲜时代南公辙《记琉球人语》记载:“自古有学问文识之士,而俗不刊书行世,如有著书者,则只誊传于子孙云云。”(注:《金陵集》卷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63页。)所以经过战争的毁坏,其汉籍文献保存至今者已不多(注:参见高津孝、荣野川敦编《琉球列岛における宗教关系资料に关する总合调查·汉籍目录篇》,日本平成四·五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总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年印行。)。
域外汉籍从其来源来看,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中国图书,有些是中国的刻本,有些则是他们的翻刻或重抄本,其中部分图书在中国已经失传;另一类是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著作,这是域外汉籍的主体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域外汉籍虽以汉文化圈为主,但并不限于此。如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特藏的一批19世纪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就达七百多种,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内容。
20世纪是中国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造成其蓬勃发展的原因,如果从文献角度认识,则要归功于新资料的发现与运用,据王国维的概括,有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四裔遗文。到了今天,学术研究工作者纷纷感到又有一些新的材料值得重视,如史前遗存、考古发掘、明清档案、海外文献和外销遗物等。而域外汉籍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新材料。
学术研究要重视史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无疑应该得到学术工作者更多的重视。这里,我想以自己的工作为例,对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略作说明。
1.《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研究唐代文学的人早就感到,唐代号称繁荣,但唐人的文学批评资料却颇为难得。明代以来就流行着“唐无诗话”(这里的“诗话”是泛称诗歌评论)之说,胡小石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稿》第十章“唐代文学批评”节中也指出这一现象:“唐代的诗文,如日中天;而论文之著作,则寥若晨星。所以后人都说唐人只知作诗,而宋人才专门出来替唐人作诗话。……假使要编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各朝均容易收辑材料,只有唐代较感困难,因为当时论文书籍都未能流传至今。”(注:《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但唐代文学批评的资料实际上并不贫乏,主要问题在于资料的散佚和真伪的混杂。从诗歌批评来看,唐代是诗格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初盛唐的诗格集中在《文镜秘府论》一书中,晚唐五代的诗格集中在《吟窗杂录》。前者是域外汉籍,后者自明代以来未曾再作刊刻(直到1997年才有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所以,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镜秘府论》中钩辑出上官仪《笔札华梁》、佚名《文笔式》、元兢《诗髓脑》、佚名《诗式》、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等,并对其时代、真伪、书名、人名等问题作了考订,弥补了初盛唐诗歌理论资料的短缺。又如,过去谈到唐代的文章学理论,一般只讲韩、柳的古文论,而对于骈文和律赋的理论则多忽略。原因之一,就是现存材料的匮乏。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域外汉籍的资料,如集中在《文笔要决》、《笔札华梁》、《文笔式》和《帝德录》中的骈文论,保存于日本的唐人《赋谱》所代表的律赋论,就可以为唐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如《笔札华梁》、《文笔式》中关于骈文写作的种种避忌,《文笔要决》中关于骈文句端词在起语、接语、转语中的运用法则,《帝德录》中对骈文句式和相应词汇的归类等。类似的书,唐人编过不少,据说陆贽有《备举文言》三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注:《中兴馆阁书目》,《玉海》卷二百一《辞学指南》引,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李商隐也编有《金钥》二卷,“以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四部分门编类”(注:《中兴馆阁书目》,《玉海》卷二百一《辞学指南》引,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但皆已亡轶。同样,唐人也编写过大量赋格类著作,进士试律诗赋,也是“依《诗格》、《赋枢》考试进士”(注:《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版,第7695页。)。此类书亦多亡轶。因此,日本所存平安末期的抄本《赋谱》就弥足珍贵。其中涉及的问题,有关律赋的句法、结构、用韵、题目等,对于我们研究律赋的特征并深化对唐代科举考试的认识,意义重大。我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的附录中,就收有《文笔要决》和《赋谱》,为今日唐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本。
2.《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与唐代比较起来,宋人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话类的著作,经过前辈学者如郭绍虞、罗根泽的全力搜讨,基本规模已经具备。但如果将眼光扩大到域外汉籍,则仍有继续补充的余地。我编校的《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实际收录了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十卷、日僧无著道忠《冷斋夜话考》一卷、日本宽文版《天厨禁脔》三卷、明抄本《西清诗话》三卷、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十卷、明抄本《北山诗话》一卷,共六种。兹就其中所涉域外汉籍略说如下:
五山版《冷斋夜话》为覆宋版,是目前所存诸本中的最佳版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至佳”二字评之。与中国所存其它版本相比,五山版文字最全,同时也最为准确。《冷斋夜话考》是日本江户时代僧人无著道忠所撰,是对《冷斋夜话》的惟一考释之作,直接引用的文献达四十三种。其基本特色是注重语句和典故的探源,兼及注解或辨证。宽文版《天厨禁脔》依循日本五山版系统,与中国所存明正德版相比,误字较少。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是仅存孤本,中国早已失传。原书二十卷,现存十卷。这是第一部分门类编的诗话总集,在中国诗话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全书分三十四门,略作比较,可以看出,后来的《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著,皆踵事增华之作。此书的重新发现,使人们对中国诗话史的认识随之而有所改变。
以上所举,有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有域外人士用汉字书写的作品,这些资料的发现和运用,无疑将推动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
中国文学是汉语文学的主流,我们从主流去认识中国文学当然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既考虑到主流,又考虑到主流与支流以及支流与支流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以汉字文学的整体为背景研究其各个部分,我们对以汉语文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就可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到先师程千帆与同学程章灿合撰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所写的都是中国的汉语文学,如果结合域外汉文学,那么,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汉文学史研究就可以真正展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学的主流,仍然是由汉语文学担当的。这一点在东方各国的文学史上,也有类似之处。汉文学在域外文学史上都曾经享有殊荣,一切正规的场合、一切正大的文体,都必须用汉语表达。在当时人看来,用汉字写成的文学可以称作文学,而用谚文所写的只是“俗讴”、“俚语”、“方言”,用假名或喃文所写的是“女性文学”(这在今日成为时髦文学或热门研究,但当时这一名词含有贬义)等。因而研究东方文学,是离不开东方汉文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域外汉文学,是既有着同源关系,又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合适对象。这一点,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已经指出:“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注:《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224页。)而在这种比较研究之中,我们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会进一步加深。以下从五个方面略作说明:
1.文学典籍的流传 我们要知道中国文学在汉文化圈内的文学中是如何起到种子和核心的作用,首先应该弄清楚哪些中国文学典籍在何时、通过何种途径流传到域外,我们可以利用现存域外文集、书目记载、当时来华使者的购书清单、中国历朝政府的赐书目录以及各国间的海陆贸易(特别注重图书贸易)展开研究。我们大概都知道唐代张,当时新罗和日本的使臣来中国,“多求文成文集归本国,其为声名远播如此”(注: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四库全书》本。)。例如他的《游仙窟》在中国从未有所著录,但在日本却保存了两种抄本(一种有注)及江户时代的刊本。我们也知道白居易生前其文集在日本和新罗已有广泛传播,林鹅峰《本朝一人一首》附录云:“嵯峨帝(809-823在位)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影印原文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435页。)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也指出:“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注:《元稹集》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5页。)所以,在日本现在还保存着最好的白居易文集的版本。由于史书和笔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白居易的文集是通过海上贸易的船只在公元815年前后渡往日本的。但有的问题未必如此清楚,如《文选》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就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通过文献考证的方式,得出离真相不远的结论。日本第一个以“诗话”命名其著作的是五山诗僧虎关师炼,这当然是在宋人诗话的启发下出现的。我们如果要了解五山诗僧能够读到的宋人诗话有哪些,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文集作一综合处理。如以万里集九的《梅花无尽藏》为例,其中提到的宋人诗话就有十四种之多。日本江户时代以下出现了不少“仿世说”的作品,如《大东世语》、《假名世说》、《世说新语茶》、《近世丛话》、《新世语》等(注:参见Nanxiu Qian,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Chapter 9,“An Alien Analogue:The Japanese Imitation Daitō seigo”.pp.319-338.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但这和江户时代对《世说新语》的注释活动是相联的。江户时代有关《世说新语》的注释本甚多,如冈白驹《世说新语补觽》(1749)、桃井源藏《世说新语补考》(1762)、释大典《世说钞撮》(1763)、恩田仲任《世说音释》(1802)、释显常《世说匡谬》(1810)、田中大壮《世说讲义》(1816)、秦鼎《世说笺本》(1826)等(注:参见大矢根文次郎《江户时代における世说新语について》,《世说新语と六朝文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第89-107页。)。这些注释本,对今天理解《世说新语》也有帮助。而且,我们还可以知道,日本人更重视的是王世贞的《世说新语补》。
2.文学人士的交往 如果我们把汉文化圈作为一个整体,把汉字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在这一整体中的文化人是如何交往的。我们需要研究域外文人、僧人来华的行踪及与中国文人的交往,中国使臣与当地文人及外国使者与中国文人的诗赋外交,更扩而大之,我们还应关注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各国文人的交往。因为汉字是当时各国的通用文字。如明万历二十五年朝鲜李睟光出使中国,就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至万历三十九年再到中国,又有与琉球、暹罗使臣的赠答录(均见《芝峰集》卷九)。康熙五十七年越南使者阮公沆《简高丽国使俞集二、李世瑾》诗云:“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注:徐延旭《越南辑略》卷二“诗选”,光绪三年版。)吴士栋《赠朝鲜国使李珖、郑宇淳、尹坊回国》诗云:“敷文此日车同轨,秉礼从来国有儒。”(注:徐延旭《越南辑略》卷二“诗选”,光绪三年版。)我们可以通过唱和诗、使者日记或旅行记录以及文人笔谈展开研究。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应该重视“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从我收集到的近四百种约六万页的各种燕行录来看,这是一个资料宝库。特别是其中的文人笔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限于文学或史学)。若就文学而言,则如现存朝鲜时代二十四种《皇华集》,皆为中朝使臣与文人的唱和之作,虽然纯粹从文学角度视之,未必说得上是精品,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视之,则是不容忽视的史料。而且,这种“诗赋外交”的制度,对于推动朝鲜汉文学的发展也是具有相当作用的。又如日本雨森芳洲所编的《缟纻风雅集》,是一部日本和朝鲜文人的唱和集。又其中《芳洲笔谈》,其中也有与文学相关者,不仅讨论朝鲜、日本的汉文学,对中国文学也有评论。元重举的《和国志》、李德懋的《蜻蛉国志》都专列有关日本文学及文人的章节,申维翰的《海槎东游录》中有对日本文人及汉诗的实地评论,都是朝鲜与日本文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史料。
3.文学读本的演变 汉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有赖于汉文学启蒙教育,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文学启蒙教育各有异同,尤其值得重视。可以通过对启蒙教育的一般内容、次第及文学教科书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演变而展开研究。我们可以拿《文选》在朝鲜和日本作一个比较。从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时代,经过高丽直至朝鲜朝,《文选》可以说一直是汉文学的基本读物。《旧唐书·高丽传》说子弟未婚之前,在扃堂昼夜读书,对于《文选》“尤重爱之”。统一新罗时代,《文选》被立为国学教材,与《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列。又制定读书三品出身之法,能通《文选》者可列为上品,而中、下品就没有对《文选》的要求(注:参见《三国史记》卷三十八《杂志》第七,明文堂1988年版。)。高丽时期,《文选》是涉及国家大制作的典范之一。到朝鲜朝,虽然启蒙读物中增添了《古文真宝》、《文章轨范》、《联珠诗格》等书,但《文选》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反观日本,《文选》在推古帝时代(592-628),即隋唐之际已传入日本,在平安时代曾被作为样板,《本朝一人一首附录》说,当时“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即使是编选本国的选本,也以《文选》为典范。如《怀风藻》和敕撰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都受到《文选》的很大影响。但是到了五山时期,文学风气改变,文学启蒙读物就不再是《文选》,而是《三体诗》、《古文真宝》、《联珠诗格》等书。林鹅峰《题侄宪所藏文选后》云:“近岁少年丛偶学诗文者,狭而《三体》、《真宝》,广而苏、黄集而已,至如《文选》,则束阁而不读焉。”(注:《鹅峰林学士文集》下,ぺんかん社1997年版,第407页。)林道春《三体诗古文真宝辨》云:“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学诗则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专以《古文真宝》。”(注:《罗山文集》卷二十六。)到江户时代中期,诗风由沿袭宋调转为崇尚唐音,于是托名李攀龙的《唐诗选》甚极一时,重印次数多达二十,印数近十万部。而且这类书上还往往印有“不许翻刻,千里必究”或“至于沧海,不许翻刻”的字样,这种版权意识也正说明翻刻此类书的有利可图。再往下诗风又转,于是《联珠诗格》又再次得到重视。山本北山《孝经楼诗话》卷上指出:
《唐诗选》,伪书也;《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妄书也;《唐诗鼓吹》、《唐三体诗》,谬书也;《唐音》,庸书也;《唐诗贯珠》,拙书也;《唐诗归》,疏书也。其他《唐诗解》、《唐诗训解》等俗书,无足论也。特有宋义士蔡正孙编选之《联珠诗格》,正书也。(注:《日本诗话丛书》第二卷,文会堂书店大正九年(1920)版,第72页。原文为日语,兹撮译其大意。)
同属汉文化圈,为何文学启蒙读物不一?为何《文选》的遭遇不同?这又是可以深入一问的。其实简单回答,就是一句话,这与科举制度有关。朝鲜实行科举制度,有科举就要试诗赋,试诗赋就离不开《文选》的样板。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所以诗风一变,文学启蒙读物便随之而易。
4.文学观念的渗透 文学观念不仅表现在对文学的认识、评价文学的标准、解释文学的方法,也体现在文人的自觉、文人的出处和操守等方面。在汉文学圈内,这些观念是以中国为核心,渗透在域外汉文学及文学批评中。我们可以具体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在朝鲜、日本和越南(资料较少)文学批评中的响应和辩驳,广泛利用中、日、韩的诗话、选本和文集,从理论批评和实际批评两方面展开研究。从韩国和日本的诗话来看,资料丰富。据韩国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所收诗话一百二十二种(其中有少数有目无书,另外还有少数遗漏,我已收集此外的韩国诗话七种)。日本在大正九年至十一年,曾由池田胤编辑出版了《日本诗话丛书》十卷,收日本诗话六十三种,此外,我又收集了二十八种。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如果把三个国家的诗话作一比较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诗话体从中国发源,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其次,在具体的诗歌作法方面,日本和韩国的诗话都遵循了汉诗的基本规则。这在日本的诗话中显得尤其突出,具有“诗格化”与“小学化”的特征。日本诗话中以“诗格”、“诗法”、“诗则”、“诗范”、“诗诀”命名者颇多,正体现了这一特色。第三,在对待中国诗话的态度上,韩国诗话亦步亦趋,日本诗话则多有辨证。朝鲜半岛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是徐居正的《东人诗话》,其内容不管是纪事、批评还是理论,即使所纪所评都是东国诗人之事之诗,但往往以宋人诗话记录者为引发,或类比,或评论,或考证。其批评与理论也总是以宋人诗学为标准衡量,或对宋人理论命题作进一步阐发。反之,以日本第一部诗话为例,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既有对宋人诗学的继承,也有驳难和辨证。这在日本诗话中几乎可以形成一个特色。在日本诗话中,有一部奇特之作,即刘煜季晔的《侗庵非诗话》十卷。从第三卷到第十卷,历数诗话十五病,一一举例以明之。对于今天我们认识诗话的价值和不足,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传统著述中虽然也有对诗话的批评,如冯班的《严氏纠缪》、赵执信的《谈龙录》,但侗庵认为:“《沧浪纠缪》、《谈龙录》为一人而作,私也;予《非诗话》为诗道而作,公也。”(注:《侗庵非诗话》卷二,崇文院1927年版。)即便章学诚《文史通义》专列“诗话”篇,但其实针对的也只是《随园诗话》一种,而不是全面批判。这与日本诗话相比,又显出同中之异。
文学观念也包括文人出处所应遵循的操守,中国文人中的一些典型往往成为域外文人的行为模范,如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等。甚至在坐骑方面,也有深刻的影响。陆游在剑门道中行时曾有这意味深长的一问:“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注:《剑门道中遇微雨》,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金源诗人李纯甫《灞陵风雪》中也写道:“蹇驴驼着尽诗仙,短策长鞭似有缘。”(注:元好问《中州集》卷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222页。)从阮籍开始,到唐代孟浩然、杜甫、贾岛、李贺、郑綮,驴成为诗人特有的坐骑,同时,这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坐骑。蹇驴与骏马相对,这也是在野与在朝、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吴师道《跋跨驴觅句图》云:“驴以蹇称,乘肥者鄙之,特于诗人宜。”(注:礼部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坚持骑驴,就是坚持席帽布衣的传统,而伟大的文学,也往往产生于以“蹇驴破帽”为象征的坎坷生活之中。高丽、朝鲜时代的诗人,不骑驴而骑牛,虽然有这点差异,但骑牛也是与骑马相对的。骑牛是脱俗、逍遥、隐逸的象征,而骑马则代表了入世、躁进和名利场,这一价值观念却是相同的。高丽时期的诗人郑枢《东国四咏》云:“何妨牛背觅诗来。”(注:《圆斋稿》卷上,《韩国文集丛刊》第五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96页。)朝鲜时代的诗人成石璘《有怀看花诸君子寄呈骑牛子》云:“牛背哦诗野趣长。”(注:《独谷集》卷上,《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册,第82页。)成伣《皱岩》云:“牛背吟诗乘雪去。”(注:《虚白堂集》诗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十四册,第274页。)朝鲜时期的文人写了众多的《骑牛说》和《骑牛歌》,充分发挥骑牛与骑马的对立之意。因此,继承的还是中国文人骑驴的精神。至于日本诗人,在王朝时代以贵族为主,五山时代以僧侣为主,到江户时代才有较多的普通文人出现,但是,写到诗中,诗人却多是骑驴。我们知道,日本国中并没有驴,因此,诗人写自己骑驴,绝非写实,这只是一种诗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注:菊池侗孙《五山堂诗话》卷六指出:“诗中铺叙不可失实,今日作者,殆不胜其病。年齿方奢,而动有衰颓之语;不出闉阇,而便发倦游之叹;四面无山,强称青岑;一时有雨,犹说夕阳;啸此不传,驴我所无,而屡言不置。凡如此类,随手滥用,不觉自陷于欺罔矣。”)。日本文学的政治性不强,所以,在日本汉诗中,也很少看到将骑驴与骑马相对立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比较,能够使我们从某一侧面看到东亚汉文学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从而加深对各国汉文学的理解。
5.文学典范的确立 中国的汉语文学对域外的汉语文学具有种子和核心的作用,不同时期文学典范的演变,往往与一时文学风气的变换相关。具体分析各类文学典范,有些是整个汉语文学世界中所共有的,有些则仅在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汉文学中存在。有些文学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有的则评价并不高。站在汉文学整体的立场上看,对一些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可能应该重新考虑。在汉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经常为人所举,这就是15世纪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这是一部传奇志怪小说,此书出版后不到百年,就在朝鲜出现了仿作——金时习的《金鳌新话》(15世纪)。此后,又出现了朝鲜人所作的详细注释——《剪灯新话句解》(16世纪),并在十六年间刻印了三版,反映了此书受到普遍欢迎。现代韩国学者甚至有把《剪灯新话》看作“朝鲜小说创作的起源”(金东旭《中国故事与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壬辰倭乱(1592),《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等书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新的仿作——17世纪的《伽婢子》和18世纪的《风月物语》,19世纪英国作家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将《风月物语》中的一篇改成英文小说《和解》(Reconciliation),广受欧美人士的喜爱。又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提到安南流行的中国典籍,就有《剪灯新话》和《余话》,所以,越南阮屿的小说《传奇漫录》也受到《剪灯新话》的影响①。在中国文学史上,《剪灯新话》可能只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而已,并没有很高的地位。但如果将此书置于汉文化圈文学史上来看,则其地位显然将大大提高。这是朝鲜、日本和越南小说的典范之一。此外,中国宋代以下的一些文学选本,如《文章轨范》、《古文真宝》、《唐三体诗》、《联珠诗格》等,都曾在域外汉文学史上作为典范而存在,而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书向来被视为俗书、陋书,或以便科举,或以训初学,地位颇低。如果站在汉文学整体的立场上看,这些书的文学史意义可能也将得到重新认识。
汉文化圈的形成,与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周边地区文化宗主国的存在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东亚文明。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人种、语言、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地区的文明却又普遍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宗教的和道德的观念、知识的结构等等,是根据某种基本原则展开的。然而不同的地域所特有的区域文化,在文学艺术中所展现的心灵的丰富性,又使得东亚文明并非纯粹而单一。这种统一文明中的多样性,这种寓多样于统一的文明,体现的就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大同思想。21世纪的世界,随着中国和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崛起,汉文化的地位也必然会得到提升和重视,汉文化也因此而有可能对未来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消除对抗,平等对话,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字文学作整体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人类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处,最终实现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必然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来源:《文学遗产》2003年第03期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圈
学习古籍版本,离不开查看实物、关注古籍网拍、了解市场价格!网拍是低成本、最方便的学习方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