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为何被广泛关注?通过三例官司来看背后的伦理困境
以下文章来源于一嘉医课 ,作者yoyo卢珊珊。

撰文 | 卢 珊
1978年,全球首例人类卵子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婴儿出生[1],由于其受精过程在实验室进行,这些孩子被形象地称为“试管婴儿”。至今四十多年,全球估计已有700万例通过IVF及其改良技术实现的妊娠[2]。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已经发展出多种改良,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配子输卵管移植(gamet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 GIFT)及合子输卵管移植(zygot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 ZIFT)[3]。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的定义,代孕(Surrogacy)指能孕女性接受委托,同意将他人的胚胎(受精卵)植入自己的子宫,由自己代替他人孕育、分娩新生儿的法律行为,该孕母不提供卵子,因此与孩子在生物学上(遗传上)无关[4]。
不论是否关注娱乐圈新闻,应该都被这两天的动态刷屏。“代孕”作为辅助生殖技术中一个具有极强社会属性的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放到风口浪尖上。今天,我们推荐3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代孕”案例,希望和大家一起从法律和伦理角度,共同探索其复杂性。
案例一
家住美国新泽西的威廉•斯特恩,其妻子伊丽莎白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由于担心此病遗传给下一代,夫妻二人于1985年2月和玛丽•贝丝女士签订了代孕合同。斯特恩先生提供精子,玛丽•贝丝提供卵子并代孕[5,6]。
合同规定,玛丽•贝丝交出婴儿时可获得10,000美元的报酬,斯特恩先生也会向辅助生殖技术中心支付7,500美元。然而,婴儿梅丽莎出生后,玛丽•贝丝却希望由自己养育,即推翻原合同约定。几经纠缠后,斯特恩先生无奈,只得提起诉讼,要求执行代孕合同,得到婴儿梅丽莎。
在此之后,玛丽·贝丝带着婴儿逃离,两个家庭间有关父母权力和道德的争议不断升级——玛丽·贝丝还威胁要自杀并杀死婴儿,诬陷斯特恩先生性骚扰......
该案经新泽西最高法院判定:根据公共政策,代孕合同无效,承认玛丽·贝丝为婴儿梅丽莎的合法母亲;此外,斯特恩先生作为梅丽莎的合法父亲,依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被授予监护权,玛丽·贝丝拥有探视权。
案例二
马克和克里斯皮娜·卡尔弗特夫妇想要孩子。不幸的是,克里斯皮娜曾接受过子宫切除术,虽有卵巢和卵子,但却无法为受精卵提供生长发育的「土壤」[7]。
1989年,夫妻二人与安娜·约翰斯顿签订了代孕合同,依靠辅助生殖技术将二人的受精卵胚胎植入安娜体内孕育。双方签署的合同规定,孩子出生后,安娜同意放弃所有父母权利,获得10,000美元的报酬及2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然而在安娜怀孕后不久,双方逐渐产生矛盾,而后安娜提起诉讼,拒不执行代孕合同。3年的法庭拉锯战让卡尔弗特夫妇——这对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几乎倾家荡产,好在最终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
案例三
1998年4月,美国纽约的法萨诺夫妇(白人)生下了肤色一黑一白的双胞胎,原因是纽约体外受精中心误将另一对黑人夫妇罗杰斯的受精卵一同植入了产妇法萨诺夫人的子宫,于是才生出了黑人婴儿阿基尔娠[8]。
经过法院审理,法萨诺夫妇同意放弃对阿基尔的监护权,但是有探视权,也同意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将唯一的亲生父母和合法父母改为罗杰斯夫妇。
这几个案例在得到了法院的一锤定音后,仿佛是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伦理导向。但是,其中有几处细节耐人寻味:
01 辅助生殖技术在法律与伦理的制衡下能走多远?
案例一中,新泽西最高法院裁定“不得强迫一个健康的母亲放弃婴儿”,其内核本质是血缘关系和妊娠胜过已签订合同的契约精神。
这个里程碑式的案例试图敦促全社会努力应对代孕的后果,特别是该思考应否允许斯特恩斯(一名生物化学家和儿科医生)发挥相对富裕的优势,让高中辍学生玛丽·贝丝(与一名环卫工人结婚)怀孕并分娩一个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婴儿?如果代孕母亲改变主意了又该如何应对?为了帮助人们生孩子,辅助生殖技术科学家能走,或者说应该走多远?这项技术的伦理边界在哪里?
自那以后,在新泽西州新型的代孕方式(即代孕母亲与孩子无血缘关系)取代了传统的有偿代孕。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师梅利莎·布里斯曼说,她每年安排约300个妊娠代孕合同,而代孕母亲不在新泽西州居住并在州外分娩,因此她们照样可以收取费用。
02 代孕合同是否在执行层面具有特殊性?
合同通常是由甲乙双方签订的旨在通过法律强制执行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合同中,双方必须有所交换,无论是金钱还是服务。然而,代孕合同有些特殊:首先合同的标的是婴儿与父母权力;其次,强制实行此类合同有可能违反人伦。
与无私(互助性、无服务费)的代孕不同,在美国,商业性的代孕服务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产业。在多数学者和民众看来,该服务既违反了天然的人类母性,又引发了诸多恶性与短视的逐利行为,并不具备一个良性基础。
案例一和二,一个不支持原有代孕合同,而另一个支持,两个截然相反的判决背后的思考,被一些学者归结为对伦理血缘的尊重,即对天然契约的尊重。
03 辅助生殖技术如何确保不引发新的伦理问题?
与和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不同的是,本文中的案例三并不是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去进行主观故意的伤害,然而即使是客观失误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一个母亲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误为代孕母亲,生下别人的孩子,甚至还是不同人种的孩子,对两个家庭和孩子的伤害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辅助生殖技术,此类伤害根本不可能存在,该技术在本质上存在着伦理瑕疵。那么,辅助生殖技术是否还会引发新的不可预估的争议和伤害?如何确保它不再引发新的伦理问题?
小结
因为有“明星”的参与,代孕这个行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关于代孕,我们思考得是否已经足够充分?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代孕均采取不同策略,有以德、法、日本、新加坡为代表的“禁止代孕”法案,有以英、澳、加、港、荷、以为代表的“允许非商业性代孕”法案,也有以印度、泰国、韩国等“允许商业性代孕”的国家[9]。
而其中,又以美国最为特殊,不同州份有不同的代孕法律法规。通过这些案例,作为医者可以思考,一纸合约是否就能妥善解决由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是否随着法院的判决就能对其盖棺定论?事实证明,涉及生物学父母、养父母、婴儿及提供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个人等多方的伦理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与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伦理话题还很多,后续还将通过更多的案例来讨论医学技术进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伦理带来的挑战与思考。
注:本文来自“一嘉医课”,经授权转发,原文标题为“3例代孕官司引发的伦理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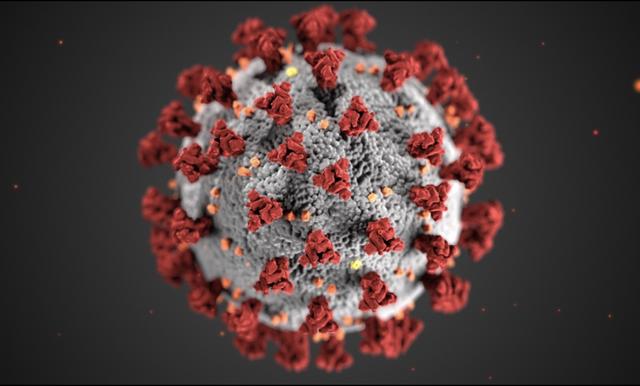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