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百花访台记——被问“越剧是越南戏吗?”

茅威涛
小百花访台记
口述 茅威涛
编撰 中新社 严格
1993年,我们浙江小百花第一次到台湾演出。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于1984年5月。虽然历史不长,但它却以整齐的阵容从亮相伊始就确立了它在越剧界甚至是整个戏剧界不可替代的位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的江南气息的优美、抒情、清新、细腻的艺术特色,为国内外观众所瞩目。 我们推出的《五女拜寿》、《西厢记》、《陆游和唐婉》等越剧广受戏迷欢迎,都是我们小百花的当家剧目。

茅威涛新版《陆游与唐婉》剧照
我是1982年毕业于浙江省艺术学校。同年进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应该说和我很多前辈相比赶上了好时光,一毕业我就赶上了浙江省首届小百花会演,《盘妻索妻》获优秀小百花奖,选入了新建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小百花已经走出了浙江,声名在外。这时候我们接到了到台湾演出的邀请。
到台湾演出是一位台湾越剧演员策划的。她叫高谨,原来是上海的越剧演员,师从范瑞娟,后来到香港定居,又从台湾演了10年的越剧,一次她回大陆偶然看到了我们小百花的演出,一下子给迷住了,她就下决心要让小百花在台湾开花,最后她和在加拿大经商的丈夫自掏腰包,安排我们到台湾演出。
第一次到台湾,说句心里话,我们都很好奇,毕竟大陆台湾分开那么多年了,我们对台湾也很不了解。
1993年11月16号,我们到了台湾。一下飞机,就有人问我,越剧是越南戏吗?连很多记者都搞不清越剧到底是什么一种戏,有个女记者问我们团长:“女的演男的,不可思议。”我们团长也没法解释,就说看了戏再说吧。
说句实话,那时候台湾对大陆也不了解,对越剧那是更加不了解了,我们到了台湾和当地越剧团体也有交流,台湾的越剧最早是军方从大陆带过去的,叫虎风越剧团,1950年国民党军队从舟山撤退时带过去的。由于从大陆撤退时戏具行头丢尽,演出时连主要角色也只好穿长衫裤上台,同时又怕台湾观众听不懂,演员卷起舌头讲国语,因为在台湾大陆江浙老乡不少,有段时间越剧在台湾还是很受欢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员年岁增大,剧团又无新一代接班人,致使演出失去号召力,剧团只好时演时停。到20世纪70年代初,不得不自行解散。
等到我们1993年到台湾,基本观众还是大陆过去的江浙沪乡亲,11月18号晚上,小百花在台北文化中心开演《西厢记》。那天我记得下大雨,可是观众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我演张生,颜佳演莺莺,陈辉玲演红娘,我在幕后一声叫场“张生来也”,就听到下面一片掌声。整个演出过程观众和我们都很投入,演出结束大家都把我们围住都不愿离去,说我们把台湾所有剧团都比下去了,我们带去的CD卡带都被一抢而空。
第二天,那个说“女的演男的,不可思议”的女记者在报纸上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小百花的表演像江南春风秦淮河的柳丝,美不胜收。”后来我看到其他报纸评论小百花西厢记场次安排一气呵成,合情合理,唱词典雅,灯光舞美配合恰宜,特别是旋转舞台尚为首见,演员是全才艺人,演出非常成功。

1993年小百花首次赴台演出,当地媒体报道演出盛况。
开门炮打响了我们又接着演出了《红楼梦》、《陆游和唐婉》、《梁祝》、《五女拜寿》几部大戏。记得演《五女拜寿》,这是一部家庭伦理戏,观众看得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动情时候剧场里是一片呜咽。观众也是一天比一天多,很多美国、新加坡华人还专门坐飞机到台湾来看戏,看完第一轮还要看第二轮。
最激动的还是我们的江浙沪老乡,他们都是全家出动,老老小小都来看戏,他们拉着我们说,以前都是演员小打小闹,现在总算看到正规大戏了,都说我们小百花早就应该来了。舟山同乡会的张老先生那时就已经70多岁了,多少年没出门看戏了,那次看了《西厢记》,他很自豪对别人说,这么好的戏只有我们家乡才有;诸暨同乡会的会长戚肩时是个老将军,开始他以为越剧就是看过的山歌小调喇叭花之类,小百花不过是以前跑江湖的的笃班,他看了以后好激动,说没想到越剧在大陆经过革新完全改变了他的印象,小百花给他洗了脑。这位戚将军,也就是那时开始成为了我们小百花的好朋友,我们到台湾他都来捧场,我们送他的影碟会反复看。后来他回浙江定居,也会经常来看我们小百花,2008年我在台北他还请我吃饭,可惜春节时候他去世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戚将军一见我就叫“茅笑价(茅小姐)”。他是一辈子乡音不改。
还有很多热心的台湾朋友不但来看戏捧场,像《海峡评论》的记者毛健,小百花一到就联络各界发起了越剧艺术后援会,成立越剧基金会,他每天晚上在剧院门口站台,号召观众参加后援会。
那次到台湾,我们还特地去拜访了我们浙江老乡陈立夫先生和蒋纬国先生。
陈立夫老先生那会大概有90岁了吧,头发雪白,人很清瘦,看到他我就想起仙风道骨,一口湖州话。看到我们带去的越剧光碟他很开心,说这下子业余生活丰富了。他和我们大谈养生之道,说每天要吃一碗小鱼,说小鱼最有营养,精华都在鱼头里,他建议我们每天都吃。我们听了心里都有点好笑,但在这位老先生面前也不敢表现出来。

图为陈立夫老先生
老先生那时90多岁还每天坚持洗冷水澡,真厉害,难怪他后来活到了100多岁,他还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淋浴房,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穴位那是什么穴位,他每天都要做局部按摩。
走的时候立夫先生说今天来了那么多小老乡,送你们每人一幅字,以前字写得不好,很糟糕,在大陆时候当教育部长,到处题字,感谢共产党都把那些糟糕的字都烧了,现在写的好多了。
就这样,我家里现在还有一幅立夫先生的字。
不过立夫先生家里很奇怪,端茶送水的都是男佣人,里里外外我们没看到一个女人,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些大概都是特务吧。那时年纪轻,喜欢瞎想。
到蒋纬国先生家是我和洪瑛、何赛飞、董柯娣一块去的,洪瑛是舟山人,何赛飞宁波人,董柯娣象山人,和蒋纬国先生是小同乡。那次去我们还特地给蒋先生准备了礼物。在离开杭州之前我们专门到奉化溪口蒋家故居丰镐房挖了一包泥土,到门口的剡溪灌了一瓶剡溪水,还带了两个奉化芋艿头,装在一个用做道具的礼盒里,蒋先生从我们手里接过这份特殊的礼物,很激动,我看他眼眶都红了。那时他眼睛不太好所以不能来看戏,但他在大陆时候看过越剧,说旋律很好听,对《西厢记》他很熟悉,说在大学里就很欣赏张生跳墙的勇气,敢于冲破封建礼教,他还开玩笑说自己年轻时候还不敢跳墙。我们还送他一套溪口照片,他指着照片用宁波话说,这里是小洋房,那里是阿拉老屋,这是我们小时候潜水游泳的地方,有个叔叔水性很好,可以在这里潜水很长时间。

蒋纬国先生
走的时候,蒋先生送我们他自己作词谱曲的《梅花梅花》录音带,梅花图案的真丝领带和纱巾,上面还有纬国的拼音。我们也邀请他回大陆看看,到杭州我们小百花陪他去奉化溪口。他当时连连说好。可是最终蒋纬国先生还是没能圆回乡的梦。
我记得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台湾还有不少人以为大陆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看了我们小百花的舞台艺术,道具布景,我们演员平时的穿着打扮,他们都感觉到能培养这样演员,这样舞台艺术的大陆不会是水深火热吧。其实我们小百花来台湾之前已经走向世界了,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日本、泰国都已经去演出过,有一次一位台胞可能觉得大陆来的小百花大概很穷,建议我们去台北旧货市场买点便宜货,一位演员当时就告诉他,自己穿的鞋子就是刚刚在巴黎买的,要好几百美金。毕竟那时大家隔离了太久太久,大家互相都不太了解。
这种隔离和社会的不同,就是我们越剧这样纯粹的舞台艺术,有时候也会碰到小麻烦。台湾剧场有个习惯,开演以前全体演员和观众统统起立,手捂胸口,高唱“中华民国国歌”。第一次在台北文化中心演出时,演出前,全体起立,我们一个字幕员正好在场内准备幻灯片,大家把注意力都对准她了,还好她比较镇定,装作听不到自管自己工作,我们总不能和他们一起唱吧,所以我们最后和剧场商量,在开演前最后一刻进场,这样进去的时候他们也唱完了,我们也开演了,我们两岸的中国人毕竟聪明,用点小智慧就解决了问题。
那次在台湾我们演出了11场,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时,剧场里观众都很激动,“小百花好,明年再来”,很多观众涌上台来,请演员签名合影留念。还有很多观众抓着我们的手,说是舍不得我们走,那个场面我至今难忘,也许是同胞之爱,在分离几十年以后通过越剧这种舞台艺术激发出来了。

1993年小百花首次赴台演出,当地媒体报道演出盛况。
那以后我们小百花几次到台湾演出,我有个习惯,每次到那里演出都要到大学里和大学生做个交流,普及越剧,特别是向年轻人普及创新越剧的时尚元素。在台湾台北大学、辅仁大学我都开过越剧讲座,我想越剧总不能永远靠我们老一代戏迷捧场吧,越剧如何才能取得与当下主流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接?为什么很美很诗意的东西,贴上越剧这张标签,在很多青年眼里就变成了落伍、老土?我原来以为台湾年轻人对越剧一窍不通可能没人来听我讲座,可是在台湾几个大学里,每次讲座都是满满的,他们听了我讲创新的艺术和创新的越剧,都说越剧也是那么时尚啊。一位女孩子还对我们小百花的越剧下了个台湾网络版的定义——越剧乱好看。
说真的,每次走在台湾街头,我都没有陌生感,满街的繁体字招牌让我好像置身老上海,台湾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保留和坚持,在很多方面超过大陆,但他这种保留和坚持是通过实验创新来实现的。我现在在小百花推广创新越剧,我一直很感谢台湾艺术家在传统艺术创新对我的启迪。1993年我第一次到台湾,第一次看到林怀民先生的云门舞集,第一次看到吴兴国当代传奇的表演,当时我惊呆了,真的一下子颠覆了我原来对舞台艺术的很多定式,戏怎么这样演啊,传统的,又是那么现代那么时尚,居然可以用最西方的的艺术载体去表现最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我就买了很多碟片回来看,后来我们小百花很多创新作品,像《藏书之家》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种实验戏剧的影响。

茅威涛《藏书之家》剧照
到后来赖声川,他采用中国传统的曲艺相声和舞台剧相结合的独创手法创作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在台湾人口只有2000万的时候,该剧的磁带就卖出了100万盒。因此有报纸称:“赖声川拯救了台湾相声。”这几年,赖声川用他的经典剧舞台剧《暗恋桃花源》征服了内地观众,迅速打开了内地市场。应该说,我们两岸的艺术家都在追寻通过创新拯救复苏传统中华艺术,我想下次碰见赖声川,我准备和他商量是不是一起合作排一场《那一夜,我们唱越剧》。
赖声川的合作还有待以后,但是我和台湾歌手齐秦倒是合作了一把。在2008年齐秦跨年演唱会,在北京、上海、成都三个城市的演唱会上,向来喜欢创新的齐秦,曾相继牵手京剧、川剧、沪剧演员,诠释当地最经典的戏剧表演形式, 在杭州他找到了我。
原来我和他并不认识,当时他们想找一位本地艺术家,结果杭州歌迷都推荐了我,主部分歌迷甚至直接建议,希望能够看到齐秦反串越剧,而茅威涛反串流行音乐。
2008年12月31日,齐秦跨年演唱会在杭州黄龙体育馆上演。站在舞台上,面对无数观众我说,齐秦和我一起表演,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干,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我和齐秦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艺术生涯,一直坚持在艺术舞台上,所以我们对艺术执着追求是相通的;而且我们都在创新,始终和时代同步,都成为了常青树,这一点也是相通的。那一晚,我唱齐豫的经典情歌《橄榄树》,齐秦穿上我赠送的巾生戏服,手执扇子,在吉他伴奏下演唱了越剧《红楼梦》里的名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腔调虽然依然是正宗齐秦式的,那动作却做得有模有样的,我们的合作赢得了全场的热烈喝彩。
应该说,那么多年来,我们来来往往台湾那么多次,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大陆的一名艺术工作者到台湾交流,和政治好像不太搭界。但从1993年第一次到台湾到现在,这十几年两岸风风雨雨,我是表演越剧的,按道理是远离政治的,可是有时候麻烦还是会找上门。2005年4月,我们到台湾演出,出发前我的手续很长时间没有办下来,因为那时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反分裂法》,而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那时还有传言说我是当时投票三个弃权者之一。这样我就被“盯上了”。申请赴台过程中,对方一再要求茅威涛必须签下“保证不在台湾宣传反分裂法”的具结书。我后来写了份声明:本人随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到台湾演出,不在台湾从事演出以外活动。这样才到了台湾,首场演出时,有两个特殊身份的人到化妆间找到了我,说让我在明天早上八点之前离开台湾。
也就在那次,姜昆到台湾访问演出也碰到了麻烦;姜昆不仅是相声名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为此台湾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同样出招,要求提出姜昆的身份证明,并期望姜昆能签下具结书。为避免造成艺术家的不便、反感,邀请姜昆来台的台北曲艺团,两度出面签下具结书,保证姜昆的身份没问题,来台后的一切行为,也不会超过邀请函的范围。几经折腾,才让姜昆等大陆曲艺家顺利赴台。
一句老掉牙的话:让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我们大陆表演团体、艺人到台湾,是单纯从事两岸艺术文化交流。如果因两岸局势紧张,就拿我们开刀,可笑。

茅威涛接受中台禅寺惟觉大和尚相赠的墨宝
(本文选编自中新社浙江分社编撰的《走向明天—浙台60年口述历史》)
来源:中新社浙江分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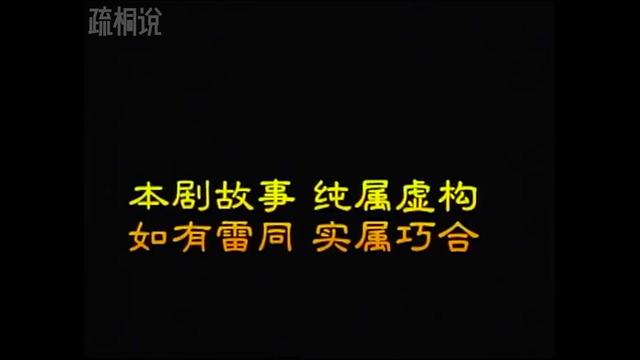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