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丨《发明自由》,抑或重构“想象的共同体”
郭晔旻

《发明自由》,[英]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九州出版社·一页folio,2020年3月出版,448页,68.00元
2020年3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历史学者丹尼尔·汉南的著作《发明自由》。这个书名的确很难让读者立即反应出本书是一部有关历史的作品。这当然不是译者徐爽先生的问题。因为这本书的英文名(How We Invented Freedom & Why It Matters)直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如何发明自由及其重要性”——依旧足以使读者如坠雾里云中。好在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改作一个较易理解又较为贴切的名字:《发明自由:英语民族如何创造现代世界》(How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英语民族”这一用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温斯顿·丘吉尔的皇皇巨著《英语民族史》(又译《英语国家史略》)。但与丘吉尔实际将行文的主要精力用于描述不列颠岛从古至今的历史(以至于只给美国历史留出了不到一个章节)不同,本书作者从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英语国家”的概念,或者用书中名词所言,“盎格鲁圈”。
这个“盎格鲁圈”,按照作者的说法,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国家为核心构成。维系这一“讲英语的国家组成的自由的共同体”内部彼此认同的“法宝”,则是丘吉尔所说的“同一种语言(英语)、同一首圣歌(新教信仰)、以及几乎相同的观念(‘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这个“盎格鲁圈”的范围,固然比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所提出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范围还要狭窄得多,但作者却毫不客气地声称,包括自由观念在内的所谓“西方价值”,实际上就是“盎格鲁圈”的政治制度基本特征。只不过,“盎格鲁圈”在将自己的价值“全球化”的同时,让人忘记了其独一无二的源头——就像西装加领带曾是英国的国服,而今却成为绝大多数人国家男子的正式场合穿着一样。作者甚至并不讳言,“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英语民族已经具备了掌握当今时代全球霸权的工具”。如此看法,无疑就是“英语民族如何创造现代世界”书名的来历。尽管作者是位严肃的历史学者,出生在南美洲的秘鲁,父母是爱尔兰与苏格兰人,因而具有相对超脱于“盎格鲁圈”的身份,但他在书中也承认,将“自由”与“盎格鲁圈”划上等号,“很可能会给一些读者造成优越感极强、必胜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印象”。
既便如此,读者大可按捺心中的些许不快,看看丹尼尔·汉南在《发明自由》一书里,究竟如何阐述“盎格鲁圈”的前世今生。
首先,作者肯定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对英语民族的起源,本书的视角稍显独特。大多数历史读物,往往将早期不列颠群岛的历史,形容为一次次的族群替换:先是罗马人征服了土著,然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民族大迁徙”中赶走了土著而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到了公元十一世纪,来自法国的“诺曼征服”又一次改变了英格兰的民族构成……但作者根据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论指出,本地族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土族裔的主体”,尽管他们“沿袭了征服者的生活习俗,以及更多的征服者的语言、法律、宗教和民族意识”。在这方面,作者甚至举出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例子:在“诺曼征服”之后,只有五个古老的英国名字(阿尔弗雷德、埃德加、埃德温、埃德蒙德以及爱德华)延续到了后来,反而“罗伯特”或者“理查德”这样的“诺曼”名字成为主流。细心的读者甚至可以发现,作者本人的家庭也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的“父母之邦”(其父是爱尔兰人)恰恰也是“征服者的语言”的牺牲品。“如今,只有不到1%的(爱尔兰)人口在家中说凯尔特语”,以至于仅仅一个世纪之前,包括“爱尔兰(凯尔特)语得以复兴”在内的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们的梦想,“仿佛来自远古”。
至于这个早期历史中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轮回的西欧小国如何成为“自由”的发源地,作者提到了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由于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庭的地位、荣誉与财富,大量次子三子在自立门户的过程中无法保住原有的社会地位。诡异的是,恰恰是这种不间断的“乡下流动”,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英国人口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开始上升,这就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做好了准备。
但更主要的原因,作者倾向于“地缘决定论”。在其看来,荷兰虽然在近代最早成为“海上马车夫”,但地处欧洲大陆、容易被强邻(具体而言,就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国)征服的地理位置,最早使其失去了“成功转型”的机会。反而英格兰这样的岛国,依靠大海的保护保证了自己的外部安全,而岛国的性质也让其不必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陆军——因此,“政府发现自己和民众相比处在劣势,当它需要通过法令时,他必须依靠代理人来确保民众的同意”。这就是本书引用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言论所提到的,“相比大陆,岛屿上的居民享有的自由程度更高”。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在作者笔下理应幸福感满满的国家,如何会在十八世纪末期陷入一场痛苦的战争,并最终丢掉了广阔的北美殖民地呢?
在这里,作者最为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盎格鲁圈”史观。众所周知的“美国革命”,并非北美革命者与大英帝国的较量,而只是一场“盎格鲁圈”同室操戈的内战。这场战争的终极根源,仍旧回到了作者青睐的“地缘决定论”:“十八世纪不可能建成跨洋帝国。”囿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没有办法可以阻挡三千英里的海洋(当时需要至少九周的航程)对政府力量的削弱,无论议会设在大西洋的哪一边,它在物理上都无法企及另一边的选民,也就无法反映后者的意志。本书引用了一个颇为戏剧性的场面来形容当时“从下令到执行”之间的漫长距离——在1812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白宫在战争中被敌军焚毁,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中,“这次战争中唯一一场大决战在和平协议已经签署后大打出手,因为停战消息还没有及时传到大洋对岸”。
同样是从“盎格鲁圈”史观出发,本书令人惊奇地将北美独立战争看作一场“双赢”。赢得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自不待言,就连英国也从战败中获取了不少好处:它再也不用在新大陆耗费大量军队和物质,因为美国会独力将英国的殖民竞争者(法国和西班牙)赶出北美大陆;而美国从英国的分离甚至大大刺激了“盎格鲁圈”的殖民运动,北美的“效忠派”北上来到了仍在英国统治下的加拿大,永远改变了这片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仍旧是高卢(法国)人天下的居民;与此同时,丢掉北美殖民地迫使英国另觅新的囚犯流放地,这就让澳大利亚也成为英国人(后裔)的天下……
最后,考虑到导致“盎格鲁圈”两大核心成员(英美)分家的地理障碍随着近现代技术的进步已经逐渐得到克服,英语世界重新整合的前景自然呼之欲出:“英格兰需要联盟,因为这个民族的将来取决于与美利坚的联合;美国也需要联盟,因为这个民族的过去不可分割地属于英格兰。”或者至少,像作者所说的那样,“盎格鲁圈正在变成一个由权力下放的、灵活的、独立国家组成的共同体”。
这样显得有些视角独特的历史叙事,在给人启迪的同时,自然也免不了引来质疑。不能不承认,作者在有些方面,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就拿其奉若圭臬的“盎格鲁圈”三大定义来说,其中就有两条明显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同一种语言”自然是“盎格鲁圈”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但如何定义“同一种语言”却是另一回事。读者不难发现,即便是作者眼中的五个“盎格鲁圈”核心国家(恰好就是目下臭名昭著的“五眼联盟”所在国)中,加拿大与新西兰其实都非英语独尊,而都另有一种官方语言(加拿大的法语,新西兰的毛利语),甚至“盎格鲁圈”的发源地英国,威尔士、苏格兰乃至北爱尔兰也各有其地方语言,就连《友谊地久天长》这样的“英国名曲”,其实也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用低地苏格兰语而非英语写成的。如果说,这些地方因其通用语言为英语纳入“盎格鲁圈”尚能服众的话,作者在书中竟尝试将印度——“日不落帝国”曾经的“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纳入“盎格鲁圈”就显得有些异样。假如只有少数人说英语的印度都符合这一条件,那“印巴分治”的孪生儿巴基斯坦为什么又处境相反呢?伦敦现任市长先生不就是个地道的巴基斯坦裔么?而且,前英国的殖民地如今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者多矣,推而广之,这“盎格鲁圈”岂不是成为“英联邦”的同义词了?哪怕是作者自己,在书中时而将新加坡、马来西亚纳入其中,时而又说爱尔兰已处在“盎格鲁圈”的外围边缘,至于尼日利亚这样货真价实的“前英国殖民地+英语官方语言”的国家,却只字未提,实在也有逻辑混乱与“嫌贫爱富”之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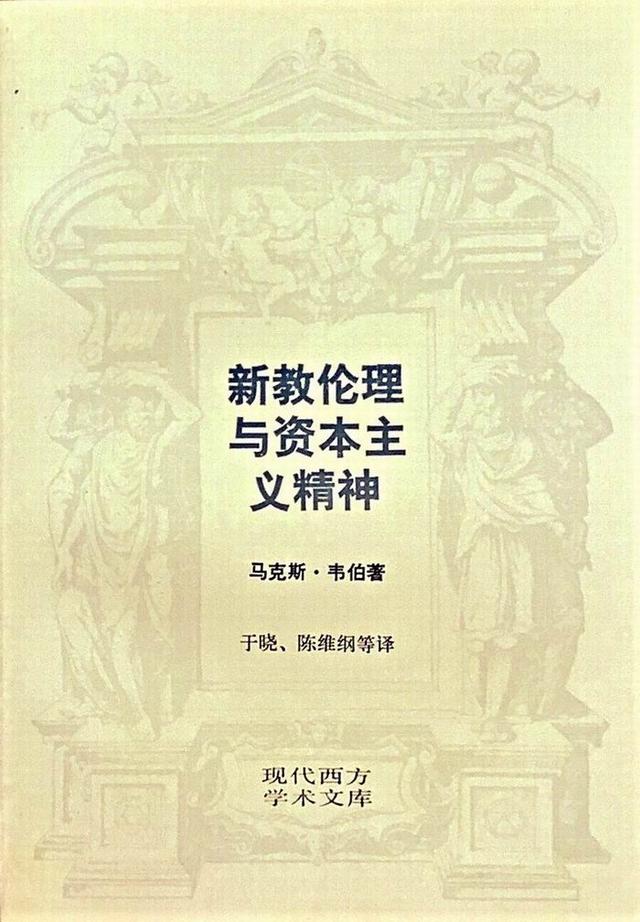
至于“同一首圣歌”方面,作者对新教的推崇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的论断几乎一脉相承,甚至还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统计作为佐证,声称“1940年,欧洲新教国家的人均GDP比天主教国家的高40%”。不仅如此,作者在本书里甚至断言,“英语民族的宗教(新教)是政治自由的保护者”,“英国因为其拥有世界上占绝对多数的新教力量而成为天佑之国”。对这样的论调,几百年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有过精彩的反驳:“(天主教徒)却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最共和和最民主的阶级……把天主教说成是民主的天然敌人,那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在基督教的不同宗派中,天主教反而是最主张身分平等的教派。”
考虑到本书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托克维尔的言论证明自己的论点,读者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怀疑,这并不是作者无意造成的疏忽。自然,也不能不让人想到丹尼尔·汉南在历史学者之外的另一个身份——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坚定的“脱欧主义者”,人称“英国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戴高乐主义者”。
这样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作者对“欧盟”这样一个非“盎格鲁圈”的超国家实体毫无好感。他在本书中哀叹,“当英国向欧盟交出主权的同时,也就相应地放弃了它的民族性中的若干元素……他们正在丧失他们的卓越”。
“盎格鲁圈”真的“卓越”么?这自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至少在作者看来,即便是奴隶制度与殖民主义这两个英美历史上的“黑点”,也可以自圆其说。关于前者,他给出的理由是全世界各民族都有过奴隶制度的存在,所以不应“五十步笑百步”(虽然美国的奴隶制度竟然持续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关于后者,作者认为“和其他选项相比,还是加入盎格鲁圈更好一些”,理由是不列颠的殖民统治最为仁慈——那些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里被绑在炮口轰死的起义者恐怕不会这么想。至于在英联邦自治领南非出现的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作者也以南非白人的多数是说荷兰语(而非英语)的布尔人作为搪塞,又“适时”地忘记了津巴布韦(南罗得西亚)只占人口百分之二的英语白人对广大黑人做过的同样的事……
无论如何,作者在书中尽力称赞“盎格鲁圈”的卓越,并将其作为英国“脱欧”后前进的方向:反过来,“如果这两个国家(英国和爱尔兰)脱离欧盟,那么一个盎格鲁自由贸易圈就得以在商品、服务和资金顺畅流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但是,很难想象,在民粹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回潮的今天,世界上的英语国家还会将“盎格鲁圈”置于本国利益之上。小小的新西兰不就因为坚持“入境军舰无核化”的原则,被美国从“盟邦”降低为“友邦”了么?作者在书中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极不感冒,而如今那位白宫的主人,打出的旗号难道不是“美国优先”而不是什么“盎格鲁圈优先”么?更不用说,就连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到如今,绝大多数盎格鲁圈国家正在逐步抛弃‘辉格党在光荣革命之前的原则’”,也就是那些作者在书中所赞颂的“盎格鲁圈”特质了。
以此看来,作者在本书中所想表达的,与其说是“发明自由”,倒毋宁说是用本书作者的那位爱尔兰老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传世之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书名概括更为贴切——“盎格鲁圈”,难道不正是一个作者打算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的那个“想象的共同体”么?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