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硅谷,全世界最著名的创新中心。但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杏李果园。这里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创新圣地的呢?发展到今天又面临哪些成长问题?美国《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回顾了硅谷的历史,并且分析了新的现实。文章指出,这里依然是机遇之地,但现在面临着自身成功的人力成本问题。新的热词是:责任心与同理心。

Santa Clara的一场黑客马拉松上,在零食、功能饮料、无糖苏打的助推下,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的学生正在构思一款为摄影师服务的增强现实app。
停车场里一堆Tesla在争夺着12个电动汽车充电站里面的一个。一大堆的人(主要是男人)聚集到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大厅里,一些人相互麻利地给了对方一个拥抱。“我的投资进行得怎样了?”一位朝屋子对面的另一位喊道。一声铃响之后,这里马上变得像教堂一样。喧闹的人群迅速涌入到礼堂变得安静起来。门关上了。Demo Day就要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来自132家初创企业的创业者,将用2分钟的时间推销已经过反复排练的关于如何改变世界的想法。结果表明有无数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养老院卧室天花板的雷达传感器。检查公用事业管线的无人机。货物托运人的机器学习。专门针对男性的洗衣液订购服务。
Michael Seibel,Y Combinator的CEO兼合伙人,他告诉硅谷投资者说,平均而言,这其中的每一组都会诞生一家未来的独角兽公司。他说:“你的工作是找出谁是那一家。”他的公司则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想法。

作为首家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苹果设定了硅谷的创新节奏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已经于2107年开放的苹果在库比蒂诺的新总部又被称为“宇宙飞船”。大概有12000名员工在那里工作,人数占到苹果在湾区员工人数的将近一半。最近苹果还担起了硅谷批评者的角色,它抨击了其他的技术公司,呼吁要为客户保守隐私。
首先亮相的是Public Recreation,以订购制方式在停车场等露天场所为练习者提供团体锻炼。其中一位创始人说:“我们的秘密武器是不用付租金。”
当每个人都在鼓掌时,我在想这是不是个大市场。如果下雨、下雪、或者有讨厌的昆虫和花粉呢?不过接着下一个大想法又来了——利用预测性算法对港口的集装箱进行优化。屋子里用鸦雀无声表示了尊重。
在我作为记者写有关硅谷故事的这些年里,我已经学会了扼杀嘲笑商业点子的冲动。那些初创企业曾经被我当作玩具而不屑,但凭着解决了我不知道大家会有的问题而赚到了数十亿美元。
也许如果A计划行不通的话,Public Recreation还可以切换到B计划,就像Justin.tv一样,原先它只是为了直播Justin一个人的滑稽动作,然后变成了直播任何人的,然后又变成了Twitch Interactive,让大家可以观看其他玩家万在线游戏。2014年,Amazon以9.7亿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
长期观察硅谷的Paul Saffo说,硅谷一直都是个“逃向未来”的地方。在这次Demo Day上推介的创业者描绘了一幅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机器人、无人机以及无所不在的传感器让生活更美好的图景。
硅谷的乐观主义以及推动硅谷向前的实用主义的梦想家一直以来都令我着迷。但最近冒出的各种各样令人事情却给大家打了一剂清醒剂。
责任和同理心是新的热词。硅谷知道自己要为所有的事情负责:劳动力的构成,被颠覆的行业,技术导致的痛苦,因为其社交网络而传播得更快的仇恨,甚至也包括创新对这里的人影响。甚至一些收入达6位数的员工解决住的问题也有困难。而在世界各地想玻利维亚这样的地方,挖掘硅谷发明的设备动力所需的锂正引起对破坏环境的担忧。
技术统治未来,但一个大家不愿承认的事实是,有时候在追求让世界更美好更高效的过程中,你也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Anne Wojcicki是基因生物技术公司23andMe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她说:“我们周围都是梦想远大的人。事实上硅谷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世界已经改变。但这种过渡绝对是困难的。我认为我们对所有那些受到影响的地方都负有责任。”

硅谷革命演进史:思想、金钱和机器汇聚之地
人人都有梦想
外地人过来参观的时候总是问我:“硅谷在哪里?”硅谷没有首都或者地零点。这里的山上也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标志宣示这是技术之都!在从东向西延伸的低矮山丘包围下的硅谷,是一个马蹄形的平原地带,里面布满了办公楼和街区。
被其环绕的是波光粼粼的旧金山湾,对路上喧嚣的拥堵和Tesla、SpaceX老板马斯克的最新突破无动于衷。我把Facebook总部大楼旁边大拇指样的“点赞”标牌指给了访客看。跟多数技术公司一样,Facebook并不安排接受游览。
当然,那个“点赞”标牌未必能令每个人满意。我们知道, Facebook的数据政策没有能够保护用户,一位研究人员把数据卖了出去,然后我们就成为了政治广告的目标,俄罗斯当局则利用Facebook作为其宣传武器煽动美国的政治冲突。
技术的中心有可能是山景城的一块地,因为晶体管的某位发明者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公司;也可能是苹果联合创始人Steve Wozniak参观过的一个地方,就因为他摸了一下那栋建筑,那里就成为了历史性的地标。
那也可能是Los Altos一条死巷内的一所房子,一位印度出生的软件工程师把自己的孩子都哄上床了之后再重新上网去做她的初创企业。或者也可以是在一辆停在斯坦福大学附近、3个轮胎已经漏气的休闲车——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Jim和他的小狗Smokey就一起在里面生活,每天用湿纸巾来洗澡。
1982年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当时《国家地理》写道硅谷“随心所欲的平等主义已经取代了农村的节奏”,并称,“表面上的泰然掩盖了背后的蓬勃发展……低矮矩形的建筑乏味地蔓生着,上面的公司标示融合了各自高科技名词,但你却从中找不到多少他们是干什么的线索。”
沿着环绕的群山上的蜿蜒道路行走,不时会看到鹿儿在吃草,自然会让人认为这里的生活是一种乡下的节奏。曾是杏李果园的这片山谷去年刚刚见证了标志性的樱桃水果摊(C.J. Olson’s Cherries水果直销店)和成立于大萧条期间的奥查德五金店(Orchard Supply Hardware)的倒闭。但硅谷还是会欺骗你:这里看似平等、开放、休闲,CEO上身穿着卫衣,风投家下身着自行车短裤,而且这里经常异想天开,上班的地方需要你脱鞋或者允许员工带狗进来。
但硅谷对自己的抱负是认真的。“相对于名字,大家对你的初创企业更感兴趣,”24岁的澳洲访客Tristan Matthias抱怨道。
硅谷今天吸引力的种子实在1990年代播下的。这个地方给当时身为记者的我的观感是有点死气沉沉。冷战结束后国防工业开始走下坡路,经济衰退导致了整个加州都在裁员。当时热门的是桌面出版、多媒体CD以及视频游戏。
甚至伟大的反叛者苹果似乎也在走下坡路。在1985年跟CEO和董事会吵架之后,乔布斯走了;他胜利回归自己创立的这家公司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
1990年代中期一个想法开始流行:如果大家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系的话,生活就会得到改变。我参观了一所学校,他们尝试用计算机跟学生联网,好让老师通过拨号modem发信息给家长。America Online想出了数字商场的点子,让大家可以去逛甚至订花。东西做得很笨拙而且难用,但一个影响很大的东西开始渗透。
北边的西雅图有个聚会。微软让计算机变得有用也让自己腰包变鼓。1995年8月,微软似乎成为了赢家通吃的技术竞赛的胜出者。午夜,它的高管在电子商店外面跳起了舞,庆祝操作系统Windows 95的发布。与此同时,各自各样的东西雨后春笋一般开始在硅谷冒头。
制作“浏览器”软件让大家网上冲浪的Netscape在其照片产品发布不到1年之后就上市了。尽管Netscape是一家未经受过检验的公司,给投资者准备的风险提示有几页纸之多,但开盘日仍以58.25美元的价格收盘,令其市值一下子达到了29亿美元。
Netscape的IPO开启了所谓的网络泡沫时代,这个时代见证了一批长青公司的诞生,比如Amazon和Yahoo!,以及一批短命公司的昙花一现,如Webvan与Pets.com。
卖化妆品、租货车、找伴侣等,大家对互联网所能做到的事情的兴奋感,给投机的股市推波助澜。1999年,有超过400家股市上市,其中大部分都是技术相关的。
2000年,市场崩溃。超过20万个岗位被干掉了。
窘迫。痛苦。尽管如此,苹果联合创始人Wozniak告诉我:“那些初创企业都是对的。在互联网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这件事情上他们都是对的。只不过大家没法办法那么快就改变生活方式。”

创新与不平等的发祥地:在高科技地区生活的高代价
因为早年硅芯片创新和生产得名的硅谷,已经从Palo Alto周围的技术前哨延伸到高科技产业遍布整个湾区,并且因为作为数字时代全球知名的地零点而不断推高当地的房价。大学、创新者、创业者已经把这个地区变成一个庞大的财富引擎。但这种繁荣并没有让所有人受益,随着“山谷”的扩大和不断变革,这里已经被房产、财富和机会的差距深深地割裂。
旧金山的独栋房通常要130万美元,奥克兰为75万美元——对于平均年薪123000美元的技术员工来说这个价格也许不算离谱,但对于每年只挣3万美元的服务业工人来说就不是了。房价最高的是Atherton,中位数也要700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一所房子价格的中位数是21.7万美元。
把失败变成积极的东西硅谷有自己的说辞。“迭代”意味着无需关心完美就让产品上市——先上市再调整。“转型(Pivoting,说的时候必须没有尴尬感)”就是在钱花光前骤然改变路线。
失败和衰退为新想法和新进入者扫清了障碍。Google占据了Silicon Graphics(这家计算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帮助创办了Netscape)曾经的地方。Facebook发展之后让旧的Sun Microsystems园区换了新颜。将互联网与电视连接到一起的尝试之路充满崎岖。但然后YouTube出现了。
社交媒体时代来到了。Facebook联合创始人扎克伯格搬到了Palo Alto,用黑客信条“快速行动打破陈规”来发展Facebook。在旧金山,一群朋友同事找到了让大家用140个字符之内更新每日动态的办法,然后Twitter诞生了。
硅谷的巨大搅动掩盖了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创新伟大的“创造性破坏”周期不是在3万英尺的高空去俯瞰到的东西,而是在个人层面上的浩劫。工作没了。技能过时了。家庭倒了。
苹果提供了另一个模板:卷土重来。1997年,随着苹果收购了自己创办的NeXT,乔布斯重新坐上了驾驶室,苹果也开始慢慢恢复元气。该公司先是推出了iPod,然后又发布了数字娱乐商店iTunes。
2007年,iPhone的发布兑现了10多年前General Magic的Magic Cap以及苹果的Newton的承诺。时间闪回至今日,技术公司都在争夺对大家生活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领导被国会叫去作证,要他们解释清楚对客户数据的使用,外国活动者利用这些技术破坏选举的手段,以及控制我们看到的东西的算法可能存在的偏见。
随着人工智能(计算机学习像人一样思考)的出现,数据(及其伙伴计算速度)变成了最重要的资源。新的石油。如果计算机有朝一日能够思考和决策会怎样?
在超过3000名Google员工联名上书表示抗议后,该公司决定不再续签跟美国国防部签订的一项合同,内容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影像。然后,2018年11月,全球20000名Google员工又走上了街头,抗议公司对性骚扰和报酬公平问题的做法。在跟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签订的合同受到批评后,Salesforce建立了一个Office of Ethical and Humane Use of Technology(技术伦理与人力使用办公室)。
我拜访了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现为Alphabet 主席的John Hennessy。他说,技术圈当前的这股清算正在引发有关硅谷目标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说:“对于公司来说现在棘手的是他们打算如何去承担责任和进行自我治理,着不仅要跟股东的利益一致,也要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
创业生活
年轻的外来者不断涌入。
Shriya Nevatia从塔夫茨大学毕业后就到了纽约北部当产品经理,他说:“一些人要坐进咖啡店听见别人在高谈阔论加密数字货币和Google的话会敬而远之。但我喜欢这个。”
在硅谷呆了3年之后,Nevatia已经换了2次工作。她说:“这听起来似乎很糟糕,但我喜欢小微初创企业。”
在Palo Alto一个树木掩映的街区,Joshua Browder坐在了扎克伯格2004年夏Facebook开始腾飞时待过的家的游泳池边。在屋内,Browder的同事在一张餐桌上弄他公司的app——DoNotPay——它就像机器人律师一样跟停车罚单作斗争,并且寻找机票酒店预订的漏洞。
平底锅沾满了番茄酱,这种厨房条件是黑客生活格式塔的一部分:在为了产品发布争分夺秒的时候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吃饭睡觉。那些活在技术里、做技术或者投资于技术的技术传奇中交织着过去与现在。
Wozniak是一位很吃香的演讲者,每年收到的邀请都有1000以上。他的吸引力部分源自他是硅谷受欢迎的起源故事,也就是苹果诞生的故事里面的“另一个史蒂夫”。在大家眼里Woz是个天才,但他却认为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家伙。他反复讲述着关于自己的那个最著名的故事:大概在1980年苹果IPO前夕,他把自己手上的部分苹果股票以IPO前的价格卖给了80位员工。
他说:“我对财富的分配问题有很多担忧。”
“兄弟文化”依旧
今天的硅谷差不多也是移民谷(Immigrant Valley)。国外出生的人的涌入正在帮助抵消美国人流出到其他地方。在某些领域,比如计算机和数学,国外出生的劳动力占比超过了60%。
那些领域的女性占比甚至更高——78%都是国外出生的。印度人、中国人以及越南人是本的确技术产业外国人的主流群体,但是国家的多样性非常丰富:2015年从事技术业的有42人来自津巴布韦,有106人来自古巴。
硅谷的国际性意味着公司,哪怕是小公司已经变成了文化和语言的大杂烩。但是也突出了哪些人没有融入到硅谷梦当中。平均而言,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人仅占到主流技术公司劳动力的12%。
女性所占的份额也严重不足,这主要是受到了硅谷所谓的“兄弟文化”的影响:Google、苹果和Facebook员工中只有30%左右为女性。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调查发现,初创企业创始人中女性仅占13%,持有的创始人股权只有6个百分点。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善。根据致力于提高女性在技术领域的参与程度的非营利组织AnitaB.org对80家公司的调查,2018年,女性占到了技术岗位的24%,在企业领导的占比达到了18.5%。
在薪酬方面,按照求职招聘机构Hired的数据,相同角色下技术从业女性拿到的薪酬60%的情况下摇要比男性少(平均差距为4%)。主要技术公司称希望团队多样性更强,但很难迅速改变员工的人员构成情况。
喝过了一杯茶后,产品经理Shriya Nevatia说:“我听说年轻女性说硅谷对女性不好,为此她们奋起反抗。”她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做Violet Society的组织来帮助女性以及没有数字化基础的人度过进入技术业的头10年,来帮助启动创业。
她对男性在大学期间通过室友以及在职业生涯早期建立的广泛关系网感到着迷。公司似乎是通过出自这些关系网络的机会联系而成立起来的。Nevatia也想通过同样的方式把女性联合起来,她说:“要产生这些偶然事件,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
Imelda Valencia平时就住在停靠在朋友私家车道的一辆拖车里面,因为她的工作是给美国最昂贵的街区之一Atherton的家庭做保洁,但是周薪只有600美元。
被繁荣挤压
随着外来人不断涌入硅谷推高了当地的房地产和租赁价格,并未置身于技术经济的很多人,甚至一些从事技术的人都感到生活越来越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住的成本上涨。
也许没有一个地方的拥挤程度比得上East Palo Alto了。这座3万人的城市拥有强大得可怕的邻居:Facebook在它的北边,南边则是Google。过去50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基本上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人为主。
但现在新的家庭正在搬进来,其中很多是白人和亚洲人。据Zillow,这里的房价中位数已经超过了百万美元,而2011年的时候还只有26万美元。一百万。这已经超过了从旧金山延伸到圣何塞的整个半岛的经济适用房价格。
对于当地很多没有享受到技术繁荣的长期居民来说,房租上涨了,买房更是遥不可及。他们只好搬到城市的边缘地区,每天上下班都要开车数小时。要不就只能搬到家人朋友那里。或者彻底离开这里。Pastor Paul Bains说:“他们就在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旁边建造百万美元的房子。”Brains跟妻子Cheryl在East Palo Alto做了一个公共事业的非营利组织。
Patricia Carter住在East Palo Alto,她的家里已经住满了人:她的儿子,3个还不到4岁的孙女,以及她的女儿都住在这里,甚至车库也租给了她儿子的前女友。身为UPS司机的Carter在2003年的时候以447000美元的价格按揭买下了这套3居室农场式房子,去年差点失去了房子的抵押赎回权,在帮助下才得以保全自己的家。
Y Combinator CEO Michael Seibel认为今天的硅谷正在出现代际转移。年轻一点的员工希望自己的公司在招聘上能体现出更多的多样性,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为了留住人才而不顾一切的公司愈发同意这种要求。
他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从耶鲁大学毕业后,Seibel打算20岁去赚钱,30岁为人父,40岁从政。2006年他搬到了旧金山创办公司。他是Justin.tv与Socialcam的联合创始人兼CEO。2012年Socialcam被卖给了Autodesk,Justin.tv最终成为了Twitch Interactive。现年36岁的他刚刚当上了父亲。不过政治出局了;他感觉现在自己已经有更多的社会影响了。
如果说硅谷有精神中心的话,这个地方也许是坐落在旧金山一所曾经的教堂里面的Internet Archive。这里的服务器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公共web的很多内容归档进众多形式。这里每周归档的视频超过了50万个。归档的网页超过了3400亿。这里是互联网的失物招领处。
在互联网档案馆的Great Room,有120多坐3英尺高的雕像散落在长凳上,这些人起码对归档做过了3年的贡献。这是互联网的兵马俑。在这怪诞又强大得一幕中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
这有点令人毛骨悚然,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有的手里拿着书,有的拿着杯子,有的抱着吉他,这样子仿佛是在做项目或者在跟唱录音,或者,也许是在相互争论做什么才对时时被打断了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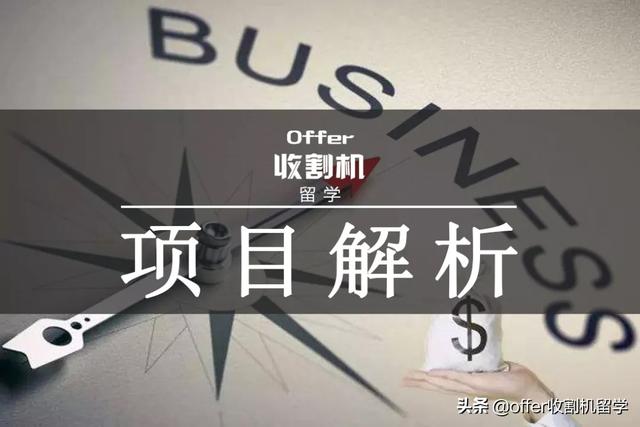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