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爱情

我相信世上是有真正的聪明人的,这正是上天才智分配不公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小伙子,他有着姣好的面庞,身材颀长健硕。无论什么事,总是占据强势。他是这样一个聪明人,本应该生在富裕之家,享受上流社会的优裕生活,却偏偏是个汽车修理工。
他穿一条黑色背心和迷彩裤子,裤子用皮带系上,脚上穿着一双黑漆漆的旧皮鞋,鞋带系得干净利落。隆起的大块肌肉把背心绷得紧紧的。你一眼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了扮演《欲望号列车》里的马龙白兰度。他和白兰度一样有一个宽大平坦的额头,还有一个结实的大腮帮子。目光深邃有神,寸头,嘴唇和下巴上留有锋利的胡茬。
和初入城市的北方小子不同,他完全没有那种自卑或者害羞的禀性,好像到哪都能适应。这大概和他的两年部队生活有关。在部队的最后一年里,他打架斗殴,把一个战友的耳朵咬掉半截,最后被迫退伍。这也让他的嘴唇上终生留下了一条长达两厘米的伤疤。之后,他就来到这座南方的城市,找了一份汽车维修的工作。
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是一个体态臃肿的胖子,红扑扑的圆脸,说起话来眼睛像麻雀一样滋溜溜地转着,显出几分讥诮和圆滑。他不仅有一家汽车修理行,还出售各种品牌的轿车。在修理行门前的树下,就停着一辆宾利豪车,车身挂着一块可供租赁的牌子,租一天的价格是三千块。车钥匙就放在修车行里,由这个聪明小伙子来联系租车的业务。
当然了,维修这个工作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坚持下来的。如果你受不了浓烈的汽油味儿,受不了一层层的灰尘,受不了风吹日晒,你最好别做这一行,这不是一个体面的工作,只能称之为技术活。每天你在天蒙蒙亮中起床,用钥匙打开卷闸门,就有人来提车。如果你不小心蹭破点皮,车主就会指责你半天,甚至让你提供赔偿。对此,小伙子已经习以为常了。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车吗?”他们说,“蹭掉点漆你都赔不起。”
他也被客人这样指责过。
工作时,你身子躺在地上,面朝着车底盘,一层层的泥灰直往脸上扑,有时候掉到嘴里,那滋味 别提多难受了。一天工作下来,脸上身上沾满了黑色的油渍,洗也洗不掉,第二天还是穿着脏衣服去工作。
没人向往这种脏了吧唧的工作,但是不干不行,这就是生活。小伙子那时向往的就是老板那样富有的生活,认为他那样才是生活,有别墅,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吃喝不愁,养尊处优,而不是像他这些维修工们一样疲于奔命,为了活着而生活。维修工们都是在工作收尾之后抽一根烟,边笑边谈这样的话题,只要每天谈一谈,一天的劳累也就在这种笑声中淹没了。
每天下班这个小伙子都会去喝一杯,酒吧是解乏的好去处。他知道有一家酒吧,那里有他喜欢的一位姑娘,他经常在那儿见到她。他一见到她,其他的姑娘他再也不喜欢了。但是姑娘从来都不理睬他。据说,姑娘是一位银行行长的女儿。这个富家女孩周围总是围绕着有钱小伙子,对他这个穷酸的大块头根本不屑一顾。他总是想,只要她能和他说一句话,要他怎么样都行。
姑娘具有富家小姐身上的一切优点美貌大方,气质优雅,也有他们身上的一切缺点轻佻浮躁,奢侈靡费。酒吧里所有男人都想和她跳舞,她昂着脖子,端着酒从这一桌走到那一桌,谈笑自如。他喜欢她抽烟的姿势,陶醉在她的舞姿中。
好几个晚上,他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个姑娘。如果能娶到这个姑娘,他就再也不用在汽车修理行里做苦力了。他就这样一边做着辛苦的工作,一边妄想着。
几天过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可以走近姑娘的办法。他花费了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西服,一条斜纹花领带,一双鳄鱼牌皮鞋。他穿上之后,站在镜子面前照了照。他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镜中的他光彩照人,英俊非凡。
一天晚上下班后,他脱下肮脏油腻的衣服,洗了个澡,换上那套西服,用剃须刀刮掉胡须,又往腋窝和脖子上喷了香水。他对着镜子望了自己足足有半个小时,然后满意地出门了。他走到修车行,从抽屉里取出宾利的钥匙,启动引擎,往酒吧开去。一路都有人盯着他看,嘴里发出由衷的赞叹,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是个阔少爷了。
当然了,老板在的时候,他绝对不敢这么做。因为他在修车行干了有两年了。作为一个毫无劣迹的员工,老板放心地把修车行和宾利钥匙都交给他保管,但是让老板知道他晚上开车子去逛,也是不得了的,老板惜车如命,他还是十分吝啬的家伙,把钱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他第一次把车开出去的时候,是趁老板去外地出差的那几天,他偷偷摸摸地把车开到路上,还有一种战战兢兢被人发现的感觉。
到了酒吧,他昂首挺胸地坐在沙发上。当姑娘和别人闲谈时,他装出很阔气的样子,一口气点了两瓶很贵的香槟酒。他挺直腰板,一边品尝着酒,一边表现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终于引起了姑娘的注意。她在人群里盯着他看了会儿,那是一种审视的目光,一种探寻的目光。后来,他又加加温,给了侍者一百块小费,让他告诉她他是新加坡船王的嫡长子,能不能请她喝一杯。这个计谋果然凑效了,姑娘一脸笑意地朝他走来。
“听说你是新加坡船王的嫡长子。”姑娘说。
“没错,是我。”
他们坐下来喝了几杯后,他问她能不能带她出去兜兜风。她立马就答应了。小伙子把宾利开出来的时候,姑娘的眼睛亮了一下。她迫不及待地坐上车,脸上发出异样的光芒。
“宾利!这是宾利吗?”
“没错。”小伙子说。
“嚯。”她激动地说,“你能带我到处逛逛吗?”
这时姑娘主动提出了这一请求,让他十分激动。
“当然可以。”小伙子说。
“我还没有坐过宾利呢。”姑娘兴奋地说。
“我们现在就在这种车上。”
他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姑娘坐在副驾驶席上。他载着她开过欧风街,在第六大道上疾驰。他从一旁打量着她,发现她穿着浅蓝色的裙子,头发从后面高高束起,昂着脖子注视着前方。她身上有一种不安分的气息。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靠近她,他们不停地交谈,他发现她身上的缺点和优点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清晰可辨。他觉得她并没有特别喜欢他,她也一样。他们就像刚开始认识的男女一样保持着社交距离,同时摸清对方的性格,但也没有那样冷淡,聪明小伙利用他的幽默感让姑娘一次次发出咯咯的笑声。他自己心里有把握,他会让她爱上他。即使刚开始对她是那么厌恶。
他又带着她逛了一会儿,然后姑娘提出带她到香樟大道,因为她说她不能回家太晚。
“在这栋楼停下!””姑娘说。
小伙子把车停了下来,面前是一栋别致的欧式别墅,门前有一个喷泉,在四周植物的掩映下,那庞然大物俨然一座富丽堂皇的古代建筑。
“我到家了。”姑娘说,“你回去吧。”
“那就这样了。”小伙带着一丝不快。
他心想起码带他上去瞧瞧也好。姑娘什么也没说,弯着腰笑了笑。小伙子把车开走了,他带着隐隐不快的心情回到寓所。
姑娘从别墅门口路过,拐进一条幽深的胡同里。
从那以后,一下班,小伙子就脱掉脏兮兮的衣服,穿上同一套西服和姑娘约会。他觉得自己正处在幸福的漩涡当中。刚开始,他只把她当成一位美貌的姑娘,只想一亲芳泽就算了,现在,在被姑娘美貌所吸引的基础上,她还是一位银行行长的女儿。
他搂着她在舞池里跳舞,开最好的香槟酒,从那些公子哥眼里射出愤怒和嫉妒的光芒。每当这时,他就彻底忘记了自己只是个汽车维修工。
小伙子高昂着头,显出一副高傲的气派。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客客气气地对侍者说话,他现在都是驱一下指头,做一个手势,从不动口,当侍者不明白其义时,他就皱皱眉头,瞪一瞪眼。
“你看他是多么不懂事啊。”他对经理说。
他第一次尝到了这种优越感的滋味。
他每天开着那辆可供租赁的宾利载着姑娘在城里转悠。一到了晚上,他就意犹未尽地把车子开回来,把钥匙锁进修车行的抽屉里。但是姑娘从不让他送她回去,她总是在喝得半清醒的状态下打车回去,或者让他把她送到那栋别墅楼下。
一段时间后,他的苦恼来了。一方面,这位富家千金的追求者很多,她总在这些有钱的公子哥之间来回走动,在那些个子高大西装革履的男人中间寻觅着。他不是她唯一考虑对象,那些人总是围着她,像一群令人厌恶的苍蝇。当他看到她举起杯子和他们撞在一块,或者他们嬉皮笑脸地搂着她在舞池里跳舞时,他就表现得极为愤怒。
为了避免她和别的男人来往,他不得不看紧她,又不得不逢迎她,又不得不装得十分阔气。他就在这些之间来回周旋,经常搞得焦头烂额。
和他一起工作的维修工们相信他这样的聪明人不是真的着了魔,他只是想和她玩玩罢了。
他的花费渐渐不支起来。为了维持阔佬的形象,他不吝金钱,在酒吧里大吃大喝,挥金如土。背地里向维修工们和家里借钱,光信用卡就透支了好几张。每当陷入这种苦恼处境时,他就在心里暗示自己:没关系,我只是在她身上做了一笔很大的投资而已。有投资就会有回报。回报就在前方,我得开着宾利一路冲过去。
他就怀着这样的心情肆意挥霍着。他帮姑娘买了一枚卡地亚的戒指,每天晚上在酒吧喝得醉醺醺的,打架斗殴,在时代广场上撒尿,把车子开到喷泉旁边,跳进去洗澡,结果不得不出动警力来驱赶他们。他开始变得放荡不羁起来,和姑娘一起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这些事,他以前是从来不做的。
只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姑娘从来不让他送她回去。总是在半醺的情况下,自己打车回去。每当这时,他都觉得自己像受到了愚弄一样。
然而,宴会总会有结束的时候。一个月后,他的账单来了。工友们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威胁他如果不还钱就把他私自开出宾利的事情告诉老板,信用公司那边每天打十几个电话催他,如果月底再不还债,他们就要报警了。
为此,好几个晚上他都睡不着觉,他觉得他们这种关系该结束了,他再也不能这样胡作非为了。
两天后,有个联谊会在酒吧里举行,姑娘邀请他参加。她要求他把宾利开过来,她晚上要他带着她的朋友们到欧风街逛一逛。他本来可以一口否决,但是还是答应了。
“这是最后一晚上了。”他对自己说。
他换上自己的那身行头,他又成了富少爷了。
那天晚上,他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他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在舞池里转来转去。他渐渐沉溺在她的美貌和富有的光辉里,发了疯似的投入,纵情欢乐,一刻不停。因为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晚了。
他深深地吻着她,那一刻,他觉得他是真的很爱她。她呢,抬起头用含情脉脉的眼光望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隐隐的担忧。
聚会结束时,他们甩下姑娘的朋友们。驾驶着车子往郊区开去,来到了一片树林的岔道里,再往前就是一片空旷的田野。车子不停地行驶,抛锚时已至深夜,眼前荒无人烟,只有绵延起伏的丘陵和从头顶刮来的呼啸的风。他们下车,爬上山坡,并排躺在一块,望着深邃的夜空。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他淡淡地对姑娘说。
“我也有一件事。”姑娘说。
“那你先说吧。”
他听到姑娘一阵局促的喘息声。
“还是你说吧。”姑娘发出一声特别的叹息。
“其实,那辆宾利不是我的。”他说,“我只是一个汽车修理工。”
姑娘久久没有说话。他侧着身子望了姑娘一眼,又躺平了,双手交叉地枕在头下面,把头侧过去。他听到她的喘息声比之前更强烈了。
“我正要告诉你,我也不是银行行长的女儿。”姑娘说,“我只是一个穷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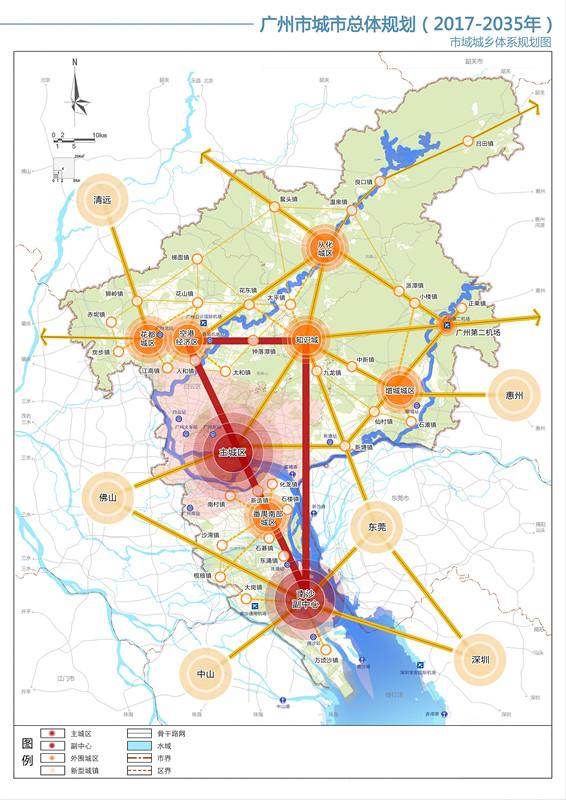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