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船员去东欧提新轮船,回国路上沉没,35人只有2人生还
生命有时是极其脆弱的,瞬间,它可能就会化为乌有。可是生命有时又无比强大,让你不能不为之惊叹。这是我们看过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之后的感触。
这部小说让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了生命本身那巨大的潜在能量,这种能量是超乎想象的,它会让你活下去。
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哪怕是吞噬你的荒野,是吃掉你的野兽,还是饥饿、疲惫,求生的本能都会帮助你战胜它。
一个没有经历过险境的人,是不会相信生命中有奇迹的,也不会相信生命力的强大。
下面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能让你感同身受。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进口工业设备主要是靠苏联东欧等兄弟国家。
罗马尼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造船业比较发达,中国的进口货轮有不少是来自该国。

1985年,中国向罗马尼亚订购了几艘货轮,其中一艘5000吨的货轮在年底建成,次年初交货。
1986年2月7日,水手长张周生等35名中国船员,兴致勃勃地来到罗马尼亚紧靠多瑙河畔的布拉伊位市。
这个小城风景秀丽,空气新鲜,让人流连忘返。可是船员们没有心情欣赏这迷人风景,他们摩拳擦掌,只想早日驾驶货轮回到祖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
这艘5000吨的货轮有个非常好听而吉祥的名字——“德堡”:“德”字多好,厚德载物,“堡”字,寓意着“坚如堡垒”。
实际上,当时罗马尼亚全面师承苏联,在经济领域方面因循守旧,没有将工资效益和质量挂钩,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没差别。
所以工厂里的质量口号虽然喊得震天响,“质量第一”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是企业管理模式非常落后,最靠不住的恰恰就是质量。
在此背景下,“德堡”轮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大家登上货轮之后,眼前看到的一切让他们有些手足无措。中国船员虽然对制造货轮是外行,暂时不能领略到轮船的内在质量,但是德堡轮的外观质量好坏,还是一眼看得出来的。
首先,船体外壳凹凸不平,就像铁匠手工打造的一样,其次,外壳喷漆时明显没有进行细致除锈,船体上面的喷漆已经微微爆皮,视觉效果方面连翻新货都不如。
进入货轮机舱之后,大家更加灰心,里面管路像蜘蛛网一样,极其凌乱,布局非常不合理,哪怕你小心翼翼,也会磕碰到手脚。
船舱内应该是崭新的密封胶条却早已泛黄,没有弹性,看得出做工很差,而且主甲板防水门密封不严,甲板上吊杆连安全销都没有插。
货舱的吊杆架,竟然用的是承重最差的电焊。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驾驶台上的仪器在试验的时候就出了故障。
中国船员简直无语了,这哪里是造船厂,简直就是废品回收站嘛,与其说是一艘船,还不如说是一颗定时炸弹。
于是,中方的船员向罗方一一指出存在的问题,希望他们认真对待,予以处理。可罗方狡辩说,还没有磨合的船,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不懂,千万不要乱讲话。
总而言之,你们人已经来了,不要也得要。

而且罗方人员还振振有词地说,船在1月份已经经过你们中方的监造小组验收合格,是你们内行,还是专家更内行?
想来这并非是监造小组不够认真,主要考虑的还是从维护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不想闹得那么不愉快。
事已至此,船员们只好在纠结和忐忑中,于3月17日离开布拉伊拉,开始了回国之路。
怕什么来什么,航行了45分钟,设备就开始“闹事”,先是机舱的配电板罢工跳闸,之后是导航的罗经仪捣乱。把中国技术员忙得是大汗淋漓,维修了一个半小时,这才排除了故障,继续前行。
一天后,德堡轮到了位于黑海西岸的康斯坦萨港之后,故障接踵而来,应急消防泵启动之后还不到一刻钟,保险就烧了。
烦人的事是一件接一件,21日晚上装货的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就像在为“仇人”工作,装的钢材松松垮垮,一盘散沙。
中国船员耐心地告诉对方,装不好的话很容易在风暴中位置偏移,偏向一侧,造成翻船事故,但罗马尼亚装卸工吊儿郎当惯了,仍旧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4月1日下午4时,德堡轮总算完成装货任务,离开码头。在航程中,配电板不时跳闸,轮船走走停停,让人不胜其烦。
4月9日,德堡轮驶出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眼看离祖国越来越近,船员们在心里暗暗祈祷,机器千万别出毛病,让我们平安回国。

但货轮可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轮机又开始罢工,时好时坏。
按理说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同小可,必须停靠维修。可一则红海附近是海盗出没的地方,二则两伊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海面上遍布水雷,如果贸然靠岸,在不熟悉海域的情况下,就有触雷的危险。
因此,只能开着病轮硬着头皮前行。
4月12日晚,德堡轮在提心吊胆中驶出红海,行将进入印度洋,船上的人暂时松了一口气。
到达吉布提水域,船长下令抛锚,对轮机进行检查。不查不要紧,一查后大吃一惊:推力轴承的推力块已烧坏,推力主颈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轮机长傻眼了,要想继续运转,必须将其打磨,可是船上哪里来的机床,总不能用砂纸去打磨吧。德堡轮只好和罗马尼亚方面联系,暂时抛锚等待,让他们送来配件。
直到50多天后,罗马尼亚人员才不紧不慢地赶到,装上备件之后连调试都没有,就匆匆离开。
换上备件后,中国船员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心里说,这之后不会再出故障了吧。
6月11日下午,德堡轮刚航行了一天,电机又开始捣乱起来。维修师傅只好在索马里海面上就地修理,用了两天时间才排除了故障,13号,继续航行。
按照预定航线,德堡轮下一步应该是穿越印度洋,绕道马六甲海峡,到中国南海,再回到广州。多番等待后,已经是6月,印度洋正刮着强劲的西南季风,在海面上掀起滔天的大浪。五千吨级的德堡轮航行时,被季风吹得像一片树叶,随着大浪一起一伏。

由于发动机的质量靠不住,难以抵御大风大浪,船长不得不舍近求远,尽量靠近赤道附近的无风带往东行驶。
6月16日晚8点50分,德堡轮再现惊魂一刻,主机突然罢工,轮船陡然没有了动力,在海面上随波逐流,几层楼高的巨浪一会把货轮抛到浪尖,一会又推到谷底。
在大浪的折腾下,船上的钢材移位了,怕什么来什么。之前担心的重心偏移现象果然发生,货轮开始倾斜,船舱开始进水,货轮随时都会倾覆沉没。
形势万分危急之下,船长只好忍痛下令,准备好救生艇,弃船逃生。
可是这时候船体已经向左倾斜严重,右舷救生艇紧挨着甲板的舷墙。救生艇落入水中,也不能正面向上,只能倒扣,无法载人。
随着大浪肆虐,船体继续向左倾斜,瞬间达到了90度,货轮开始下沉,海水迅速地把船体吞没,只有5个人上了救生筏。

他们是:32岁的水手长张周生,30岁的机工郭卫朝,50岁的副水手长朱亮杰,31岁的一级水手郭德胜,30岁的二副周海龙。
5个人在惊涛骇浪中相互依偎着,相顾无言,每个人眼里噙满泪花,在惊恐和悲痛中度过了一生最漫长的一个夜晚。
随着第二天黎明的到来,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阳光洒在茫茫的印度洋上,但是光明并没有驱赶走恐惧。
因为所有的设备都葬身海底,不能发出求救信号,他们的救生筏脆弱得不堪一击,只能听天由命。
要想渡过难关,只能齐心协力,具有10年航龄的张周生自告奋勇当大家的头,他负责给大家分发仅存的压缩饼干,组织大家轮替休息,向外排除涌入救生筏里的海水,努力保持救生筏的平衡。
除了风浪的危险,他们还面临着食品短缺和饮水困难。
压缩饼干充其量只能够让大家吃一个星期,即使不吃东西,只要有水喝,存活十来天也不是问题。
可要命的是,救生筏上没有一滴饮用水。

万般无奈,大家只能用容器接自己的小便,补充淡水,尽管味道难闻,比喝药还难受,但大家都没有犹豫。
他们明白,不这样做大家就会脱水,生命垂危。
尽管不能向外界求救,但是大家并不感到太悲观,因为按照之前的约定,德堡轮每天至少要和总部进行一次联络,汇报轮船的方位。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总部要求进行两次汇报。这样的话,如果总部联系不上货轮,肯定会做最坏的打算,采取积极措施,展开搜寻营救。
可是他们忘了在没有定位设备的情况下,总部即使派人来这里搜寻,找到他们也跟大海捞针一样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子越来越难熬,困扰他们的仍旧还是饮水问题。没有水分的补充,只靠喝尿液注定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在人体循环中,水分是在不断减少的。
到了第五天,排出的尿液越来越少,只能以滴来计算,大家开始出现嘴唇干裂,扁桃体肿大,口鼻出血等现象。
天公也不作美,故意跟大家作对,不但没有一次降雨,反而天天艳阳高照。如此一来,大家没有了唾液分泌,饼干也难以下咽。

在烈日的暴晒下,所有人都出现脱水情况,肌肉开始萎缩,到了生命极限,开始陆续告别人世。
七天之后,郭卫朝、朱亮杰、周海龙先后牺牲,救生筏上只剩下两个人——张周生和郭德胜了。
说真的,他们也已经陷入绝望,等到救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他们不甘心,如果他们就这样倒下了,他们这次遇难的真相将永远成为秘密。
最可怕的是,布拉伊拉造船厂还有七条货轮没有交货给我方,这些船还有可能“害死”自己的同胞,悲剧会再次上演。
所以他们相互用目光交流着,鼓励着,一定要活下去,回到祖国,把真实情况回报上去。
直到获救之后他们才知道,船运公司联系不上他们后,当时并没有做出及时反应,捱到货轮失联的第八天,才不得已向交通部汇报。
此刻的两人已经在海上漂泊了数百海里,脱水严重的他们奄奄一息,命悬一线。
到了第9天,苍天开眼,一阵凉风过后,天空中淅淅沥沥的小雨飘然而至。

在他们看来,雨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雨滴比金子都珍贵。
于是他们不知道从哪来的力量,不约而同挣扎着张开嘴拼命吮吸着,似乎那从天而降的不是雨水,而是琼浆玉液。喝足喝饱之后,他们恢复了一点体力,这才想起用袋子收集雨水。
老天不下雨则已,一下雨就不停,一连五天降水不止,他们接的雨水也有几十斤,足够十天饮用,再也不用喝尿了。
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的滋润,他俩焕发生机,心里燃起希望之火。
郭德胜幽默地说:“大张,看来是老天不让我们走,我们要挺过去,不能不给他老人家面子。”
张周生点点头:“是呀,那样显得咱多不够意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又开始一点点减小。到了第17天的时候,他们吃掉了最后一块压缩饼干,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至多只能撑一周左右,死神在狞笑着一步步向他们走近。
郭德胜的反应最敏感,他开始绝望,话明显少了起来。
张周生毕竟大两岁,显得非常沉着,他说:“小郭啊,你读过长征的故事吗,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过程还记得吗?”
郭德胜回答说:“怎么不记得,吃草根、树皮,还有皮带。”
说到这里,他突然来了灵感,把目光停留在橡皮筏上用来充气的皮老虎上。他一把就把上面的一小块牛皮扯下来,分成两块,递给张周生,两人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就这样,他们吃光了筏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
从那之后,他们开始抓偶尔落在救生筏上面的海鸥。有时候海浪也会把小生物“送”到救生筏周边,让他们美餐一顿。
但是这样的美餐实在太少了,他们的体力一直在下降,最后连坐起来都很困难,即使海鸥再落上去,都没有了抬手抓他们的力气。
1986年7月10日,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泊了24天,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似乎听到了死神的终极召唤,生命之灯,眼见得就要油尽灯枯。
下午5点多钟,他们的耳边突然传来隐约的汽笛声。

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将头伸出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艘船向他们驶来,由远而近,在离橡皮筏几十米的地方停下。
两人想呼唤,但是没有喊出任何声音,只能瘫软在橡皮筏上。尽管他们没有发出声音,但是他们依旧得救了,因为他们的橡皮筏的位置距离主船道不到一公里,船上的大副眼尖,早就发现了他们,立即开船向他们靠近。
可是当他们走近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救生筏上的人,大副估计船上的人已经昏迷或者在睡觉,就拉响了汽笛,以叫醒他们。
汽笛一响,救生筏上果然有人伸出头来,大副又惊又喜,将他们营救上船。
此刻,他们已经漂泊了一千海里,快到马尔代夫。
那艘搭救他们的货船是日本的三井丸船,船长叫白木昭治,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大约50岁。得知他们是中国船员之后,他们马上联系日本外务省。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从日本外务省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
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得知后,很快就做出判断,他们是失踪近一个月的德堡轮的船员。于是他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与三井丸号取得联系。
7月15日,三井丸号停靠在新加坡,他们二人终于登上了陆地,之后便坐飞机回国。

临走的时候,他们满含热泪于日本船员告别。确切地说,是日本船员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在日本船只上,他们已经恢复了体力。
在海上漂泊的24天里,他们没有过一次大便,肠子已然粘连梗阻,无法排便。船上的日本医生像伺候自己的亲人一样用开塞露为他们疏通肠道,直到他们能排便为止。
船长知道他们的胃消化不好,专门给他们安排开小灶,为他们熬又烂又黏的稀粥,甚至亲手把苹果榨成果酱,一口一口喂他们吃。
7月15日,他们离开之前,全体船员欢聚一堂,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白木昭治船长还为他们深情地唱了一支日本民歌《北国之春》。
张周生也用中文唱和了一支日本电视剧插曲,可是,因为太激动,只唱了两句,就声音哽咽。
临行前,热心的日本朋友还将自己崭新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
这时候,中国驻新加坡商务处的代表和中国远洋公司的船运代表登上了三井丸号。看到亲人,他们的泪水奔涌而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船长亲自扶着他俩走下舷梯。甲板上,日本全体船员以水手的礼仪列队为他们送行。
他们紧紧握着船长的手,再次留下感激的泪水。
三井丸号驶抵日本后,中国驻日大使馆特地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宴请所有船员和他们的家属,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张周生和郭德胜以惊人的毅力战胜困难,挽救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杜绝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悲剧。
德堡轮沉没几个月后,布拉伊拉船厂建造的另一艘5000吨货轮“柳堡号”也到了交货时间,交通部汲取了德堡轮的教训,我国航运公司安排其返航的时候,特地派了两艘船紧紧跟随,进行护航,保证了它安全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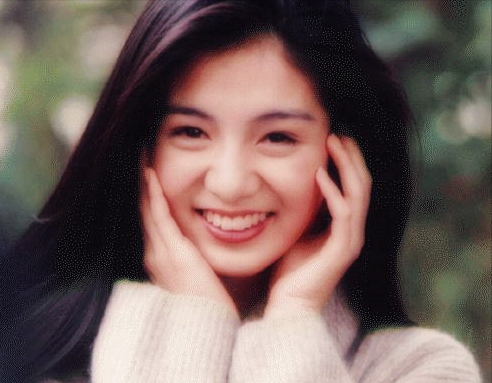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