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若:女德班只是用国学包装来吸引学生而已
近日,歌手孙楠一家为送孩子学国学从北京搬到江苏徐州的消息引发热议。原来,孙楠为孩子选择的是一家主打国学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学校“华夏学宫”。视频资料显示,孙楠的几个孩子能熟练背诵《弟子规》,潘蔚还会在家教女儿们女红,为的是让她们“用针线传递爱”。潘蔚在视频中强调自己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平静而倾心于国学的,她个人也在这所学校担任女红、茶文化老师。
国学教育往往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但这些教育也往往由于与现代精神的违背而饱受争议,而往往与国学教育绑定的“女德班”则更是常常爆出耸人听闻的课程,以东莞蒙正“女德班”为例,他们将“德行”解释为三道:姑娘道、媳妇道、老太太道。“每道都有女人要守的本分”,然后才能拥有健康和财富。
“女德班”频遭诟病却又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已多见诸报端。例如,性别研究专家宋少鹏认为女德班是市场需求的产物,女德班满足了部分中国女性想要缓解作为“个体人”与作为“家庭人”的结构性冲突的需求。她认为,面对赤裸裸的性别不平等,女德班用传统女德来正当化“男女不一样”的运作原则。女德班教导女人与其在两种互相冲突的原则中受煎熬,不如接受一种原则来化解内心的痛苦,并能更好地接受现状。
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年来的公共讨论里,女德班总是和国学“绑定”在一起?女德班和 “国学热”存在自然而然的联系吗?澎湃新闻也就此问题采访了旅美政治文化学者张善若。
张张善若博士于2007年在美国加州⼤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学位, 师从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M. Kent Jennings 教授,现为美国加州理⼯州⽴⼤学政治学系教授。她的英文著作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Actionable Account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已于2015年出版。
张教授是中国出生、成长的学者,同时因为在美国生活近20年,她对美国社会有长期的观察和个人经验,她的女性身份,也使她在探讨相关议题时可以提供女性视角。从此次大众文化事件切入,我们和张教授聊了聊她对女性主义以及女德的看法,儒家思想的复杂性,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产生的对儒家的误解。
张教授认为,首先,女德和儒家以及国学是不应该放在一起讨论的,因为儒家塑造的文本里面的女性形象其实多种多样的,并不是流行印象里的“女德”那一种;第二,那种认为儒家思想里找不到性别平等的思想资源继而等于文化糟粕的观点毫无道理,我们也谈到了外国学者为什么研究儒学,以及从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第三,国学班这种反潮流的文化现象在美国也出现过,张教授认为,文化的发展里面总会参杂一些反潮流的东西,不必过分惊恐,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

张善若教授
【对话】
“儒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并非流行观点中‘女德’那一种”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看待女德这个概念的?又如何看待女德班往往和国学或者儒学的绑定?
张善若:我认为“女德”这个概念其实它掩盖了很多现实,道德当然是好的,学习道德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要把某一些道德专门标榜成女德?为什么只有女性才应该具有这样的道德?所以女德这个概念,看上去是以德作为闪光点,但本身它就有一定的不平等的内涵。为什么没有男德的概念呢?当然这个社会对男性也有某些具有刻板成见性的要求,但是从实践上讲,为什么只有女孩子被送到这些学校,去学女德,为什么男孩子不被送到学校去学温良恭俭让呢?
而且女孩子到这些学校,除了所谓的国学传统经典之外,其它实践完全又脱离了这些美德教育。比如我搜索了女德班的相关新闻,马上照片就出来了,可是他们那些具体细碎的行为规范,也和所谓的儒家美德譬如三从四德没有必然联系。我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些女孩子要跪在地板上擦地,中午吃饭要等到男孩吃完了以后才去吃,这些和道德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它的实质是从价值观到行为,一系列的这种点点滴滴的渗透灌输,强行压制进去男女不平等的一个观念啊!
国学或者儒学其实是很丰富的,为什么非得挑出女德这一块来教或者来营销?当然,如果硬要讨论,我们也可以讨论女德和国学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个关系是非常疏离的,女德和国学不存在一个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一个联系。女德也并不是国学的一部分。如果讲女德的时候打着国学的旗号,是很值得商榷和怀疑的。女德这个概念和儒家没什么关系,据我了解,很多是用国学或儒学来包装女德班吸引学生而已。
澎湃新闻:为什么他们的联系并非自然而然?
张善若:国学这个词是清朝中末以后,西学越来越盛行的大背景下被提出的。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属于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问就是文史哲,那么儒家框架下的文史者,如果说因为孔子说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一句话,那么现在这种“女德”就是儒家文史哲的一部分,我不认同。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叙事和话语都看做是庞大的“儒家文本”的体现,那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穆桂英、花木兰、《孝女传》、《烈女传》都是这一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女性形象,倡导的究竟是什么呢?不是女德班教的那些具体的细琐家务和照料责任,这些与“国学”和“儒家对女性的定义”都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这个女德是儒家思想体系庞杂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小支流的话,我可以想到的文本是三从四德这些东西,那么三从四德又和让女孩子们跪在地上擦地板有必然联系吗?和让女孩子们等男孩子吃完了饭以后再去吃有必然联系吗?女德和国学是不应该放在一起讨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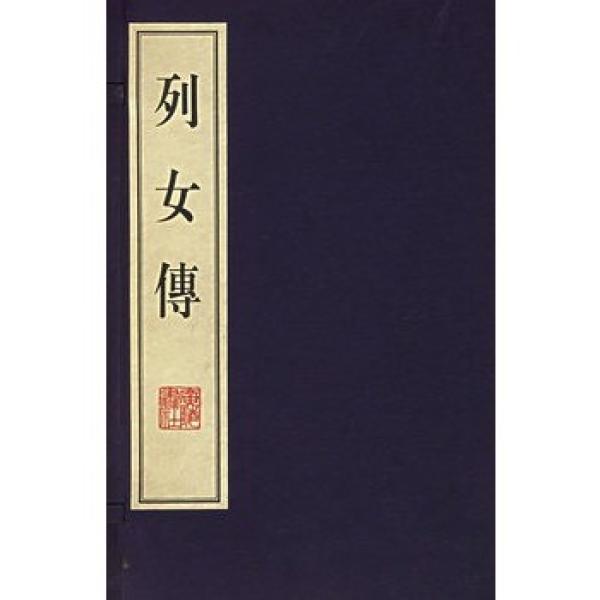
澎湃新闻:在《列女传》或者《孝女传》里面,其实并没有如今这些女德班教的东西是吧?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是温州的女德班,也是记者暗访的,很多家长送孩子去。记者拍到的视频里面,小孩上完课得出的结论是:“我妈妈生病都是因为我不孝顺,”家里面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孩子不孝顺。
张善若:儒家有《孝女传》,《孝女传》里面这些孝女究竟是什么样?那是大孝大勇大智啊,而不是趴在地上擦地板。不是现在的女德班里的那些如何做家务的内容。
另外,在儒学经典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女性是很有力量的。 儒学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文本体系。如果只是基于所谓的儒家经典,比如四书五经,甚至现在在孩子教育中流行的《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文本,就给儒家盖棺定论的话,我觉得儒家就冤死了。当我们提到儒家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像活化石一样的,就那几本书,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话语体系,一个话语体系,一种思想体系。比如说孟母三迁,孟子的母亲,这些有见识有能力,有魄力的女性,小说中女性的将领(如穆桂英),这些难道不都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女性形象吗?
这些具体的课程内容是打着儒家或者国学的名义在造假,特别是在我们现代的视角下,一种对女性的故意打压,如果这些学习班通过这样的做法去向女孩子们灌输一些观点,还堂而皇之地挂上国学的旗号,这就是糟粕了。
澎湃新闻:我好像确实会带有偏见,可能我会把儒学思想当成活化石,然后那些强大的女性,就觉得好像跟儒家没关系,没有想过她们其实也是该体系里的产物。
张善若:她们当然是这个体系中的产物,我们现在过于看重孔子说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以及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所以儒家是被简单化了。儒家是什么?儒家是孔子的学说,还是董仲舒后来发展的东西,还是朱熹王阳明后来的发展出来的宋明理学呢?儒家是一个非常庞大浩瀚复杂的一个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里关于性别平等的思想资源少不等于儒家就是文化糟粕
澎湃新闻: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认为儒家的整套理念思想里是没有任何可以去学习的了,特别在性别这一块,因为现在舆论争论的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到底如何做女性的问题,有人可能就觉得没有必要再看这些东西了,它完完全全已经是跟不上时代的事,是完全的糟粕,你又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张善若:刚才讲过儒家经典本来就是非常的纷繁复杂,它内部也存在很多的多样性,也是分阶段的,它也并非一致性非常高的东西。当然,儒家所谓的经典以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关注低,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在其他的国家,历史也是差不多的,可能全球范围都会有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女性地位经历了从低到高的过程,这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农业社会的时候,生产就是靠体力,男性是更主要的一个生产力的来源,那么逐渐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对体力的要求就越来越少了。那么女性的智力,女性的情商,女性的沟通能力,语言能力协调能力就逐渐的慢慢都凸显出来了,包括一些创造力也都体现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在儒家传统里面的女性社会地位很低,一方面它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当时社会的现实又是在秦汉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封建家长制,也就是说现实和思想是互动的关系。当时的这种生产方式使得男性有一个更加显赫的地位,这样的“男权”式的知识体系又制造了很多思想和学说来合理化以及巩固这样的状况,有意无意的巩固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一套思想体系中,我觉得现代女性所需要的那些资源和思潮在儒学里面可能真的是很少的。
也就是说,儒家没有像我们现代女性希望的那样给女性一个平等,但是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么一个时代,没有平等的现实的条件。但是,这一套思想体系里面没有特别现代的关于女性的意识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把它定位成糟粕呢?
再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到儒家里面去找到资源呢?难道我们要说,2000年前他们没想到我们2000年后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没写到这个《大学》里头,所以它就是糟粕吗?!这毫无道理。
澎湃新闻:一直很好奇,外国人研究儒家,他们是基本上有什么样的共识,或者是他们认为这个研究的重要性是在哪里?
张善若:这个问题很好,研究这些的一般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学政治思想的,他们是从美国的角度或者西方角度出发,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西方的问题,东方智慧给我们提供什么资源,他们发现了哪些资源?他们发现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团体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英语叫做“communitarianism”,因为对他们来讲,针对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东方的团体精神是一个解药。
举个例子,前两天,我们学校的残疾学生援助中心派了一个人来到我教室里说,班上有一个同学没法自己做笔记,需要一个同学自愿帮助他,只要把他的笔记拍成照片然后放到网上就可以了,这个人问有谁愿意,全班静默了好几秒,没有人愿意,这些东西在中国可能都不太成问题。但是在美国就成了非常显著的问题,因为他个人主义特别的严重。我上博士的时候,全班有十几个同学,我那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韩国人,全系当时就只有我们两个是亚洲人。然后每一次班上需要同学把这篇文章复印一下,然后放到网上大家都能看的,或者班上要吃一些东西,有没有同学愿意到哪去取一下,这些事情永远都是我和她在做。其实我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为集体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但是她就很生气,她说,你有没有发现每次都是我们两个亚裔的女孩儿为大家服务?
儒家使得外国学者有兴趣的另一原因是东亚经济崛起对欧美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他们没有想到在二战结束以后二三十年的时间,日本韩国这些他们以前认为非常穷的地方,新加坡以前都是殖民地,突然经济可以发展成这样。所以像哈佛的杜维明写的东西,就是讲儒家的这种团体精神以及刻苦精神,勤奋精神等相当于欧洲的新教,欧洲是因为新教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么东亚就是因为儒教发展出了资本主义。
第三种情况,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是说“冷战”以后,如何去研究如何去看待中国的发展?大家就逐渐看到除了社会主义视角以外,还有一个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视角,所以又有一些书,包括我自己的就是在探讨这些东西,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发展有哪一些是需要从1949年以前历史为基础来解释的。一方面是想说中国政治有中国政治的特点:一个是这种精英主义,一个是善治,中国的体制能够很有效地把精英把最聪明最能干最刻苦最投入的人放到治理系统里面去,于是中国的治理才如此的有效。那么这一种治理方式从哪里来的?从文化传统来说,就是从儒家来的。
澎湃新闻:所以你的研究是理解儒家思想对当代的中国政治实践的影响,你认为儒家思想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如果一定要否定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不尊重现实,并没有要去推广它或者是复兴它,是这样吗?
张善若:对,这么说吧,如果把儒家剔除出去,我们是无法完美地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不是断裂性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很多儒家的思想确实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此出发,中国需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中国也正是在自己的道路上的,我们需要很踏实地很安心地去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
但是虽然我研究儒家对当下政治文化的影响,但我个人的立场也不是要把孔子当年写的文本或者董仲舒的那些文本,这种几千年以前的思想在当下复活。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也不等于要去复兴儒家,要去穿汉服,要把几百年以前的东西拿回来,也并不是这样。难道大家都穿了汉服了,中国就复兴了吗?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我们现在生活在2019年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世界有那么多精彩的思想,在中国能接收到世界各地的学者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我们为什么要把精力单一地花在推广儒家上?这样的做法和我们现代的进步的思想以及日新月异变化飞快的中国实践都是不相吻合的。我不赞同这样的做法,我不会送我的孩子,男孩女孩我也都不会送他们去学这些东西。
从历史诠释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社会、文化对自己传统的认识,永远是不可能真正地回到那个时代文本被制造出来的时代那样去认识和实践的。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激活儒学,怎么样去让它为我们的现代来服务,而并非把2000年3000年以前的社会风俗,家庭、习惯人际关系等在现代社会重演!这样做一是背离时代精神,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澎湃新闻:儒家的哪些资源你觉得是特别积极的?
张善若: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关于话语和讨论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比如说中国人一直就讲同情心、怜悯之心,其实放到现在话语里面,不就是共情的意思吗?就是你能够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和看待问题。我们中国人讲和就是以和为贵,这句话里面富含长年累月积累的历史经验。这个和谐如何形成,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里,通过共同的讨论和真正的深层交流,能够让社会形成一定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也不是不变的,它根据现实能够形成一些引导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儒家里面积极的资源很多,比如说学行合一。这是多么大的智慧,知识论和实践论结合在一起,是儒家文化中对现实非常实用理性的一个概念。当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为什么中国人马上就接受了?为什么这个概念如此容易被接受?因为这就是我们思想深处的东西。
儒家这个概念作为一个符号,对不同的人来讲,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我其实也都不太说儒家,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从夏舜禹的时候开始,我们的政治历史开始发展,然后历史学家们政治家们通过对这样的历史发展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发展出我们自己的政治理论,然后用这样的政治理论去指导我们的政治实践,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政治的操作是我们很独特的一份宝藏。
这样的政治的经验,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去研究和学习的,而不是说一些什么带了儒家标签的价值观,或者说观念,或者说女孩子要去做手工。做了手工你就变成好女人了吗?你会刺绣你就变成好女人了?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对女性的定义、期待不应该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作为有思考能力的人,她在学的过程中,也会去想知和行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女德班中学到的东西对我现在2019年面对的我这个现实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我想学生们也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那些学习儒学的人,或者那些上女德班的人,最终学到的东西是不是也是不一样? 在此次热点事件里,当事人女孩就坚称她上的那些课,她不认为是女德,她也不希望网友评论她的所学。
张善若:当然,学习永远是很个人的过程。我给学生上课,上课虽然教一样的东西,每个学生都从自身的角度去学习,他们去摄取和反思知识,最后变成自己的理解。每个人的理解也都是不同的,他把这个理解重新融入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当中,然后再把这一套东西投射到他的实践里面,实践又跟外部世界相互动,所以每个人学习的经历以及其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谈儒学也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读《论语》读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是把孔子当时说的文本,通过我们的现代的视角去摄取进来的。我们也只是摄取部分,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摄取到论语的全部。我们只是去抓取对我们这一刻来讲最有意义的那一部分,然后把它拿到我们的世界里来进行理解和诠释,其实是把孔子当时的视域和我们现在的视域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对论语的理解以及现在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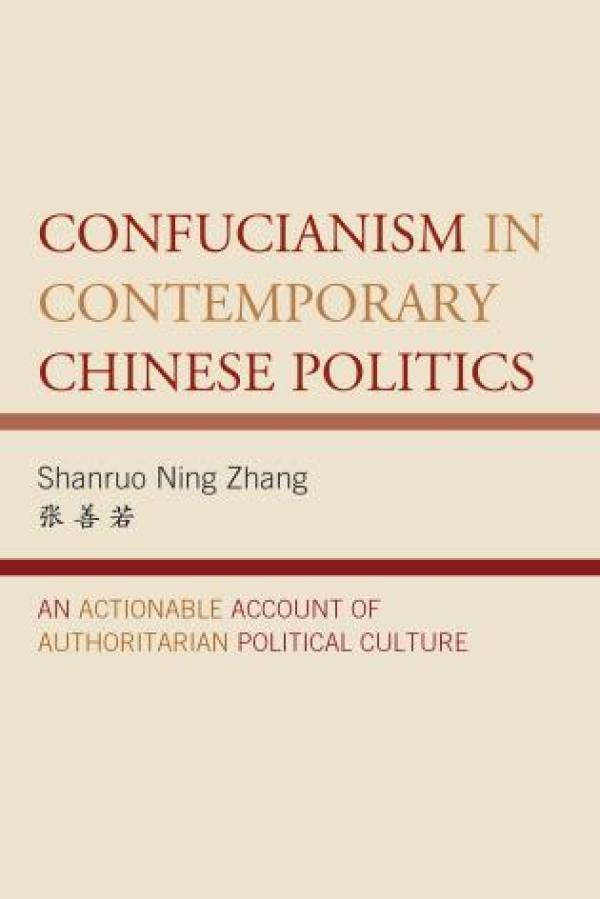
张善若所著《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儒家思想》
“文化运动中必然有反潮流的部分存在”
澎湃新闻:女德班为什么会出现?对于这种现象,你是如何理解的? 如何看待这种卷土重来的“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类似这样的说法和写作?
张善若:文化的进步就是亦步亦趋的,不可能是线性一元性发展,一定是一个多元性的发展,有人要往左走,有人要往右走,有人要飞速的近现代化进步,有人想要留住传统文化的发展,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必然是有反潮流的部分的。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如此,比如说美国女权运动从女性争取选举权开始就开始了,就是100年以前1920年左右,那个时候已经如火如荼了。但是最近几年在美国南部比较保守的一些地方,却开始重新讨论女孩子的贞操。有一些当地女孩18岁生日的时候,就会在左手无名指上带一个象征贞操的戒指,并且会发一个誓言,说我在结婚之前不会有性行为。这些人基本上是比较虔诚的教徒,受地方文化氛围的影响很大。
我记得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的各大媒体也都做了很多报道。我和同事因为在加州,文化就比较开放,就觉得特别无法理解。
女孩长大的过程中,她的价值观就是被培养的被社会塑造的,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学者们认为人就是十七到二十五岁这个阶段思想最为开放,二十五岁以后人的价值观就不会有大的改变了。这个阶段在学术上叫政治社会化。人刚出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小baby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价值取向,然后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从一个脑子一片空白的个体,变成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一份子的过程就叫做政治社会化:通过给你灌输一系列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等,让你变成了社会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这个反潮流算是一个贬义词吗?
张善若:看从哪个方向讲。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挺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正常不代表我赞许,不代表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更多。只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预见到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我不赞同现在流行的这种国学课或者女德班,但是我也不觉得应该把它一棒子打死,因为你把这个声音压下去,他们也不会被消灭掉。因为这确实也是一部分女性的声音。我们可能没有这种观念,不能不允许别人也没有。人们的经历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如果这是他人真实的想法,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空间去实现。
澎湃新闻:说到“女性形象”的潮流与反潮流的问题,现在表现出特别顾家反倒成为一个不合潮流的事情。前段时间女星伊能静一个微博发言,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想把重心放在孩子和家庭上,她下面的评论中点赞最多的是:你给现代女性做了非常不好的榜样。意思就是说她作为一个女明星,她应该给女性的榜样是如何去追求自己的事业的。这些评论人的眼里面就是你回归家庭,等于你不再是一个独立女性了。这样的观点我是不太认同的,成为独立女性的这种声音在城市里面是非常强的。大家看到只要女明星不再是这种所谓大女人的人设,她表现出特别顾家反倒成为一个不合潮流的事。
张善若:现在家庭主妇的做法可能确实是反潮流,因为现在的潮流是女性主义嘛,潮流是独立女性,但是所谓的女性独立追求的最后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一个选择的自由。
我们之所以现在讲女性独立,是因为女性一直不独立,她没有选择的自由,她想上学没学上,她想上班没班上。因为她在经济上它依赖于男性,所以她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现在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女性一个选择。但是以前只能向左走,现在只能向右走,那不是又没有选择了吗?
同样,这个现象也不光是中国有,美国十年以前就有很大的讨论,一些家庭主妇就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支持她们的,她们从社会和文化里得不到资源得不到支持,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职业女性,就是越职业越好,越不顾家越好。
我认为只有当女性获得这样自由以后,男性也获得了这样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就是说一个男性他如果说我想呆在家里面做一个好丈夫,只要他们两个人能够商量好,社会不应该对他有任何的歧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两性自由。所以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在解放男性。这个结果就是两个性别都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的自由,这个才是我们的进步的目的。
澎湃新闻:谈到美国的话,我也了解到一些私校有男女分校。在男女校里面是不是他们学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女生就有一些手工课,而男生没有?你对这种男女性别分开接受教育是不是也不太认同?你认为应该是一视同仁地接受教育,接受社会化?
张善若:因为以前女孩子就不受教育,只有男孩受教育,后来一些比较开明的家庭愿意送女孩去上学,也许已有的学校不知道该怎么聚焦于女孩子,或者可能认为男女孩子一起上学会有一些麻烦,他们没有这种管理的经验,所以可能就专门给女孩子们开一个学校。
回到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做手工当然没问题。我想强调的是,随着机械化以及电脑化的这种发展,其实很多手工的男女界限开始消失了。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我的好几个女性朋友都开始学做木工了。我9月份去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个教授朋友,她快退休了,她退休的计划就是准备搬到缅因州的一个地方去学做木工,包括木雕等。我回到学校以后,发现我的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同事最近也开始做木工。
然后同时又有一些男性他会去做一些可能我们认为比较偏女性化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男同事,我经常在菜市场、超市碰到他,他经常下了班去买菜。我在街上看到爸爸推着婴儿车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现在美国25%的家庭里面,女性的收入已经超过男性了。电视电影里面看到女的CEO越来越多了。
澎湃新闻:有些人倒也不是不承认家庭主妇的贡献,但是他们会强调在职场的女性,她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是更高级的满足感,照顾孩子获得的满足相对是低级的满足。这些人认为家庭主妇也在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家庭主妇沉浸在一种低级的劳动里面,会忘记了女人还可以做更高级的事情。
张善若:我觉得这个关于低级还是高级的决定还是让当事人自己去做吧!我觉得当一个好妈妈要对个人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当妈妈要做各种各样的判断,采取各种行动,不是一件不如工作的事情。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选择,有的人当妈妈都很快乐很开心,甚至要比你工作起来可能满足度要更高。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做一种判断。而从社会来讲,一个好的社会,它的功能就是给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提供支持。那么当一个职业女性她想生孩子的时候,你就给她产假,你让她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把孩子的最初降临到世界里的一段时间的这种急需的要求给它处理好,给她一些灵活的空间,让她能够兼顾孩子和工作。然后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很想回家当妈妈,然后也放弃一段时间工作,这个社会也不要歧视她,让她很开心很安心的去当妈妈,因为一个快乐的妈妈才能教育出快乐的孩子。
快乐的孩子对这个社会也是很重要的。当一个妈妈把孩子养得差不多了,在孩子上学后她又有空闲的时间,她又想回到工作岗位。社会也不要歧视她,要给她机会去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社会应该给女性提供的保障。同时我也认为也应该给男性提供产假,比如说在美国我的男同事,他们妻子生孩子他们也有产假。男性的产假肯定会减轻女性的负担,能让女性更快地回到工作岗位。
一个女性如果说我生了孩子,但是我特别热爱我的工作,我就是想回去工作,然后夫妻两人都同意,说男性可以呆在家里面管孩子一段时间,社会也不应该歧视这个男性。我觉得好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对别人下判断。
澎湃新闻:还有一种看法是,那些选择去做家庭妇女的女性,她根本就没有反思过,譬如那些偏远城市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女人还有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这种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会觉得要矫枉过正,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女性,不要去学女德那套教女人顺从的东西,而是鼓励她们像男人一样去工作,他们会认为在现在的社会是应该强有力的去鼓励大女人的。
张善若:我周围的很多女性都是女博士,但是最后这些人做的选择也又有不同。有的人就是会更顾家一些,有的人就是会在事业上走得远一些。我的经验是,我的每一个女朋友的情况都那么错综复杂,每个人的现实都那么的真实,每个人都是那么一步一步的攀登,然后每一个人面临的这种机会结构又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往往我们认为可以轻易做到的,别人可能真的就是做不到,可能就是没有空间。反过来也一样,在别人的生活轨迹中似乎非常自然而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却也觉得困难或者有阻力。
所以我觉得精英从自己的这种制高点,不管是什么样的制高点出发去评价别人都不好。我能够理解矫枉必须过正的想法,这样一种策略,也相信用意是好的,但是在我的人生实践中没有成功过,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温和的支持者的态度,才能够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速度一点一点地去进步。
澎湃新闻:你希望社会对国学班或者女德班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不只是女德班,现在也有太太班,出现这样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她们?
张善若:我觉得应该加强理性的讨论,不应该有那种自动性的“膝跳反应”。不能因为这种做法跟我不一样,我不会这样做,那我就自动认为它是错的。我觉得如果能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暂时的脱离出来,大家能够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在动态的发展状态中去讨论一个现象,文化发展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经历和需求是不一样的,社会给每个人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人们想要学什么,需要获得一些什么样的知识,这些都不同,我们很难从一个外部的角度去判断。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