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科还是学理科?从“文理对立”到“知识大融通”
我们总是把专业自动划分为“文理对立”的两大阵营,中学时普遍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语,言下之意,也就将文科生自动地鄙薄了一番。在我们一贯的传统印象中,人文学科和科学曾被看作是风格迥异的两极,一个感性而缥缈,一个理性而坚硬。文科生和理科生更是宛如生活在两个世界,相互戏称对方为“文傻”和“理呆”。
甚至,这种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不仅影响着专业的研究者,更型塑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观念。就在最近,一名高考考出高分的考生因为希望报考北大考古专业而遭到许多人的质疑。“文科就业差、不挣钱”的观念颇有市场,但少有人去追问,仅仅用文科和理科这样二元的划分去界定就业前景是否合理。

《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 斯蒂芬·杰·古尔德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6月
在新近出版的《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一书中,美国科学史家斯蒂芬·古尔德就向我们揭示,人文学科与科学这两块知识疆域“本是同根生”,只是因为种种原因遗憾地渐行渐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距离开始越来越近,包括古尔德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认识到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裂痕的重要性。人类社会的知识版图正开始进入一轮“大融通”的阶段,正无限接近爱因斯坦的名言描绘的美好愿景。今天,我们希望围绕古尔德的这本新书,聊一聊人文学科与科学“相爱相杀”的历史。“文科”和“理科”之间注定是对立的吗?在当下的社会里,它们又有怎样融合的可能?
这些问题看似宏大而缥缈,但与我们大家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本文的讨论注定挂一漏万,但或许它能转换我们看待所学的专业的角度,开启我们理解所从事职业的不一样的思考。
撰文 | 刘亚光
去年暑假,因为恰好在新加坡参加活动,我参观了位于滨海湾的著名地标性建筑新加坡科学艺术博物馆。顾名思义,这座外形酷似莲花的博物馆中的展览致力于打造一个科学与艺术交汇的平台,游客们能站在光滑的屏幕前触碰缓缓飘过的古朴汉字,目睹“鸟”“木”慢慢如水墨般散开,生动地化作这个字所指代的那个图案。当游客们把自己用蜡笔填涂得五彩斑斓的交通工具放进展厅专门准备的打印机中,它们就会开动起来,出现在背后一块电子显示屏幕上呈现的巨大虚拟城市中...
博物馆的入口悬挂着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我们能体验到的最美丽的东西是世上万物的神秘,而这正是所有人文艺术和科学的起源”。作为一个高中读文科、大学继续学习人文专业的正统“文科生”,我把这句话认真地拍了下来。
作为现代科学的代表人物,爱因斯坦的看法也昭示了某种看待艺术与科学的“现代”姿态。
1
两种文化?
被夸张的“文理对立”
说到“文理对立”,历史上对此最有影响力的论述应该来自英国科学家C.P斯诺。1959年,斯诺在剑桥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在斯诺看来,彼时的英国社会文化已经分裂成泾渭分明的两极——“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他们“相互憎恶,存在一条完全无法理解的鸿沟......他们眼中对方的形象古怪而扭曲,他们的看法是如此不同,甚至在情感层面也找不到多少共同语言”。这篇演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古尔德认为,斯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他只不过是把独属于英国的地方现象扩展到了一般情形中。而事实上,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斯诺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我们把时间从斯诺发表演讲的日子往更久远处回溯,会发现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这所谓的“两种文化”可能分明就是“一种文化”。
以最古老的人文学科哲学为例,哲学学者陈嘉映在专著《哲学·科学·常识》中,将古代的哲学就称为“哲学-科学”,以体现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连续远远大于断裂。在陈嘉映看来,当我们阅读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时,我们同时在阅读科学作品和哲学作品。这些早期的思想家期待打造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们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出发,同时希望能够解读出这其中的“意义”。现代人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日月星辰的运转,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好的政治”,在那个时期,这两个问题被编织在同一个思想体系中。
这个传统在历史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及至笛卡尔和牛顿,哲学和科学依旧是携手共进的,牛顿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其最为著名的作品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命名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两种文化》 斯诺 著,三联书店 1995年2月
哲学与科学的同源性可能是一个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射到更广阔的人文学科领域,会发现同样的故事处处都在上演。
在《人文学的历史》中,荷兰学者仁博德考察了早期“语文学”发展的历史。作为一门有关文本考订和修复的古老学问,在15世纪时,这门学科致力于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考辨史料和文本的真伪。任博德特别提及了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对语文学的贡献。波利齐亚诺发展出了一种“系谱学”的考订方法,在这种方法的观照下,一组“完全一致”的史料仍然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它们处于同一系谱链的话。当甲乙丙丁四份史料呈现的叙述一致,然而如果乙丙丁全部以甲的叙述为基础,此时这些甲的“析出史料”都应该被排除。基于一份史料在系谱链中的位置,语文学不仅可以精准地辨识史料的真伪,更重要的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提出预测并进行证伪的机制。此时一份新发现的史料可以通过一种有序的模式被进行检验,并有可能支持或者反驳既有的理论。
在仁博德看来,这种“理论与经验的互动”正是15世纪的人文主义传统与科学精神相通之处。
然而,随着科学革命的进行,哲学以及传统的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分离开始加速。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现代教学与研究机构的不断完善和建制化使得学科壁垒日益森严。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描绘中,“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特征就是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这种学科专业化的细分,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社会,也是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形成紧张对立的一个大的背景。
如果现实果真如此,为何古尔德会指责斯诺的“两种文化”说以偏概全?这源于他的另一处精彩的历史爬梳。古尔德发现,虽然社会环境的变动确实影响了人文学科与科学由联合走向分裂,但这种影响并非如此夸张,在更多时候,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二分思维”建构了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的对立。古尔德的信心来源于对许多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模式的观察:人类学家施特劳斯对自然-文化的二分;哲学二元论对物质-精神的二分;埃德蒙·伯克对美-崇高的划分等,这些深深影响人类观念的思想都用“二分法”作为处理复杂世界的基本框架。

《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 仁博德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除此之外,通过细细考察那些历史上著名的“人文-科学”论战,古尔德发现这些著名论战的双方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却只不过是在先入为主地“发明”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对立。20世纪,二者之间的对立曾经表现为科学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针锋相对。
科学史家们强调科学的社会建构属性,而科学家们则强调科学的客观实在属性。1996年5月18日,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社会建构论者的主要期刊《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然而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陷阱——索卡尔作为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佯称自己已经赞同了对手的观点,并在《社会文本》发表了文章后立马撰文指出他的真实意图,使得对手颜面扫地。

电影《美丽心灵》剧照。
在古尔德看来,索卡尔的行为暴露了《社会文本》“编辑们的傲慢与懒惰,他们被来自‘另一方’旗帜鲜明的支持所诱惑”。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糊了编辑部的理智,“尽管他们对索卡尔文章中讨论的物理问题一无所知,却没有进行同行评审的标准程序”,最终催生了这场学术闹剧,“索卡尔事件”反过来也进一步巩固着这个二元对立的叙事。
人们为何会倾向于二分思维?古尔德除了是一名科学史家,同样也是一名演化生物学家,他给出的解释是:“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大脑的结构简单得多,其构造只为快速做出决定,打或逃,睡或醒,结婚或继续等待”。这种追根溯源的生物学解释是否有解释力,可能还需要打一个问号,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在当下的社会里,“文理对立”的二分思维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古尔德的研究启发我们,“文”和“理”的区隔有着许多人为建构的成分,它并不应该成为桎梏我们探寻可能性的枷锁。
在《科技公司为什么需要“人类学家”》一文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帮助我们破除了一种公众对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固有印象,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作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人类学家似乎都是一群深入热带雨林、偏僻岛屿的浪漫的探险者,与充满硬核技术元素的科技公司格格不入。然而,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特尔就曾邀请人类学家成立“人类与行为研究实验室”。如今,前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贝尔也担任英特尔公司的互动及体验研究事务总监。张劼颖认为,人类学家的介入可以让数据变“厚”,通过田野调查,人类学的思维可以挖掘出科技公司的用户生活背景的丰富性:文化传统、社会关系、身份认同、世界观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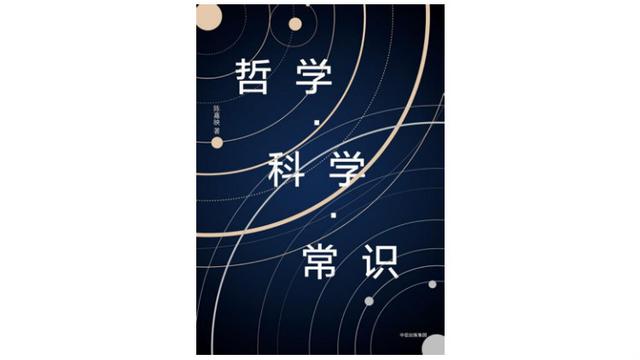
《哲学·科学·常识》 陈嘉映 著,中信出版社 2018年3月
作为一名青年人类学者,在此前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详情可见《垃圾分类为何难以贯彻?我们需要重新想象与“垃圾”的关系》),张劼颖也曾提到人类学家同样可以给当下社会中的垃圾治理问题做出贡献,比如人类学家会思考不断增长的电子垃圾背后的生产与消费问题。她认为电脑软件系统的升级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越来越‘大’,以及需要越来越高能耗、大体量的硬件配置,比如Linux这类开源系统就不同于微软这种封闭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硬件迭代的过程。“技术本身是具有许多社会效应的,比如环境效应,我觉得人类学家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技术演进的路线是一条更加环保的路线”。
当我们积极地转换视角,破除旧有的二元对立思维,努力地寻找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的“重叠领域”,会发现在共同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工程师与人类学家完全可以各施所长,文理之间的壁垒可以被打破。我们对于既有的专业和职业的想象也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2
“爱奥尼亚式的迷情”:
如何走向知识的融通?
当我们从对“文”“理”边界的固守中跳脱出来,会发现在当今社会的知识蓝图中,人文学科与科学的交融正在频繁地发生。
比如,许多古老的哲学命题正在现代实验方法的帮助下焕发新的生命力。《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伦理学史中最著名的困境之一“电车难题”的最新研究进展,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等单位的科学家合作,通过实证方法调查了人们对于电车难题不同牺牲场景的认可度。而在《正义之心:为什么我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一书中,美国学者乔纳森·海特也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探寻了人类历史中更广泛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来源。作为著名的“象与骑象人”理论的提出者,海特认为人类的心理直觉犹如那只大象,掌控着骑象人——道德判断——的大方向。在一场心理学实验中,被试者听到一段姐弟乱伦的故事,在被问及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被允许时,绝大多数的人在还没有形成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凭自己的直觉做出了道德判断。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海特建立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主义模式”,“直觉先行,推理通常在判断形成后才作出,其目的只不过是影响别人。”

《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 乔纳森·海特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这种寻求文理知识融通的理想,被美国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称作一种“爱奥尼亚式的迷情”。既然人文学科、艺术与科学的知识融通在当下已然发生,下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融通”?
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因为知识的融通与知识的消亡完全可能是一体两面。威尔逊在《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中给出了一种“还原论”的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所有有形的现象,从恒星的诞生到社会制度的运转,都基于可还原为物理定律的物质过程,无论其中的次序多么漫长、迂回和曲折”。比如,对于人类历史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心灵”问题,威尔逊主张“心灵是一连串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经验。基本上它是一种密码,代表感官印象以及对这些感官印象的记忆和幻想”,是前脑各个特定部位之内与之间错综复杂的神经活动模式构成了心灵的活动。
古尔德认为,对于心灵的哲学思辨,被威尔逊还原为一种生物学的解释。对于这种知识融通的路径,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在古尔德看来,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的知识绝不可能运用还原论的原则被融入到科学之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人文学科不仅仅处理事实问题,同样也处理“应当”的问题。将人类的道德原则还原为生物演化论可能可以部分解释道德“是什么样”,但却并不能够帮我们回答“道德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如果弑婴绝对符合达尔文式的生物学理由,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此的道德争议和学理探讨可以止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威尔逊式的融通在古尔德看来,只会抑制人文学科的潜力,他提出一种“一视同仁的融通”作为替代方案。这种融通方案强调“理解这两个领域对任何智识和精神上都‘’完满”的生命的绝对必要性,并力图强调、滋养无数世纪重叠且有着共同关切的领域。”一言以蔽之,古尔德希望能够以回答人类重要的问题为导向,发挥人文学科与科学各自的长处。

电影《美丽心灵》剧照。
这听起来也是一个过分理想化的方案,但类似的实践也已经开始起步。比如,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工开万物》一书的作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Dagma Schafer)曾于去年受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汇报过她应用“数字人文”进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运用LoGaRt工具,薛凤教授将全部已经数字化的地方志整合为一个大的数据库,据此开展了对宋元两朝桑灾时空差异的大规模分析。不过,薛凤教授也强调了对数据“质性意义”解读的重要性,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应该是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良性互动。虽然“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的研究领域仍然面临诸多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似乎大体上也在朝着古尔德所期待的知识融通方向迈进。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古尔德最终给出了一个融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具体方法论。我们大概都会承认,即使科学与人文、艺术曾经是同源同生,但历经千年,人类知识体系的内容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再希望回到那个将日月星辰与政治制度统一起来的时代已无可能。另一方面,所谓“求同存异”的融通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显得过于模糊。正如同古尔德向读者们揭示了有关二者对立的“二分法”只不过是被建构出的神话,他对于“融通”的倡导更重要的其实是建构出一套二分法之外的重新审视人类知识的观念。

《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 爱德华·威尔逊 著,中信出版社 2016年10月
3
教育中的“文理融通”:
跨学科的难题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了:开拓人类知识的边疆听起来似乎过于“阳春白雪”,这和我们并不专门从事研究的普通人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其实,知识的融通不仅仅关乎人类知识的生产与创新,更通过教育的渠道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人类知识的过分分化,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一书中,安德森诟病于工业革命以后自然科学精细化发展的需要使得大学的学科加速专业化与职业化,这割裂了各个学科之间沟通的话语,窒息了思想的潜力。与之相反,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恰恰得益于他跨学科的阅读与知识的融会贯通,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奥尔巴赫的《摹仿论》都曾在不同层面上给予他启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2015),知名学者,民族主义研究、比较政治学、东南亚研究专家。代表作包括《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等。
安德森不仅认为打破知识壁垒的跨学科教育会真正激发一个人的思想活力,他还给出了教育领域“知识融通”的具体方案,比如在课程中增加多学科的参考书目、强化任何一个科目中“思想史”部分的教学、倡导在写作中省去不必要的专业化术语、力求通俗化等。
不过,虽然安德森强调跨学科,但他也承认各个学科内部确有自身的一套相对稳定的学科逻辑和规则。古尔德“求同存异”的知识融通理念希望能够实现知识壁垒的打破,却又不至于像威尔逊的方案那样消弭掉学科的独立性,这究竟如何落实于教育中其实始终是一个困扰巨大的难题,而这些思想家提出的理想化改革方案往往也需要更宏大的制度层面的支撑。
这一难题也堪称围绕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条主线。美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设起于对德国式的专业化、研究型大学理念的借鉴,然而,历代的美国教育思想家们也都不希望摈弃强调综合素质培育的文理学院传统。
19世纪末,查尔斯·艾略特校长在哈佛大学开展的“自由选课”制度,主张放弃一切限制和组织,完全根据学生意愿自由选课。艾略特希望这既能够保证学生可以接触足够宽广的知识面,也可以让他们根据自身的偏好选择专业的发展路径。然而这样的模式却迎来了猛烈的批评,许多主张通识教育的学者认为学生选课依然按照自己的喜好而缺乏系统性的规划,这样的自由选课仍然只能为他们带来碎片化的知识。虽然此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中,教育家们努力地克服这一问题,但正如学者李猛对此的评论,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课程中梳理教育的线索、铺设知识的阶梯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李猛:《在研究与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学院问题》)。

《椰壳碗外的人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谈论的实现知识融通的难题还是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部,如果换成古尔德、威尔逊等人所谈论的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怎样真正在教育中地实现知识的有机融合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难题。
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法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哲学的重视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关注。法国的高考首日都会进行哲学考试,考生会根据自己报考专业的类型分为不同的组别并分配到不同的题目,如文科组、经济社会组、科学组和技术组等,这些题目本身既属于哲学的基础问题,同时也照顾了各个组别的特性。例如2019年的法国高考哲学试题中,文科组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是否可以逃脱时间”、“一件艺术作品有什么作用?”,而科学组的考试题目则要求解释弗洛伊德在《幻象的未来》中的一句话。而回到中国的语境,许多大学近年来也做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比如,武汉大学于2018年开始开设《人文社科经典导引》、《自然科学经典导引》两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基础通识课程,学生可同时精读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经典。
1869年,艾略特在接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讲道:“究竟语言、哲学、数学还是科学提供了最佳的心智训练?通识教育主要应该是人文的还是科学的?这样一些无穷无尽的争论,今天对我们来说,毫无实践教益。我们的大学不承认文学与科学有任何真正的对立,也不赞同在数学与古典、科学或玄学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狭隘选择。这些我们都要,而且要达到最好。”
这是一个教育家理想主义式的宣言。尽管如何实现知识融通的问题看似依旧悬而未决,但一百年后,这项事业依然值得被继续。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乎人类的知识能够更好地解释“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更关乎每一个人能通过教育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作者|刘亚光
编辑|张婷
校对|张彦君
来源:新京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