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Pi的奇幻漂流(十)

第二部 太平洋
第37章
船沉了。它发出一声仿佛金属打嗝般的巨大声响。船上的东西在水面上冒了几个泡泡便消失了。一切都在尖叫:海,风,我的心。在救生艇上,我看见水里有个东西。
我大叫道:"理查德·帕克,是你吗?我看不清楚。噢,雨快停吧!理查德·帕克?理查德·帕克?是的,是你!"
我能看见他的脑袋。他正挣扎着不让自己沉下去。
"耶稣啊,圣母马利亚,穆罕默德和毗湿奴,看见你真好,理查德·帕克!别放弃啊,求求你。到救生艇上来。你听见哨声了吗?瞿!瞿!瞿!你听见了。游啊,游啊!你是个游泳好手。还不到一百英尺呢。"
他看见我了。他看上去惊慌失措。他开始朝我游过来。海水在他四周汹涌地翻卷着。他看上去弱小又无助。
"理查德·帕克,你能相信我们遇到了什么事吗?告诉我这是个糟糕的梦。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告诉我,我还在"齐姆楚姆"号的床铺上,正翻来覆去,很快就会从这场歷梦中醒来。告诉我,我还是幸福的。母亲,我温柔的智慧守护天使,你在哪里呀?还有你,父亲,我亲爱的经常发愁的人?还有你,拉维,我童年时代倾慕的英雄?毗湿奴保全我吧,安拉保护我吧,耶稣救救我吧,我受不了了!瞿!翟!翟!"
我身上没有一处受伤,但我从没有经受过如此剧烈的痛苦,我的神经从没有被如此撕扯过,我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疼痛过。
他游不过来的。他会淹死的。他几乎没在前进,而且他的动作软弱无力。他的鼻子和嘴不断地浸到水下。只有他的眼睛仍然注视着我。
"你在做什么,理查德·帕克?难道你不热爱生命吗?那就一直游啊!瞿!翟!瞿!踢腿!踢啊!踢啊!踢啊!"
他在水里振奋起来,开始向前游。
"我的大家庭怎么了?我的鸟、兽和爬行动物?它们也都淹死了。我生命中每一件珍贵的东西都被毁了。而我却得不到任何解释吗?我要忍受地狱的煎熬却得不到天堂的任何解释吗?那么,理性的目的是什么呢,理查德·帕克?难道它只在实用的东西上——在获取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时候闪光吗?为什么理性不能给我们更伟大的答案?为什么我们可以将问题像网一样撒出去却收不来回答?为什么撒下巨大的网,如果没有几条小鱼可抓?"他的脑袋几乎要沉到水下去了。他正抬着头,最后看一眼天空。船上有一只救生圈,上面拴着一根绳子。我抓起救生圈,在空中挥舞着。
"看见这只救生圈吗,理查德·帕克?看见了吗?抓住它!嗨唷!我再试一次。嗨唷!"
他离得太远了。但是看见救生圈朝他飞去,他有了希望。他恢复了生机,开始有力地拼命地划水。
"这就对了!一,二。一,二。一,二。能呼吸就赶快呼吸。小心海浪。瞿!瞿!瞿!"
我的心冰凉。我伤心难过极了,但是没有时间吓得发呆。我在受到惊吓的同时还在行动。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不愿放弃生命,不愿放手,想要斗争到底。这样的决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
"难道这不是很有讽刺意义吗,理查德·帕克?我们在地狱里,却仍然害怕不朽。看看你已经离得多近了!瞿!瞿!瞿!快啊!快啊!你游到了,理查德·帕克,你游到了。抓住!嗨唷!"
我用力把救生圈扔了出去。救生圈恰好掉在他面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前抓住了它。
"抓紧了,我把你拉上来。别放手。你用眼睛拉,我用手拉。几秒钟后你就会到船上来了,我们就会在一起了。等一下。在一起?我们要在一起?难道我疯了吗?"
我突然清醒过来,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我猛地一拉绳子。
"放开救生圈,理查德·帕克!放手,我说。我不要你到这儿来,你明白吗?到别的地方去吧。让我一个人待着。走开。淹死吧!淹死吧!"
他的腿用力踢着。我抓起一只船桨。我用桨去戳他,想把他推开。我没戳到他,却把桨弄丢了。
我又抓起一只桨。我把它套进桨架,开始用力划,想把救生艇划开。但我却只让救生艇转开了一点儿,一端靠理查德·帕克更近了。
我要打他的脑袋!我举起了桨。
他的动作太快了。他游上前来,爬到了船上。
"噢,我的上帝啊!"
拉维是对的。我真的是下一只山羊。我的救生艇上有了一只浑身湿透、不停颤抖、淹得半死、又咳又喘的3岁成年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在油布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看到我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耳朵紧贴着脑袋两侧,所有的武器都收了起来。他的脑袋和救生圈一样大,一样的颜色,只是有牙齿。
我转过身,从斑马身上跨过去,跳进了海里。
第38章
我不明白。许多天来,船一直在前进,它满怀信心,对周围环境漠不关心。日晒,雨淋,风吹,浪涌,大海堆起了小山,大海挖出了深谷一齐姆楚姆都不在乎。它以一座大陆的强大信心,缓缓前进着。
为了这次旅行,我买了一张地图;我把地图钉在我们船舱里的软木告示板上。每天早晨,我从驾驶台得知我们的位置,然后用橘黄色针头的大头针把位置标在地图上。我们从马德拉斯出发,越过孟加拉湾,向南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新加坡,向北朝马尼拉开去。我喜欢在船上的每一分钟。船上的日子令人兴奋。照料动物使我们整日忙碌。每天晚上我们倒在床上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在马尼拉停留了两天,为了补充新鲜食品,装新的货物,另外,我们听说,还要对机器做常规维修。我只注意前两件事。新鲜食品是一吨香蕉,而新的货物,一只雌性刚果黑猩猩,是父亲独断专行的结果之一。那吨香蒸上布满了黑色大蜘蛛,足有三四磅之多。黑猩猩就像个头小一些、瘦一些的大猩猩,但长相要丑一些,也不像它的表亲那样忧郁温柔。黑猩猩碰大黑蜘蛛的时候会耸耸肩,做个鬼脸,像你我一样,然后它会用指关节将蜘蛛压碎,这却不是你我会做的事。我觉得香蕉和黑猩猩比船腹里那些吵嚷肮脏的奇怪的机械装置有趣多了。拉维整天待在机器旁边,看船员们干活。机器有些问题,他说。修理有问题吗?我不知道。我想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答案成了一个谜,正躺在几千英尺深的水底。
我们离开马尼拉,驶进了太平洋。进人太平洋以后第四天,在去中途岛的途中,我们沉没了。在我的地图上被大头针戳了一个洞的位置,船沉没了。一座大山在我眼前坍塌了,消失在我脚下。我周围全是消化不良的船只吐出来的东西。我的胃感到恶心。我感到震惊。我感到心里一片空落落的,接着又被沉寂填满。很多天以后,我的胸口仍然因痛苦和恐惧而感到疼痛。
我想发生了一次爆炸。但我不能肯定。嫌炸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发生的。爆炸声将我惊醒。这艘船并不是一艘豪华邮轮。它是一艘肮脏的辛苦的货船,它不是为付钱乘船的乘客或为了让他们舒适而设计的。任何时候船上都有各种噪音。正是因为这些噪音的音量一直保持不变,我们才像婴儿一样睡得很香。那种寂静什么都不能打破,无论是拉维的鼾声还是我的梦话。因此,如果的确发生了爆炸的话,那爆炸声就不是一种新的噪音。那是一种不规则的噪音。我突然惊醒,就好像拉维在我耳边吹炸了一只气球。我看了看表。凌晨四点半刚过。我探出身子,朝下铺看去。拉维还在熟睡。
我穿上衣服,爬下床去。通常我睡得并不沉。通常我会接着睡。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起来了。这似乎更像拉维做的事情。他喜欢召唤这个词;他会说冒险活动在召唤。"然后在船上四处巡视。声音又恢复了正常,但是也许有了一种不同的音质,也许变得低沉了。
我摇摇拉维。我说拉维!刚才有个奇怪的声音。我们去探险吧。"
他睡意朦胧地看着我。他摇摇头,翻过身,把被单拉到下巴。噢,拉维!
我打开船舱门。
我记得自己沿着走廊走。无论白天黑夜,走廊看上去都一个?
样。但我能在心里感到四周的夜色。我在父亲和母亲的门口停下脚步,考虑要不要去敲门。我记得自己看了看表,决定不去敲门。父亲喜欢睡觉。我决定爬到主甲板上,迎接黎明。也许我会看见流星。我边爬楼梯边想着这个,想着流星。我们的船舱在主甲板下面两层。我已经把奇怪的声音忘了。
推开通向主甲板的那道厚重的门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外面的天气。那能算是暴风雨吗?当时确实在下雨,但雨并不大。当然不是你在季风季节看见的那种大雨。风也在刮。我想有几阵狂风能把伞掀翻了。但是我在风雨中走过,并没有什么困难。大海看上去波涛汹涌,但是对旱鸭子来说,大海总是使人激动,令人生畏,美丽又危险。海浪涌来,白色的泡沫被风卷起来,吹打着船侧。但是我在其他时候也见过这样的景象,船并没有沉。货船是一种巨大的稳定的装置,是工程学了不起的设计。货船的设计可以让它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漂浮在海上。像这样的天气当然不会让船沉没的吧?嗨,我只需关上门,暴风雨就会消失不见了。我走到甲板上。我抓住栏杆,面对着自然环境。这就是冒险。
"加拿大,我来了!"我大喊,雨水将我淋得透湿,让我感到冷飕飕的。我感到自己很勇敢。天还黑着,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亮?可以让我看清楚了。那是地狱之光。大自然可以上演令人激动的剧目。舞台那么广阔,灯光那么夸张,临时演员多得不可胜数,制造特技效果的预算完全没有限制。我前面是风与水的奇观,是感官的地震,甚至好莱坞也编排不出。但是地震在我脚下停止了。我脚下的地是坚实的。我是安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的观众。
我是在抬头看见桥楼上的救生艇时才开始担心的。救生艇并不是垂直地悬挂着。它面朝船倾斜,与吊艇柱形成了一个角度。我转过身,看看自己的手。指关节发白。我并不是因为天气恶劣才紧紧抓住栏杆的,而是因为如果不抓紧我就会跌倒。船在朝另一面,即朝左舷倾斜。倾斜度虽然不大,却足以让我感到吃惊。当我朝船外看去时,发现斜坡不再陡直。我能看见巨大的黑色的舷侧。
一阵寒颤传遍我全身。我肯定那确实是一场暴风雨。该回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松开手,匆匆走到船壁,走过去把门拉开。
船里有噪音。机器构造的低沉呻吟声。我绊了一下,摔倒了。没有受伤。我爬了起来。我扶住栏杆,一步四级,朝楼梯井下跑去。刚跑下一层,我就看见了水。很多水。水挡住了我的路。水像喧闹的人群一样从下面涌上来,汹涌着,翻滚着,冒着泡泡。楼梯消失在了黑暗的水中。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水是怎么回事?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仿佛被钉在了原地,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疑惑,不知道下面应该做什么。我的家人就在下面。
我跑上楼梯,跑到了主甲板上。天气不再令我感到乐趣。我非常害怕。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船倾斜得很厉害。纵的方向也不平。从船头到船尾出现了明显的倾斜。我朝船外看去。水看上去离我们没有八十英尺。船在沉。我简直无法理解。这就像月亮着火一样令人无法相信。
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都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在靠近船头的地方,我看见几个人在黑暗中奔跑。我想我还看见了动物,但是我把这当做是雨和影子造成的幻觉,并没有在意。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把分隔栏顶上的活板抽开,但是在任何时候动物都是不能离开笼子的。我们运的是危险的野生动物,而不是农场上的家畜。我想我听见有人在叫喊,就在我头顶上,在桥楼上。
船晃了一下,发出了那种声音,那种巨大的金属打嗝般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人类和动物抗议即将到来的死亡而一每
尖叫吗?是船自己正在完蛋吗?我摔倒了。又爬了起来。我再一次朝船外看去。海面在上升。海浪正向我们靠近。我们正迅速沉没。
我清楚地听见猴子的尖叫声。什么东西正在摇晃甲板。一只白肢野牛——印度野牛——突然从雨中冲出来,从我身边冲过去,发出轰隆隆的声响。它受了惊吓,变得狂怒,无法控制。我看着它,惊愕不已。天啊,究竟是谁把它放出来了?
我跑上楼梯,朝桥楼跑去。高级船员就在那儿,他们是船上惟一会说英语的人,是我们命运的主宰,是能纠正这个错误的人。他们会解释一切的。他们会照顾我和我的家人。我爬上中间的桥楼。右舷没有一个人。我跑到左舷。我看见三个人,是普通船员。我跌倒了。又爬起来。他们正在朝船外看。我叫起来。他们转过身来。他们看看我,又互相看看。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迅速朝我走来。一阵感激和宽慰涌上我心头。我说感谢上帝我找到你们了。发生了什么事?我很害怕。船底有水。我很担心我的家人。我去不了我们船舱的那层了。这是正常的吗?你们认为……"
这些船员中的一个把一件救生衣塞进我怀里,大声用中文说了些什么,我的话被打断了。我看见救生衣上挂了一只橘黄色的哨子。他们正用力朝我点头。当他们用强有力的臂膀抓住我,把我举起来时,我没觉得什么。我以为他们是在帮我。我太信任他们了,当他们把我举到空中时,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当他们把我从船上扔出去时,我才感到怀疑。
第39章
我像跳蹦床一样,弹落在半卷起来盖住船下面40英尺的救生艇的油布上。我没有受伤,这真是个奇迹。我把救生衣弄丢了,但哨子还在我手里。救生艇被放下去一半,挂在那儿。它朝远离吊艇柱的方向倾斜着,在距离海面20英尺的地方,在暴风雨中荡来荡去。我抬起头。两个船员正低头看着我,发疯一般指着救生艇大叫。我不明白他们想要我做什么。我以为他们会跟在我后面跳进来。但他们却掉过头去,一脸的恐惧。这时这只动物在空中出现了,用赛马一般优雅的动作跳了下来。斑马没有跳到油布上。这是一只雄性格兰特斑马,体重五百多磅。它哗啦一声重重摔在最后面一张坐板上,砸碎了坐板,把救生艇砸得左右摇晃。它叫出了声来。我以为会听见类似于驴叫或马嘶的声音。完全不是。只能说那是一阵吠叫,夸—哈—哈,夸—哈—哈,夸—哈—哈,声音因为痛苦而极其尖利。这只动物的嘴张得大大的,站得笔直,浑身发抖,露出了黄色的牙齿和暗粉色的牙床。救生艇掉了下去,我们撞进了沸腾的海水。
第40章
理查德·帕克没有跟在我后面跳进海里。我准备用来做棍棒的船桨漂在水上。我抓住桨,同对伸手去抓救生圈,现在救生圈里已经空了。在水里太可怕了。水又黑又冷,汹涌澎湃。我感到仿佛自己就在一座正在碎裂的井底。海水不断打在我身上。刺痛了我的眼睛。把我往下拉。我几乎不能呼吸了。如果没有救生圈,我连一分钟也坚持不下来。
我看见在离我15英尺的地方有一只三角形的东西正划破水面。那是一只鲨鱼的鳍。一阵又冷又湿的可怕赓颤在我的脊椎蹿上蹿下。我以最快的速度朝救生艇一端,就是仍然盖着油布的那一端,游过去。我用胳膊撑住救生圈,直起身子。我看不见理查德·帕克。他不在油布上,也不在坐板上。他在船底。我又抬起身子。那飞快的一瞥只让我看见斑马的头在船的另一端猛烈地来回转动着。当我跌回水里时,另一只鲨鱼的鳍就在我面前划过。
鲜艳的橘黄色油布被一根结实的尼龙绳拉住,绳子穿过油布上的金属索环和船另一侧的钝钩子。我碰巧在船头旁边踩着水。油布经过艏柱——艏柱有一个很短的突出的前端,如果长在脸上,就是翘鼻子——的地方没有在船的其他地方系得牢。就在绳子从艏柱一侧的钩子穿进另一侧的钩子的地方,油布有些松。我举起船桨,朝这处有些松的地方,这处救命的细节,捅过去。我尽量把桨往里捅。现在,救生艇的船头突出在波浪之上了,虽然有些歪。我让自己立起来,双腿环绕住船桨。桨柄顶起了油布,但是油布、绳子和桨都支持住了。我已经离开了水面,尽管随着海面的起伏,我与海水之间的距离只有2英尺或3英尺。大浪的浪尖还在不断地拍打着我。
我独自一人,孤立无助,在太平洋的中央,吊在一只船桨上,前面是一只成年老虎,下面是成群的鲨鱼,四周是狂风暴雨。如果我用理性思考自己的前途,就一定会放弃努力,松开船桨,希望自己在被吃掉之前能被淹死。但是我不记得在相对安全的最初几分钟里我有过一点点想法。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天已经亮了。我紧紧抓住船桨,就那么抓着,只有天知道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充分利用了救生圈。我把救生圈从水里提上来,把船桨从中间穿过去。我让救生圈沿着船桨向下滑,直到套在我身上。现在我只需要用腿勾住船桨就行了。如果理查德·帕克出现了,从船桨上掉下去会更加尴尬,但是一次只能经历一种恐惧,我选择太平洋而不是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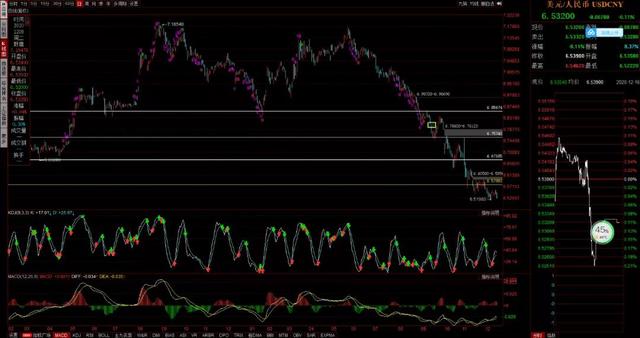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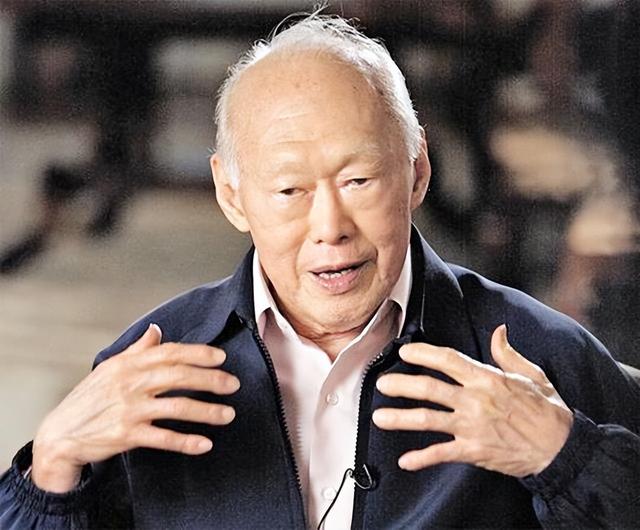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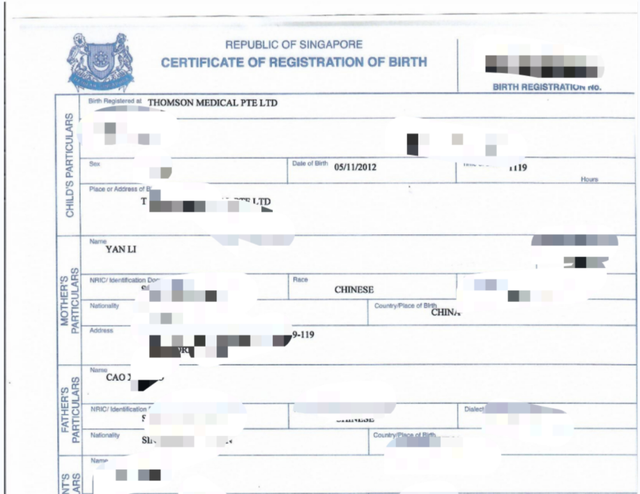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