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评《威权式法治》︳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新加坡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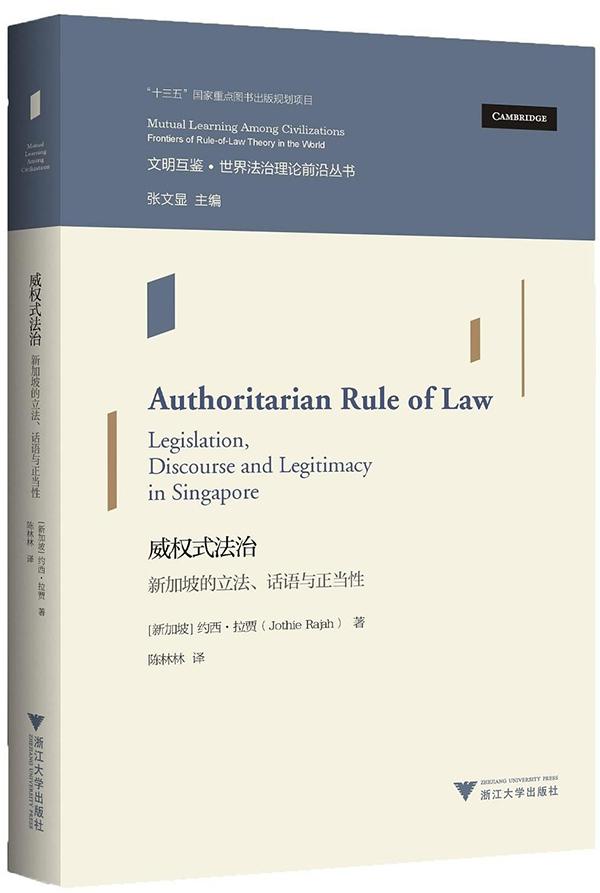
《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 [新加坡]约西·拉贾(Jothie Rajah)著,陈林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343页,78.00元
和俗话所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很相近的是,一个外来者往往能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能发现本地的文化特色。《威权式法治》这本书也是这种情况,一个来自于印度的法学生以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求学的意外遭遇,引发了对新加坡法治的兴趣,开启了自己对新加坡法治的研究之旅,并且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作为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的职业体会中继续这项研究,得以做出这项研究成果。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的成功典范,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18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达到了六点四六万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七;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五点五五万美元,全球排名第六。在社会政治上,新加坡一直以其政府的高效而廉洁闻名,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按照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历年数据,新加坡都一直稳居在前五位。
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界,对这个城市国家政治体制的评价却争议很大。根据本书作者的统计与罗列,新加坡政治体制在西方国家法学界得到的各种评价有十四种之多:“威权式的”“半威权式的”“柔性专制”“亚洲式民主”“准民主”“非自由主义民主”“社群主义民主”“专政”“虚假式民主”“有限民主”“强制式民主”“专制政府”“开明的非民主政府”“强权选拔式的威权政府”。同样,新加坡政府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法治评价,在西方国家的法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本书的评价就属于其中较为主流的一种:新加坡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
作者在本书开始时就明确他所谓的“法治”的定义:自美国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后,法治“其核心要领是必须维护和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并信奉法律的统治,“相信对政府应当施加一些不容违反的根本性法律约束”。由此作者认为:“新加坡政府既不遵循前自由主义有阶段就存在的对政府的约束,也不认为个人权利是不容侵犯的。新加坡政府挪用并阉割了威斯敏斯特式制度和意识形态(指英国式政治),以使它们(指法律)成为威权政府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制约手段’。”作者进一步指出,新加坡政府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通过攫取话语权,不断渲染新加坡立国的脆弱性——体量很小的城市国家,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袭扰等等——成功地将法治转变为政府施政的完美工具。
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分析了新加坡立国之初的法律体系建设,认定在建国时,当时的国家领导阶层就有意识地改造了原来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英国法传统,尽可能地剔除了其中的自由主义内容。比如新加坡官方法律体系中剔除了殖民地时期的“习惯法”,法院的判决不接受原先汉明帝时期法院接受的一些民族“惯例”作为依据。新加坡政府还解散了原先殖民地时期存在的各种自治性社团,从而能造就“一个静默且顺从的民间社会”。
为了证明新加坡政府将西方式法治“阉割”成了政府实行统治的“法制”,作者采用了立法史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了新加坡的几部法律的立法及实施过程,来论证这一基本观点。
作者选中的第一部法律,是新加坡在1966年通过的《惩罚破坏性行为法》。这部法律以恢复殖民地时代曾经存在、后来被废除的鞭刑而闻名,至今犹是新加坡法律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作者认定这部法律开始制定的实际目的,是试图制止“社阵”等左翼党派团体的政治活动,将张贴涂写标语、展示图片旗帜、污损公私财物等行为,尤其是成年人唆使未成年人实施的此类行为,都上升到“反国家行为”高度,因此对指使者以及实施者都要施以“棍棒教育”。犯此罪者不得保释,原来按照《轻罪条例》拘禁一周罚款五十元的处罚加重到处鞭刑三至八下、拘禁最高三年、罚款最高两千元。作者还列举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适用该法的一些著名案例。到了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该法律名称上去掉了“惩罚”二字,主要针对的也不再是左翼社会运动,而是笼统的“反社会共同体”的个人行为。作者详细分析了1994年发生的美国人费伊等三名青少年污损他人汽车而遭到逮捕法办、费伊被处以鞭刑的案件。认为这件案件显示出新加坡警方、媒体、法院、政府高度一致地将这几个青少年的恶作剧(十天内对十八辆汽车喷漆)渲染为持续的、蓄意的、“非常严重的罪行”。作者引用了当时担任资政的李光耀、担任总理的吴作栋两位领导人就此案件的言论,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导致的破碎的家庭、放任纵容、缺乏规训视为新加坡国家的危险源头,需要以《破坏性行为法》的鞭刑来阻止,并防止社会道德的衰败。
作者选择的第二部法律是1974年的《报业与印刷新闻业法》。同样从立法的历史背景分析出发,作者认为这部法律是1971年以后新加坡政府逐渐收紧媒体的言论控制,分化打击殖民地时期保留下来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民间媒体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一家老牌的民营报纸《南洋商报》就新加坡政府的中文教育政策提出批评,引发关于中文教育的社会讨论。作者认为新加坡政府就此怀疑这家报纸“煽动华人种族意识”,危害新加坡社会的稳定,最后对这家报纸的四名高管实行了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而另外两家具有国外股份的报纸也被怀疑为外国势力代言,政府对之进行了处罚。由此1974年制定的这部法律,规定所有媒体的股份必须区分为普通股和管理股,普通股一股一票,管理股一股二百票。但管理股的持有者必须要经过政府批准。实际上是将殖民地时期媒体的申报备案制度改为政府审批制度,从而有效地将报业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作者选择的第三部法律是1986年的《法律职业法(修正案)》。新加坡律师业比其独立国家的历史还要悠久,很早就有律师执业的有关法律,国家领导人李光耀本人就是一名著名的律师。但新加坡建国后,律师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群体,几乎从未参与社会公共议题的讨论。1969年新加坡政府准备取消陪审团审理制度,在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法》时,律师公会对政府的草案提出了批评,这件事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立法机构遴选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李光耀亲自出马(听证会向律师公会提出的三百五十个问题中,李光耀提出了两百五十七个),以指控盘诘的态度,严厉指责律师公会理事会当时负责人马绍尔试图将律师公会的职能政治化,并且否认律师公会提交的意见是集体讨论结果,认为其是马绍尔别有用心的个人行为。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本身反而没有讨论。这个事件在当时也没有得到公开的报道。1971年马绍尔在为《南洋商报》的四名高管辩护时,因为将辩护词提交给了海外媒体及国际组织,遭遇了纪律处分,被停职半年。1986年开始修订《法律职业法(修正案)》,律师公会再次提出了意见,而政府的对策是再次召开听证会,不是就法律的草案,而是就律师公会提出的意见进行审问式的质询,并进行了电视转播。听证会上向律师公会提出了一千六百零九个问题,其中李光耀亲自提出的就有一千一百三十九个,仍然将律师公会的立法意见视为起草者的个人行为,是对国家稳定的威胁。律师公会理事会的四名成员包括当时的会长萧添寿后来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其中两人被指控参与了“马克思主义阴谋”活动而遭逮捕,在电视上认罪后才得以保释。作者梳理了这两场听证会,认为这样的听证会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就是教育新加坡人民,只有政府能够代表社会公众,没有什么其他的团体身份和团体责任可以来对公共事务评头论足。由此形成的《法律职业法(修正案)》也就完全排除了律师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发言权。

作者选中的第四部法律是1991年公布的《维护宗教和谐法》。作者认为这部法律出台的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所谓“马克思主义阴谋案件”。这是一个由政府指控的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松散团体,成员都是接受过英文高等教育的职业人士,包括了律师以及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由此新加坡政府认定有必要制定专门法律来规范宗教界人士。通过这部法律,授权内政部长可以对“激发他人对总统或政府的不满情绪”“引发不同宗教团体间的敌意、怨恨、憎恶或对抗情绪”的任何人发布限制令,限制其人身自由。
作者选择评论的第五部法律,是2009年的《公共秩序法》。作者同样认为这部法律的起因也是一次挑战政府的事件。2006年9月在新加坡召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的政治反对派人士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游行,试图引起国际关注。同样的情况是在2007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峰会,有一些国际反对缅甸军政府的非政府组织与新加坡的反对派人士合作,组织了抗议活动。新加坡政府为此决定制定新的法律来消除针对公共批评的法律漏洞。这项法律在2009年4月得到通过,规定凡是一人以上的任何聚会和集会,只要其目的是“(1)支持或反对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府的意见或行动;(2)宣传一项事业或运动;(3)纪念或庆祝任何活动”,就必须事先获得警察的许可。作者认为这项法律将前四部法律的精神发扬光大,“是新加坡政府用‘法制’重塑‘法治’的最新表现”。
在本书的总结部分,作者再次强调了新加坡法治的非自由主义特性,认为新加坡政府宣称自己的法治来源于英国法,是戴雪式的法治。但是实际上其沿袭的却是英国的殖民地法,将新加坡人民当作了“始终被殖民化的公民”,而将法律当作了一种执政者的“治理术”。他分析了前述几部法律颁布的时机,都处在大选前夕。而且每次大选前,政府都会根据《内部安全法》剥夺一些人士的人身自由,通过渲染社会不稳定因素,来“优化和强化政府指导过程”,从而将政府本身“塑造为唯一有效的超验力量”。
从以上的介绍,读者可以发现,作者进行的不是一般法律史的法条研究,而是着重从立法的历史背景,立法的目的与理念,尤其是立法前后的重大案件的分析来加以阐述。由此避免了法条研究会带来的大量的术语套话,除了法律专业人士外,一般读者也能够顺利阅读。典型案例的说明也相当精彩,能够很好的加深读者的印象,加强了作者观点的说服力。
阅读全书,读者会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作者完全是在以批评的态度在开展这项研究。俗话说批评总是最容易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捷的研究。正因为新加坡政府一贯以法治国家自诩,所以作者集中揭示实际上新加坡的法治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由此作者忽略了其他的一些研究的角度。比如在立法的研究中,仅仅揭示政府的立法动机,没有进一步去分析,这种动机有没有实际的社会需求?政府所渲染的社会危机是否真实存在?满足社会的需求或者对付社会危机这项立法是否是最好的途径?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读者也许会觉得作者有点缘木求鱼,将法治当作一种先验的神圣的教条来一一对照新加坡。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西方法学界相当流行的,中国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教条主义”。如果作者能够结合原来同样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或者印度国家的法治状况来进行对比,或许能够更好的凸显新加坡法治的特色,这个研究成果或许也就更容易被理解。
好的阅读体验应该是一种探索,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发现问题、激发更多的阅读与体验。本书可以说是令人信服地揭示新加坡法治的实质是将法治当作了政府施政的工具、即使施政中可能损害民众的个人权利也在所不惜,从而不是制约而是扩大了政府的权力。那么读者自然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很少受到法律制约也不受媒体批评的政治体制,没有陷入腐败的深渊?为什么在政府强大影响下的司法体制,被限制提出公共问题的律师,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能够公正公平并且高效地处理社会纠纷?法治究竟仅仅是一种应然的教条,还是可以视为一种实然的社会调节方式?我想读者在阅读完本书后一定会有更多的探索欲望。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