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门学科,3间大学,45年炼成新加坡开山宗师

前言
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当年简称新大)任教,最初签了三年聘约,后来续约三年,之后又续约三年,然后就留下来。如今算来竟是45年了!这45年来,一直在教学研究的学术园地里努力做个尽职的园丁。70年代加入第一代社会学的团队,从当年的武吉知马校区到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肯特岗校区,开拓新加坡社会基础研究。1992年应南洋理工大学詹道存校长之邀,西迁云南园,创办传播学院。2003年又应南大第二任校长徐冠林之请,筹划成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协助南大转型为综合性大学。2008年加盟新跃大学(现称新跃社科大学),于2012年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开始回归文化原乡的寻根之旅。
回顾这45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
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荫下听雨的时候了。当然,南国的赤道雨,不似南宋江南春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词《虞美人》】。回首前尘,有风雨相伴的日子,更不缺那雨后的彩虹。南国杏坛听雨,有回音,有回响,仔细聆听,或许还有羽音阵阵、余音袅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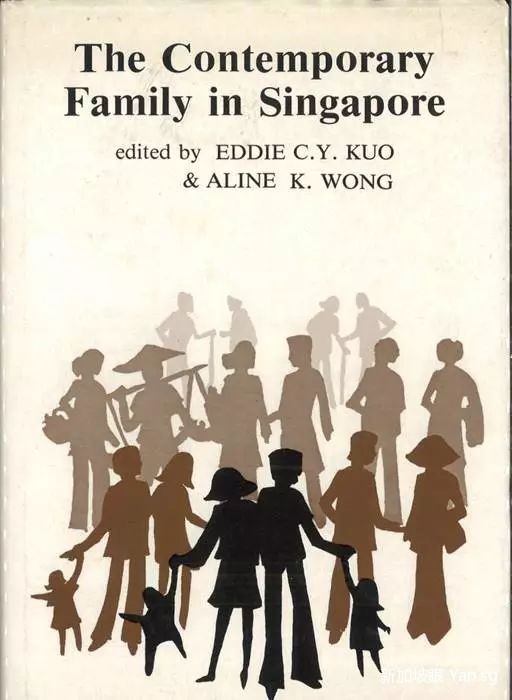
初识新加坡
(一)
1973年6月,我和妻儿一家四口,告别美国威斯康辛州清水市(威斯康辛大学清水校区所在地Eau Claire ),启程回归亚洲。第一站到蒙坦那州波兹曼(Bozeman),探望海菲妹一家,也一响夙愿,畅游黄石公园;然后经过洛杉矶,檀香山,旧地重游,探望老友。最后经东京回到台北,停留两周,拜望双亲四老以及老同学老友。六月底经香港于六月29日飞抵新加坡巴耶里巴机场。(当年没有长途直航客机,短程转机乃是常态。)
代表学校来接机的是社会系同事陈寿仁,是系里一位资深(也是当时唯一的)本地学者,后来共事多年,也合作了几个研究项目。
当晚寿仁把我送到校园旁Nassim路口的大学招待所,那是二战前的老建筑,相对简陋,晚上挂蚊帐点蚊香,在蛙鸣和虫声中入眠。次日早起推门而出,顿觉青天白云鸟语花香,好一片南国风光。原来这武吉知马校园,紧邻新加坡植物园(201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而社会系馆所在,就在隔Cluny Road山坡上独立的House 11(11号楼),是一栋1920年代的老建筑。据说这曾是莱佛士书院时代副校长的住宅,是座独立洋房,屋后有仆人(想来包括帮佣,司机,厨子等)住处以及厨房车库等,看来风水不错。只可惜这片旧校区多年前已经划归给植物园,第11号楼也早已拆除,不见踪影了。

武吉知马校园
7月2日星期一,我依约到社会系报到。按在美国工作的习惯,我准时8点到校,第一个见到的是同事简丽中。据她后来的回忆,我当时穿了一件紫色无领的T恤。她批评我说:哪有人第一天到大学报到这样穿着的!我回想起来,也不能了解当年为何如此随便。其实我无意冒犯,只是在美国校园随意惯了,真没有用心。
简丽中来自香港,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社会学博士。当年柏克莱是美国自由主义大本营,新大聘用她,我觉得是开放的象征。在第11号楼,我和简丽中办公室相邻,墙上开了小窗口,共用一个电话分机。我们又都主修家庭社会学,曾经合作开课,又合作多项研究计划,出版专书和论文。她先生黄朝翰是新大经济系同事,两家都住大学College Green 外来教师宿舍。两家稚龄小孩,年龄相近,在大杂院一起长大,可说是通家之好,如今算起来是45年的情谊了。她在80年代从政,当选国会议员,90年代被延揽担任官职,曾官至教育部和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巧合的是,2010年我从南大退休,到新跃大学(现在的新跃社科大学,简称跃大)担任学术顾问,和同任顾问的丽中再次同事,而且办公室又是毗邻而处。她后来荣任跃大名誉校长(Chancellor),是新加坡各大学中第一位女性名誉校长。我这老友与有荣焉。那是后话。
(二)
新大的社会学系创立于1965年,和共和国同年。创系系主任Murray Groves,来自澳大利亚,是位文化人类学者。原来在英国学术传统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密不可分,和美国二者泾渭分明情况大不相同。新大社会学第一年基本必修课是Soc101社会学概论和Soc102人类学概论。我也开始和人类学同事交流学习,接触到他们“接地气”的田野研究,有别于社会学偏重调查及统计分析的做法;让我大大开拓了视野,获益良多。
我1973年加入新大社会系时是第二任系主任Hans Evers当家。Evers来自德国(当年还是西德),主修发展社会学和东南亚研究。他1971年到任,大刀阔斧扩展社会系阵容,从原来5,6人,增加到10人,其后几年大约维持在10-15人之间,其中不少是短期(一到三年)访问学者。Evers自己也只来三年,1974年就另有高就,回西德了。他多年来还是活跃于学术界,经常来访。
当时的社会系非常国际化,除了英美澳德之外,还有来自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的同事。只有两位是新加坡本土学者。和早期(1970年以前)纯然“西方”学者主导的情况相比,到了70年代,有本土和港台及大马学者加入,或可说是“去殖民化”的第一步。不过严格说起来,系里同事都受过欧美(特别是美国)一流大学社会学的完整训练,教材内容以及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来自欧美,严苛说起来,是“代理殖民化”。要“去殖民化”,谈何容易。真正本土化的落实,至少要经过一个世代的反思觉醒之后,才看得出成效。
新加坡大学原属大英联邦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学制和美国大有不同。首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本科采用三年制,学满三年毕业,可获得学位。少数优秀学生(约20%)可继续进修荣誉学位,一年毕业后依成绩可以获得一等,二等,或三等荣誉学位。毕业后就业职位薪金高低通常依学位成绩而定。因而学生对考试和分数非常重视,因为这关乎一辈子的事业前途。新加坡社会一向重视考试和成绩,早年申请工作,甚至还要求小学会考成绩!当年的学制和文官制度如此,如今教育当局要“翻转”观念,不以学位和成绩定终身,只是积习难改,遗毒难消,“翻转”还需努力。
英国学制还有另一惊奇。大学课程采学年制,学生每年选8门课,每门课上足上下学期,30-35周课程,一年一次学年考试,学生必须8门全数及格,通过年级考试,才能升级进修下一年度课程。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要重修所有8门课程!我初来时非常不解,询问之下,才知道在此一制度下,所谓考试及格,指的是通过整个学年考试,包括所有课目。通过学年考试,全数及格,大一学生才能升为大二学生!
(三)
我当时教一门大二必修课“社会研究法”,是要求较多难度较高的一门课,每年总有几位学生被“当”掉。每年决定最后成绩,我总是犹豫再三,非常不忍,因为“当”他们一科,他们就要多读一年。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要到1990年代,新加坡两所大学步向“美国化”,改采学分制之后,才纠正过来。
谈到我教的研究法,由于课程性质,内容偏于抽象枯燥,但是这又是一门训练逻辑思维基本功的必修课程。我接受挑战,在课程中强调推理逻辑,也要求学生实际操作,要能发掘研究课题,设计研究方法,进行田野观察访谈,分析资料,最后完成研究报告。多年之后,偶遇早年学生(如今多已退休!),谈起这门社会研究法,还得到回馈说印象深刻。看来这门课还算教得成功,很觉欣慰。
我那个年代教的学生,资质都很优秀,原来那时大学生人数只占同年龄人口的百分之三,根据人口智商常态分配曲线,都是“精英”,和今日努力培养25%年龄层进大学的“普及”模式,大有不同。然而,更让我讶异的是,有不少学生来自普通甚至弱势家庭,学生中有母亲为洗衣妇,父亲为司机者,辛苦培养优秀子女上大学,令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新加坡社会发展刚起步,各方急需人才,这段时间应该是新加坡社会流动性最大的年代。到今日,40年后,社会阶层趋于定型,甚至僵化,世代间的流动性反而缓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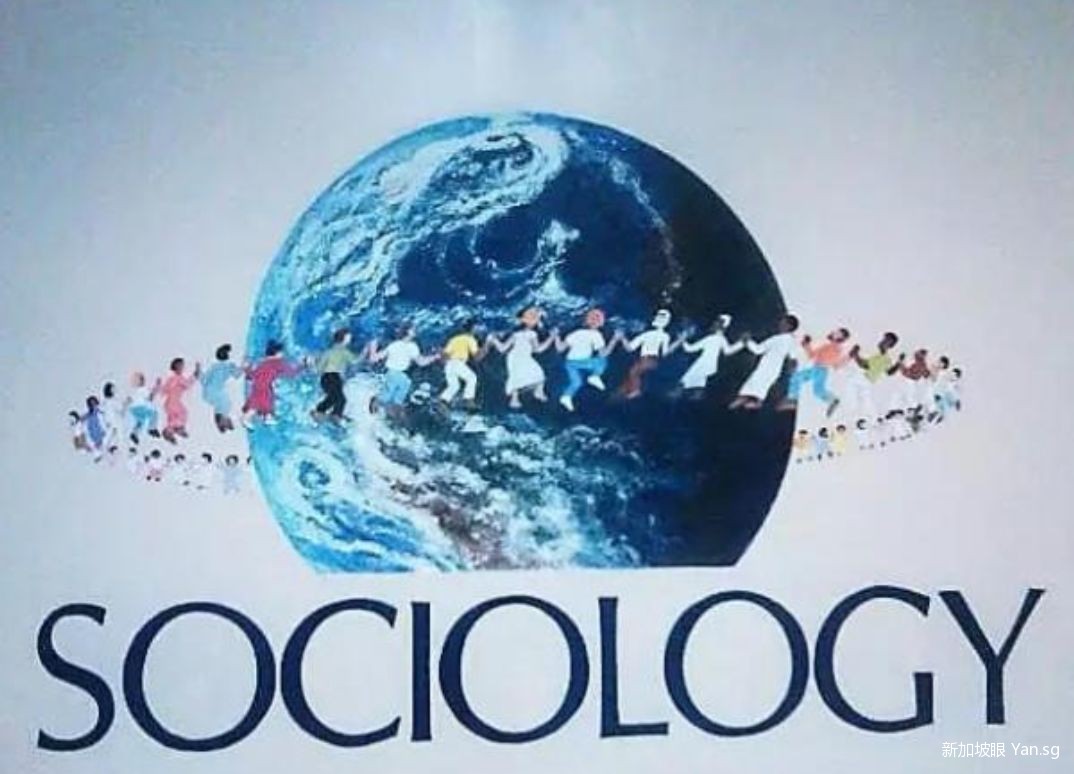
谈到社会研究法,当年还有一个难忘的经历:1976年9月9日,“伟大舵手”毛泽东过世,我当即指派学生进行一研究项目,调查民众信息来源及传播路线:从何处得到此一消息?何种媒体?何时何地?是否转告他人?这是效仿早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受刺身亡后,传播学一个经典研究。我想借毛氏之死,探讨新加坡社会人际信息传播的模式,或可做比较研究。当时我指定学生采用quota sampling(配额选样),到乌节路等公共场所面访公众。三天之后,系主任陈寿仁找我谈话,问起此事。原来“有关当局”发现新大学生的这项调查活动,表示“关注”。看来我是踩到了红线,不过关切之余,倒没请我去喝茶,想来这位郭某还算动机纯良无不良记录,给过了关。至于有没有留下什么档案记录,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份历史性的调查资料,终究没有发表,现在还埋在书房某处的资料档案中,见证第一次和“有关当局”的邂逅。
当年我教的另一门课是荣誉班的“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是当年当红的发展社会学中一个重要课题。据我所知,这应该是新加坡的大学首开大众传播课程。而19年后,1992年,我应邀在刚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学创立传播学院,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
(四)
新大社会学系当年在系主任Evers领导下,建立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也成就了他立志要建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强社会系”的豪语目标。
当年具有影响力的一项新传统,是每周三下午的“学术研讨会”(Research Seminar),除了本系教师和研究生轮流做研究报告之外,也邀请过境学者以及其他学系同仁分享研究心得(当时经济系的林崇椰和政治系的陈庆珠都曾前来做报告) 。那时社会系的研讨会很受重视,每周三来自其他学系的旁听人士不少。这样的聚会,一方面让大家交换研究心得,另方面也无形中对一些年轻学者施加压力,要努力准备上台报告。更重要的是在系里建立一个非常正面的研究文化研究风气,大家能坦然分享心得,互相切磋。或许是70年代80年代大学校风学风较为纯良,我很怀念那时同仁问学问道的乐趣。
那时学术研讨会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贩中心)的研究报告。她在开场白之后,很慎重地努力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中文字:“小饭“,说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贩卖食物(小吃)的地方。这是我初次接触体会(新大)大学生如此中文水平,令我心惊。
还有一次是一位人类学学者在研讨室讨论演化论,只见窗外几只猕猴探头探脑,似在探班。一时传为“佳话”,是社会学系口述历史常提到的一个“都市传奇”(urban legend)。其实第11号楼紧邻植物园,经常有猕猴来访,只是那次探访碰上演化论讨论,自由自在的猴子,对比关在窗内的人类,难免令人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五)
我们这批第一代社会学者当年教学时首先面对的挑战是新加坡社会基本资料的匮乏。无论是人口,婚姻,家庭,宗教,种族,教育,社区组织,社会阶层,等等社会学课题,都有待搜查(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有了这些基本资料,才能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快速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面对的挑战。早期同仁各凭自己专长,努力研究发表论文,可以说是边教边学边研究。
以我个人而言,除了教学以外,作为一位初学者,也非常自觉地努力做研究,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到新大的第二年(1974),我的第一篇学术期刊论文,发表在美国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社会心理学学刊》)。那是我根据博士论文其中一章改写的研究报告,主题是家庭和儿童双语发展,用的是美国案例,却非常吻合新加坡情况。系主任Evers很表赞赏,我自己也大受鼓舞。
我的新加坡研究,重点有二:一是家庭社会学,二是语言社会学。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79年和简丽中(Aline Wong)合编出版The Contemporary Family in Singapore(《当代新加坡家庭》);1980年又和Evangelos Afendras 合编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前者收集了12篇论文,我署名的有三篇;后者包括论文11篇,我署名的也有三篇。两本文集都由新加坡大学出版社出版。(Afendras来自希腊,当时在“区域英语中心”RELC任教,是当年少数研究语言社会学的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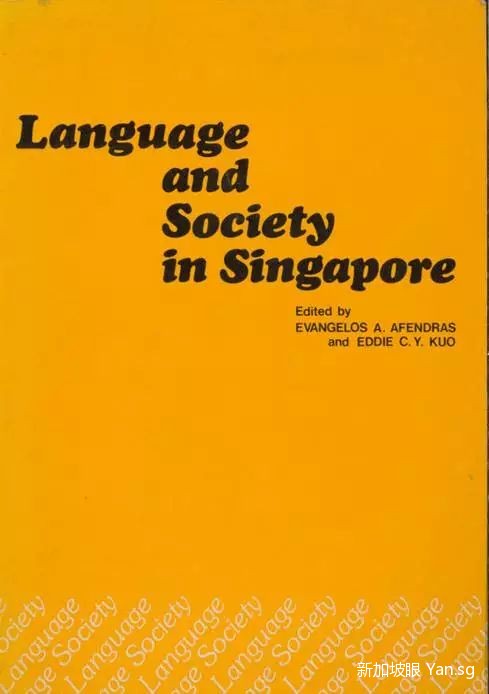
有了这两本著作,基本上奠定了我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基础,自认对新加坡社会有了初步认识,可以自称为第一代新加坡社会学者而无愧了。
来源:怡和轩俱乐部
作者:郭振羽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本文原题《初识新加坡》,发表于2018年10月27期的《怡和世纪》。 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