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的主调子就是改革。去年的三中全会决议出台了336项改革方案,今年的四中全会又出台了180多项。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改革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这些改革方案一旦落实,必将改变中国的制度体系。然而,如果人们把眼光放在官僚机构层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就会变得悲观起来。尽管大家都在讨论改革,但没有多少人在行动,呈现出普遍不作为的现象。改革不仅是顶层设计的问题,还要解决谁来干活,谁来改革的问题。至少如下几个原因影响着官员的不作为。
首先,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以往的分权式改革转向集权式改革,这表现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新权力机构的成立。集权式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早期的改革比较容易,“穷则思变”,人们拼命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改革充满动力。但到今天,既得利益觉得现在的利益格局够好了,不仅不要改革,反而阻碍和反对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的分权反而会导致情况恶化,没有集权,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不过,集权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从分权到集权,方式一转变,很多官员不知道如何作为。在集权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就会说:“反正权力都在你手里,那么你去干活吧。我没有权力,只能等着看。”
其次,反腐败运动也对官员的作为产生影响。反腐败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官员的腐败的高度(层级)、额度(金钱的数量)和广度(所涉及到的领域),已经超出了一般人可以理喻的程度。如此的腐败使得执政党合法性低迷,需要大规模甚至是超常规的反腐败,才能赢得社会的再信任。从执政党生存和发展来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这里,不难理解“不作为要比乱作为好”的说法。不过,反腐败运动既遏止了官员的“乱作为”,也遏止了官员的“作为”。改革需要官员有所作为,否则改革的举措无从落实。
再次,官员任务导向的转型,即从以前的经济指标的单一目标,转型成为多元目标。这种转型也使得很多官员不知如何行动。学术界已经发现,中国的体制在实现单一目标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以往的GDP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单一目标。当然,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对各级官员和政府来说都是正面的,因为大家都可以获得利益。现在,政府官员的目标多元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再追求GDP指标,但其他的指标例如环保、社会满意度等多了起来,无论是体制还是官员,都表现出劣势来,很多人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第四是来自民意的压力。因为腐败等因素,今天的中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互信极低。从前的一些改革,不仅没有给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利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老百姓因此不信任政府官员。在人民不信任官员的情况下,官员就无法作为。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也是想做一些好事情的,但老百姓不相信,一些改革举措,一旦出现来自社会的压力,政策就缩回来。民意的压力也来自今天中国社会利益和声音的多元化,做什么样的改革,总会出现阻力和反对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反对者具有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聚集足够的反对声音,甚至挟持改革方案。
不作为具有严重恶果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官员的不作为,具有严重恶果。从经济上说,如果官员不作为,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以来,全球只有十多个经济体逃避了这个陷阱。这大部分是石油国家,其余的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有作为的政府,配合市场的作用,是东亚经济体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人们因此称东亚模式为发展型政府。无论是产业的升级、环保的改善,还是中产阶级的塑造,不仅仅是市场的行为,而是和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扮演了类似东亚经济体那样的角色。如果政府转向不作为,必然影响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型。
其次是社会治理问题。日本是一个不需要政府的社会。前些年发生地震、海啸、核泄露三大灾难,日本政府不作为,但社会是有作为的。社会自身维持秩序,有效救灾。这些年的灾后重建,社会力量也在扮演主要角色。欧洲社会也差不多,因为预算原因,政府关门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问题,社会还是运作良好。但中国社会力量至今仍然发展不起来,政府又开始不作为。政府不作为早些年已经显现,例如政府不是通过社会改革来缓解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反而是通过过度使用专政工具,即维稳体制,来强行维持社会的稳定,结果导致了更大的不稳定。尽管现在在纠正这种情况,但要社会具备自我治理能力,还要走很长的路。一旦政府不作为,社会本身无能力作为,国家有可能陷入失序状态。
解决和克服政府不作为的问题,必须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再分权。集权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而集权本身不是最后的目标,要推动改革,就需要再分权。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中央政府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也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例如财政税收、金融等。但在很多领域,中央本身不是改革的唯一主角,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才是主体。因此,在向既得利益要回权力之后,要重新把权力下放到改革的主体者那里。行政审批权的大规模下放是个起点。现在政府不作为了,但理论上权力仍然在政府手中。如果不能分权,企业和社会也不能作为。
第二,要处理好改革的法律基础问题。以往中国的改革经常都是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体现,领导人一换,一项改革就不了了之。改革的法律化可以使得改革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替和变化而中断。同时,改革没有法律基础,也很容易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社会压力一出现,改革就半途而废。法律基础上的改革可以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改革要进行下去,就需要处理好改革和现有法律的关系。在中国,改革经常是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中国的改革开始时往往是“非法”进行的,一段时间之后才去修改法律,把改革合法化。如何处理这一矛盾?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首先需要清理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长期执政,在法律和法规上只能做加法,很少能做减法,因为后来的领导层往往不能否认前任所制定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很多法律和法规,大都是把以前的利益合法化。要改革,首先要把恶法、不合时宜的法律和法规清除,之后再立新法,这样既为改革清除障碍,也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处理好多元化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三中和四中全会推出了全面推动改革的方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要有一个先后秩序,尤其要找到突破口。突破口仍然很重要,没有人或者领导集体,能够同时推进这么庞大的改革计划。如果真的推动了,更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颠覆性”结果,这是必须竭力避免的。改革还是必须循序渐进。同时,改革目标的优先次序也非常重要。例如,要处理好不动产登记和私有财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不动产登记之前,首先需要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规;否则财富就会外流。原因很简单,首先要把财富保护在中国国内,然后再讲分配方面的公平。改革的突破口和优先次序的确立,更有助于解决官员的不作为问题,给他们一个行动路线图。
第四,要处理好民意和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者必须处理好老百姓的短期利益,和整体社会的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只要是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的改革,即使遇到了不利的民意,也是需要做的。新加坡政府就是这样做的。改革不能被少数人的利益和民意所挟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挟持民意。在社交媒体时代,少数人很容易挟持多数人的意见。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政府既不能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看着民意治国,只能越来越糟糕。政府应当进行有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改革,赢得民意的支持,而不能让一些民意挟持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议程。
第五,要处理好反腐败运动和提供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政府官员的“乱作为”就是腐败。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现在基本上遏止住了“乱作为”,但没有提供另外的激励机制,这也是目前官员不作为的经济因素。这方面,中国有很多的改进空间。主要有三个问题。
合适的奖励人才机制
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和其额外的收入不成比例。中国是唯一公务员的各种补贴远远高于基本工资的国家。举大学为例,大部分教员,尤其是年轻教员的基本工资,只占其年收入的30%甚至更少。这就要求教员通过各种方式去创收,例如申请项目、写赚钱的文章或做演讲,甚至从商。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知道滋生了多少的腐败。教育界的专业主义精神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很多教员来说,教书培养人、从事科研是副业,而到处赚钱则成了主业。官员也一样,权力寻租是主业。世界上各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是主体,甚至是全部的收入。中国如果能够调整工资结构,国家所花的钱总数差不多,但效果完全不一样,可以让公务员安心工作,教员安心教书培养人才。
其二是高薪养廉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总体来说,通过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感谢郑永年教授授权新加坡眼发布本文。作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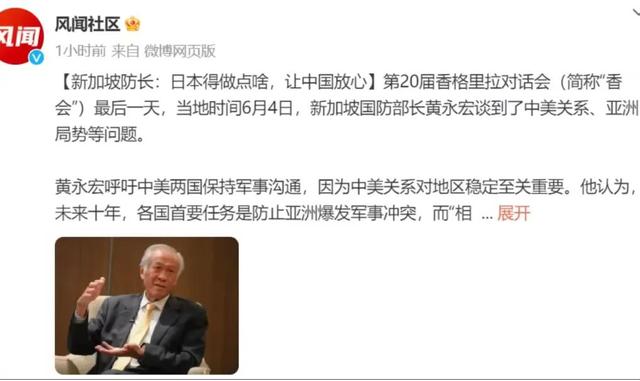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