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住房经验探析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要求回归住房居住属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房住不炒”的定位,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今年,“房住不炒”又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三稳”目标。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3.89%,城市数量达687个。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发展的重点已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如何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议题。
新加坡自1965年8月正式宣告独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在城市保洁方面有着“花园城市”的美誉。作为一个人口密度较高的岛国,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脏、乱、差的“贫民窟”形象提升成为“宜居”的国际化都市,其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本文着眼于新加坡住房体系的更新实践,分析其“居者有其屋”的成功经验,以期为我国城市更新提供启示意义。

作者:李婧,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政府强力推动,法律体系完善
新加坡的住房体系中,政府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统筹保障住房的供给。20世纪60年代初期,与东南亚很多城市一样,新加坡面临着住房短缺、失业率高、贫穷肮脏、传染病高发等城市问题。
1961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成立,标志着新加坡大规模工业化运动的展开。此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形成进一步加重了城市中心区的严重拥挤。[1]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有超过80%的家庭与他人共用住房,50%的住户处于极端拥挤,22%拥挤但不严重,28%不拥挤。[2]
在这一背景下, 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Singapor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取代了原先由殖民地政府组建的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 SIT),并开始建设公共住房(组屋),以安置和疏散人口。
1964年,新加坡提出“居者有其屋”计划,由政府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房。同年为提升拆迁安置工作的效率,新加坡市区重建局(Singapor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URA)成立,其职责包括发展规划、开发控制、历史保护等,同时负责编制概念规划和总体规划。[3]
另一方面,新加坡通过概念规划(Concept Plan)、总体规划(Master Plan)以及开发指导规划(Development Guideline Plan)三级规划体系,提供全面融合的规划制度。[4]
新加坡概念规划是综合性的长期规划体系(40-50年的发展),确定长期土地使用政策,与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相似。
新加坡总体规划主要侧重于实施层面的发展控制,是中期性的规划体系(10-15年的发展),依据概念规划中的宏观政策,为地区提供实施性规划,与我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相似。
开发指导规划则是在总体规划的框架下,将新加坡划分为5个规划区域(DGP regions),再细分55个规划分区(planning areas),制定编制分区域的指导规划,具有很强的实施性。组屋的选址和规划就是依照新加坡的规划体系,由总体规划确定土地开发强度分区,概念规划确定土地利用及新镇体系布局,在控制和引导层面对住房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在政府的强力推动模式下,新加坡形成了以公共住房为主、私人住宅为辅的住房体系。新加坡的公共住宅不仅满足了居民的住房需求,同时以可持续性为目标实现社会融合。1989年颁布的《民族融合政策》中规定,组屋必须按照各种族人口比例设定,形成种族混居。
2012年推出的“多代同购优先计划”,为父母与已婚子女联合申请的家庭提供优先权,鼓励跨代际混合居住。[5]此外,随着“主要翻新计划”“家居改进计划” “再创我们的家园计划”等住房更新政策的推进,组屋的社区服务功能日益完善,逐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品质需求,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核心目标。
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新加坡的住房体系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首先,土地以国有为主,政府不依赖土地财政。对于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来说,面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如何最大化且高效的配置土地是十分重要的。
为解决住房问题,1966年新加坡颁布的《土地征收法》中就已规定,在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前提下,赋予政府可低价征用土地的权力,为新加坡大规模低成本组建组屋提供了土地保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加坡国有土地面积占比由建国初期的44%增长至2006年的87%。[6]
新加坡以国有土地为主的模式使政府在土地的规划、出让、管理等层面拥有主导权,为建屋发展局提供廉价土地以用于开发建设组屋,有效促进稀缺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运作。
其次,组屋的价格由政府统一定制,遵循居民可负担原则。组屋的价格定制以居民收入水平作为参照,房价收入比控制在3-4倍,相当于普通居民年薪中位数的3-4倍。此价保证了90%的家庭可承担三房式组屋的价格,70%的家庭可承担四房式组屋的价格。[7]
对于组屋的申请人,建屋发展局有着严格的资质要求。申请新组屋的家庭必须至少2名新加坡公民或1名新加坡公民和一名永久居民组成的家庭,且家庭月收入不得超过12000新币。申请二手组屋则没有月薪限制,且两名永久居民组成的家庭也可以申请二手组屋。
另外,政府也为购房者提供了额外安居津贴、家庭津贴和近居购屋津贴三项补助金方案,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
再次,中央公积金制度为组屋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支持居民购房。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是在立法规定下的强制性个人长期储蓄,不属于政府预算。
从个人的角度看,该制度规定雇员和雇主依照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按月缴纳存入中央公积金,用于养老、医疗、购房等。据相关数据显示,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用于购买住房占比最重,约为47.1%,其次是养老占比24.4%,用于医疗9.2%。[8]雇员可提取个人公积金账户的储蓄金购买组屋、偿还房贷,或支付印花税等其他相关费用。
从运营层面来看,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运营由中央公积金局负责。除了雇员个人提取外,其余约80%的公积金主要用在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保障了公积金用于住房补贴的可持续性。
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相匹配
新加坡的住房建设阶段与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初期,新加坡面临着城市环境恶劣、人口严重拥挤、住房严重短缺等问题。这一阶段新加坡的城市更新是以清除贫民窟、改善物质环境为目标,开始大规划建设组屋。
20世纪70年代步入工业化后期,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与工业化的发展,新加坡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城市更新以商业区的更新和现代化建设为重点,引入概念规划,形成了两级规划体系。
1970年,建屋发展局实施“职业与居住接近”政策,规定社区20%的用地为工厂用地,鼓励新建跨国公司及工厂,提倡发挥“个人生产力”,为组屋居民提供就业机会。1979年,建屋发展局对“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进行了划分,明确了申请组屋的资质要求。[9]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产业升级转型带来了社会经济矛盾,城市更新重点关注转向提升城市质量兼顾历史遗产的保护。
1982年,建屋发展局提出三代家庭申请组屋具有优先权,鼓励代际共同居住。1987年“新人口政策”的实施,为三孩家庭提供了优先权。[10]随着组屋市场化进程的加快,1989年,新加坡颁布了《民族融合政策》,提出了种族设限居住政策,推动多元种族移民的社会认同感。
21世纪以来,新加坡城市更新以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经济竞争力以及维持环境的可持续性为目标,进一步实现包容性发展。[11]2001年启动的“电梯翻新计划”、2007年启动的“邻里更新计划”“家具改善计划”“再创我们的家园计划”等都以优化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作为目标,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品质需求。
据相关数据统计,2018年新加坡已有83%的人口居住在组屋中,住房拥有率更是高达91%。2019年,为了使更多家庭拥有住房,新加坡又一次将申请家庭月收入调整至不高于9000新元。[12]
在“居者有其屋”的理念下,新加坡实现了公共住房的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完善居民居住环境、促进文化融合、保持社区活力、提升城市风貌,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结语
自建国以来,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为核心理念,大力发展公共住房建设,覆盖了超过80%的居民,形成了以公共住房为主,私人住宅为辅的住房体系。
政府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清晰的土地产权划分,主导并保障了公共住房供给。另外,新加坡住房建设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拆除重建,再到小规模的社区更新,与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密不可分。
回溯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制度理念,其公共住房体系具有普惠性、可支付性特点,同时保障了公共服务及配套设施的均等化。
与新加坡相比,我国幅员辽阔,住房市场在各省、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大,民众的刚性需求十分重要。可借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理念,在提倡“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完善顶层设计、保证政策法律的融会贯通、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体系,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回归住房的“居住”属性。
参考文献:
[1]王才强,沙永杰,魏娟娟.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与发展[J].上海城市规划,2012(03):136-143.
[2]戴志玲:《住房政策与生活改善:新加坡公共住房研究》,第44-45页。
[3]贝贝,李刚.新加坡旧城改造经验及启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09):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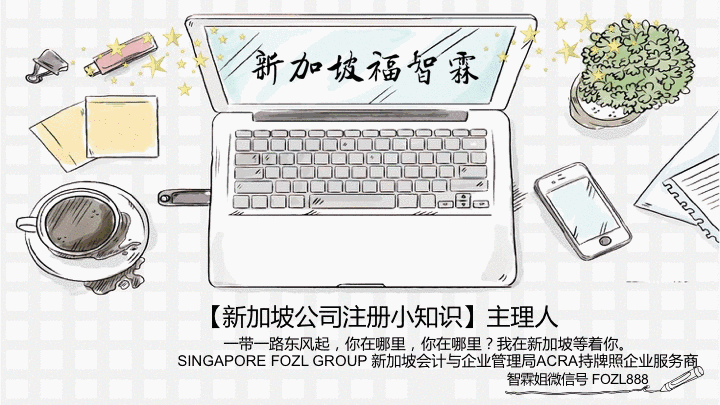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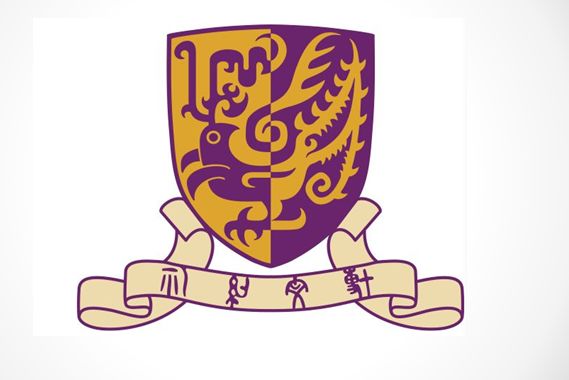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