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顶级华人俱乐部怡和轩,成立百余年,秘史初次公开
沉寂多年的怡和轩,在世纪交接的时刻酝酿转型。1978年就加入怡和轩的林清如曾经连任6年主席(2007-2013),之前也担任总务多年。他曾经是旁观者,无心插柳,所以旁观者清,后来又是参与者、决策者,无风而动,所以当局者明。他通过口述,畅谈这个关键时期怡和轩的方方面面。

(林清如先生)
“先从陈共存的“降格论”谈起
2008年,陈共存在陈嘉庚先贤馆成立时的《献词》中提到,“由于客观环境的关系,怡和轩俱乐部‘降格’为一般性组织,实为可惜。”我觉得这句话重了点。回想怡和轩成立之初。未尝不是为了消闲。
后来陈嘉庚把它引入社会,变得伟大,且光芒四射,那也是客观形势使然。从陈嘉庚到陈六使,怡和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超越一般社团的功能,扮演举足轻重的公民社会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中华总商会,领导一场又一场跨帮派的全民运动,为华社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当然是值得讴歌和敬仰的。

(陈嘉庚在怡和轩致词)
但是,陈共存痛陈怡和轩“降格”,也有其中肯的一面。或者说,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后陈六使时代,孙炳炎从高德根手中接过棒子,怡和轩“沉寂”了36年(1966-2000)。
其实,那也正是一个强势政府,如何有步骤、有计划地驱使社团边缘化的时代。中小学教育经过整顿、改革,辅助学校改变为全津贴学校,华社无须再筹款办学,拿谁的钱,听谁的话,谁受推崇,被打压,客观形势洞若观火,大家心知肚明,什么可做,何时缩手。80年代南大不复存在,华校前仆后倒,华文媒体大一统,整体局面已受控。
华社从沉寂到配合,这才有新的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出现,实际上是民间力量的体制化。观察孙炳炎时代,纵使他心里想要怡和轩“积极参与本区域和新加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有心发展怡和轩,也难物色志同道合者,充其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怡和轩的长期沉寂是必然的结果,当然再也看不到陈六使时代参与教育甚至创办大学的轰轰烈烈场面,也看不到高德根在10万人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词追讨血债的激愤情景。
孙炳炎守住底线 孙炳炎长期领导怡和轩,难免会有人闲话,但他的功绩是应该被肯定的。所有对孙炳炎的正面评价我都能接受,如蔡天宝在追悼孙炳炎时所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宽大精神,以及其他优点。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领导怡和轩时,言行始终洋溢他对嘉庚精神的景仰,始终保持怡和轩的无党无派地位。孙炳炎本人对政治也是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他对政治缺乏判断力。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提起,当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因为当初他本来就觉得新加坡不应该加入马来西亚。 但是,他一个人当了36年怡和轩的主席,不能不说是值得深思。在陈嘉庚之前,主席一职无年限,1923年陈嘉庚掌管怡和轩,订立章程,其中一条规定主席不能连任三届,那时每年改选,三届即三年。所以从1923年至1948年(日治时期不计),每有林义顺、李俊承出面轮替,陈嘉庚退居常务委员,参与怡和轩工作。这说明陈嘉庚建立了优良的换班制度。 战后至今,时代变了,章程也变了,怡和轩成为由会员担保的责任有限公司,主席任期不受限,所以陈六使连任主席十余年,孙炳炎任期更长达36年,直至90岁高龄才下野。究其原因,当时出任怡和轩主席的人经常也是中华总商会的现任或前任会长,有财有势,因此少有人胆敢问津怡和轩主席的职位。孙炳炎在任后期怡和轩沉寂,活动以打麻将消闲为主,或许也有人认为做主席的也应该是会打麻将的。当然,孙炳炎的近乎终身制,难免引来关于个人山头、保守封闭、任人唯近等非议。但无论如何,孙炳炎对怡和轩的贡献非凡,他是先贤精神和怡和轩宗旨的忠实守卫者,怡和轩在他手中保住本色,守住底线。
沉寂中听见阵阵闷雷 1978年某日,何瑶琨需要我的法律咨询,,我去怡和轩谈,刚好孙炳炎、林子勤、郭亨升等熟人都在打麻将。我从小就喜欢打麻将,甚至在被政治拘留的时候,在牢里也打起麻将。办完事后,何瑶琨把我拉下场,大家看到我其实还是好此道者,让我填了表格,当场入会。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每天一早打完高尔夫球后去上班,傍晚三四点就到怡和轩消闲去。十几年一晃而过,未曾想过能为怡和轩做些什么。直到1987年何瑶琨去世后,我才顶替他的空缺,从候补董事转正。下来12年,我忝列董事名册,最多也是从末座上升到中位,没有任务,没有作为。
1995年怡和轩欢庆成立100周年活动时,我看到怡和轩积极的一面。那年我已经58岁了,对工作开始感到厌倦,想起应有退休的准备,自然就考虑到那边的环境。
孙炳炎要搞百年大庆,我虽然并未全力参与,但懂得前后经过。100周年大庆,孙炳炎表现积极,他要重温怡和轩的历史。来自中国各省和不同团体的一百多位客人,许多是早年陈嘉庚的左右手,如张楚琨等都来了;还主办一个新加坡文物展和儿童画展,并向报界宣布怡和轩要设立一个文物馆。那时我才感觉到,或许怡和轩不会永远沦为一个搓麻将的地方,可能还会有些有意义的事可以做。

(孙炳炎-怡和轩100周年)
百年大庆过后,怡和轩面对两个问题,一是会所受到地铁工程的影响,成了危楼,须与陆交局谈判,在重修与重建之间作个抉择,我的专业略有用场;另一是孙炳炎年近90,接班人问题愈显迫急,退与不退,他总是举棋不定。1999年是董事换届的年份,选举前听说孙炳炎有意退下,相传是孙炳炎属意的人找我谈,表示他或会接任主席,希望我出任总务协助他。为了实现换班,我答应了。可是进行复选时,情形出乎我的意料,孙炳炎连任主席,但我倒是真的出任了总务。
为什么换班不成?我一时不去猜想个中原因,然被选为总务,就开始认真做,谈不上使命感,我根本也就没有什么使命感。 记得我推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入会费从5000元减为3000元,主张招收新会员,也立即引进了如陈醉在、王如明、孙泽宇、陈远腾等人。传言中的换班没实现,人事关系突然变得微妙复杂,几个月后我辞了总务的职位,但是还答应孙炳炎,留下来协助他推动文化活动,同时关照与陆交局谈判会所受损的事。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班子,除了刚进会的王如明、孙泽宇等人,还有1995年就成为会员的潘国驹。潘国驹提议设立史料小组,协助实现孙炳炎四年前提出创办文物馆的愿景。史料小组于2000年成立,杨松鹤、王如明、孙泽宇和我都是小组成员,聘请了黄今英负责收集与梳理历史资料,出版了他撰写的《陈嘉庚》。
同年6月还邀请南大校友、南澳弗林德斯大学历史教授杨进发博士,到中华总商会礼堂主讲“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吸引450名听众,一炮而响,之后讲座不辍,出版活跃,蔚然成风。 说怡和轩转型搞文化,这算是开始吧。

(先贤馆 - 林少彬摄影)
进入后孙炳炎时代 2001年董事部改选前的几个星期,有一天孙炳炎召集我们10几个人到中华游泳会的餐厅吃饭。席间他表示这回决意退下,建议黄鸿美接任主席,我则重做冯妇当总务。大家没有意见,班子就这样定了,下来的一切就是手续而已。2002年四月孙炳炎与世长辞,怡和轩进入后孙炳炎时代。
新班子面对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没有了一个家长式的领导中心,却有一个日愈破损的会所要处理。2001年地铁工程大致竣工,是与陆交局“算账”的时候。陆交局始终坚持,会所可以修补,不会坍塌。这些时候出入怡和轩的,多是些打麻将的人士,他们同时隶属几个消闲性质的组织,一般态度是“哪里凉哪里坐”。因此就有不少人认为,只要陆交局肯修补,并保证没有坍塌危险,那就得过且过,何必多事想要重建。还好这时团队里有好多人认为应该从长远着想,应该花些钱找专家测探,要是屋身结构有问题,就得坚持要重建。这本是费时费钱的事,但是大家觉得责任在身,再麻烦也要做。
2003年我已经66岁,主席黄鸿美也刚过70,我心里想,总务一职应该由比较年轻、有潜能者出任,为领导层的自我更新做准备。洪宝兴是毕业于南大的专业会计师,在我的劝说下,在2003年董事换届时出任总务。我以董事部秘书的身份留下来,协助会务,特别是与陆交局争取赔偿的事。谈判冗长费时,陷入僵局,我们决定诉诸法庭。开庭前夕会务顾问蔡天宝出面调解,索赔问题终在建筑物必须重建的基础上获得解决。
由于会所倾斜程度日渐严重,2004年9月董事部租用隔邻适可俱乐部为临时会所。洪宝兴身兼一间行业公会和一间乡亲会馆的主席,觉得分不了身照顾怡和轩,2005年董事换届时决意卸任,我只好再当起总务。租用适可俱乐部的会所需付不少费用,为了节省开销,同年7月怡和轩搬到位于客纳街76号中华为基利俱乐部会址,与租用该会址的友竹俱乐部共用会址。

(怡和轩外观 - 林少彬摄影)
重建后的怡和轩,何去何从 重建后的怡和轩应该何去何从?这是重建前就应该想好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应该利用会所的商业价值,比如说部分出租开餐馆、KTV厢房、办公等用途,一劳永逸解决经费的问题。有些人觉得老祖宗从来不曾把会所当商业用途,我们最好别破例。就在这个时候,怡和轩元老陈共存站了出来。他大力主张由陈嘉庚基金接管怡和轩,开辟为“陈嘉庚馆”,甚至在报章上公开呼吁,很多怡和轩会员对此疑惑不解。
有一天,陈共存约黄鸿美、潘国驹和我到他的住家吃饭,请来了杨荣文部长,大概以为杨部长也会同意他的想法。杨部长向我们了解了怡和轩现状,认为可以考虑双方如何合作。当晚,黄鸿美邀请杨部长来怡和轩走走,于是才有杨荣文、许通美、王赓武和三位夫人等嘉宾于2003年的怡和轩之行。杨荣文认为合作是可行的,应该把怡和轩保留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物(living heritage),不要沦为没有人气的博物馆。
怡和轩董事潘国驹同时是陈嘉庚基金的副主席,了解怡和轩内部情况,在推动怡和轩的重建工程上贡献很大。
2005年的一天,就在董事部要开会讨论重建大计前的一天,我与王如明赶到东陵俱乐部面会潘国驹,他当场献议合作方案:怡和轩让出地面层给陈嘉庚基金设办事处并附设一个文物馆,陈嘉庚基金赞助怡和轩建筑费100万元,限期若干年另谈。
2006年怡和轩会员大会批准了与陈嘉庚基金合作的方案,确立了怡和轩未来弘扬先贤历史、传承文化的方向。

(先贤馆开幕)
“同仁错爱,我当了主席” 重建工程于2006年7月9日由会务顾问蔡天宝主持动土典礼,2007年9月即告竣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同仁杨松鹤、柯宝国、廖德能、吴文国和吴添乐等人日日轮流伴我出入工程场所,劳苦功高。一座崭新华丽大厦终于出现眼前,个个喜形于色。
董事部任期2007年届满,黄鸿美决定卸任,同仁错爱了,我被推了上去。这一年,我已经70岁了,我只能当它为一项“应急措施”地接受了。同年12月8日,怡和轩从位于客纳街76号的临时会所搬回去,而友竹俱乐部与中华为基利俱乐部的租约也到期。这一来,常在这几个俱乐部打麻将消闲的人面对了一个相当混乱的局面,怡和轩免不了受到冲击,董事部以明确的立场、坚定的态度朝既定的方向走。
2008年11月9日怡和轩联合陈嘉庚基金假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三庆大典,其一庆祝会所重建落成、其二庆祝怡和轩成立113周年纪念、其三庆祝陈嘉庚基金先贤馆开幕。场面热烈,两位内阁部长(尚达曼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杨荣文)同为嘉宾。在庆典上致词时,我呼吁“各界人士以新的眼光看待怡和轩,支持怡和轩,共同为保存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文化传承,为建立一个更为优雅的新加坡社会尽一份力”。
庆典当天我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李慧玲访问时也说,“怡和轩的重建和先贤馆的设立可说是民间团体一项自觉性的工程,当然只是一个小项目罢了。要是类似的社团能塑造一个共同的远景,实际地行动起来,我们或许可以为国家开辟一片清新的天空。制造一个文化的大环境是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凝聚并发挥民间的力量,强大的民间力量才是传承文化的真正力量。”

(早报报道)
换了血的怡和轩 在她沉寂的年代,加入怡和轩的人多为了打麻将消闲而来。1999年起怡和轩改变方针,决定打开门户,广招各方有识之士。虽然初期的反应不理想,从2000年至2006年的6年里还是吸引了40多名新会员。
2007会所重建竣工后,配合2008年三庆大典的成功举行,怡和轩以崭新姿态重现。在2007-2009年度里怡和轩接受了整整120名人士的申请入会,当中不少是事业有成的南大校友。此后董事部以比较节制、稳定的态度继续开放门户,从2010年至2014年的阶段,平均每一年引进20至25名新会员。新陈代谢的结果,2000年以前原有的200左右名旧会员,至今只剩下80几名。在现有会员名册上的300多名会员里,有超过2/3是2000年以后加入的新会员,怡和轩是换了血! 新近加入怡和轩的会员,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成功人士、在各自岗位为社会服务的各界精英。他们不是为了打麻将或其他消闲而来,他们明白也接受,参加怡和轩其实是一种付出,是有别于参加乡村俱乐部,不能抱着期待物质回报的态度。
怡和轩会员以认同与发扬上代人的精神财富为豪,因为那是一种激励人生的奋斗的力量。通过发扬这段历史教育自己,也教育后代,这就是文化传承。我相信现任领导班子不会刻意发起招募新会员运动,但会继续欢迎和物色不同领域成功人士的加入。因为对我们而言,每一位会员都是一份资源。

会员自觉自愿的承担 都说怡和轩是富人俱乐部,应该有大把钱。事实不然,怡和轩会员有钱,不等于怡和轩有钱。除了会员年捐、入会费,会员消闲活动时的娱乐捐,怡和轩没有其他的收入。利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常年开支,有很多时候是不够的。每逢举办特别项目(如修理会所或周年庆典),就得向会员筹款。筹款所得扣除开销,剩余的就当活动储备以应付常年开支的不敷。
1985年怡和轩举行90周年庆典,筹了20多万元,扣除开销,还剩近10万元,应付至1995年的开销。1995年庆祝100周年,孙炳炎筹了100多万,虽然那回庆典开销大,还剩好几十万元,2001年我做总务时,有足够的钱聘请专业人士与陆交局交涉赔偿。
2005年敲定重建计划与蓝图,盘算重建费用,需要250万元左右。除了陆交局赔偿118万元,陈嘉庚基金的100万元,欠缺好几十万元。
2006年7月工程已动土,我们在2007年3月才决定向会员筹款,好在会员响应令人鼓舞,在短短两三个月里,筹募了130万元左右。2008年11月9日举行三庆大典,我们又向会员伸手,再筹了50万元左右。两次的筹款,应付重建与庆典费用后,尚有可观的余款。
会所重建完成后,怡和轩会务方针有更明确、更稳定的转变。董事部决定从长计议,认真恢复怡和轩的形象,从而争取全体会员对于怡和轩自觉自愿的承担。因此,从2010年起会员年捐由$480调高至$720,这是个果断、大胆的决定。董事部坚持透明作风,所作决定得到全体会员的支持。自会所重建以来,财务状况良好,每年收支平衡。

一个人文小天地 2008年11月9日先贤馆由财政部长尚达曼开幕,潘国驹与他的陈嘉庚基金团队为先贤馆付出心血。除了介绍陈嘉庚、李光前,先贤馆展出陈六使史迹图片,是闹市里的社团仅有的。先贤馆的设立对怡和轩形象的重构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它能不断提升。
2011年怡和轩与先贤馆应马来西亚有关团体的要求,联合举办一场重游滇缅公路的壮举。6月25日车队由怡和轩门前出发,浩浩荡荡,轰动一时。2012年怡和轩、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及先贤馆响应各界人士的呼声,决定共同立碑纪念南侨机工。2013年,一座纪念南侨机工的巨型雕塑终于在晚晴园竖立起来,并于同年3月4日由时任外交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的陈振泉揭幕。
新会所落成后,为文化活动提供了方便。曾有一段时期怡和轩的周末小型讲座吸引大批听众,往往把二楼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办的讲座受欢迎,主要原因是课题多方面,我们谈社会、历史、甚至政治课题。政治上怡和轩立场超然,决不涉及政党政治,但是关注政治、谈论时事应是人人都有的权力,也是该做的事,这是我们与很多社团不同的地方。这一两年我们办的讲座较少,一来是周末很多团体都会办讲座。二来我们把精力集中在提升《怡和世纪》的出版。三来我们已经不满足过去的小型讲座方式,在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能够在素质方面提高,重质不重量,也不妨重名人效应,重讲座的规格,藉以提高怡和轩的形象。
为了唤起会员对怡和轩的关怀,我们在2002年出版了会讯。从此平均八九个月出版一期,篇幅从最先的四页逐渐增加到八页。后来不少文化界人士加入怡和轩,其中包括了陆锦坤、许福吉等人。他们帮忙推动了会讯的提升,于2010年把会讯改为比较有分量的《怡和世纪》,每四个月出版一期。至今连续出版了15期,每期准,篇幅从最初的30多页逐渐增加到目前的144页。
所有的编辑人员(包括后来加入的谢声远、李秉萱、南治国、谢声群等人)都是义务效劳,劳苦功高。《怡和世纪》目前通行量5000本,免费赠阅。除了收入,《怡和世纪》同仁也于2012年间召集一批热心会友,筹了一笔基金资助出版费用。
《怡和世纪》目前已是新加坡文化界的盛事,深得读者的赞赏。内容涵盖社会焦点、时评、史料整理、文化传承、财经、会友风采、艺文等方方面面。座右铭是:报道翔实,以发扬求真精神为己任:论理客观,既不标榜,也不媚俗:门户开放,思想碰撞,集思广益。


限于主观、客观条件,我们这些年来能做到的,极其有限。
要是我们已做的一切,能对华社团体的文化活动起些微推动的作用,那就意义非凡了。必须指出,在怡和轩,我们想的不会是福建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等,我们不会特意搞民俗文化。我们首先注重怡和轩和先贤的事迹,这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挖掘、整理和分享一切有关新加坡的人文史料,所谓的本土文化,自有其自己的活水源头,常常会是我们优先考虑的。 怡和轩能走多远
一路走来,其实并不容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改革都会伤害到一些既得利益者,会受到阻挠。这些年来,我们身历其境,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幸一直都有一批志同道合者。怡和轩能有今天的场面,是所有同仁群策群力、衷心合作、相互包容的结果,不能太过强调任何个人的作用。
谈起转型,虽然是上了路,我们是否成功转了型,仍说不定。
怡和轩换了血是事实,但脱胎换骨就言之过早了。有抱负、愿承担者应该站出来,有效地强化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能力,那时候转型才算成功。否则新人却步,旧人硬撑,到一定程度大家也就会心灰意冷,前功尽弃。
怡和轩当然不可能恢复往日的光辉,她能走多远,很大程度决定在于客观环境的演变。面对一个“大统一”大趋势的压力,怡和轩要如何继续保持超然的态度,那就要决定于我们大家的胆识与魄力了。
2011年怡和轩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探讨华社能否有一个新方向。林清如主席以个人身份发言,提到应该以较为宏观的思维、从一个新加坡公民社会角度展望华社的未来,赋予华社以新的时代使命,从而鼓励与引导更多有抱负的人加入行列,通过华社的渠道参与公共事务,成为推动社会的力量。在现阶段来说,这是曲高和寡,甚至还会引人发笑。但是他坚信,形势会改变,他抱乐观的心态展望怡和轩的未来。”
(本文作者:怡和世纪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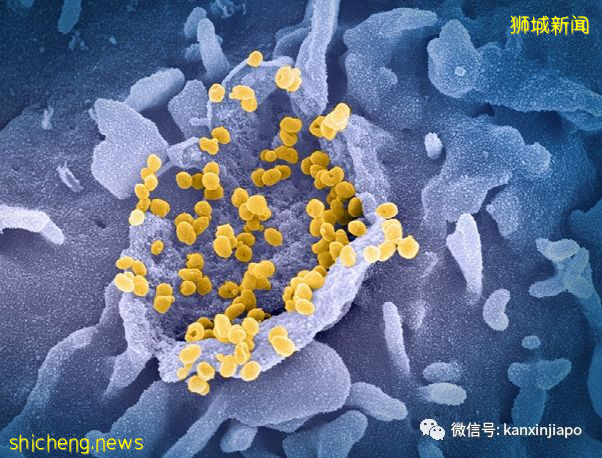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