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北京三甲医院,我去新加坡做了家庭医生
人生是一条有很多岔路口的长路,要面临无数的选择。
2010年的夏天,我从协和医学院毕业,拿到了临床医学博士学位。踌躇滿志的我拒绝了北京某三甲医院的offer,背起行囊,只身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想在这里见识不同的风景、认识一群不一样的人。

初来广州,我顺利进入了综合实力排名全国前三的一家肿瘤医院,尽管这家医院一直以“难进”著称。一流的平台、优秀的领导、友善的同事,当然还有广州温和的气候和驰名天下的美食……这么好的条件,似乎我该安顿下来过上一个稳定安逸,并且“有保障”的生活。然而,刚工作了一年多,我就开始“不安分”了。
在协和,我们那一届一共有100多人,毕业后,90%以上都做了临床医生,而这其中大约80%都去了北上广这三个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剩下的去了一些二线城市。还有一些同学去了海外行医,包括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
那是2011年的国庆黄金周,我记得很清楚。
某个清晨,我打开手机,开始刷微博,忽然一条信息跳出来:“别了,北京!别了,祖国!新加坡,我们来了!”
这是我同班同学L发的信息,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是他和夫人(也是我同学)一起辞去了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工作,踏上了去新加坡的旅途。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被点燃了:我也想出去看看!
这突然滋生的念头就像疯长的野草般不受控制。我不想继续在体制内的医院待着,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我这样对自己说,也这样对家人说,并成功的说服了他们。有支持你的家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我是一个行动派,想到就立刻开始行动。我在微博上联系了L同学,详细咨询了他申请去新加坡行医的流程后,甚至没有等过完国庆黄金周就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L也很热情,帮我联系了新加坡卫生部在中国招募年轻医生的负责人Danial。
这里不得不赞叹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员的效率:发邮件给他们一个小时内就有了回复,并且很快给出了详细的后续指引,当然,这或许是因为新加坡和我们中国没有时差的关系吧?哈哈。后面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准备材料,通过新加坡方面的资质审核,赶赴上海参加他们的面试,拿到offer,再然后就是准备托福考试,准备各种文件,同时在肿瘤医院递交辞职信办理离职手续,最后在2012年的9月18日,我从上海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飞机。
2010年我选择离开北京,前往广州。
2012年我再次选择离开广州,前往赤道边上那个在地图上几乎看不到的弹丸小国——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称狮城,1965年正式独立,国土面积仅为北京的1/24,或广州的1/11。新加坡虽小,但在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即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国民福利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新加坡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本地医疗资源与经济高度发达后人均寿命延长、社会老龄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供需缺口,所以早在2010年前后就一方面加大医学教育投入,在本地原有一家医学院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到三家;另一方面大力从海外包括英国、澳洲、中国、印度、马来等地招募医学毕业生或是年轻医生前来工作。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新加坡。
初来乍到,总是会经历各种不适应。
语言是第一关。虽然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70%以上是华人,但英语才是官方语言,在医疗系统中更是如此。尽管在国内,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一直有英语课,来新加坡之前也考了托福,但是这和真正的日常应用还是有差距。而医学领域的专业词汇又特别多,再加上新加坡本地特殊口音的Singlish(新加坡英语),听和说真的是两大难题。
那个时候最怵的就是夜里值班时打电话和接电话:半夜里睡眠剥夺状态的值班医生们本来就脾气不好,然后如果病人的病情比较紧急,再碰上我这样新手上路、讲著磕磕绊绊英语的小医生,被骂几乎是一定的事情了……其中比较凶的医生还会直接让人特别尴尬难堪:“让别的医生来和我通电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不同的医疗体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冲突是第二关。我在新加坡工作的第一个月就被安排在了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新加坡中央医院的普通外科,该科室向来以工作量大、压力大、待低年资医生不友善而著称,当然它的综合临床和教学质量也的确是新加坡首屈一指。而我又被安排到了科室下面的血管外科这个专业组。刚开始我还想着自己好歹临床实习的时候也轮转过血管外科,不至于两眼一抹黑,谁知道这里的病人情况、疾病谱和国内大三甲完全不同。
国内医院外科系统收治的住院病人多是在门诊挑选过后的“合适”患者,也就是说手术指征明确,基础身体状况良好,没有特别复杂合并情况的,入院就是奔着手术来。而这里上到九十几岁、合并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依然要入院做主动脉瘤支架植入,下到普通外周血管病变的患者,合并反复伤口感染同时还进行着透析治疗、动静脉瘘时好时不好用,一次次入院抗感染治疗,基本就没有单纯只是“血管外科情况”的患者。作为管床住院医生的我要事无巨细、内外科各种情况一把抓。
除此之外,Physiotherapy(物理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职业治疗)和Speech therapy(语言治疗)等在西方国家已经成熟和标准的Paramedical(辅助医疗)系统,以及关注于患者家庭长期护理计划和财务状况的Medical Social worker(医疗社工)在新加坡的本地医疗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作用。其中,医疗社工细致到甚至会调解患者家庭内部纠纷,比如谁来照顾患者、谁来支付长期的医疗费用等等——感觉就像中国的居委会大妈,但这确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专业。
请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国内工作和实习的时候,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广州,都完全没有听说过上面这些东西,完全不知道患者手术后的康复原来可以分的这么细:有人专门管怎么走路、运动,教家属如何把患者从床上搬到轮椅上,轮椅上搬到轿车上;有人管怎么吃饭、穿衣、刷牙洗脸上厕所;还有人管什么时候只可以进流食,什么时候在流食中逐渐添加增稠剂,什么时候可以过度到固体食物。更不知道,医疗社工会上门访谈了解家庭的实际情况,或是在医院召开家庭会议,帮助家人规划长期的看护计划以及如何向什么机构申请什么类型合适的补助或救济。在这样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医疗系统中要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单有临床知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医生在这一切过程中需要一直处于核心的统筹调度位置,要知道什么时候动用什么资源,从而为患者获取最大利益。
尼采说过,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工作的第一个月,我碰到的一个主治医生,真的非常严厉。可能是觉得我拖她带领的医疗小组的后腿了,什么都不懂,需要教,所以每天都是各种呵斥。我有时对她查房说的一些英文药物名称不熟悉,会请她重复,或是拼写,她在这种时候说的话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虽然对我一点不留情面,但是不得不承认,她专业上雷厉风行很有决断力,对待患者时又非常耐心温柔,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压力很大,每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明天就辞职不干了”……然而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又是斗志满满的给自己鼓劲加油,继续努力“不能让这帮人小瞧了”。实践证明,人果然在有压力的时候才成长得最快。

转行GP
忙起来的时间总是飞快,一转眼我已经在新加坡待了七年。
七年间,我轮转了好几个公立医院,已经适应这里的医疗系统了。而中国来新加坡行医的医生团体也日益壮大,从最开始小猫三两只到现在有一百多号人。要知道整个新加坡所有执业医生也就才一万出头。
与此同时,政策的风向也在开始转变。新加坡自建的几所新医学院校都开始有毕业生陆续进入临床工作,对医生的需求不再紧缺,所以政府逐渐减少了招收名额直至完全取消。
新加坡的医疗市场容量比较有限,所以政策制定者们对于每年每个专科需要多少医生、预期未来几年会新建几所医院从而产生多少缺口都有着明确的规划。那些热门的科室自然是僧多粥少,竞争格外激烈。刚开始还有一些中国医生以著外国人的身份就能match上住院医生培训,但是到了后来,如果不是永久居民或是公民,几乎就不再可能。我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难度最大的外科之一进行match,可是连续三年都落选了。无奈蹉跎了三年,最好只好重新选择了家庭医学,并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完成了相应的培训和考试,成为了一名全科医生。
2018年初我从政府公立医院辞职,加入新加坡本地最大的私立医疗集团之一,成为了一名私立全科医生。
新加坡的医疗资源配置很有意思,严格的二八法则:初级医疗也就是全科方面,大约80%由私立诊所提供,只有20%由政府公立提供;与此同时,专科诊疗则80%是公立提供,私立只占剩余的20%。因此可以说私立全科服务是整个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基石和守门人,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去看一次专科医生,但是一年至少会去看几次全科。遍布新加坡全岛各处大大小小的私立诊所集团,以它们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和就诊时间的灵活性,成为了本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私立诊所的GP生活可以说是相当舒适,待遇很高,工作强度也不大,没有了让很多医生都头疼的科研压力,也没有了医院惯常的值班加班。如果真的有工作超时,很多诊所都有详细的规定,每超时10分钟都有相应的报酬,对医生的劳动力是真真正正的尊重和认可。

除此之外,多点执业这个在国内一直被反复讨论并在近年才开始逐渐落地的政策,在新加坡却一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只要是完全注册的医生,在自己执业范围内都可以自由去不同的诊所执业。这也催生了本地一个很大的“兼职医生”市场:诊所运营者会在市场上放出有需求的诊所地点和时段,而有空余时间的医生则会从中选择自己方便的前去工作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医生和诊所之间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而非依附关系,一方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一方则是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场所。医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灵活掌握,决定每周是工作20个小时,还是45小时,甚至60小时或更多。
新的开始
人生就是一个围城。
年少的时候上大学就想着要离开家乡远远的,所以选择了一个人去北京读书;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总觉得有这样那样不合理的地方,一心想着要飞得更高更远,要出来看看世界;在国外生活了这么些年,虽然早已经拿到了永久居民,但是从来没想过转换国籍,因为越是看尽了大千世界的繁华炫丽,越是懂得洗净铅华背后的朴素隽永。毕竟,我的根还在中国——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城。
自己是临床医生,又在国内外都执业过,所以一直对国内医疗行业的现状很关注。看到从大数据、云计算到人工智能赋能新医疗的变革,看到从移动医疗到互联网智慧医院的升级,看到国家卫健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更看到新中产的崛起和整个国民的消费升级对更快更好医疗的需求,可以说中国的医疗产业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我目前工作的新加坡医疗集团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建成了两所独资的医院,更不用说早在那之前已经布局的连锁诊所。而其它几个我了解的美国和英国的大医疗集团亦也在中国抢滩登陆。至于本土的连锁品牌和医生集团在过去几年里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这是一个崭新大时代的开端。
是安心在新加坡继续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还是积极拥抱变化,主动投身甚至为时代的变化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呢?
我又一次面临着选择:向左还是向右?而这一次,所有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本文首发:医学界
本文作者:骆毅
责任编辑:李兴鹏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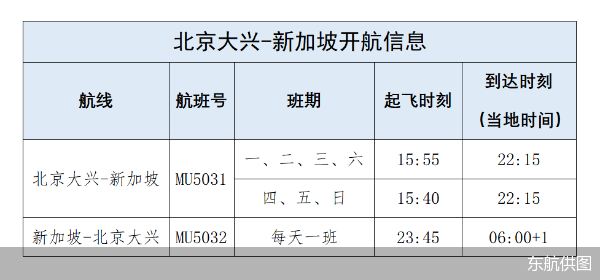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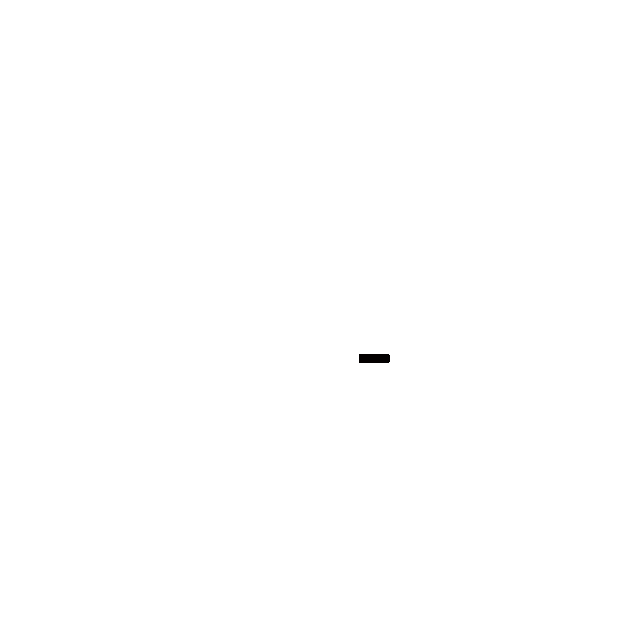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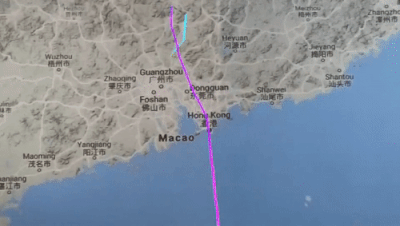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