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白桥的故事
带四姐去看美娥中医。诊所在白桥熟食中心边上。下了车,四姐忍着背上的痛,嘟著嘴说话:“那天大雨来得无声息,在急忙中收衣服扳竹杠时,闪到了背。”走在身边听她说话,我转头看去,平视线高于她发梢许多,她本是廋小的身型,这一看觉得她突然间短了半截。

病真是折腾人来的呀!
刚到诊所,便下起倾盆大雨,暴雨如柱、从天而降,以万马之势从苍天裂口奔腾下来,
一瞬间,大雨把白桥淹没在一片白茫茫的水色中。进了门,走来了个青年男医生,低声和蔼的问话,然后引我们到一空房。那房里摆了三小单床,床之间都安上了一道挂帘,一拉上便成了三个小隔间,方便医生看诊。这时来早的我们,只能在房里耐心等候。雨天中的空调徐徐吹来,一阵又一阵让人瑟瑟发抖的冷风。
好在美娥看病很利落,刚听到了轻快的脚步声,她一袭白衣便亮相在眼前。温和的问候,是用沉稳叫让人放心的声音,这可是长期锻炼出来的临床功力。
大概是医生的亲和力使然,四姐轻轻冒出一句:“晚上睡觉时还发痒不止”。美娥一听后,手拉上挂帘,把我支到另一隔间里。然后让姐解上衣,以便她仔细诊断病患处。没过几分钟,她又利落地拉开挂帘,说:“这是生蛇。”然后露出一丝笑容,嘴角叨著信心满满的一划。
“好在发病不久,到西药房取用抗生素。吃一周药后,就不碍事了。”她又补一句。那句话最后的四字,如一颗灵丹入口,烫平了病人的五脏六腑,一块大石顿时落下。
在道谢后,我们倒退走出房。当四姐等药还钱之际,我先从诊所出来,冷不防看到半张熟脸,因带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俊好的面容掩在黑罩下。他一开口叫我,我立马认出,原来是春茂,中学的同学。我拉开大门,邀他到门外的五脚基去,户外拉话,数算着人和人之间,那无法解说的缘分。

四姐出来了,我便和老同学挥别上路去了。此时大雨已停,像做了一场恶梦,白桥刚被洗刷一新,屋外操场一大片青草地,在雨后的黄昏下,泛著新绿的微光。
二十几年前,太太也在白桥,距美娥诊所一石之遥处,开了一间托儿所。那是她开的第二间托儿所,就在隔座的新组屋,一楼的“防空壕”里。在开业前,我常开着一辆老白车,陪她到此。
记得开业第一天,在那偌大的防空壕里,孤零零得只有三个小朋友,空荡荡中弥漫着冷清。我心底正在琢磨,这生意该怎么做下去时,太太却信心满满得说:“我的首间托儿所开始也是一样,也和现在美娥刚开的诊所一样。开始的新生意都是如此,门可罗雀的。”一句话道出了那一代妇女,都兼有东方女性吃苦耐劳的优点,总能从小做起,守得住寂寞,直到云开见月明。
后来,我去上海工作,往后的日子,太太把两间托儿所,一天天的做大做强。最后为了陪我到上海,把她自己心爱的事业卖了。纪念这一往事,感谢太太为我和一家人所奉献的种种牺牲。
白桥这地方,原是一座跨过梧槽河上的桥而得名。古远之日,我们先辈们从岛国市区沿着汤申大路北上,要离开拼搏的大城前,北上之路的第一座桥。北向的一路上共有九座桥。

1919年,我爸刚七岁。一天清晨,他和三弟两人从北部三巴旺的(汫水港)老家,赶了一牛车上的三桶净水到小坡牛车水,卖给城里缺水的居民,那时三大桶水能卖得三分钱。卸下水后,他们沿汤申大路向北走回程。半途中,爸突然间头昏脑涨手脚冰凉,肚子开始阵阵发疼,想呕吐却吐不出。他让三弟赶牛车,自己躺在车斗的木板上喘息。
当车要过白桥头前,天下起暴雨。在骤雨中,他们在竹脚一带找到歇脚避雨的一处。避在雨顶棚下的车斗上,我爸昏昏沉沉得睡了一觉。睡梦中,朦胧间听见一个阴气森森的声音,夹在风中,不断呼唤着他的名,接着一重物紧压着他肺部,不能喘气。一直到天上闪电后,再打一记暴雷,才驱走那一怪声,也把他吵醒了。醒后刚才的肚疼头涨,也消失得无踪影。

大雨已经停了,做了一场噩梦后,爸随着弟弟慢悠悠得上路,走过跨在河上的白桥,他们看见一道彩虹,挂在北边的天际线上。
至今的白桥头,依然涂上纯洁的白漆。对这些穿梭不息的人们,当他们在城里闯荡而身上累累伤痕之时,只要从白桥过,一定不要忘记,把身上的一切是非、得失和成败,都一股脑儿得抛至九天外。让纯洁如雪的白色,和内聚其中的那一种无可斗量的治愈能量,抹平人们心中的创伤,医治人们身上的一切病痛。
过了桥后,以健康愉快的心情,踏上康庄大道,迈向岛国清新的北部绿野去,一个崭新的生活就在前方。
白桥依旧,亲情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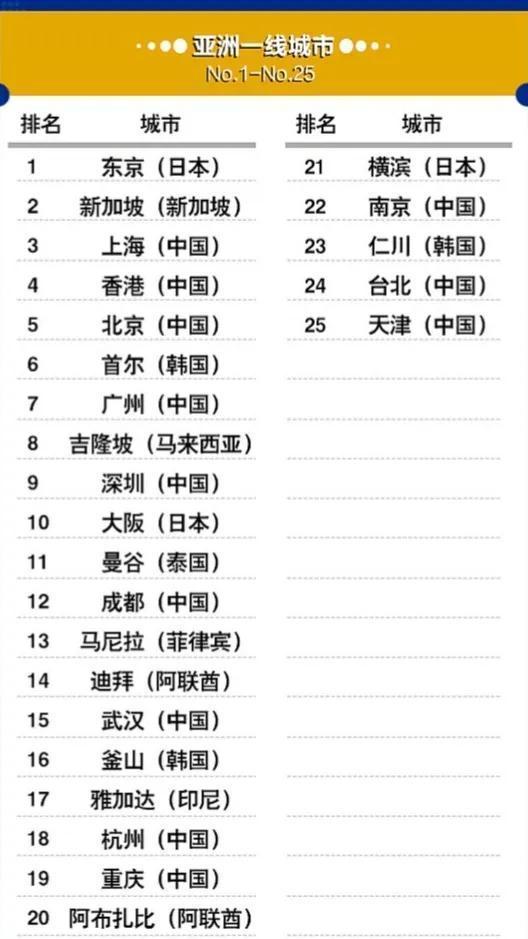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