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法院认定:外国紧急仲裁裁决在新加坡具有可执行性
信息源于:环中商事仲裁

导言
临时措施一直是国际仲裁中的重要手段,对于及时保护当事人权利、实现裁决利益而言尤为关键。近些年来,随着快速解决复杂国际商事争端的诉求不断增多,当事人也越来越多地寻求紧急仲裁员临时救济。众多司法辖区和仲裁机构,包括印度、美国、英国、德国、中国以及国际商会和斯德哥尔摩商会等仲裁机构陆续修订了其相关规则,将这一更新、更便捷的纠纷救济形式纳入其中。然而,在紧急仲裁立法变化的背景下,仍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执行紧急仲裁裁决的障碍,二是紧急仲裁裁决对保护当事人利益的效果。
2022年10月7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对CVG诉CVH案[1]作出裁定,虽然以外国紧急裁决违反自然公正为由拒绝执行,但明确认定:外国紧急仲裁裁决在新加坡具有约束力,具有可执行性。本文将以YasaschandraDevarakonda在Kluwer Arbitration Blog上对该案的评述[2]为基础,与读者探讨紧急仲裁员所作外国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问题,其执行障碍有哪些?是否有立法基础?司法实践如何?为学习交流之目的,环中仲裁团队编译此评论文章,以飨读者。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01、案件背景
2012年,新加坡修改了其《国际仲裁法》(“《国际仲裁法》”),将“紧急仲裁员”纳入该法案第2(1)条中“仲裁庭”的定义之中。但这一修订却并不适用该法第3部分有关“外国裁决”的规定,包括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规定。因此,外国仲裁中,紧急仲裁员以裁决形式作出的临时救济措施在新加坡能否得以执行,一直未有定论。
CVG诉CVH案中,双方当事人从事特许经营业务。仲裁被申请人CVH是仲裁申请人CVG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的特许经营商。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受四种不同的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约束。申请人同时允许被申请人在线上分销其商品。
2020年6月,申请人根据《美国破产法(1978年)》第11章,成功完成破产保护诉讼,后被另一公司收购,申请人公司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化。此后,双方就某些涉嫌违反《协议》的行为发生了争议。被申请人以重大违约和/或预期违约为由提出解除《协议》,因此与申请人的公司集团脱离关系。对此,原告关闭了被申请人在其全球订单系统中的权限,并取消了被申请人此前的未结订单,被申请人则因此认为申请人接受了《协议》解除。
2022年5月25日,申请人向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ICDR)提起仲裁。仲裁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由宾夕法尼亚州法律管辖程序。申请人同时寻求紧急措施救济。在紧急措施的庭审中,申请人主张适用《协议》中所约定的合同解除后的条款(post-termination provisions)。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庭审后提交的材料中,申请人却又主张《协议》尚未解除。紧急仲裁员作出裁决,责令各方当事人在《协议》解除前维持现状。即,作出该裁决的基础是申请人视《协议》为仍未解除。
申请人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执行该紧急裁决,被申请人对此表示反对。被申请人的主要理由是:1)案涉紧急裁决不属于《国际仲裁法》所规定的可以通过《纽约公约》予以执行的裁决;2)案涉紧急裁决超出紧急仲裁员的管辖范围;3)案涉紧急裁决违反自然公正原则。最终由高等法院作出本案的生效裁定[3]。
02、裁定结果
经修订后的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2(1)条所规定的“仲裁庭”(arbitral tribunal)定义明确包括“紧急仲裁员”(an emergency arbitrator)。但是,该条仅适用于新加坡法下的国际仲裁,不适用于本案所涉通过《纽约公约》执行的外国裁决。《国际仲裁法》第3部分有关“外国裁决”的一章中,第27(1)条规定“仲裁裁决”指的是“《纽约公约》所定义的裁决,但同时包括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有关本法第12(1)(c)-(j)条所列事项而作出的命令、指令”,但该章却并没有对“仲裁庭”进行定义[4]。
本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则对《国际仲裁法》的立法意图和计划进行目的性解释,认为该法第2(1)条中“仲裁庭”的定义应当延伸至该法第3部分第27(1)条中有关外国裁决的规定。
然而,高等法院很快就作出了反对执行该紧急裁决的决定,理由是该紧急裁决违反了自然公正原则。针对申请人在庭后陈述中的某些意见,被申请人无法发表意见、陈述其案情。而在紧急仲裁庭审期间,虽然仲裁庭询问了申请人提出的其他意见,但未批准申请人所请求的紧急措施。在向当事人提出的问题清单中,仲裁庭也曾提出相同的问题,要求当事人根据这些问题提交庭后意见。
根据《国际仲裁法》第31(2)(c)条的规定,如果被执行人证明外国裁决具有以下情形,法院可拒绝执行此类裁决:“未向当事人发出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当事人因其他原因在仲裁程序中未能陈述其案情”;第31(2)(d)条规定,“裁决处理的是未经考虑的事项或不在提交仲裁之列,或者裁决书中内含对提交仲裁的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也属于不予执行外国裁决的法定理由[5]。
在考虑《国际仲裁法》第31(2)条中有关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规定时,高等法院认为,尽管申请人有关《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认定涉及后续新案件,但这一问题已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考虑,因而符合该法第31(2)(d)条[6]的要求,但是该紧急裁决却是基于申请人在庭后意见阶段的不同陈述所作出的,且申请人的庭后意见大大偏离了其先前在庭审阶段的立场,最高法院最后裁定,因案涉紧急裁决违反《国际仲裁法》第31(2)(c)条而不予执行。
03、案例评述
新加坡高等法院的上述裁定很可能带动支持快速仲裁程序(如紧急仲裁)的浪潮。通过厘清《国际仲裁法》第2(1)条与其第3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高等法院采取了支持仲裁的方法,以确保外国紧急仲裁裁决在新加坡的可执行性。如高等法院在本案中所言,若不存在其他理由不执行的情况下,应当执行外国紧急仲裁裁决。尽管如此,只要各法域对紧急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执行性存在不同的司法解释,优先将紧急仲裁作为寻求临时措施的替代手段仍然可能存在一些不利后果。此外,《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并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指导,软法中也缺乏统一的准则和方法。
这种情况凸显了仲裁机构、仲裁从业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建立适当司法框架的必要性,以此促使外国紧急仲裁裁决的执行更加统一。必须认识到,承认和执行此类紧急仲裁裁决的最终权力仅属于各国法院。因此,为了快速仲裁程序的成功落地,需要认识到围绕此类程序合法性的司法判例的重要性,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需要与各法域修改立法、主要仲裁机构修订规则同步进行。在Amazon.com NV Investment Holdings Inc.诉Future Retail Ltd.案中,印度法院对这一问题的阐述颇具参考意义。在该案中,尽管1996年《印度仲裁法》没有支持紧急仲裁裁决的明确立法规定,但印度最高法院同样采取目的性解释,适用了法律委员会报告中关于支持仲裁的原则和建议,进而支持了SIAC紧急仲裁裁决的有效性。
新加坡高等法院的裁定也在提醒当事人和仲裁员:虽然寻求紧急措施一向具有紧迫性,但仲裁程序的基本原则不应因此妥协。对于希望规避风险的当事人而言,明确紧急仲裁的曙光并不以牺牲程序效力为代价,而仍应该符合当事人的最佳利益,这也许更令人欣慰。诚然,本案的程序已经随着新加坡高等法院的这一裁定而落幕,该裁定将如何激励新加坡立法机构积极处理紧急仲裁问题以及紧急裁决的可执行性,仍有待观察。
环中观察
鉴于各国立法、司法实践并不统一,关于临时措施紧急裁决的可执行问题一直颇具争议,因此很多专业人士仍会建议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临时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快速仲裁的发展。除了本文提及的新加坡法院和印度法院在上述案例中倾向于采取支持仲裁的目的性解释、认可外国紧急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之外,很多国家对此问题仍未有定论,其根本在于,虽然《纽约公约》没有明确规定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裁决应当是最终裁决,但司法实践中,作出临时措施的中间裁决可能被认为并非最终裁决,不具有终局性,因此不属于《纽约公约》所规定的裁决,不能得到承认或执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对这一问题并非没有指导。《示范法》第17(2)条规定临时措施是“以裁决书或其他形式作出的任何短期措施,仲裁庭在发出最后裁定争议的裁决书之前任何时候,以这种措施责令一方当事人实施以下任何行为”,包括:“在争议得以裁定前维持现状或恢复原状”;“采取行动防止目前或即将对仲裁程序发生的危害或损害,或不采取可能造成这种危害或损害的行动”;“提供一种保全资产以执行后继裁决的手段”或“保全对解决争议可能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证据”[7]。不同于《纽约公约》,《示范法》主要是以临时措施最后实现的内容为标准定义临时措施,与临时措施是以命令或终局性裁决作出无关[8]。只要其内容符合该条定义的“临时措施”的范围,根据《示范法》第4节第17H(1)条的规定,即应当被确认为具有约束力。而按照该定义,此类决定应包括以紧急裁决形式作出的临时措施。如果不具有第17I条中拒绝承认或执行的情形,就应当获得执行,不论该措施是在哪国作出的[9]。因此,在适用《示范法》有关规定的法域内,紧急裁决的可执行性问题相对比较确定,如,全面援引上述规定的澳大利亚、韩国等国。而在非《示范法》法域,上述规定可能仅能起到参考作用。
部分《示范法》法域也会对上述规定进行调整。如,《香港仲裁条例》一方面通过其第35条接受了《示范法》第17(2)条对临时措施的定义;一方面在第61条修改了《示范法》17H(1)条的部分内容,指出:外国仲裁庭就仲裁程序而作出的命令或指示,与当地法院的命令或指示具有同等效力,经法院许可,以同样方式强制执行[10]。因此,经香港法院许可,紧急裁决在香港即具有可执行性。类似地,本案涉及的新加坡《国际仲裁法》也没有完全援引上述规定,却在其司法实践中体现了支持外国紧急裁决可执行性的倾向性判断,明确认定:外国紧急裁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的标准为其是否具有约束力(“binding”)而非是否具有终局性(“final”)[11]。
相比之下,有些法域的法院则不认可执行紧急仲裁员所作决定或裁决的可执行性。在此前的微信文章中,我们也曾与读者分享过[12]。如,俄罗斯法院一直认为只有终局性仲裁裁决才具有可执行性;《瑞典仲裁法》对于仲裁庭下令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可执行性没有规定,但其立法准备工作文件(travauxpréparatoires)则显示,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命令在瑞典无法执行;《芬兰仲裁法》没有关于仲裁员所作临时措施的可执行性的规定,但实践中,临时措施通常不会被视为可执行的裁决。
在我国大陆地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明确了紧急仲裁员所作临时措施的可执行性[13],但从篇章设置来看,该规定仅针对国内仲裁,且修订稿尚未生效。而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14]、第一百零四条[15],中国法院仅为境内仲裁程序提供临时救济措施,包括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对于境外仲裁中的临时措施或紧急裁决的可执行性则没有规定。实践中,我国大陆法院倾向于认为关于临时措施的紧急裁决属于中间裁决,不能根据《纽约公约》得到承认或执行。经检索,环中仲裁团队亦未发现我国大陆法院成功执行境外仲裁庭作出的有关临时措施裁决的案例[16]。
因此,正如本案例评述文章所述,在实际考虑以何种方式申请临时措施时,需要注意执行地有关执行外国仲裁中临时措施类裁决和决定的法律规定,特别关注相关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变化,综合考虑施加临时措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基于所寻求临时措施的形式,采取不同的争议解决策略。同时,各法域的法院作为承认和执行此类裁决和决定的主体,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实现维护司法主权、支持仲裁和保障公正的平衡,也值得共同探讨和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CVG v. CVH, [2022] SGHC 249.
[2]YasaschandraDevarakonda, When Not to Enforce: Status of Enforcing Foreign Emergency Awards in Singapore, 原文参见: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2/12/06/when-not-to-enforce-status-of-enforcing-foreign-emergency-awards-in-singapore/.
[3]CVG v. CVH, [2022] SGHC 249, Para 21.
[4]新加坡现行《国际仲裁法》(2020年修正)第2(1)条、第5条、第27(1)条、第28条,法条参见:https://sso.agc.gov.sg/Act/IAA1994?ProvIds=P13-#pr27-。
[5]新加坡现行《国际仲裁法》(2020年修正)第31(2)(c)条、第31(2)(c) (d)条,法条参见:https://sso.agc.gov.sg/Act/IAA1994?ProvIds=P13-#pr27-。
[6]按照《国际仲裁法》相关规定以及裁定原文,将评述文章原文此处“第31(2)(c)条”校对为“第31(2)(d)条”。
[7]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06), Article 17(2).
[8]Margaret L. Moses,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st Edition, pp. 105-106.
[9]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06), Article 17H(1).
[10]《香港仲裁条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第609章)(2018年修订)第35条、第61条。
[11]CVG v. CVH, [2022] SGHC 249, Para 40.
[12]见“环中商事仲裁”文章:《紧急仲裁员所作决定的可执行性问题》,原文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OD38rSprpZfBrtW0wMJTbA。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庭组成前,当事人需要指定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可以依照仲裁规则向仲裁机构申请指定紧急仲裁员。紧急仲裁员的权力保留至仲裁庭组成为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16]通过关键词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北大法宝、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等数据库,均未发现相关案例。另参见杨伟国,“在中国执行境外仲裁程序中临时救济措施的可能性”;董纯钢、顾湘,“境外仲裁中的临时措施及在中国法下的可执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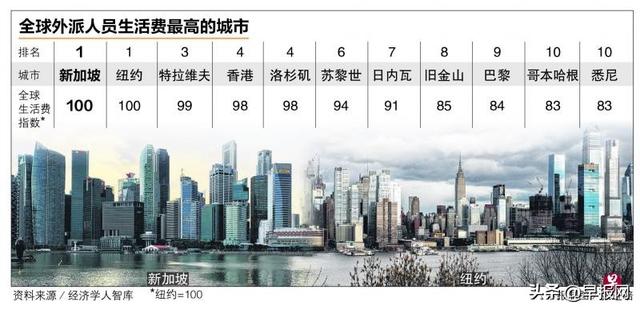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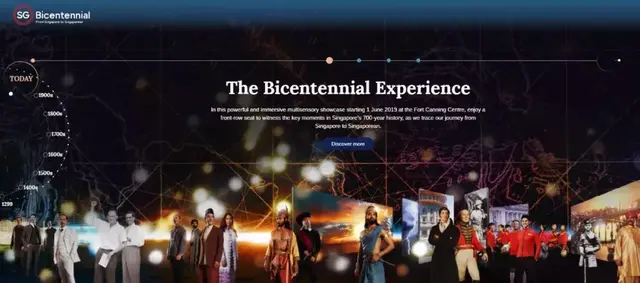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