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女主回归?啪啪打脸
淘宝买买买,闲鱼卖卖卖。
闲鱼用户54%是90后,平均年龄28岁,平均一个月来访近10天,相当于每3天就逛一次。物欲横飞,成为某种习以为常的现象。
有时不禁想:
物品像流水一样从我们身边短暂停留,又快速流走,我们放在物件上的注意力剩多少呢?
小时候最心爱的玩具、老妈做的衣服、前女友织的歪歪扭扭围巾藏哪纳灰了?
阳光明媚的春夏,.导演纳瓦彭·坦荣瓜塔纳用一部电影,设置了一个旧物人群实验。
买下一件东西,丢掉一件东西,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时光机
ไทม์แมชชีน

导演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大学时自学成才,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天才训练营,是泰国最大的电影制片厂GTH的编剧。
《时光机》是他第七部长片作品,获得第15届大阪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女主是《天才枪手》茱蒂蒙·琼查容苏因,这是她和导演第三次合作。
男主是《把哥哥退货可以吗?》桑尼·苏瓦美塔农。

这次茱蒂蒙·琼查容苏因演的小琴是个“凶狠”的断舍离高手。
留学归国搞设计,好不容易接个大单,对方想看看她的工作室。
所以她打算改造自己家,开启”断舍离“之旅。到这,我以为讲的是老套的“自我清理、轻装上阵”之类的,没想到清理旧物只是一个切点,讲的是“人”:
一类人对一类人的挑衅;反过来,一类人对一类人的控诉。
先说小琴所代表的,看似理性的人。
她崇尚快消费。

茱蒂蒙·琼查容苏因饰演这个角色很对味。
眉眼细长,淡淡地装点在脸上,五官间隔远,面相冷清。
日常黑色齐耳短发,一个素白超大衬衫勾勒出简约还有——
乏味。
就像她的主张:丢掉所有旧物,断舍离。再装修成最有逼格的极简风,刚好符合自己作为设计师的品味。
在妈妈看来,这就是乏味。不仅乏味,还很“神经”。
妈妈看上去又太守旧了。
一出场,坐在杂物堆砌的房间,随意倚靠在桌边,拖着粗长的有线麦克风对着老式电视,青筋暴起地K歌。
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都是同一首歌。


阿琴想丢掉抛家弃子的爸爸留下的钢琴,正义凌然地质问:
爸爸走那么久了,现在还有谁弹吗?
妈妈弓着背,拖着脚,慢慢走过来,食指指腹往琴键上一戳——
戳住不放,下巴微微扬:
我有,可以吗?
不要碰别人的东西你懂吗?
是的,这是看似理性的阿琴对看似过分感情用事的妈妈的挑衅。
又被妈妈毫不示弱地呛了回去。

未果,阿琴动员哥哥先整理各自的房间。
泛黄杂志,丢。翻盖手机,丢。
卡通笔盒,丢。歌手唱片,丢。
一边丢,阿琴还一边暴躁地飙着脏话。
轰轰烈烈,“战绩显著”。


直到朋友阿萍来看她,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张CD:
这个也不要吗?
她头都没抬,懒洋洋地说“是”。她侧目瞥见CD在她额前不动了。
才想起来,CD是阿萍以前送的礼物。
萍,我家里太多杂物实在没地方放。你用不着那么激动。
—激动?你不要了不可以还给我吗?我要。
闹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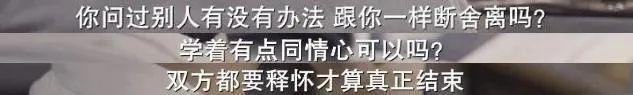
这给了沉浸在“断舍离”快感中的阿琴响亮的耳光:
你不需要的,你忘记的,难道就该丢了么?
别人呢?别人也都忘了吗?
在收垃圾的阿伯载着堆成小山的黑袋子离开,阿琴突然从画面外发射一般冲进你眼前,朝远处飞奔:
我不卖了我不卖了。
破音,焦急。

她还把一包包垃圾扛回家,堆满了客厅。她倒像黑色海洋中的孤家寡人:
我突然有些愧疚。

是嘛?她不过是被朋友突然翻脸而诈尸似良心发现:
原来,被人丢掉自己千辛万苦做的礼物是恼怒而失望的。
就像她在垃圾堆里发现哥哥也丢掉了她一织一线勾出来的围巾:
妈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确很伤人。

她决定把礼物一件件物归原主,不能再像和阿萍一样,将自己设身被动的背叛中,但不仅麻烦,还很尴尬。
就像前男友安哥送的胶卷相机。
是她甩了他。
出国留学时,她一声不吭地和他断了联系。
再见,他在阳光下还挺好看,一点都不像被她丢掉的“垃圾”。
她弯着眉头说着迟来的抱歉。
他听着似乎“与我无关”的话,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
没有回应,她很焦灼:
你可以骂我一下吗?你一言不发反而让我难受。
但你看安哥的表情。望向别处,温和,却憋着一口气,嘴角有点淡淡的笑意。
不是欣慰、不是原谅,像暗自叹了口气,又像发自内心的轻蔑。

再后来,碰见他的新女友,得知以前对她很好的妈妈已经去世,临死前心心念念的还是她煮的汤。
她看着伯母的骨灰,反问:
你当时怎么不联系我呢?
—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复的邮寄、电话、明信片了。
我不能再沉浸在过去,我得靠自己,不该联络你。
遇到好事我很想打给你,可是我不能。遇到坏事时,不知道要打给谁,我也不能打给你。
沉默……

她的出现,也打破了新女友和安哥的平衡,安哥发现自己旧情难忘,和女友分手了。
处于愧疚,小琴去质问安哥。这次安哥情绪激动地说出这么多年的心里话:
你来道歉时我很生气。感觉就像道歉以后就不必负责了,我就一定得原谅你。如果我不原谅你,那就是我的问题,不再是你的问题。
就像你来劝我和女友复合,都是为了不让自己愧疚而已啊。你就承认自己自私,继续去过你的人生就好了。

极简是一种好看的体面。
她却不能再体面了。
小琴像一下被人撕开了伪装,双手挥舞着,扭头气急败坏地急急离场:
我已经道歉了,我都已经说了对不起了。
说了对不起又怎样?把别人像垃圾一样失踪式分手,又想轻轻松松获得原谅求安心?
小琴离开,镜头缓缓地停留在垃圾袋上。
再一次,安哥被她像丢垃圾一样扔在自己生活之外。


安哥虽然旧情难忘,但他也明白,自己凭什么配合你“又当又立”的假象。
更何况,小琴不会变的。
她一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理性到淡漠,形成了一种难以察觉的自私。
而五官浓郁,总是温和充满钝感的安哥 ,反而是另一类人的代表:
看似感情用事,其实深情难自控。
这是第一次,深情对自私的控诉。
第二次控诉,是来自于妈妈。
还是因为那架爸爸留下的钢琴。
木质透出时间蚕食下的酥松感,像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泛黄的琴键上蔓延处细长的裂纹,像是老树跃出土地的根。
她打电话给爸爸征求去留意见。
可那个男人,已经不认出自己女儿的声音,更不要说这件被他一起抛下的破旧钢琴。
哥哥找出来的旧照就像一架时光机。

时光那头,爸爸还弹着生日歌给她庆生,妈妈坐在爸爸身边扯着麦克风唱歌,哥哥和她都笑弯了眼。
对的, 妈妈那么喜欢唱歌,是因为爸爸。
可这头,他们想念的,已经被爸爸彻底丢弃。
回忆错位,让她下定决定扔掉钢琴。
所以她自私地选择在饭桌上和妈妈复述,那个丢下他们母子三人,让她孤家寡母拉扯孩子长大的男人最直接的否定:
他说我们可以把钢琴卖掉。他说他不会回来了。
妈妈停下扒饭的手扔下碗筷,又闭眼举双手喊停,肢体语言抗拒得几乎要集体出逃:
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

阿琴还是残忍地强灌:
他已经不要我了。你不要一直活在过去。你想怀念的,不是我们想怀念的。
妈妈努力维持的生活“原样”,被她一锤子砸个稀巴烂。她一会儿猛拍桌子,一会儿又元气全失地干瘪下来,眼神下望,失魂落魄:
我自己好好的,为什么要一直提。是要我忘了他,你们要负责吗?
你要忘就自己去忘,为什么要逼我忘记?
阿琴不懂,她以为劝妈妈遗忘负心的爸爸是好心。可在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妈妈难道不知道爸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吗?
她当然知道,却不想忘记,不过是因为:
那不仅仅是一个永远不会回家的男人,那还是一个女人永远无法倒回的、被辜负的美好青春。
而现在?庞然大物倒了,根都拔了。

第二天,她叫哥哥带妈妈出去玩。
趁机卖掉了钢琴。
她让妈妈觉得留不住一个男人,连一点念想也捍卫不住。
门,几乎要被敲烂:
你出来和我谈谈,你把钢琴弄到哪里去了?
在一片愤怒、哀伤的叫声中,她缓缓戴上耳机,打开主动降噪模式,平静地闭上眼睛。
讽刺地是,临行前,妈妈还邀请她一起出去玩。
还忍不住关心:回来要不要给你带吃的。
没想到,遭受的,是她蓄谋已久的突袭。

在妈妈的嚎叫中,有一句话给人当头一棒:
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和你爸爸一样自私!
是的,自私。
这种残忍的自私仿佛会遗传。
从安哥的质问到妈妈的败北。
这场理性和感性的极端博弈,以阿琴的胜利告终。
而这也是我说的,片子大胆的可看之处。
它用一个绝对主流、绝对时髦的女主,骗你跳进她的逻辑思维里,再狠狠踹你一脚,告诉你:
看似主流、时髦的女主并不一定正确。
而这种不一定正确的野蛮反倒胜利了。
阿琴的极简断舍离看似是一场自我清理,实质是一场对他人粗暴的圈层管理。
以自我为圆心画圈,有用的物件、人事留下来;没用的人,“无谓”的感情丢出去。
即使面对自己最好的朋友阿萍、至今仍旧深爱自己的前男友,含辛茹苦背负父亲伤痛拉扯她长大的妈妈,她都用自己的标准,以绝对的强势判定圈内物件的来去。
越高效,越自私。
末了,还在新年临近时搬去酒店。留下哥哥收拾烂摊子。
新年夜,电视里烟花绚丽。
窗外,也烟花绚丽。
她蜷缩着身体坐在床上,没开灯,烟花已经足够亮。
她该是欢喜的。很快,极简工作室就能如愿以偿。

第二天退房。
清洁阿姨来到床前时——
那张唯一的全家福“时光机”被撕得稀巴烂。
只迟疑了几秒,"时光机"就被丢光扫净。
白色的床单一扯,平整如同没存在过任何旧物件。

阿萍又来找她:你和安哥怎样?
我想他真的放下跟我的纠葛了。我上次和他谈,口气都很正常,我想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而且他很快就会跟新女友搬去新加坡工作了。

明明最后一次见面,她摔门而去,他们不欢而散。
自私,这次已经渗进她骨头里。
想体面很简单,不用归还旧物,不用与他人和解,打个响指——
撒谎就好了。
因为此后,长情的妈妈和安哥再没有镜头。他们不再有为自己的主张申辩的机会了。
而阿琴还能表演。
刚说完慌,就有一个长镜头:
泪水一点点艰难地在眼角被分泌、凝结、汇聚……
啪嗒。

当泪水从眼角滑落时,她自己顿了下——
自己被自己的眼泪吓到了。
哭什么呢?表演么?
恐怕她自己也不明所以。
一个细节,当她面无表情,毫不留恋地打开堆满旧物的房间门时,刚开的灯像闪电打在旧物上。
惊悚如同恶魔降世。
不过没关系,很快她就能在极简的空间里接受访问,优雅阐述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理念。
这是极简的全面胜利,也是自私的全面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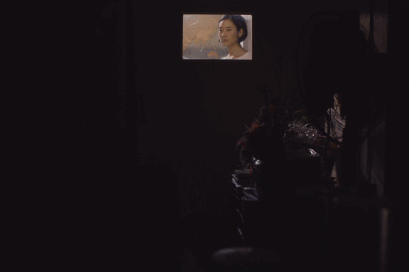

想起有个朋友学美术的,装修时迷恋过一阵子极简。后来再去她家,极简的墙上挂满了各种杂物。
老公只穿过一次的衬衫、孩子稚嫩的画,婆婆送的平安福……
她说,后来不怎么迷恋极简了。极简需要不定期狠心丢掉一些东西,可是好些东西舍不得丢。再说,烟火气也挺好。
其实。简约和烟火气没有绝对,理性和感性没有对错。
自私和长情也不永远割裂。
我们不需要强求形式上清爽而刻意斩断情感。
也不该放纵自己沉浸过去无法自拔。
但如果没有情感,极简的墙面不是雅净,只是一片空空如也的惨白。
理性到冷漠,甚至自私的程度或许更高效,却让人像一个干巴巴的机器,快速运转,没有温度。
而深情看似迂腐,愚蠢,却不该被嘲笑。它有它的可贵,值得被尊重。
毕竟,人类最可爱的地方,不在于他们的高度统一。
而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还时常处于某种混沌状态。
不永远冷酷直达未来,也不永远浸泡在过去。
介于两者之间,才是常态。
爱德华有一套“决定性混沌”理论,认为:
人类本身都是非线性的,与传统的想法相反,健康人的脑电图和心脏跳动并不是规则的,而是混沌的。混沌正是生命力的表现,混沌系统对外界的刺激反应,比非混沌系统要快得多。
摸摸你胸口的心跳,第一次和喜欢的人对视能怀揣一只鹿,闭眼冥想又能像滴水穿石;
听听你的脑海里喷涌的想法,音乐的节奏像海浪,猫的绒毛触感像白云。
我们温暖又复杂,才是人类特有的“人味”,不是吗?
极简滚蛋,混乱靠边。
时常友好,偶尔鸡贼小自私,就挺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