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富陈天桥皈依佛教,捐10亿美元研究人脑:众生皆苦,不如自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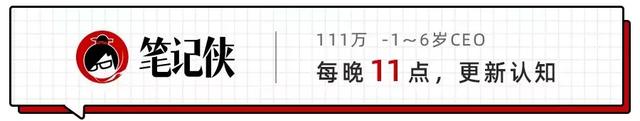

内容来源:内众生皆苦,不如自渡。创业邦(ID:ichuangyebang)首发,笔记侠经授权发布。封面设计 & 责编 | 丽丽第 3877 篇深度好文:7128 字 | 18 分钟阅读
精选笔记·科学
本文优质度:★★★★★+ 口感:红豆
笔记君说:
26岁白手起家,创立盛大,31岁公司上市,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陈天桥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突然长时间消失,现在专注于脑科学研究的公益事业。
缘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对创业、科学、宗教、心理又有何看法?
以下,enjoy~~
作为盛大网络董事长兼CEO,陈天桥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1999年白手起家,他和妻子、弟弟等人在上海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创办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陈天桥和妻子雒芊芊
2004年,盛大获得软件银行集团4000万美元的融资(这是当时互联网领域最大的投资),同年,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陈天桥也以88亿资产在《胡润2004IT富豪榜》中排名第一,当年,他31岁。
当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还不是阿里巴巴或者腾讯,而是陈天桥的游戏运营公司——盛大网络,在这个位置上,盛大甚至保持了近5年时间。

不过,陈天桥“志”不在游戏,之后,盛大奇袭新浪,折腾“迪士尼互动娱乐传媒帝国”和平台战略。但盛大的基因里实际上就没有平台,哪怕把旗下游戏、文学、视频等业务用户全部打通,也只是一个个分散的Zynga,而不Facebook。
之后,盛大定位从内容公司专为技术驱动型公司(支付、云计算、精准广告投放),2009-2011年又冲上了一个小高峰,但2011年后业务整体下滑。
拼尽全力推出的盛大盒子被广电一纸文书叫停,文学板块卖给了腾讯,游戏也慢慢拼不过网易、腾讯。最核心的原因是:陈天桥生病了,患上了“惊恐发作”。
这种病的英文名叫Panic attack,为急性焦虑症状之一,患者会突然出现强烈的恐惧症,感到“死亡将至、大难临头”或“失去自控能力”的体验,同时伴有呼吸困难、心悸、胸痛或眩晕、呕吐、出汗、面色苍白、颤动等。
每次可持续发作几十分钟,过程非常痛苦。有些人甚至会连续不停地发作。
Panicattack在长期工作压力过大的创投圈或刚刚失去亲人的人群中发生概率不低,但很多人对这种病症缺乏了解,发作后被送到医院也不知道自己其实经历了惊恐发作。
舆论导向这块石头更是亚得陈天桥喘不过气。那时候发生了传奇玩家玩游戏致死事件,还有玩家因为装备问题跑到盛大公司自焚,数以千计的中学生因玩游戏荒废了学业,连人民日报都以头版批评盛大。
这对从小就是学霸,对游戏无感的陈天桥来说,心里十分委屈。
他内心十分渴望大众能够承认自己,而不是被贴上“电子鸦片贩卖者”的标签:“我年纳税过亿,却没办法昂头挺胸的向大家说出这件令人自豪的事”。
2010年,陈天桥携家人移居新加坡,将盛大私有化,同时出售其在子公司的股份。
之后,陈天桥又被检查出癌症,他开始卖掉盛大所有运营业务,转型做投资,并将“脑研究”作为了事业的下一站。
为此,2016年陈天桥捐助10亿美元致力于神经科学的研究。
据统计,这笔钱捐赠是中国富豪在全球著名学府前沿科学领域的最大笔捐赠,陈天桥计划捐赠十年,每年捐赠一亿美元,希望帮助那些和他一样遭受过痛苦的人。
笔记君注:其中,包括他和妻子雒芊芊用于建设陈氏研究院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的1.15亿美元,这1.15亿美元,是人类在基础学科研究方面获得的最大一笔捐赠。
自此,陈天桥和妻子雒芊芊从新加坡搬到了硅谷,监督其捐款的使用,并在San Jose买了两百亩地的一个校园作为研究基地。
陈天桥在外媒Medium的采访中,谈到了他投巨资成立“陈天桥和雒芊芊脑科学研究所”推动脑科学研究的种种心路历程,也谈到了佛教信仰和大脑研究之间的关系,科技造成的问题需要科技来解决的逻辑,以及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涉及创业、科学、宗教、心理及哲学。
以下是陈天桥接受Medium(以下简称M)采访的访谈要点:
一、压力
M:随着盛大的出现,你很快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你也谈到,在管理企业时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陈天桥:我在1999年创办了公司,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专注于业务。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压力下挣扎。
即使是在2008年,当时我们的股价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我也并没有感觉好一点。在2009年,我们筹集了12亿美元把游戏业务分拆出来。公司发展很好,但我想我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积累起来了。
当然,我的妻子总是一直在陪伴我,这对我帮助很大。但我还有1万名员工,他们都指望着我。
我还记得有次正在睡觉,大早上,我的一个同事打错电话,给我拨了过来。
然后,我突然惊醒,心跳也变得很厉害,砰,砰,砰。还有一次,在飞机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心脏病发作了,但这不是,而是一种惊恐发作。

所以我意识到,我身上可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2010年,在我的惊恐症发作后,甚至癌症也被诊断出来之后,我们决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我想我的整个人生都开始改变了。
M:离开自己建立的公司,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
当然,这对我来说非常难。在我搬到新加坡后,我们至少花了2到3年的时间来适应。
我会回头看看中国,看看这些竞争对手,那时候我把他们看作是第二梯队的参与者。他们逐渐地来占据我们的市场份额。你想回去,即使你知道你不应该回去,所以我内心非常挣扎。
但我一直在跟我的妻子讨论,她也一直在鼓励我。她说,大多数人只能爬上一座山,但也许你可以爬上第二座、第三座。我可以开启我的人生新篇章。
许多人沉溺于过去的成功,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一切。
所以我总是和我们这一代的企业家交谈,告诉他们,“你的生活不仅仅是这家公司,请抬头看,你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
但我能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挣扎,因为竞争,因为各种压力,他们的生活非常紧张。
二、宗教
M:现在你是一个佛教徒,这是你重新选择的一部分吗?
陈天桥:坦白说,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真正相信宗教。
我的妻子会和一些佛教大师交谈,我总是说:“不要浪费时间。”但是当我36岁的时候,我被诊断出癌症,那时候我意识到佛陀说的是对的。
我有很多钱,我拥有我想要的一切,包括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但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快乐呢?为什么我有恐慌症?为什么我总是没有满足感?
佛陀说,我们必须在内心寻找答案。
事实上,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受苦,这也是佛陀教导的基本原则:生命是痛苦的。
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但生命的确是一场苦难,因为即使你有了快乐,有了漂亮的房子,也终究会失去这一切。最后,你必须面对死亡。最后,你必须经历这种痛苦。即使在这一刻你是快乐的。所以我说,“这是对的。”
所以,当我们决定重新开始,把我们的钱捐出来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减轻这种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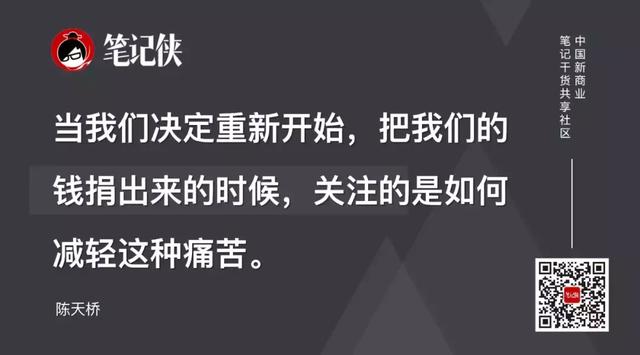
当我们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一些人说:“不,不,不!你为什么选择痛苦?疼痛是一种症状。你应该治愈疾病,因为没有疾病,就没有痛苦。
我告诉他们,“不,疾病也是一种症状。”疾病是死亡的征兆,疾病是通往死亡之路。死亡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疾病。我们必须承认,死亡不是我们能治愈的。即使在硅谷,也没有人敢说能够做到。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能治愈生命的痛苦,这是治愈死亡的最好方法。如果死亡没有痛苦,那就像人睡着了一样,而治愈它的方法就是学会接受它。
最后,我们认为,死亡和痛苦是我们未来应该关注的焦点。之后我们去见了许多科学家——到目前为止,几乎有300名科学家。
三、科学
M:你知道科学研究的重点是神经科学吗?
陈天桥:神经科学是理解我们大脑的瓶颈,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部分。
我一直告诉人们,尽管我们关注的是神经科学,但我对这个研究所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与大脑和精神相关的不同学科的垂直综合研究所。
所以不仅包括神经科学,还有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神学等等。我想把所有这些不同的学科结合在一起,但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了神经科学的瓶颈,因为我们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痛苦?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意识是什么?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自于宗教,哲学,社会学,以及所有这些。
甚至在几千年前,哲学家们也问自己这些问题,没有人能阻止你这样想。但是自上而下的方法面临着一些问题,因为现代人总是说,“给我看看。”
M:是的,他要看证据和数据。
陈天桥:是的,“告诉我确切数字”,神经科学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学科。
让我们以精神病学为例,到目前为止,精神病学诊断仍然主要依赖于面谈,它仍然是主观的。
我和精神科的院长交谈:“你什么时候可以安装成像?什么时候可以安装某种生物标记来检测抑郁症?”我觉得我有一些精神障碍,我相信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一些化学物质或者我大脑里的东西。
举个例子,当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知道这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我还是很害怕。
但我吃了一片药后,恐惧感就不见了。这就是所谓的恐惧,精神抑郁,你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检测它,但它就像精神科疾病一样停在那里,没有进展。
神经科学是理解我们大脑的一个瓶颈。
我对此非常失望。我们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检测到癌症。但到目前为止,大脑和精神方面的研究仍然和50年前一样,没有进展。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合适时机。
四、慈善
M:为什么通过慈善的方式?10亿美元是一大笔钱。为什么选择这种方法而不是进行投资?
陈天桥:我们研究了不同的方法,来改善一些慈善投资的方式,但我认为对于大脑和精神领域研究来说,必须选择一个非盈利性的方式,因为我们缺乏对大脑的一些基本方面的理解,这是一个瓶颈。
所有这些研究都还在大学或研究所,这些都是非盈利组织。
举例来看,埃隆•马斯克曾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初创公司Neuralink能够实现将芯片植入大脑。我们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谈过,他们说不可能,那是50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想要给科学家提供基本的支持,我们想要解决根本问题,不是只有赚钱能让我们满足。
五、投资
M:关于大脑和神经科学领域,你也参与了风险投资。在这些领域,哪些领域你看到是在增长的?是药物吗?还是脑机连接?
陈天桥:就像我说的,这是基础研究,这是由人类的好奇心引发的,人类喜欢寻求真理。但是,在基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我认为它可以满足人类的三种需求。
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大脑治疗,处理一些快速增长的精神障碍疾病,我认为这将是未来的一大挑战。
不仅是精神障碍,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症,这些类型的疾病总有一天会到你身上。

抑郁症已经成为头号疾病,我想我们可以帮上大忙,我们真的相信,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基础研究将为这一领域做出很大贡献。
下一阶段是“黑客大脑”,只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才能显著提高满意度和幸福感。
第二个问题我们称之为大脑发育。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造福人类,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然后让汽车,房子等一切事物能够读懂你的想法,让这个世界满足你。
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改变你的身体,我认为这些都是未来的杀手级应用。
第三个是我们的终极愿景。我们试着回答这些比较大问题,比如什么是意识?我们是谁?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拟的?这似乎太学术化了,但对我和许多人来说,这真的很重要。
几千年来,这些一直都是全人类的终极问题。我想我们这代人可能会发现这个真理,也许我们是幸运的。
六、哲学
M:世界只是感知?
陈天桥:这是另一个哲学问题。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真的相信世界是虚拟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肉眼,能有显微镜那样的功能,当然,显微镜比我们肉眼更真实,对吧?
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应该看到的是细胞里的原子,我可以在空气中看到有多少个水分子,这里有多少氧原子在周围漂浮,这是真实的。但我看到的是经过我们的肉眼编辑的东西,这是知觉。
另一位科学家,我们的导演大卫·安德森,他可以操纵老鼠的情绪。当他打开一个按钮时,鼠标突然变得非常平静;当他打开另一个时,老鼠突然就会打架。
所有的攻击行为都是由一组神经元控制的,这是我的另一个假设——我们是化学机器人。
在未来,也许我可以戴上头盔,下载一些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激活神经元——也许我可以为你创造一个世界,这是有可能的。
M: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
陈天桥:我只说事实,没有好坏,没有价值判断。当然,好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技术,尤其是神经科学技术,在未来会有多么强大。
七、人工智能
M:我们看人工智能,目前的方法似乎是收集和挖掘尽可能多的数据。但这不是人类认知的工作方式,而且似乎已经远离了人类大脑的模式,把人类从这类工作中移除是一个错误吗?
陈天桥:人工智能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这些。
我总是用我两岁大的儿子举例子,他总能在街上认出这是一个叔叔还是阿姨,他永远不会叫错,但是一台电脑必须经过数百万次的训练才能知道“这是一只小猫,这是一块饼干。”
现在我们只教会机器一种价值表达:效率。

机器提高了效率,机器总是知道如何快速找到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机器统治世界,它会说,“杀死所有的老人和病人,因为他们对于资源是一种负担,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教会机器公平和同情,但是当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定义的时候,如何教会机器呢?
M:有些人担心人工智能将成为一种威胁,你害怕机器人统治世界吗?
陈天桥:我认为可能存在有两种威胁。
一是机器人会抢夺人类的工作,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科技将为人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有一些痛苦,他们可能需要时间来接受教育或训练,但对人类来说,我们会适应。
第二个担忧是,机器人可能会进化出意识,然后超越我们。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已经计算得比我们快得多,但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意识,一定存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奥秘,就像一台没有装对软件。
也有些人说,机器有机器的权利,就像人类有人权一样。他们有变得更聪明的权利,我们不应该让机器实现人类的价值体系。也许有一天,机器会变得有自我意识,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
我认为,可能是,但那将是一个新物种。为什么我们要煞费苦心去创造一个新的物种呢?地球上有如此多的人仍在遭受痛苦和饥饿,许多物种仍然面临灭绝,为什么要去创造新的物种呢?我认为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混乱的。
八、虚拟现实
M:你刚刚提到对虚拟现实非常感兴趣,作为一个在数字娱乐领域发家致富的人,你如何看待塑造未来的方式?
陈天桥:我一直说虚拟现实的终极版本是梦想。我们的大脑足够强大,可以创造出一个虚拟的现实,可以模仿现实的声音和感觉,这是最令人惊叹的。

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必须依靠谷歌头盔?我们对自己的大脑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能控制自己的大脑,继续做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每当我从一个好梦中醒来时,我总是很感到很低落。
如果我能在晚上继续我的梦呢?如果你能继续做梦,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我一直说那将是娱乐产业的终结者。
我已经请教了科学家,包括我的研究所,是否能模拟感觉。
目前,你只能模拟声音和视觉效果。如果你能感觉到什么,那么大脑就可以模仿一切。所以我认为虚拟现实的最终版本应该来自我们的大脑本身,因为它是如此强大。
M:我们已经讨论了技术对我们的幸福可能带来影响。如果我们能在虚拟现实技术上做到这一点,是否会有风险?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吗?
陈天桥:我认为这只是增加了趋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之后,很多电影都是从香港和美国引进的。它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那时候我是个好孩子,我妈妈唯一一次责骂我的时候,是我在朋友家里看电影的时候。
她说,“你为什么看这些东西?他们会让你沉迷,他们会让你……。电视连续剧,电影,他们会给你介绍坏的东西,让你不去学习,不去上班。”
然后,在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当我在盛大的时候,我的用户的父母,他们每天都批评我,说我们的产品让人上瘾。
我认为,如果技术更加生动,这一趋势将会得到加强。你总会发现有些人对它上瘾,就像一个药物。这种药物是如此的强大,它可以控制你的大脑,让你感到快乐。
但如果它和药物有同样的效果,我们的政府可能已经有了监管了。我认为,即使VR能产生更多让人上瘾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药物监管作为基准,我认为它可以被监管。
总结
M:最后,你对我们的技术和脑科学的发展方向感到乐观?你认为我们能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快乐吗?
陈天桥: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点悲观的原因。
我认为技术产生了很多问题。我所能做的就是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减轻这种技术的可能后果。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非常糟糕的后果。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加入笔记侠官方圈子,与牛人一起交流进步,付费圈子&免费圈子 都有好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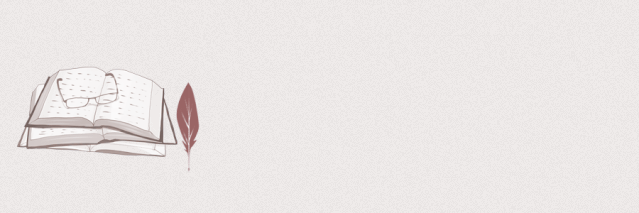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