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中国剧团在东南亚》︱回应:戏剧研究与文化史、跨国史对话
张倍瑜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博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张倍瑜与四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中国剧团在东南亚:离散地的巡回表演,1900-1970年代》(Chinese Theatre Troupes in Southeast Asia: Touring Diaspora, 1900s-1970s)。本文为作者对四篇评论文章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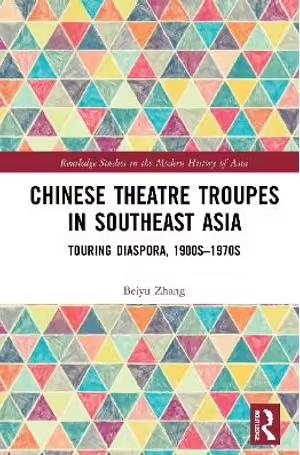
2021年5月,拙作Chinese Theatre Troupes in Southeast Asia: Touring Diaspora, 1900s-1970s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暂定为《中国剧团在东南亚:离散地的巡回表演,1900-1970年代》。非常感谢此次书评召集活动,让我得以学习到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书评人对本研究细致、深刻、旁征博引的评论。在等待书评反馈的时间里,我的内心是惴惴不安的,因我深知该研究仍有许多未尽之处,内心感到愧疚。但是,阅读四份书评后,让我深受启发,看到了未来继续探索的可能性,同时也为遇见四位知音般的书评人感到欣喜,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合作和探讨。借此机会,我想在这里先回顾一下该研究成型之路,以及对书评人提出的意见作进一步的回应和解答。
一、研究起源和历程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期间,修了两门对我影响颇大的课程,一门为《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另一门为《历史学方法论》。两门课的教授都是文化史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史经典著作的解读、分析和批判对我的研究有着深刻影响。修读这两门课时,我接触到了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著作,他曾论述到,历史学和人类学陷入了对立二元论:对历史研究而言时间很重要,但是对人类学而言,社会结构更为重要。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强调稳定性,而历史研究强调变化和偶然性,于是,稳定与变化便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阻碍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萨林斯研究西方殖民者与夏威夷土著的“相遇”(encounter),他认为这种相遇虽然给土著社会带来了巨变,但是外部力量导致的变化总是能被当地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再生产规训和内化,成为当地人世界观的一部分。萨林斯认为文化人类学研究需要看到历史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需要结合其社会内在的文化结构来分析。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需要从认识论上打破二元对立,意识到文化是变与不变的综合体,任何一种文化变迁都是一种再生。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可以看作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历史书写。在这种跨学科思维的影响下,我开始构思另一种“相遇”,一种由移民导致的同族群(co-ethnic)的相遇。中国剧团旅行至离散地,与海外华人的相遇发生于某一偶然的历史时刻,但是,正如书中潮剧一般,无论是出于外部何种力量而发生了变化,其方言为纽带的乡音、对原乡浪漫的想象是由海外华人内在文化逻辑决定的。
一直以来,历史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科研究一样,有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讲究的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论证分析和结论。但是在出版专著的时候,我要展现给公众的不仅仅是我的博士研究,而是一个故事,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这一点也是深受文化史的写作手法的影响。文化史的书写要求我们去写生动的历史、人的历史。故事里有人物、情节、高潮和后记,这些元素往往并非按传统的、严苛的时间排序发生,对这些元素的深耕细作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具体的文化叙事,以及从叙事中抽离出来的文化阐释。它们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诉说着不同时代下个体与民族国家命运的交集或分叉。
二、对书评提出问题的回应
1. 对本书结构上的质疑
拙作是一本以中国剧团在东南亚流动、跨界和旅行为线索的历史研究,涉及的表演艺术体裁冗杂,区域分布广泛、时间跨度长,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的确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在著书过程中,如何将零散碎片的剧团逻辑地串联起来是困扰我的一个难题。有评论人指出“相对于通贯的专著,本书在体例上更接近于一册主题相近的专题研究合集。各章之间虽有线索相连,但在第一部分中,无论对象差异或时间跨度都有过大之嫌,对读者而言,阅读时难免感觉跳跃过快,其间尚有不少空白不曾填补”。我曾尝试按传统的时间线索来安排,但是发现不同的剧团和巡演在时间上或重合、或时间跨度过大,并不理想。书中每个剧团诞生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受当时不同社会思潮影响,所传达的意识和思想也各有不同,可以说每个剧团都是对变化着的、不同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反映,因此更切合主题式的结构。
在经过一系列考量后,我最后决定将时间和主题结合起来,首先,整本书按时间顺序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的是二十世纪初至二战后中国与东南亚走廊上的旅行剧团,第二部分以1950年代开始的冷战为分界线,论述了冷战环境下中国剧团在海外的“头脑与心灵之争”。在大的时间框架下又可按主题细分为不同主题的旅行剧团的巡演历史。唯一的遗憾是,第一和第二部分的时间衔接并不顺畅。战后到1949年期间,中国歌舞剧艺社的南洋巡演应加入单独成为一章。著书过程中,因资料缺乏,未能写成。
为何要如此安排?而剧团的选择依据为何?首先要明确的是,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从中国不同城市出发前往东南亚旅行演出的剧团多如牛毛,许多更是除了一个剧团名字,毫无资料可循。光是我书中探讨的第一类方言戏班,便可细分为潮剧、粤剧、福佬戏(福州方言)、梨园戏(闽南方言),而每种“下南洋”的方言戏班多达数百个。我作此书的目的,并不是罗列一份史料索引(当然前辈们所作的史料索引的确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在此深表感激),而是选取具有足够详细历史记载的剧团,结合它们旅行过程中当地社会的背景,透视“相遇”背后的文化意义,以此来剖析中国与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华人社会的文化互动。
第二,书中所选剧团并非毫无逻辑可言,而是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每个剧团都是在特定社会思潮影响下,诞生于不同历史阶段且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在介绍具体旅行剧团之前,我用第一章来阐述了海峡殖民地的剧场的物质空间的形成和演化,这么安排的原因是跨域的、互相联系着的剧场空间的形成是剧团做跨国巡演和旅行的物质基础,为接下来的巡演做铺垫。首先登场的是潮剧戏班。潮剧代表着潮汕方言、潮汕族群的区域文化联系。紧接着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的上海中华歌舞团的诞生及其海外巡演。中华歌舞团旨在海外宣扬中华民族意识,唤醒侨民统一的民族情怀。抗日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孕育了一系列以救亡、爱国、救国为主题的表演形式。从武汉出发的救亡剧团下南洋进行筹款义演,向离散地输入爱国主义的同时,宣传激进的左翼思潮,为战后新马华人的反殖抗英运动埋下了种子。冷战的国际格局改变了潮剧的文化功能,使其从一个民间的传统乡音,变为文化外交的手段,再而经香港的商业包装,潮剧电影成为东南亚娱乐市场的畅销品。
由此,我们看到潮剧如何与外部环境的适应、产生新的文化形式。以潮剧为线索,这一主题追溯了乡音和原乡情节是如何贯穿始终得连接离散地和祖国,在变与不变中形成一个综合体。最后到了1960至197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离散地华人社会处于隔离状态,香港的左派艺术团担任了文化使者的角色,分别在新、马建国的关键时刻进行表演,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的一个动态关系。
2.关于史料的运用和选择
书评人提出本书史料分布不均,许多论述只给人敲了边鼓之感。例如, 评论指出“史料的分布不均阻碍了本书更深刻地剖析东南亚华洋与当地人杂处的演出环境”。另一份评论也指出,本书主要依赖的华文和英文报纸资料无法全面地展现华人与其他族群的交流。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华人与本土族群的互动在不同东南亚社会呈现差异化,这种差异化直接导致了华人的表演艺术和文化呈现不同程度的杂糅融合。例如,石峻山博士研究荷属印尼的福建戏中杂糅了闽南语、马来语及荷兰语,当地爪哇人表演华人的布袋戏亦是家常便饭; Caroline Chia认为源自福建的高甲戏在菲律宾表演时融入了大量的他加禄语。我书中的潮剧戏班和电影、中华歌舞团、抗日救亡剧团和香港银星艺术团的足迹主要是在新马地区,而新马地区与东南亚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在于,当地华人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因为自二十世纪初,新马社会(包括海峡殖民地)的“新客”移民大量增加,他们深受祖国社会思潮的影响,更易成为中国剧团的支持者。
在这里,与“新客”相对应的是“土生华人”,前者是鸦片战争后英殖民者从华南地区招募而来的劳工和苦力,又被称为“猪仔”。他们大部分是迫于生计而南下,对家乡和祖国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也可以说是更加“中国化”的一部分侨民。新客华人在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引导下,更加依赖族群内部的宗族和血缘网络,形成较为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华人社会。不同的是,后者“土生华人”是在15世纪南下从事商贸活动,且已与当地马来人通婚的闽南籍后裔。他们于欧洲殖民者涉足东南亚之前便形成了一个富裕的阶级,在语言和文化习俗上都已经本土化。印尼和菲律宾华人的表演文化呈现与当地人的杂糅和交流,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土生华人占主导地位,例如,印尼土生华人有自己的报纸,这些报纸所使用的语言杂糅了福建方言和马来语。虽然新马地区也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土生华人,但是其经济势力已很大程度上被新客赶超。在新客的主导下,新马的华文报纸成为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少部分土生华人则主要阅读英文报刊,如The Straits Times。
在跨域跨文化的框架下,史料往往呈现分布广泛而零散的特点,因而学者需要对史料展开筛选,而这种筛选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一定的逻辑支撑的。在著书过程中,我的逻辑便是依据旅行剧团主要涉足和停留的当地社会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对史料展开筛选。由于我研究的剧团主要活动的地方是受新客影响较大的新马地区,在史料上自然集中于华文报刊,这是由我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的。
虽说没有发生表演和语言文化上的杂糅,但是我在书中尝试去弥补新马华人跨族群交流的这部分论述,通过剧场的建筑空间去构建一个打破“分而治之”的种族主义秩序。由此,读者看到了土生华人的望沙湾剧团融合了阿拉伯、马来和中西的文化元素,暹罗女演员用马来歌曲为华人庆祝春节,游艺场开放的空间设计为各族群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物理空间。这么做的目的是将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景观复杂化、情景化,让读者了解到华人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即使是在新客占主导的新马地区,仍然有着跨族群融合的例外。
另有评论指出,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上,相当倚重于报纸围绕剧团演出所作的报道。此一方法用于专门分析左、右双方立场的篇章时便恰如其分,但在用以讨论离散地受众之反应时,则难免因媒体对夸大而失之片面”。我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涉及到非精英阶层文化(也就是不存在官方书写的史料时),报纸、回忆录,甚至是地方民间的志略都是可利用的资料。学者不必要拘泥于史料是否权威,是否有夸大之嫌,因为即使是所谓的“官方”档案,也难以逃离被构建、被筛选、被夸大的嫌疑。本质上,我们所写的历史只有努力去靠近真相,而不可能复原真相,因为历史学家使用的任何资料都已是经过层层构建的了。要还原一段仅存在于短暂时空中的剧团历史及当时观众的反应,首先要找到关于这场巡演的报道。报纸作为第一手资料,虽然有可能被操纵而夸大,但仍旧是最合适的选择,研究者能做的就是避免按图索骥地使用报纸的报道,而是进行“逆纹理解读”(read against the archival grain)。我在书中除了报纸之外,还利用了口述史和回忆录,视觉资料,例如,唱片封面和海报。事实上,关于离散地观众对“左”和“右”的文化输出的反应,我的观点是他们并没有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囊中之物”,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潮剧电影:潮剧这一以方言为纽带,构建着浪漫的侨乡想象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突然于冷战期间出现的,而是拥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延续性。许多老一辈华人收集潮剧海报和唱片卡带,将这些物件视为集体记忆的体现,足以从侧面印证剧团表演对当地华人产生的影响之大。


作者在马来西亚槟城田野调查过程中偶遇当地华人收藏的旧戏本和潮剧磁带
另一则关于史料的评论指出香港银星艺术团在接受新马国家邀请演出时,是否有史料来研究其节目的调整和决策过程。评议人的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研究官方表演团体和民间剧团的本质区别:谁来书写它们的历史?在前两章中,我谈到广东潮剧团的性质在建国后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从民间的戏班转变为国家文化外交的行为体,这也是为什么在叙述潮剧团前往香港(及未能成行的新加坡)表演时,我花了大篇幅铺成整个过程,包括节目的选定、决策的摇摆不定、行前对演员的思想工作等。作为文化外交的潮剧,已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一部分,自然有官方的档案存留。较之建国前的潮剧戏班,此刻的转变对潮剧而言是幸运的。正因为有了档案,才有更多后人去书写他们的历史。回到问题本身,香港银星艺术团虽然是左派的文化团体,但并不直接接受中共领导,它依旧是一个民间的艺术团体,坚持左翼现实主义思潮来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不公。缺乏官方的“背书”,使银星能够以模棱两可的身份进入新马,但也正是因此,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广东潮剧团那般官方档案对其巡演进行详细的记载。但是我相信,这中间肯定有曲折的决策过程,如果此研究早十年进行,可以通过口述史采访当时剧团的成员。可惜在我著书时,大部分银星艺术团当年的成员已不在世。庆幸的是,银星艺术团将最后呈现出来的演出节目单出版成纪念刊,让学者得以管窥当时的情景,并以此书写这段演出历史。

1963年香港银星艺术团前往新加坡与李光耀合影
3. 对潮剧的若干问题的回应
社会主义时期的潮剧改革本身便是一个值得单独研究的课题。中山大学的林立博士就这个话题写过一本专门的论文,可谓非常详尽。在本书中,潮剧改革是一个时代背景,是潮剧由民间小戏转变为国家文化外交手段的关键一步。因此,关于潮剧改革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并不是本书主要关注点。由于篇幅原因,无法一一解答,我在这里将选择若干和本书宗旨相关的潮剧改革问题加以回应。第一,有评论问道大陆的潮剧改革抢救和发掘了一篇传统剧目,对日后海外宣传标榜的“传统文化”起到何种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它涉及到Eric Hobsbawm的经典论著《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我们所谓的传统,实质上是当权者出于现实的需要,对过去的文化资源加以征用、改编以巩固新的民族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历史延续性。社会主义改造初期,许多旧戏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被禁演。一夜间,戏班应缺乏剧本和题材而无法正常演出,观众又对新兴的工农戏不感兴趣,曾经一度造成戏改工作的困难。可以说,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挖掘传统剧目的工作被赋予了紧急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挖掘的过程是对旧剧目里的封建迷信、糟粕落后情节加以删减和改良,例如,男女私奔的戏被重写成妇女追求婚姻自由。
回到问题本身,潮剧作为“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输出时,其“传统性”不仅在于挖掘出具有历史价值的剧本,更多的是对内容的“优化”和“改良”,这点也在离散地华人报纸上得到宣传和强调,很大程度上助力了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的“传统文化”的宣传,甚至刺激了离散地的潮剧团进行改革,本地潮剧团纷纷提出要模仿新中国的戏改,剔除他们表演中不合理的元素。同时,新加坡要求剔除封建残余落后的元素和当地的反黄运动诉求是一致的、因为反对黄色文化运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我在书里讨论银星艺术团时介绍过这个背景,但是可能在潮剧这边显得有点脱节,其实是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有评论问道戏改废除了童伶制度,由成年男子演唱小生声腔,导致男女同腔,大小生的作品是否曾进入东南亚市场?如有,看惯女小生的南洋市场对其艺术评价如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这种政治环境下催生的新声腔是否引起关注?回答这一问题有一定难度,因为南洋长期以来并没有专门从事戏曲理论、声腔研究的艺术家。大部人戏班艺人将唱戏演戏看作是一门糊口的手艺活,对艺术上的创新还是保留传统,并没有过多研究,因此缺乏相关评述资料。我只能从华文报纸对大陆潮剧电影的报道略作推断,总体说来,东南亚观众并没有像侨乡观众般对新的声腔产生抗拒。当然,报纸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也比较明显,比如《南洋商报》会报道新中国戏改的成功,赞扬社会主义艺术的优越性,所以整体上所报道的内容都是积极的,极少会涉及侨乡戏改负面的消息。另一方面,南洋观众(包括潮汕人)一直以来还是粤剧和京剧的爱好者,而其他这些剧种是没有童伶声腔一说的,男女同台同腔早已不是新鲜事,由此可以推断东南亚市场更容易接受大小生这一转变。
第三,评论人提到南洋现代剧场与潮剧商业化无关,因为它们没有演出过潮剧,而潮剧仅在游艺场中驻演使观众获得一种现代的文化消费,反观京剧粤剧模仿西方戏剧进行改良而更具备现代性。我不认可此论述。首先,我在第一章中论述现代剧场时以演出粤剧的梨春园为例,并不表示潮剧没有进入剧院演出。事实上,这也和剧院老板本身所属的方言族群有关。梨春园的老板为广府人士,所演剧主要为粤剧,而潮剧也有自己的剧院,如哲园和怡园,便位于潮汕人聚居的地方,经常有侨乡和曼谷的戏班前来演出。曼谷唐人街方面的剧院,更是被潮剧戏班垄断(第二章中有详细论述)。潮剧如同其他方言剧种一样,也模仿西方戏剧进行了改良,尤其是曼谷戏班的改良人士前往上海学习文明戏和当时风靡一时的机关布景,并且在引入南洋时,根据南洋观众的喜好进行了改良(见第二章)。还有评论问道为何没有提及南洋的儒乐社,这是因为儒乐社已属于离散地自发组织的社团,即不做旅行表演,也并非严格意义上来自中国的剧团。再者,儒乐为当地享有社会文化资本的“精英”业余娱乐爱好,而不是职业剧团,因此不符合本研究的范围。
四位书评人给出的点评不仅对我的书作出了精湛的概括,而且在很多地方提出了各自的理解,超出了我自己的视野。例如,有书评人提出“潮剧分香”的模型,又提出潮剧“大众化”和“艺术化”这一看似悖论,实则相辅相成的关系。还有评论将潮剧搭建的跨国走廊与著名的“汕—香—暹—叻”贸易体系或“海洋潮州”作类比。对我第二部分“危险的接触地带”(dangerous reaching out) ,有评论人提出了补充,指出这种危险感不仅体现在戏剧,而是整个冷战年代各行各业的一个普遍心态,包括出版、印刷、外交、商贸等。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可以开启另一个关于冷战时期华人身处夹缝中是如何在当地社会的各行各业谋求发展的研究。
三、结语
最后,我想回到该研究的初衷。2012年初到新加坡求学时,我所住的组屋楼下一到中元节便会搭上简陋的舞台,唱上大戏或是歌台表演。台下的观众多为当地年长的华人,因为舞台设置在居民区,旁边便是巴刹(kopitan/hawker center),常有马来人和印度人驻足观赏,不同族群的孩童嬉笑打闹。我因而对这种独特的文化表演空间产生了兴趣,在本地朋友的带领下,我又相继参各种场合的戏曲表演,包括当地华人庙宇的酬神戏,社区乐龄人士举办的粤剧、马来西亚槟城九皇诞、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华乐团交响乐演出等,在这里,艺术的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即有着乡音为纽带的原始的祭祀表演,也有着现代化的剧院演出。我开始对离散地如此丰富多样的华人表演文化遗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频繁地走入舞台后与演艺人接触,起初,我想通过口述访谈的形式挖掘离散地华人表演文化流动的历史,但是发现存在许多困难,因为采访对象年纪都不算大,能回忆的历史也大多从新加坡建国(1965年)后开始,这样短的时间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够沉淀和积累的。偶然的机会下,我翻阅到了新加坡口述档案馆当年的一组访谈材料,遇到了我书中序言所述的白言、叶青、王沙这些老一辈下南洋的艺人的口述史,他们大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南下,一生都在南洋各埠从事着颠沛流离的演艺生活。这些剧团与演员们本身便是搭建中国与东南亚这条跨国跨域走廊的桥梁,是一个世纪以来侨乡/祖国与离散地文化互动的见证者,个人的故事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起伏交织,勾勒了一副鲜活的历史文化图景。我希望以此书开启戏剧研究与文化史、跨国史等议题的对话,更多地看到舞台背后的戏剧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是如何与不同的社会建制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

作者(中间)在本地朋友带领下观看新加坡的庙宇酬神戏

新加坡本地艺术爱好者为庙宇戏班作画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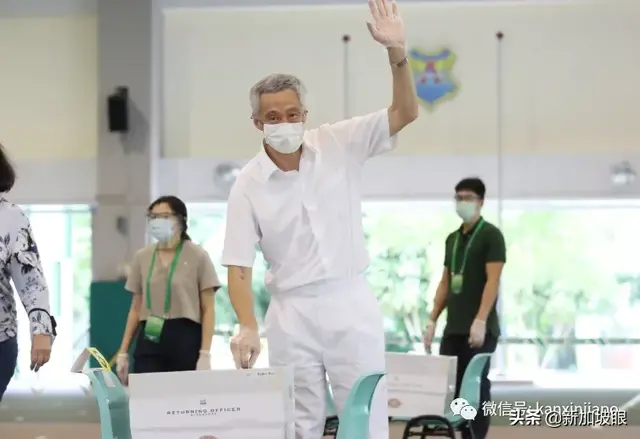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