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访问记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和江湖一样好玩。

2008年12月,接受作者采访时的金庸
“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浏览1966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年,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位于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金庸的书房最为豪华。我忍不住随处看看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书架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间,秘书送来热腾腾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粤语打来电话:“查生想跟你通电话。”随后我听到金庸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先生,吃过晚饭没有?”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
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我们在采访中用普通话,闲谈则多用粤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我听了这种“小说家言”,不禁笑道:“我听余先生讲,他和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7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

2010年8月26日,上海世博会澳门馆里的“金庸书房”。书房里展出了金庸当年在《明报》工作时用过的屏风,上面雕刻着《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我采访过的学者近况。一些学林趣事,他听得兴味盎然。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不赞成有‘金学’”
江湖上传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这四位,我都见过。记忆里,第一个见的是黄霑,并不是谈他的歌词,而是谈他参演一部舞台剧。难忘黄霑带着朗朗笑声和不遮拦的粗口,想约他另找时间做长篇专访,没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他三位我倒是都长谈过。
当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即刻说:“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倪匡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他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后,陶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我和陶杰第一次见面是在晚上12点以后,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金庸听了我的转述,微微一笑:“陶杰妈妈跟我同乡,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乡,吃的东西差不多。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我们聊起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说:“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我便说:“钱锺书也是无锡人。”金庸说:“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很锋利。”
一谈起做学问,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对《红楼梦》有独到见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冯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我说:“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金庸朗声道:“我不赞成有‘金学’!”

1963年,香港艺人张瑛(左)与金庸签约购买《倚天屠龙记》电影版权
“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一生功业,以办《明报》为重,有人还写了专著来研究。我说:“听说您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金庸说:“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我接话:“您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没想到金庸说:“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我问:“您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金庸说:“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的同样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我说:“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年您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金庸说:“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40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问:“您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金庸答:“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在聊起报界前辈的近况后,我问:“您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金庸说:“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我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这些同学就接受这个观点。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以前英国人统治的时候,跟英国是完全一样的。”
我问:“您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金庸说:“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的,有人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1960年,金庸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左起)谢贤、金庸、南红和梁素琴
“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
作为“金迷”,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我说:“您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勾来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我随即说:“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金庸说:“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便问:“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金庸说:“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我又问:“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金庸说:“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我笑道:“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金庸也笑道:“《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我说:“其实您在创办《明报》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您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小说里?”金庸一听,不禁微笑:“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80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金庸说:“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
金庸想了几个问题,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从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金庸认为这条路线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金庸说:“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近代,所谓真的历史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金庸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高的分数。
接着,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杀掉了。金庸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古代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金庸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访问金庸两年后,他终于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86岁。(文/李怀宇)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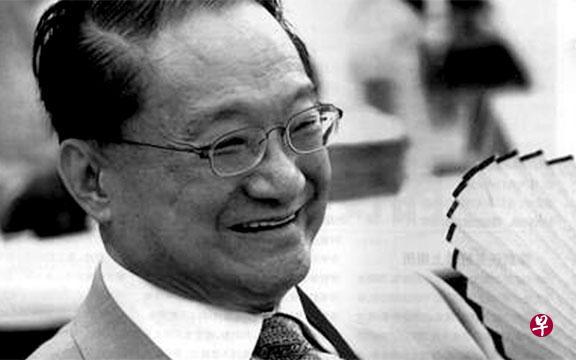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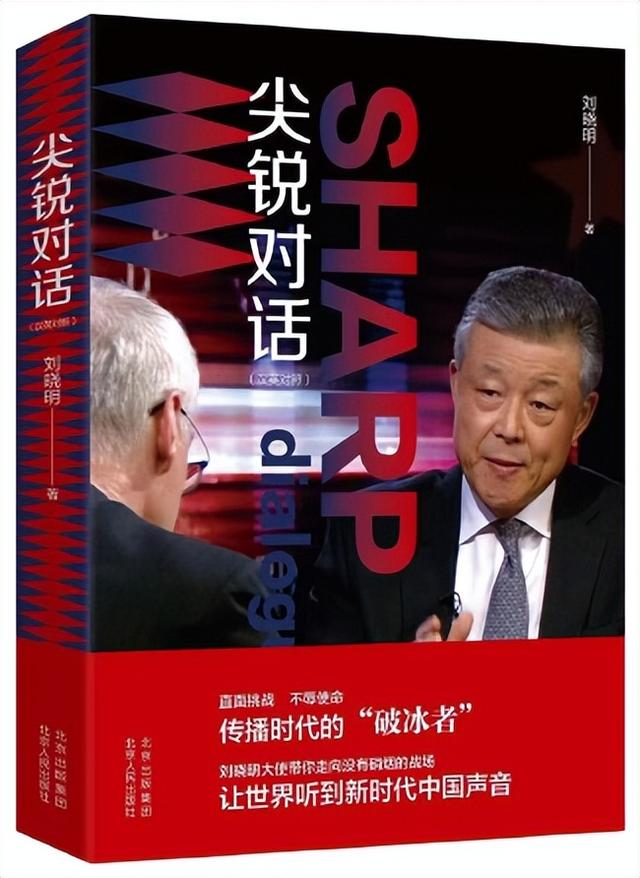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