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事件不了了之?专家:调查复杂,许多疑点待解
2018年11月,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孩,在中国健康诞生。报道称,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并且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基因编辑婴儿幕后的“操刀手”,是来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
消息一经公布引起巨大震动,贺建奎的行为被科学家们强烈谴责。“基因编辑”也引发了“人造人”是否允许、未来是否将沦为“超人”统治一般人的社会等等对人类伦理以及生命安全问题的探讨和争议。
然而事件过去近两个月,除了此前媒体报道的“卫生部门已介入调查”之外,没有任何进展的披露。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业内人士、中科院院士邵峰,试图对该事件及背后要素进行科普意义的探究。
此前,邵峰曾就“基因编辑”事件发声,认为该技术“没有什么科学创新,只有对伦理和道德无底线的突破,亟待需要在法律、伦理上有一个清晰的界线”,并希望相关部门应对此立法。
“基因编辑事件背后调查因素复杂”
北青报:基因编辑事件,目前后续进展如何?为何公众感觉不了了之了?
邵峰:据我了解,目前仍处在调查处理中。最终处理结果,卫生行政部门一定会按程序发布。
北青报: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处理?
邵峰:因为这个过程调查起来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贺建奎是南科大的一名副教授,所以学校这个层面是怎么让他进行这个基因编辑实验的?他毕竟是有学校编制的,这个经费是哪儿来的?学校各层面的审查委员会知不知道这件事?再者,他还得跟医院合作,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不了人工授精的。他可以做基因编辑,但不能给人取精子卵子,所以一定要有医生跟他一起做。所以哪家医院或哪几家医院参与了?那么医院也有伦理委员会,怎么审查通过的?这些疑点都尚未明了,都需要在扎实的调查后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北青报:即使调查出结果了,现在没有涉及这方面伦理的法律依据,能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邵峰:不管怎么说,最后走什么法律依据,都得先调查,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先调查清楚,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学校、医院参与人员、学生,还有地方监管人员,包括志愿者,都得调查。只能先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再决定怎么办。对于基因编辑这类行为,卫计委也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如果触犯了这方面的规定,大学应该开除这个人等。但现在很多情况还没调查清楚就开除,这肯定也不合适。
北青报:除了开除,会有更严重的处理结果吗?
邵峰:那就得看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其他环节,可以去找对应的法律依据,因为就这件事本身没有司法依据,但比如做基因编辑用于受精卵,最终有没有造成人身伤害,比如对那两个女孩来说,她的基因是否已被人为破坏,涉事人员是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是有法律规定可以对应处理的,但现在还没有进行鉴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需要司法解释,需要法律方面的专家进行分析。
“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永远不让俩孩子知情”
北青报:现在问题是,作为基因编辑人,两个孩子已经出生了,以后怎么办?
邵峰:这个非常非常难办。现在业界也讨论,就觉得是不是要出一笔钱让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去到谁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部门进行跟踪,就跟装GPS定位一样。其实这里面最大的挑战是,这两个女孩将来能不能结婚?要结婚的话,生孩子就会遗传下来。
北青报:您觉得她们允许结婚么?
邵峰:这个没有答案。
北青报:您认为怎么处理最合适?
邵峰:要我处理这个事情,就是永远不告诉她们是被基因编辑的,允许她们就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合适最好的选择。
“这个个例还不足以影响人类基因大池”
北青报:您作为业内权威专家,对这件事的最大担心是什么?
邵峰:我们主要担心两个安全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两个孩子将来有可能不健康,但咱们正常人也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所以如果出现不健康就只能自己去面对。还有一个安全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对于人类种群的影响,但是这个个例对大面只是“点”位影响,一小滴水还不足以改变整个池子。
北青报:为什么说不足以改变整个人类基因池子?
邵峰:因为这个个例还不足以带来对这么大种群的影响,就这个“小点”,对种群还造不成大规模的影响。下一代可能就只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而已,那只是基因互相的代际之间的影响,只能往下传,因为它不是传染病,所以这一个点位不会造成整个种群的基因影响。你往整个基因池里放,立马就稀释掉了。
北青报:所以最大的危害到底在哪儿?
邵峰:是基因编辑这个大门一旦开了,人类很快就完了。我们知道人身体里的基因有2万多个,所有一切都由这些基因决定,就是所谓DNA的概念,现的生物技术,可以随意地去改它(基因),你想改成啥就改成啥。应该说这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生物科学最革命性的技术。任何一个物种都能被改,比如你想让一个狗发绿光,你也可以让它多长条胳膊都可以,你可以任意来做这件事。这个技术非常强大。但非常可怕的是,稍微训练过的人,有个实验室就能做。这个技术的门槛极低,一个掌握这门技术的人拿个几万块买点设备就能做。
北青报:但国外已有基因编辑的医疗运用,这又是什么情况?
邵峰:人类有两种细胞,一类是体细胞,一类是生殖细胞。简单来说,除了精子卵子之外都是体细胞。国外有人在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疾病,针对的都是体细胞。比如有些人因为某个基因的突变失明,用这个技术来编辑眼睛里的细胞,有些失明可能就能恢复视力。再比如现在做得最多的是肌肉萎缩,在干细胞里把坏的基因恢复,这样肌肉就不会萎缩,国外在推这个东西。但国外严禁在精子卵子里使用这个技术的,也就是说不能在生殖细胞里做。因为在体细胞里做编辑,如果不成功,像肌肉萎缩最多可能就是导致一条胳膊废了。但如果在精子卵子里做,影响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贺建奎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恐怖,因为就是在生殖细胞里做了基因编辑。
北青报:您刚说到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很好操作,可能一个研究生就能做这件事。现在是否还有人在做这件事?
邵峰:在北京是不太容易让人去做这件事的,像北大清华这些学府,伦理委员会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就像我们研究所,我们要知道你做这件事,立马就是开除。学府、医院其实是有伦理委员会的,这次事件目前说是发生在民营医院内,要是在正规公立医院,伦理委员会肯定过不了。现在只能说是没有刑法相关的规定,但行业的行为法规是有的。就像我们实验室做超级细菌,如果搞个超级病毒,容易得很,这种杀伤力巨大。但是科研界医学界都是有法规规定的,不是说你想做任何一个病毒你就能做。每个研究单位都有个伦理委员会,这个伦理委员会不会让你做这些事情。
“伦理委员会是把双刃剑”
北青报:在这类实验中,伦理委员会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邵峰: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的科研文化体制还不够健全的地方。在西方国家伦理委员会的权力很大,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你拿小白鼠做实验,要做之前你要清清楚楚地把小白鼠用多少只、什么时候拿它干什么、做什么样的解剖、做什么样的实验,你要写得一清二楚,交给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批了才能做,否则学校就可以开除你,这个严格到即使这一次的程序批了,下一次做实验的时候把小白鼠换成小黑鼠,就要重新走一遍伦理流程,改任何一点都要重新审批。
北青报: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
邵峰: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各个学校也有伦理委员会,医院也有。要做一个实验,我们也要做伦理审批流程,我们的实验不涉及人,都是用动物做实验,所以伦理这些东西其实没有西方那么严。
北青报:那如果把这个审查加严呢?以最高的规格来要求,是否就能避免基因编辑?
邵峰: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不必要的严格规范,对研究又有影响。我们现在打造科创中心,科研水平的提升很重要。像我知道新加坡做小鼠实验的规定是,任何实验,最终都不能导致小鼠死,要让小鼠死必须是人为的促死,但不能是实验直接导致它死亡。但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规范,小鼠在实验室死了就死了,因为有时候就是要看,这个药我打了五只,它会死多少只,要做这个统计。但新加坡不可以,只能在小鼠要死没死的时候,人为地去促使它死。这就是他们的伦理规范。
北青报:这其中的差别在哪?是伦理的界定问题?
邵峰:这就是他们的伦理界定,但这样的规定也造成了科研人员一定的困扰。但就是有这种伦理规定,它是有戒律的。所以为什么国外实验室很少有人做猩猩、猴子这些灵长类的实验,因为灵长类和人最接近,所以涉及的伦理规范更高,就是限制你做。
“基因编辑在没有建立规则时不能做”
北青报:在没有规范形成的背景下,如果是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这件事危害大么?
邵峰:这个不像新药的研发。比如我们要研发一个感冒药出来,这一套程序是很成熟的,你得一步一步审查。现在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虽然有些西方国家是可以的,但是国内基因治疗过程还没有形成这一套规范,它是细胞治疗,这样的科技手段并不像药物,比如药监局批了药就是安全的,咱医生就可以用药了。但基因治疗有没有效果不好说。作为新生事物,要建立一整套流程,也需要专业的人来配合做这个事,说白了因为都是新事物,很多人也不了解怎么才合适。换句话说,现在都还没有足够多的专业的人可以来给这件事立规矩。
北青报:您的建议是什么?
邵峰:没有伦理的立法是肯定不行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希望会推动中国生命安全的立法。关于生命医学的伦理立法,我们也写了相关的报告。因为这个门一旦打开了,非常可怕。
人物介绍
邵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带领的团队,在病原菌入侵和人体防御机制的研究方面,领跑全球,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期刊上频频亮相。2016年,邵峰曾就韩春雨基因编辑技术研究遭质疑事件,向河北科技大学校长致公开信,建议河北科技大学按照国际惯例启动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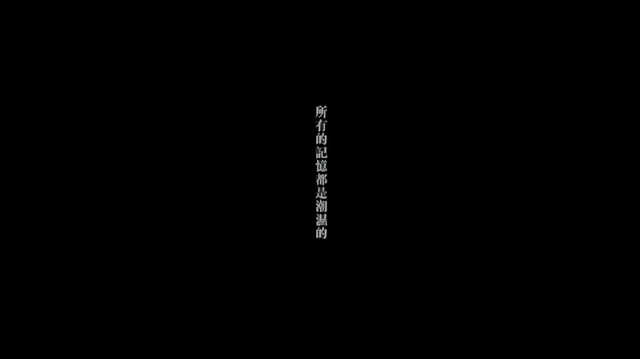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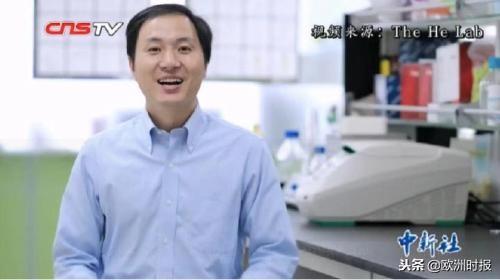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