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19世纪澳洲华人研究及其社会生活史转向

一、19 世纪澳洲殖民地“华人问题”的产生
澳洲殖民地的历史始于1770年英国库克船长抵达澳洲东海岸,宣布英国对澳洲大陆享有主权,随后英国陆续在澳洲建立了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北领地及塔斯马尼亚这六个殖民区域。华人与澳洲历史亦有着漫长的渊源,据传早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船队曾从帝汶岛南下,抵达今澳洲西北部。19世纪早期开始,已有华工零星地由香港、新加坡等处抵达澳洲,从事农牧业与垦殖。随着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清王朝海禁政策日益废弛,陆续有商船将华人劳工运送到澳洲。1847年,由英国驻中国的德记洋行安排,一艘名为“宁罗号”(Nimrod)的商船从厦门搭载120名中国人于1848年10月2日抵达悉尼港,这是有确切记载的第一批入澳华人。1852年,英国殖民当局公布了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等地发现金矿的消息,来自欧洲、美国、中国等地的淘金者开始蜂拥而至。据澳大利亚学者估计,在1855—1856年间到达澳洲的华人多达27272人。大多数华人淘金者来自香港和广东。
随着华人的大批到来,“华人问题”(Chinese Question)开始在澳洲殖民地浮现出来,其最直接动因是来澳华人性别的严重失衡。19世纪50年代的华人淘金工和乡村雇工全是男性。据当时的人口统计,1861年,在新南威尔士约有13000名华人男性和2名华人女性,在维多利亚大约有25000名华人男性和8名华人女性,从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单身汉社会”(bachelor societies)。很难确切统计这些华人男性的婚姻状况,据文献中零星记载估计,约1/4至一半的华人男性已婚。1868年,牧师杨(J.W.Young)所做的一份报告称,维多利亚殖民地18000名华人男性中,大约有8000名在中国有妻子,也即保罗·苏(Paul C.P.Siu)所说的“已婚单身汉”(married bachelor)。无论已婚还是未婚,淘金热的确带来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华人男性入澳,加剧了澳洲殖民地本已严重的性别失衡。
在当时澳洲白人的观念中,大量单身男性聚集是危险的。传统的基督教伦理认为,女性是促使男性“文明化”的力量,家庭则是保持社会正常秩序的稳定器。由于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华人男性被认为与大量的道德失范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相关联,包括强奸、同性恋、恋童癖、嫖娼、赌博、酗酒、抽鸦片等,严重影响到澳洲殖民地的安全和稳定。同时期报纸上开始大量刊登针对华人的尖锐批评。从19世纪50到90年代,澳洲殖民地议会和媒体都在不断讨论如何解决华人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事实上,英国在全世界的许多殖民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曾出台政策,以提供财政资助等方式鼓励华人劳工携带妻子同行。然而,鼓励华人妇女入澳并没有得到殖民地主流社会的认可,因为担心会在澳洲迅速繁衍出庞大的中国人口,其数量足以压倒欧洲白人。保罗·帕克斯(Paul Pax)在1852年提出引入其他非白人女性,比如马来女性,作为华人男性的妻子。而总体上看,基于澳洲殖民地白人社会普遍对华人的厌恶和偏见,因此不认可异族婚姻(intermarriage) 是华人性别失衡问题的解决之道。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推行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出台了《限制移民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全面禁止华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可以说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对“华人问题”所形成的既定观念驱使的结果。

二、澳洲华人研究的传统视角及其反思
二战以前,澳大利亚史学界已有研究在澳华人的著述问世,主要以研究殖民地时期尤其是淘金热中的华人为主。 不过,早期的研究大多基于白人种族主义立场,围绕“华人问题”展开,呈现出单向度、类型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对澳洲华人恶意中伤,竭力散布“黄祸论”,为“白澳政策”辩护。在史料运用上,主要局限于英文史料,包括殖民地时期的政府报告、人口统计数据、移民档案、入籍记录、法庭记录、警察记录,以及大都市报纸、杂志和排华集会(anti-Chinese meeting)记录等其他出版物。这些文献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男性,受制于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或者“19世纪思维”(nineteenth-century thinking),本身就充满了殖民主义偏见。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些材料以及进行表面化的解读,对于“华人问题” 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偏见的引导,形成关于华人家庭生活的刻板成见。
1.个体、家庭以及女性群体的缺失
19 世纪在澳洲的华人男性被认为没有家庭生活,除非他们返回中国,或是极个别情况下妻子也移民过来。杨进发(C.F.Yong)认为,“缺少家庭生活是华人社区最突出的特征”;凯瑟琳·克 罗宁( Kathryn Cronin) 称华人男性“缺少女性和家 庭的陪伴”;维维恩·柏雷奇(Vivien Suit-cheng Burrage) 将“缺少家庭生活” 视为一个悲剧性的因素,导致华人社区无法健康、正常运转。这些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华人女性群体的存在——作为妻子、母亲、女儿、女仆或者其他雇工,同时也忽视了那些与华人男性建立亲密关系的非华人女性,包括欧洲白人女性和澳洲土著女性。此外,对于华人男性在中国国内的家庭,即亚当·麦基翁 (Adam McKeown)提出的“跨国华侨华人家庭”(transnational oversea Chinese family),早期的研究者也基本没有关注过。来澳华人男性的家族关系,如父子、兄弟、表亲等,都不在研究范畴之内。在官方报告中“华人”往往是一个匿名的群体,很少提及个体,除了极少数富有、杰出的华人。这些研究缺失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关于19世纪澳 洲华人史的单向度的分析框架和巨大的信息真空,将 19世纪澳洲华人史书写为没有家庭的男性的历史,华人女性、非华人妻子以及她们生育的孩子,都被视为奇特的例外,而非华人社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如同 1857年7月23日亨利·帕克斯在《帝国报》 (Empire)上的评论所说:“(华人男性)这样一伙人完全不能适当地融入本地人口,对国民持久力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能落地生根,他们无助于国家构成,他们只是他们自己。”
2.跨种族交往(interracial relationship)的污名化
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发生亲密关系,被视为少见的、不符合自然天性的、不可接受的现象,因为华人和欧洲人之间存在着巨大而不可逾越的界限,不仅仅是基于种族、生理因素,更是由于文化、语言以及生活习性等的深刻差异。由于缺乏家庭 生活,金矿地的中国男性经常光顾妓院,也时常引诱白人女孩。1881年悉尼杂志《公告》(Bulletin)刊登了一则故事“A Celestial Lothario”,讲述华人蔬菜小贩约翰(John)引诱纯洁、浪漫的白人女孩伊万杰琳(Evangeline),后来被女孩的哥哥发现后打跑。这类《公告》中的故事将华人男性类型化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小贩“John”,因有机会光顾白人家庭的门廊,从而形成对上层白人女性的威胁。
而那些与华人交往的下层白人女性,则被塑造为堕落、丑陋、遭人嫌弃的形象,由于其本身也是“社会垃圾”,因此无助于华人男性的道德改善,最终自己也会陷入悲惨的命运。1861年,在悉尼郊外的“华人村”棚户区(Bark Huts),21岁的白人女孩伊丽莎·戴维斯( Eliza Davis) 的孩子出生就夭折了,这一事件引发了殖民当局召开质询会,因为孩子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个中国劳工。包括《帝国报》在内的多家悉尼报纸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还去伊丽莎家做了实地调查,在报道中详尽描绘了这个非婚同居家庭的赤贫,以及迪克“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消瘦,衣服打满补丁”——典型的华人男性形象——崇拜偶像的野蛮人、宗教和道德极度贫乏,整个华人村都充满了 污秽、邪恶。伊丽莎的故事迅速被类型化为下层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交往会带来贫穷与堕落的悲惨故事,建构了关于这一类跨种族交往的不道德话语。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告》等报刊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激烈言论,警示华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交往以及生育混血儿,会对英国种族纯洁性造成污染,并衍生出一系列对于华人男性的道德指斥,包括频频光顾鸦片烟馆、嫖妓、引诱白人妇女等,最终在政策层面触发了限制华人移民的立法在殖民地各州先后出台。而像迪克和伊丽莎这样的底层男女个人的选择和声音,则被淹没在甚嚣尘上的关于异族婚姻的污名化观念之中了。
关于当时异族婚姻的数量很难精确统计,1868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在维多利亚大约有50—60名欧洲女性与华人男性结婚;而截至1877年,异族婚姻的数量大约为217。187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南威尔士大约有350名欧洲女性与中国男性同居或结婚。根据殖民地政府的婚姻登记,19世纪下半叶,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异族婚姻数量达1000,而据估计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非婚同居的数量与此相当或者更多。可以与上述统计相互对照的是关于混血儿的人口统计,1901年,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总共有约3000个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儿,主要居住在新南威尔士(1041)、维多利亚(1002)和昆士兰(800)。这些混血儿被贴上“杂种”(hybrid or half-caste) 的标签,代表着虚弱、危险和污染,破坏了纯洁的欧洲血统,是不同种族相遇的负面结果。鉴于当时存在华人后裔因害怕被歧视而隐瞒血统的情况,上述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了。安·柯托伊斯(Ann Curthoys)、克罗宁、安得烈·马库斯 (Andrew Markus)等学者的研究中注意到,对种族混合的恐惧使得殖民地时期的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以及跨种族交往持有非常负面的刻板成见,即认为华人男性由于缺乏家庭生活,导致普遍的道德堕落,而只有同样贫穷、堕落的白人女性才会选择与他们结合。

三、社会生活史转向下的几个新研究路径
二战以后,由于国际移民的增多,澳洲学者对于华人移民群体的兴趣也与日俱增。1966年,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推行种族平等的多元文化政策。1972 年,中澳实现关系正常化。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促使澳洲学术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华人移民史的热潮,并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以往研究中的种族歧视和对少数族裔的偏见。这样一种研究立场的根本转折形成了澳洲华人移民研究的鲜明特色。
首先是一些学者作为华人后裔,对华人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更深刻的了解,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比如吉恩·基廷斯(Jean Gittins)于1981年在墨尔本出版《从中国来的淘金者:金矿场上华人的故事》(The Stories of the Chinese on Goldfields) ,以写实手法再现了澳洲金矿场的华人生活。基廷斯出生于香港,并在香港度过了前半生,父亲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华人。抗日战争期间,她曾被日本囚禁了4年,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由于从小就听家族长辈讲澳洲淘金华人的故事,她的这部介于传记文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作品,充满了真实可感的细节。还有像马来西亚华裔学者杨进发,先在新加坡上学,后去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0 年移居澳大利亚,在南澳佛林德斯大学任教,主讲东南亚华侨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社会史著作《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 1901—1921年》(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以比较开阔的视野考察了澳洲华人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团体、文化生活 等。华裔学者亨利·陈(Henry Chan Min-his) 出生于移民商人家庭,他大学毕业后辗转于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等的大学,从事历史学的教育与研究,尤其致力于对华人移民史的研究,并参与推动了一些探索历史遗迹的项目。1993年,他提出在澳大利亚中国社区研究中引入女性、婚姻、家庭等视角,并在 2001年开创性地提出“侨乡路径” ( Qiaoxiang/native place Approach ) ,即对19世纪澳洲华人的研究不能仅局限在澳洲,还需要返回中国,追溯华人与其故乡的关联,将中国家庭生活与文化传统纳入研究视域之内。
其次,也有一些与华人并无血缘关联的澳洲学者,纯粹基于个人经历或学术志趣,介入了这一领域研究,比如沃伦岗大学历史学者凯特·巴格纳尔(Kate Bagnall),1997年从悉尼大学毕业后,曾到中国珠海做了一年英文教师,由此对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珠海是近代华人移民的重要来源地,于是,当她返回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时,便选择了新南威尔士的华人移民家庭作为研究方向,进行了持续20多年的研究,并多次访问珠江三角洲,寻找华人移民与其故乡的历史关联。此外像克罗宁这样对华人持同情态度的学者,1982年出版《殖民地的受害者:早期维多利亚州的华人》(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深入探讨维多利亚欧籍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了华人移民在殖民地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历史。历史学者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他的《白色的大谎言》 (Big White Lie)一书中,亦对华人的历史贡献持肯定态度,认为华人移民是澳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反对澳洲历史学界长期以白人为中心的历史论断。
这些研究致力于反思和抨击早期华人史研究中的种族歧视和男权主义倾向,或者称之为单一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主义框架,力图建构多元文化的历史叙事。他们总体上理解华人移民的困境,肯定华人对澳洲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认为长期以来对19世纪澳洲华人生活的解读并不是基于华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存在着大量的缺失和误读,因此试图通过对华人生活史资料的深入挖掘,呈现真实的华人生活,改变以往研究中将华人群体边缘化、污名化的状况。新一轮研究中,除了对已有的英文文献进行再审视与再利用之外,大量民间史料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包括中文资料。比如澳洲华人庙宇记录、商业信息、家族文献等;在澳商会、领事馆、同乡会等华人机构记录;华人社区、华人后裔访谈、调查等构成的口述史资料;照片、图绘、信件、日记、自传、私人文件等中英文个人资料;以及考古、物质文化、历史景观资料等,比如,乡村墓地是19世纪华人生命史最直接的证明,每一个墓碑都昭示着一个曾经在澳洲土地上存在的鲜活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被概念化的、模糊的群像的一部分。此外,1992年开始启动的澳大利亚报纸计划(Australian Newspaper Plan),搜集、整理大量的老报纸进行数字化处理后,放到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网站上,供公众免费检索和使用,其中包括曾经散落各地的乡村报纸、社区报纸、家族报纸等。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淘金热中,由于大量华人移民的到来,金矿地开始出现了中文报纸。1856年,英国人罗伯特·贝尔 (Robert Bell)在墨尔本附近的金矿区巴拉腊特(Ballarat)创办《唐人新文纸》(The Chinese Advertiser),是澳大利亚最早的英汉双语报纸,后改称《番唐人新文纸》,之后又更名为《英唐招贴》,这也是“澳大利亚报纸计划”中已经数字化上网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其余两份是《广益华报》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1894—1923)和《爱国报》(Chinese Times,1902—1922)。这些报纸尽管刊载的信息量有限,且多以广告、商品信息为 主,但也成为研究19世纪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同时,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也数字化处理了大量殖民地时期和“白澳”时期的档案文献。这些史料的拓展改变了以往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开始形成自下而上的、将中国社区和华人个体置于研究中心地位的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力图展现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明显的社会生活史转向,并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
1.地方史和社区史路径
对悉尼、墨尔本等大都市唐人街和其他华人聚居区,以及澳洲腹地许多小镇地方史资料的发掘,填补了以往史料的一大空白。尤其是那些在19世纪50到80年代淘金热中兴起的著名小镇,如比奇沃思(Beechworth)、桑德赫斯特(Sandhurst)、巴拉腊特(Ballarat)、英迪戈(Indigo)等,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留存了许多历史资料和遗迹。大量地方性报纸、社区报纸等,也提供了丰富的19世纪华人生活史资料。
在南澳土生土长的作家、曾经做过乡村报纸记者的莉兹·哈弗里(Liz Harfull),多年来致力于搜集和整理自己家乡的史料,其中之一便是对南澳小镇罗布(Robe)的研究。罗布是淘金时代一个非常特殊的华人中转枢纽。1855年6月,维多利亚当局通过了限制华人移民法案,规定来澳船只每10吨位准载华人1人,入境华人每人须交人头税10英镑,这是澳洲历史上第一部排华法案。但由于当时澳洲还未建立独立的国家,几块殖民地各自为政,华人为了避开维多利亚的入境限制,转而从最靠近维多利亚的罗布登陆,然后再经过400多公里的丛林小道步行到维多利亚的金矿场。 从1856年3月到19世纪60年代早期,总计约16000名华人在罗布登岸。罗布原本只是一个经营羊毛出口的小港,镇上没有银行,刚刚建好了电报站,有两家旅馆,常住居民只200人。大量华人涌入对宁静的罗布小镇造成了剧烈的震荡和冲击。华人在这里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漫长而艰难的徒步旅程中又遭遇了什么?哈弗里尚 未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提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线索。

巴里·麦高文(Barry McGowan)长期致力于研究新南威尔士著名淘金地布雷德伍德(Braidwood)的华人淘金史,后来由于参与新南威尔士一个大型的历史遗迹考察项目——“追寻龙”(Tracking the Dragon),开始接触到大量新南威尔士华人的历史遗迹,包括散布于新南威尔士乡村的华人市场、种植园、店铺、墓地、老宅、矿场以及各种手工制品等,开始寻求以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的视角来解析金矿地的华人生活。麦高文观察到华人和欧洲人在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相互依赖,通过联姻、信仰基督教、共同参与慈善活动等,形成当时澳洲殖民地少有的种族融合的良好状态。另一位历史学者凯文·雷恩斯(Kevin Rains)的研究与此相类。雷恩斯运用社会能动性和网络理论(social agency and network theory),对库克城(Cooktown)的华人社区进行解析。1873年北昆士兰约克角发现金矿,大量人口开始涌入,库克城作为金矿区的商业中心迅速繁荣起来。淘金热之初,金矿区只有30个华人,是从昆士兰中部内陆长途跋涉过来的,到 1875年,华人人口猛增至9000人,远远超过了欧洲人口(5000人),以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子为主。传统研究将华人总体上视为外来者或旅居者,对当地经济、社会毫无贡献,华人社区是同质化的、保守 的、封闭的,与当地社会的交往和互动相当有限,拥有少得可怜的社会权利,行为方式主要由种族决定,这些结论在社会能动性和网络理论研究下受到挑战。雷恩斯具象地考察了库克城的华人社区关系网络,发现同乡、亲属(包括拟制亲属关系)、商业伙伴等关系盘根错节,事实上形成了具有能动性的、积极参与的社区形态。尽管与欧洲人占据着装备业、酒业、畜牧养殖业等不同,华人主要从事店铺经营、蔬菜食品贸易等,但两个社区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关联和相互依赖。同时,华人与欧洲人不仅存在经济驱动下的暂时友好关系,也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交往,包括婚丧嫁娶、孩子出生庆典、打官司入籍申请等,形成长期的合作和友谊。雷恩斯还通过解析华商杰米· 阿福(Jimmy Ah Foo)的个人生涯,揭示出华人与欧洲女性结婚,既通过“同化策略”(strategy of assimilation) 融入欧洲社区,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保持了自己的华人认同以及同华人社会的关系纽带,最终摆脱了“旅居者”的身份而成为定居者。同时,这样的异族婚姻生育的子女,可以进入当地小学接受教育,与当地孩子建立亲密的交往,这些儿童也因此成为种族沟通的重要纽带。总的来看,雷恩斯和麦高文等学者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关于华人社区的刻板成见,呈现出一个具有能动性、复杂性、多维度的19世纪澳洲华人社区形象。
2.家族史路径
由于长期的“白澳政策”,华人移民后裔为避免被歧视,往往有意识地毁掉自己的家族印记,包括放弃中文姓氏,改为英文姓氏,烧掉有华人祖先的家族照片等,造成了许多家族史资料散佚,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研究华人家族面临的一大困境。而随着人口的流动迁移,许多华人家族的老宅、店铺、庙宇、墓碑等都不复存在。不过,20 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地方史、口述史资料的发掘,华人家族史资料也一点点被搜集和整理出来,许多不为人知的家族故事浮出水面,澳洲华人的家 族史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拉格·洛赫(Morag Loh)和克里斯蒂娜·拉姆齐(Christine Ramsay)开创性地访谈了33个历史悠久的澳洲华人家族,推出“生存和庆典”(Survival and Celebration)摄影展览及相关论著,回顾了华人在澳洲定居最初100年的历程,尤其突出了对华人女性的关注。几乎同时,华人后裔莫妮卡·坦基(Monica Tankey)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己家族故事的文章,她的祖先1851年从中国来到新南威尔士。随后,波琳·鲁尔(Pauline Rule)、黛娜·黑尔斯 (Dinah Hales)、桑迪·罗布(Sandi Robb)等学者也开始从家族史视角切入了对澳洲华人的研究。麦高文对布雷德伍德金矿地四个华人家族发展史的解析认为,华人男性与欧洲女性的婚姻并非以往研究中所说的“不道德的稀有之事”,而是更加常见、稳定,并使华人得以成功地融入欧洲白人主流社会,成为种族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建立在家族成员自身感受基础上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关于华人家族的单一维度解读,呈现出更鲜活、生动、复杂的面相。
巴格纳尔对华人盛氏家族(Shing)的研究,主要结合了访谈家族后裔威尔玛·康罗伊(Wilma Conroy)的口述史资料,以及家族早期居住地、维多利亚淘金热中兴起的小镇英迪戈的地方史资料,包括邮局目录中的英迪戈店铺记载,官方记录中的家族成员出生、死亡、结婚等信息以及地方报纸中的零散报道。康罗伊是华人查尔斯·盛(Charles chin Shing)和“盎格鲁-华人”混血儿杰茜(Jessie Shing)的孙女,她详尽地回忆和描述了这个家族在英迪戈经营店铺和庙宇的生活场景。中国式庙宇是当时澳洲乡村和金矿区常见的风景,19世纪中叶开始建造了几百座。1925年查尔斯·盛去世,庙宇终因无人打理而关闭,家族成员迁往悉尼定居。饶有趣味的是,1898 年有几份地区报纸都刊登了关于19岁的杰茜打伤丈夫查尔斯的报道,杰茜被告上法庭时称自己当时喝醉了。这生动呈现出了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交往的另一重面相,即可怜而非威胁性的形象。同时期悉尼杂志《公告》和《帝国报》上亦有过类似故事,华人男性由于孤独、缺少朋友、不太会说英语,以至于无法控制他们那些孔武有力、缺少教养的白人劳工女性伴侣。
通过对盛氏家族的研究,巴格纳尔还发掘出了另一些华人家族的故事。查尔斯·盛的店铺合伙人象明(Chong Ming)娶了爱尔兰妻子威妮弗蕾德·米纳汉(Winifred Minahan),1882年象明带了5岁的儿子詹姆斯·米纳汉(James Minahan) 回到中国家乡广东新会的小村庄石渠里(Shek Quey Lee)。詹姆斯在那里生活了25 年,1908年返回墨尔本,想做一名语言教师,然而政府已不承认他的澳大利亚身份,他作为非法移民被告上法庭。巴格纳尔在2009年两次访问了石渠里,寻找当年从“新金山”(即墨尔本)流回来的财富对这个远隔7000公里的中国村庄产生影响的痕迹,并且在石渠里陈氏家谱中查询关于象明的记载。此外,杰茜的妹妹路易莎(Louisa)也嫁给了中国人威利(Willie Ah Poy),他在奇尔特恩(Chiltern)经营一家蔬菜水果店。路易莎生育了9个孩子,她的后代散居于澳大利亚各地以及加拿大,其中一位是加拿大首任华裔总督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威利死后,路易莎改嫁给爱德华· 马哈维(Edward Mahlook),他来自墨尔本的申氏家族(Shin),其祖父潘·阿申(Pan Ah Shin)于 1857 年与爱尔兰女孩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在墨尔本结婚,他们生育了8个孩子。就这样通过联姻、合伙经营生意等方式,许多碎片化的家族故事被勾连起来,形成纷繁复杂、盘根错节的华裔“家族树”,同时,家族关系网络对于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更深入的揭示。
巴格纳尔的研究承继2001年历史学者亨利·陈所倡导的“侨乡路径”(Qiaoxiang/native place Approach),即对19世纪澳洲华人的研究不能仅局限在澳洲,还需要返回中国,追溯华人与其故乡的关联,将中国家庭生活与文化传统纳入研究视域之内。这里的侨乡,指19世纪澳洲华人的主要来源地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以及广东开平、新会、台山、恩平“四邑”(See Yap)及南海、番 禺、顺德“三邑”(Sam Yap)等。克罗宁统计维多利亚80%的华人都来自新会和台山,而一半的华人人口仅来自9个姓氏。通过大量的社会史资料的发掘,研究者们关注到,19世纪华人移民在中国的家族和家庭一直作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借由信件、汇款和返乡探亲等方式,这些华人移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地缘、血缘关系。尤其是那些以“信用票”(Credit Ticket System)方式筹借旅费出国的华人,其在海外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他们在国内的家庭、亲人的命运和家族的声誉,而他们的家庭、家族也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们来去澳洲的自由。如赵昌所说,中国传统宗族结构并没有随着近代中国地方经济结构的破产而崩解,其对海外移民运动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华人所娶的白人妻子以及她们生育的孩子会返回中国村庄短暂停留,甚至永远居住下来。麦克·威廉斯( Michael Williams)认为,由于中国家谱遵循的是父系宗族谱系,许多嫁给华人的白人女性从家谱上往往查不到她们的名字,或者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简单描述。因此,通过“侨乡路径”,将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可以大大地丰富和拓展澳洲华人家族史研究。
3.女性史路径
传统研究主要聚焦于华人性别不平衡对殖民地的影响,华人女性群体长期被忽视,只是偶尔作为妓女、被抛弃的妻子等提及,或作为一个稀奇的现象而被媒体报道,比如,1869 年《悉尼先驱晨报》等以猎奇的口吻,报道了新南威尔士布雷德伍德金矿区一个华人新娘到来的消息。艾瑞克·罗斯在《澳大利亚华人史(1800—1888)》中也好奇地提及1875年5月一个华人贵妇从布里斯班来到库克城的事件,“她的到来吸引了大量欧洲人的注视,他们都渴望看到她的小脚、涂彩的嘴唇、眼睫毛、佩戴的高贵头饰以及身边的丫环”。然而关于这个华人贵妇的身份、家庭、生活状态等却没有任何具体信息。麦克·威廉斯认为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对华人女性巨大的认知鸿沟,不过在他自己对移民、社会机构、商业、法律、农业、采矿业等的专门史研究中,依然是由男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未能成功地将女性纳入。洛赫、亨利·陈、巴格纳尔等都注意到了传统研究中的父权制视角(patriarchal perspectives)导致华人女性长期被忽视。当然,华人女性数量的稀少以及史料难以寻觅,也是研究缺失的重要因素。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华人女性这一“不可见”(invisible)的群体开始逐渐浮现出来。历史学家麦高文和人类学家林德西·史密斯(Lindsay Smith)通过对布雷德伍德博物馆以及当地社区资料的深入挖掘,揭示19世纪金矿区华人家庭以及女性的日常生活。拉姆齐、K.H.廖、莫斯等学者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自传性质的文献,生动再现了华人的家庭生活、婚姻状况、旅行及悉尼唐人街生存状况等。库奇曼追溯了墨尔本唐人街少数有史料记录的女性生活。克莱尔·赖特(Clare Wright)描写了金矿区的女性生活,认为金矿区尽管由男性主导,但女性也并非完全缺席。巴格纳尔通过对一个华人女性金·林恩 (Kim Linn)命运史的细致梳理,具象地呈现出金矿区的女性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等,金是1871年在新南威尔士登记在册的 12个华人女性之一,丈夫阿豪(Ah How)于1857年来到澳洲,19 世纪60年代在新南威尔士洁白可林(Jembaicumbene)金矿开商店、酒馆,逐渐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领袖人物。金与阿豪的社交圈同时包含了华人和欧洲人,生育、医疗、庆典、工作、经商等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各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如同历史学者艾伦·迈恩(Alan Mayne)所说:“华人是金矿区活跃的参与者,与欧洲人之间同时存在着合作、共识与争吵、排斥,他们既是竞争者,也是能分享牛奶和愉快闲聊的邻居。”这些研究脱离了男性中心主义视角,更近距离地将华人女性这一被遗忘的群体呈现出来,特别强调对华人女性个体体验即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女工等的个人感受关注,以及她们对于19世纪澳洲华人社区的重要性。尽管澳洲华人女性人数远远少于华人男性,但并不能因此将她们的历史一笔抹掉,她们同样构成 了历史复杂性的一部分。
此外,与华人男性结合的白人女性的生命体验也被研究者关注。大部分与华人男性结成夫妻的白人女子都出身平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往可能与白人男性有过失败的婚姻。她们和华人男性一起生活,一方面是解决生计温饱,另一方面也是寻求男性的保护。乔斯林·格鲁姆(Jocelyn Groom)在研究墨尔本的申氏家族如何定居下来的历程中,特别关注了家族成员潘·阿申(Pan Ah Shin)所娶的爱尔兰妻子凯瑟琳·马丁,她生育了8个孩子,由于居住环境差、营养不良,加之生育太多、太频繁,36岁就去世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出身中产以上家庭的白人女子,比如玛格丽特·斯加利特与华人梅光达(Mei Quong Tart)一见钟情,后来梅光达功成名就,成为著名的富商和华人领袖。玛格丽特在1911年丈夫去世后出版了传记《梅光达的一生》,称“他是一位出色的父亲、丈夫,堪比任何一个白皮肤的人,他甚至做得更好”。对白人女性和华人男性结合这样一种婚姻形态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以往对于华人移民如何融入澳洲殖民地社会的解读。
4.微历史(micro-histories)路径
微历史路径强调对某些历史场景、社区、家庭和个体的深入研究,试图还原殖民地时期华人真实的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揭示跨种族交往作为常态化的存在,更多是出于华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个人选择,包括经济因素、个体安全、寻求陪伴、 爱情、相互安慰以及性需求等,其中包含着大量复杂、微妙、相互矛盾的人性故事,这样的研究路径打破了以往对于跨种族交往的刻板成见,拓宽了对于华人婚姻形态和家族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揭示了以往在澳洲华人家庭生活研究中被忽略掉的部分,比如多妻(同时在中国和澳洲拥有妻子)、华人移民家庭返回中国以及他们在澳洲出生的子女的命运等。
巴格纳尔通过对华人男性中的一个典型群体“蔬菜小贩”的研究,展现19世纪澳洲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交往的复杂面相。在殖民地时期,白人女性被划定为需要远离中国男性,而白人家庭的门廊则成了走街串巷的华人蔬菜小贩与白人女性唯一的接触区域(contact zone)。尽管华人小贩会时常遭遇羞辱和攻击,比如1881 年《图绘悉尼新闻》(Illustrated Sydney News)展示了一个白人女性吼着“滚蛋吧约翰,带着你的天花”,用长柄扫帚驱赶华人小贩的场景,但通过巴格纳尔所称的“跨越门槛的交往”(across the threshold),部分白人女性却产生了和主流男性社会完全不同的对于华人的认知。她们看到了中国小贩的诚实、耐心、可信、干净,同时能够记住顾客的喜好等;而相比于欧洲蔬菜商,中国小贩的蔬菜更价廉物美,这会让白人家庭主妇逐渐对中国小贩产生信任和好感。这样的情感完全是从实际生活中自然产生出来的,而非《公告》故事中所说的被华人“诱骗”的结果。1888 年,一封写给《公告》的信展示了一个普通的劳工阶层家庭主妇对“华人问题”的态度。她的丈夫是一个反华联盟的成员,正在参与推进一个抵制华人蔬菜的运动,然而她发现白人卖的蔬菜要比华人贵三倍,而这些蔬菜其实也是从华人那里买来的,所以她认为这种抵制毫无意义。巴格纳尔的研究在一些非学术性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比如1896年,玛格丽特·艾格顿 (Margaret Egerton)在《宇宙杂志》(Cosmos Magazine)上发表的半自传连载小说,讲述了白人医生妻子安妮(Annie)由于对语言有浓厚兴趣,参加教堂的语言班,学习广东话,同时也教授一群中国人学英语,其中有个60岁的中国蔬菜小贩,八年来安妮一直从他那里买蔬菜,两人会互赠礼物,相互关心,形成了一段超越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纯洁温暖的友谊,显示出白人女性和中国男性的交往并非一定与性有关以及会带来危险。正是这些个人故事的大量发掘,呈现了一个虽不全面但真实可感的华人生活史面相。
四、余论:建构华人移民的跨国研究 框架和多元叙事
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澳洲淘金热是近代国际移民运动的关键推动力之一,也深深影响和重塑了澳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结构。华人作为淘金热中一个数量庞大的族群,在澳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对19 世纪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制于史料的单一匮乏和研究视角的殖民主义偏见,存在着很多的缺失和误读。社会生活史视角的引入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对于推进这一领域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同时也为中国学者介入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二战以来,港台地区学者首先开始关注澳洲华人华侨群体,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作品,包括台北中华书局1953年出版的雷镇宇的《澳洲华侨概 况》和司徒泽波、陈本健的《斐济国、所罗门群岛、西萨摩亚群岛华侨概况》,以及刘渭平的《澳洲华侨史话》和刘达人的《澳洲与中国》,成为研究澳洲早期华人华侨状况的重要参考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些纵向梳理澳洲华人史的作品,如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以及黄昆章出版的同名著作。他们都是主要从政治和经济的脉络呈现澳洲华人的发展历程。此外,郑寅达与费佩君的《澳大利亚史》、张天的《澳洲史》、侯敏跃的《中澳关系史》以及阮西湖的《澳大利亚民族志》等著作中,也散见有关于澳洲华侨华人的概述。而从横向剖析华人社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华人社团、华人经济等的专门研究。近年来,一些尝试从政治、经济框架之外对澳洲华人史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开始出现,比如费晟从环境史的视角研究澳洲淘金热中的“华人破坏环境”问题,乔瑜从白人女性的视角解读19世纪澳大利亚华人男性形象。不过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学界对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未来,可以尝试将中国已有深厚研究基础的宗族史研究以及丰富的家谱资源,与“侨乡路径”结合,建立起华人移民家族的跨国研究框架;广泛吸纳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视觉文化研究等,融会多学科研究方法;进一步开拓更丰富、多元的研究视角,除了家庭史、女性史、地区史等之外,医疗史、疾病史、健康史、传播史等也可以纳入进来,目前,这一类型的研究还处在相对空白阶段。而基于语言因素,大多数海外学者直接阅读中文文献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面对19世纪以广东话书写的中文报纸、文件档案、墓志碑刻等时,这恰恰为中国学者介入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者简介:王敏,博士,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重庆市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动态研究咨政中心研究员。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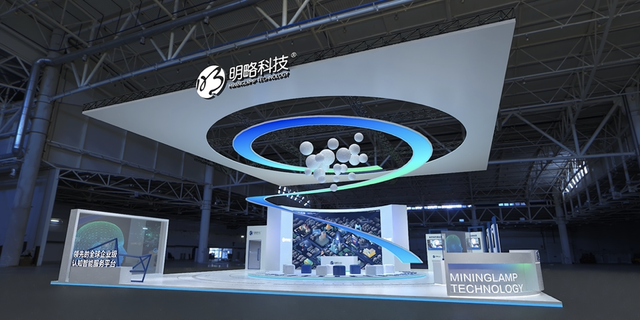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