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代的女鬼都没好下场?

文丨花吃爱丽丝(山东大学)
《夷坚志》乃是南宋洪迈的大作,这位老先生也是传说中的毛主席枕边书《容斋随笔》的作者。不同于《容斋随笔》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夷坚志》却是贩夫走卒耳边之语,洪迈自陈:“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

此书当年也是享誉社会各阶层,上达天听,下至平民,很多人甚至专门给洪迈写信以求自己身边的奇闻异事能够被收录其中,称得上是包罗世间万象了,所载故事也不仅限于南宋时事,北宋时期的鬼事也被纳入其中。
《夷坚志》里的女鬼类型
《夷坚志》全书完成时共有420卷,但在元代就已散佚,目前能见到的仅有207卷,据洪迈语鬼事即有五成以上,仅就现存文献来说,其中涉及鬼魂描述的故事已有390则左右。
在这鬼气森森中,漂亮大姐姐当然要占重头戏——凡涉情爱、性欲之事的女鬼传说有94则左右。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要使用“情爱”、“性欲”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风花雪月的人间美事呢?
这是因为他们一点都不风花雪月,也根本不是人间美事啊!
或许在宋代男人的眼中,女鬼早已失却了盛唐间灯下陪读、红袖添香的温柔小意。美丽的女子眼波中流转的不是绵绵情意,而是引诱他们覆灭沉沦的诱惑;纤纤玉指抚过的并非是鼓噪着满腔爱恋的胸膛,而是颈侧只有薄薄一层皮肉保护的动脉;耳鬓厮磨间吐露的更非甜蜜的爱语,而是毒蛇吮血啮肉前夕的冷笑与嘶鸣。

这场相会并非是姻缘前定的偶遇,而是早有预谋的谋杀。
当然,《夷坚志》中的女鬼也有清纯不做作的恋爱故事,只是数量比较少而已——在女鬼故事中只占三成,其中happy ending更是只有4则。比如《胡氏子》中,男子与亡女之魂相爱,在父母的授意下设计让女子吃下食物,女子的身体竟因此从亡魂变为生人,胡氏一家非常高兴:“冥数如此,是当为吾家妇。”女方家长来查验,发现果然是家中亡女,两家成礼而去。但其中也提到“读书尽废,家人少见其面,亦不复窥园。唯精爽消铄,饮食益损。”虽有甜美的结局,肾虚的过程还是免不了的。
悲伤的是,剩下的31则恋爱故事全部是惨淡收场。比如中间有一则《建昌王福》,故事中郡兵王福夜遇妙龄少女,与之欢好,数月后王福羸瘠如鬼。后被父母发现追捕,女子逃至天王祠而消失不见,抬头一看,才知那女子分明是天王像边的捧装奁侍女,王父引王福相见,王福只低头不语。于是王父击碎其像,王福掩面悲泣,踰旬而死。在这类故事中,女鬼通常容貌姝美,于夜主动献身,缠绵数月后男子病弱憔悴,被父母、道士或僧人发现后强行介入,男子或留有余情,但毕竟人鬼殊途,最终任他人拆散,女鬼下场凄凉,但男子之结局也不乐观。
这些恋爱的结局虽非圆满,至少女子的倩影是隐没在了美好的回忆中。在更多的故事中,女鬼们则是以冶艳诱惑的形象出场,以危险可怖的面目谢幕。或是含冤女鬼前来报复,男女本有夫妻(妾)关系或有婚礼之约,但因男子背约或做下对不起女子的事情,而遭到女子亡魂的报复。即使男子能够得到道士僧人的帮助,也难免暴死的结局。在这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复仇面前,不管是得道高僧、大德仙师还是阴曹地府都会退让三分,不予干预。

或是只为采阳补阴的“白骨精”,这些女鬼与男子本无前怨,只为贪恋欢爱,吸食精气,采阳补阴,而与男子一夜风流甚至长期相伴,但其中并无多少情爱可言,男子一旦发现其真面目则立刻翻脸,而男子的最终结局多不幸,或大病濒死,或前途尽毁,只有少部分受高人庇佑才得以善终。更有甚者,有的男子只是因为娶了来历不明的女子(实为女鬼)做妾就丢了性命,既无前怨,也无近仇,堪称莫名其妙。
光从《夷坚志》所载事迹来看,与唐代文学中美好的结局和形象相比,宋代女鬼故事确实少有幸福的结局,与女鬼欢爱的男子皆形销骨立,或大病,或暴死,或丢官,或流放,少有善终,女鬼的形象美丽却潜藏危险,男子一旦与之扯上关系,便有可能遭受不幸。
女鬼与冥婚
关于女鬼故事的成因,台湾政治大学刘祥光先生认为与“冥婚”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参照了人类学家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广东顺德、三峡溪南所做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发现未婚而亡故的男女死后会作祟以求冥婚的情况,应是鬼恋故事的原型。在各地案例中,以台湾冥婚最接近于宋代女鬼故事,男子与亡故的在室女结为夫妇,新婚之夜的第二天,男子会感到精力全无,十分疲惫。但不同于冥婚有正式媒合的程序,宋代女鬼往往自己主动找上门来,并给男子带来了潜藏的祸患。
确实,《周礼•地官•媒氏》即言“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这从侧面说明冥婚在民间是由来已久的民俗,其中迁葬是将成年鳏寡的男女死者合葬,使其成为阴间夫妻,嫁殇则是现世男子迎娶未嫁而早夭的少女。吴光正也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一书中写到:“不死的灵魂总是与人世有着密切的联系,人鬼之恋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种。

人鬼恋故事的原型为古代的冥婚,是人世的亲人给死去的未婚男女举行的一种婚礼。但是随着男权文化的确立,这种对女鬼和男鬼的性安慰却演变成了女鬼与凡男的恋爱故事。”而女鬼吸食精气之说则与道教文化中的阳精崇拜有密切关系,这种采阳补阴的观念在道教文化对宋朝百姓的广泛影响下更是深入人心。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解释女鬼与生人欢狎的原因为:“盖鬼为余气,渐消渐灭,以至于无。得生魂之气以益之,则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与人狎,摄其精也。”那满满艳情色彩的女鬼采阳故事,可能一方面是宋代女性通奸和淫行事迹的映射,另一方面则是宋代父系社会价值观对于女性情欲的抵制和恐惧,两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便是以悲惨的故事结局来警戒世人了。
宋代家庭中多蓄婢妾,这些婢妾可直接从市场上的牙婆或女侩家手中买到,非常方便。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在婢妾问题上专列数条:“婢妾常宜防闭”、“侍婢不可不谨出入”、“婢妾不可供给”、“暮年不宜置宠妾”、“婢妾不可不谨防”、“美妾不可蓄”,认为婢妾极有可能“或多挟此私通”、“至与外人私通有姙”、“反与外人为耳目,以通往来”,混淆主家血统,严重时“至破家者多矣”。袁采的严厉态度固然是为了维护血统纯正和家庭稳定,但若无婢妾私通淫行现象在前,袁氏也不至于无端紧张至此。
宋代家庭内不仅婢妾有私通之事,妻子也可能出现婚外情,《折狱龟鉴》中就记录了多起妻子与外人私通,反过来谋害丈夫或其他亲戚的案件。如《折狱龟鉴•释冤上•庄遵审奸》就记录了一起妻子与奸夫合谋杀掉丈夫,被小叔子发现后反而倒打一耙,诬告小叔子因为强奸她而杀害兄长的案例。
据王文渊《唐宋女性犯罪问题探研》中唐宋女性家庭或家族外社会犯罪案统计表可知,和奸罪在唐代有63例,宋代虽锐减至27例,但各种罪行中和奸罪比例仍是最高的,达到31.8%。且唐无淫行罪,宋代违反婚姻道德关系的女性“性”犯罪类型除了和奸之外又多了淫行罪,共5例。相对于和奸罪,淫行罪并无明确定义,王文渊在其文章中提出,南宋淫行罪的出现并未意味着其发案率高于北宋,只能说在南宋,民众和士人开始关注女性的性越轨犯罪,乃是理学在南宋后期进入官方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的性观念、贞洁观呈收缩态势的结果。
但冥婚和“采阳补阴”的影子自女鬼传说诞生起便紧随其身,难以解释与前朝相比文学作品中宋代女鬼形象的丑化。前面总结过,宋代女鬼传说中形象较差的多为报复类和采阳类,其中报复类的故事则常涉及到夫妻间、男子与妾室乃至家庭之外的各色女子的爱恨情仇,然而什么朝代都有辜负真心的风流浪子,这似乎无法作为足以解释《夷坚志》多有报复类女鬼传说的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在《夷坚志》女鬼故事中遭到报复的男子身份多为官员士大夫,而下场尤为酷烈。除《翟八姐》《郑畯妻》《梦前妻相责》中为商人,《张客奇遇》中男子身份不明外,《张夫人》原是太常博士,后为大司成;《太原意娘》在江南为官;《满少卿》是鸿胪少卿、《杨大同》是命里本该登科的士子;《袁从政》原是郴县尉,后调桂阳军平阳丞;《小溪县令妾》是小溪县令;《红奴儿》是池州青阳主簿。
《夷坚志》女鬼遭负心而来报复的故事中,男性之所以结局都那么悲惨的原因,或许正是缘于他们的官员身份。刘祥光先生认为宋代明显对异类女性持负面观感,这些异类女性代表的就是来路不明的女子,男性与这些女子纠缠多半不会有好下场。《夷坚志》中所载女鬼传说中,来路不明的女子的社会身份从官家儿女到妓女皆有之,但故事中的女鬼身份或更多与剧情相关联,要论现实生活中若说能够较为随意出现在男子生活中,来路不明,容色美丽的女子的话,便是以妓女为代表了。宋代妓女分官妓、营妓、军妓、市妓与家妓,虽在宴会、盛典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协助或增色作用,然皆属贱籍,且政府对于其人身自由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同样,宋代官员与妓女的交往也受到法律的诸多限制。据《庆元条法事类》中的明文规定,宋代官员不能要求官妓陪他们私下饮宴或出游;若沉迷于妓乐宴会中而怠忽政事也会遭到惩处;官员参与妓乐宴会的时间有严格规定,在劝农、公务等时期禁止赴会;某些官员则被禁止参宴。

狎妓并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好事,一旦被抓住作为罪名进行惩处,还是会对当事人的仕途有所打击,其名声也会受损,其政敌也相当于抓住了一个把柄,随时都有遭到弹劾的危险。不过这些或许还不是士人们最害怕的,为狎妓而获罪透露出未来的一种趋势——他们有可能因纵情声色而滑入情欲深渊,从此怠惰政事,招致皇帝或上级的惩罚,从而仕途受损,家族也因此而蒙羞——这才是身为家族希望的士人们最恐惧的事情。
作为来路不明的女子的代表形象,妓女可能会给与之欢好的男子带来如此多关于厄运的联想,更不必说其他的女子了。宋朝家庭之外的男女关系都是不被看好的,性行为被认为是用来传宗接代,应发生于家户内,非家户外。现实中艳遇的可怕结果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变成了以妓女为首的来路不明的女子化身妖艳的女鬼前来勾引士人,能够守住男女大防之人便能得到中举长寿的福报,轻易被诱惑的士人与官员则会与那亨通官运和光明前途失之交臂,身体健康与寿命都受到损害,家庭甚至会因此而破裂。
《夷坚志》中大量此类故事的存在,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投射,也是讲述人与洪迈的一番苦心劝诫。
参考文献
(1)[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乙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宋]郑克:《折狱龟鉴》,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03年。
(3)[宋]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4)[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7)刘祥光:《婢妾、女鬼和宋代士人的焦虑》,《走向近代》编辑小组编:《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东华书局,2004年。
(8)刘祥光:《宋代日常中的卜算与鬼怪》,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
(9)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0)王文渊:《唐宋女性犯罪问题探研》,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
(11)杨果、柳雨春:《宋代国家对官员宿娼的管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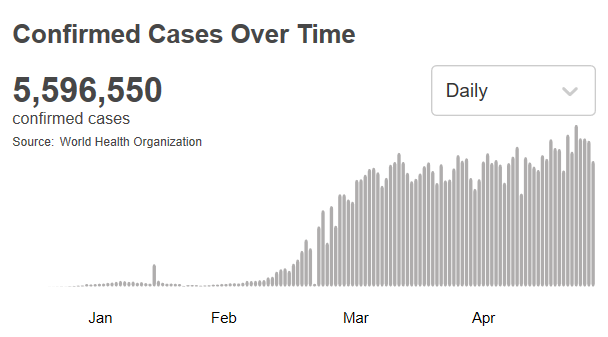















评论